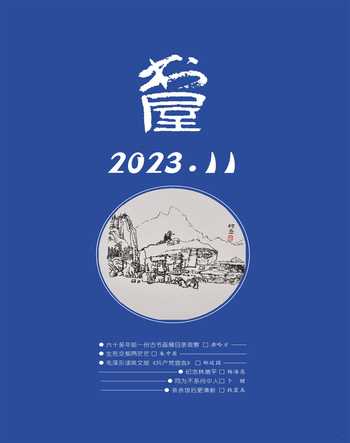生死交契兩茫茫
朱中原
一
新見一書信,乃梁啟超致江建霞信札,現藏于國家博物館。內容如下:“建霞編修先生:伻來得書,盛意相招,敢不如命。殷勤獎飾非所克當。頃定擬初七遄行,望前必當抵湘。文從北行當以何時?千乞少待,一罄積想。匆匆先布,相見不遠。不一一敬復。專承道安。弟啟超頓首。十月五日。”
此信雖無年款,但考其史跡,當寫于1897年10月,此為目前所見梁氏最早書跡之一,殊為難得。字體為行草,瀟灑流暢中略帶碑意,頗有少年之意氣風發。信中“建霞”即江建霞,也即江標,“建霞”乃其表字,元和(今蘇州)人,曾任翰林院編修之職,故梁信中稱其為“編修”。所謂“盛意相招”,是江邀請梁就任新辦之湖南時務學堂中文總教習之職。江時任湖南學政,與湖南巡撫陳寶箴、兩湖營務處總辦熊希齡、湖南代理按察使黃遵憲等維新派骨干共同主持湘省維新變法大業,尤其在改革新式學堂上不遺余力,與譚嗣同、唐才常等湖湘才子結為莫逆之交。
湖南維新運動之發軔,以時務學堂為根基,時務學堂之創辦,陳寶箴、江建霞等皆有首創之功,梁啟超言時務學堂教學批答內容“皆當時一派之民權論,又多言清代故實,臚舉失政,盛倡革命”。時務學堂可謂后來庚子自立軍起義及辛亥革命之人才大本營,而身為湖南學政的江建霞于此功不可沒。時務學堂之外,江建霞又創辦《湘學報》,邀其同鄉好友兼門生唐才常任主筆。《湘學報》之創辦,實開湘省維新變法言論之大端。譚嗣同認為“諸新政中,又推《湘學報》之權力為最大。蓋方今急務在興民權,欲興民權,在開民智。《湘學報》實巨聲宏,既足以智其民矣”。江建霞慨然而言:“湖南真人才淵藪哉!他日天綱潰弛,出而任天下事者,其在茲土乎!”可見其對湖南這片土地的莫大期許。
江建霞于實學用心頗多,且能以其學而施政。在湘任職期間,他大力改革弊政,推行時務,屢次向湘省巡撫陳寶箴上書興辦礦務:“因思今日天下之貧,若不以礦務為開源不可救藥,若任上官辦理而下民阻塞亦不可救藥。推原其故,皆因不知開礦之法,徒知開礦之利,上之興也為民,而民之謀也為己,不顧大局,不知利害,皆在于不知礦學。”(《上陳寶箴書》)又說:“西人欲興一利,必開一報館而專論之,以筆代口,知者易而改者速。”因此,他建議,欲興礦務,必先辦礦學報,這也是他力主創辦《湘學報》之緣由。以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黃遵憲、唐才常、江建霞等為代表的維新派,之所以大興報務,并非為了辦報而辦報,而是以報館為開啟民智之言論機關,由報業而興辦時務,故其根本是為了興辦時務,而辦報,不過一言論工具而已。
梁啟超與江建霞謀面甚晚,但訂交甚早。江生于1860年,長梁十三歲,其非僅以言論著稱,且以實行著稱。康、梁維新運動之所以對湖南頗為倚重,其中一重要原因即在于有陳寶箴、熊希齡、江建霞、黃遵憲、譚嗣同、唐才常諸豪杰。如今提及湖南維析運動,多言陳、譚、唐等人,然對江、熊等則言及甚少,蓋因江英年早逝、熊后為袁世凱重要臂膀之故。
二
江建霞其實與譚嗣同一樣,是個不折不扣的官宦子弟,光緒十五年(1889)中進士,官翰林院編修,與當朝大臣文廷式、費念慈“年相若,才相等”,其出任湖南學政,整頓校經書院,增設史地、算學等科,可謂開一代教育新風。湖南時務學堂亦為近代新式教育之始。
時務學堂雖為官辦,由時任湖南巡撫陳寶箴奏請創辦,然其實質則是由維新派主導的新式學校。創辦之初,陳寶箴委派黃遵憲、熊希齡具體負責學堂籌備事宜,任命熊希齡為提調(即校長),主持一切行政事務,聘請梁啟超為中文總教習,李維格為西文總教習。中文分教習有譚嗣同、唐才常、韓文舉、葉覺邁、歐榘甲,西文分教習為王史,數學教習為許奎垣。第一次招考就錄取學生四十名。
時務學堂之師生,皆與康、梁密切相關,“康門十三太保”中大多曾就讀于此,將時務學堂稱作康門之大本營亦無不可,其中耳熟能詳者如譚嗣同,無須多述。唐才常為譚嗣同、梁啟超好友,湖南瀏陽人,與江建霞既是莫逆之交,又有師生之誼。唐出任《湘學報》主筆,乃江所舉薦。唐亦是維新運動中的骨干分子,庚子年自立軍起義運動的重要領導人之一,唐才常文武兼修,頗具豪俠義氣,在兩湖、川、陜等地的江湖會黨中亦廣有影響,其時自立軍起義運動中的骨干人物,皆為唐好友。梁啟超、譚嗣同、唐才常相交甚契,然在梁啟超到來之前,譚嗣同、唐才常、江建霞三人則為莫逆之交。梁到來之后,四人成好友,并時有佳話。頗為遺憾的是,譚、唐二人皆先死,譚死于戊戌變法之斷頭臺,唐死于自立軍起義失敗后之武昌花園山,后又有江死于戊戌變法失敗后之罷官,三人皆死于維新變法。此三人之亡,是為維新派力量的重要損失,梁啟超痛失三友,亦失其重要臂膀。
梁啟超成為時務學堂的中文總教習,與江建霞等人之大力舉薦有密切關系。梁在任時務學堂總教習之前,因主持《時務報》筆政而名滿天下,但他那時與《時務報》總經理汪康年之間矛盾加劇。而恰在此時,康有為欲用梁啟超赴湘主持時務學堂。于是,經黃遵憲、江建霞等人推薦,時年二十四歲的梁啟超成為時務學堂中文總教習的首要人選。但汪康年不放人。為此,陳寶箴專程為梁送去聘書,再由熊希齡想盡辦法對汪康年施加壓力。但陳、熊二人主政皆在湘省,汪可以不理會。于是,作為汪摯友的江建霞再次出馬,力勸汪放梁入湘:“此間時務學堂擬敦請卓公(梁啟超)為主講,官紳士民同出一心,湘士尤盼之甚切也。弟亦望卓公來,可以學報事交托。”(江建霞《致汪康年書》)在各方軟硬兼施之下,汪康年終于松口,梁啟超于1897年11月偕吳人李維格以及廣東同門韓文舉、葉覺邁、歐榘甲從上海抵達長沙。
江建霞雖為吳人,但其仕宦重要之地卻在湘省。1894年,江任湖南學政。這是他仕途的頂點,但也是其仕途的終點。在湖南學政任上,江建霞與陳寶箴、熊希齡、黃遵憲一起主持了湖南學風的改革。陳寶箴將創立時務學堂這一任務交給了湖南文壇領袖、士紳王先謙,王和皮錫瑞、葉德輝等均是湖南今文經學的領袖,隨著辦學風潮的興起,湖南一時成為今文經學的重鎮。然王先謙和葉德輝思想保守,與維新派矛盾日漸加劇,甚至成為阻礙維新變法的力量,湖南維新事業陷入停頓,亦與此二人密切相關。
相比于《時務報》的言論,時務學堂更成了梁啟超施展才華的廣闊天地。時務學堂更側重于實務,其所倡皆為民權革命,而且經過梁啟超的精心策劃和布置,時務學堂培養了后來在轟轟烈烈的庚子自立軍起義、辛亥革命及護國戰爭中均大展身手的一批佼佼學子,其中就包括蔡鍔、林圭、秦力山、范源濂、石陶鈞、畢永年等人,這批人也成為清末民初劃時代的豪杰。
三
梁啟超在江建霞面前屬于晚輩,但二人卻成為忘年之交,不論年齡長幼。江建霞對梁啟超的才華十分推重,二人惺惺相惜,時有詩文唱和。
這其中還有一段與菊花硯有關的士林佳話。
是時,湖南凝聚了一大批維新干才,上有巡撫陳寶箴、代理按察使黃遵憲、學政江建霞等實力推導,下有譚嗣同、唐才常、梁啟超、陳三立、熊希齡等鼎力相助,作為戊戌變法試點的湖南,新政辦得很有聲勢。唐才常此時與梁啟超初識,訂交之際,贈其菊花硯一方以為紀念。譚嗣同因是二人相交的介紹人,于是為石硯題銘曰:“空華了無真實相,用造莂偈起眾信。任公之硯佛塵贈,兩君石交我作證。”
首句用佛家語解硯上的菊花紋,既非真花,故曰“空華”,下句承上句而來,“莂偈”均為佛教文體,分指散文與韻語,“起眾信”此處指開通民智,全句意為希望梁啟超用此硯寫出足以轉移人心的啟蒙文章。在時務學堂中,因譚嗣同介紹,唐才常首次與梁啟超相識。其中“任公”是梁啟超的號,“佛塵”是唐才常的字。
恰好江建霞離任前一日去梁啟超寓所辭行,見硯與銘,便乘興為之刻石。至此,這一方刻有銘文的硯石已不是普通的菊花硯,因緣際會下,于一時間薈萃四位風云人物的心力,凝聚著同道者的真摯友情,同時,它也成為中國歷史上這段不尋常時期的珍貴紀念物。
光緒二十五年(1899),也正是江建霞去世這一年,亡命日本的梁啟超、韓文舉、歐榘甲、梁啟田、麥仲華、張智若、梁炳光、陳國鏞、羅潤楠、李敬通、譚錫鏞、黃為之十二人,在江之島的金龜樓義結金蘭,宣示效忠帝黨,反對慈禧太后,立志實現大同理想。不久,又組織保皇黨,推行勤王運動,鼓吹君主立憲。這一結義,正是梁啟超、唐才常等于庚子年策劃自立軍起義的預備。鮮為人知的是,自立軍起義,是康、梁維新派大規模武裝斗爭的一個重大事件,由康有為在海外籌款謀劃,梁啟超策劃部署,唐才常、歐榘甲、韓文舉等人奔走于兩湖、兩廣及江浙,廣泛聯絡江湖會黨組織,聲勢浩大,建立起了十萬余人的龐大武裝力量,并欲擁戴湖廣總督張之洞“東南互保”,令中國南方震動。張之洞雖然亦有此心,但又怕得罪慈禧,首鼠兩端,故只能提前下手,秘密逮捕并殺害了唐才常等起義軍骨干二十余人,起義失敗。當時,張之洞弟子中的吳祿貞因被派往其他地方公干,僥幸逃過一劫。事后,康有為寫萬言書,痛罵張之洞坑殺士人,且唐才常等亦是張之洞兩湖書院弟子,令張羞愧難當,幾欲自殺謝罪。自立軍起義的失敗也標志著維新派勢力的衰落,自此,維新派與革命派分道揚鑣,一部分維新派勢力奔赴孫文革命派。但是,自立軍起義卻成為后來辛亥革命的先聲,若沒有這一醞釀和預備,辛亥革命也斷難成功。自立軍起義中尚未殞命的時務學堂子弟,日后也成為辛亥革命的中堅力量。
經歷諸事紛擾,尤其是自立軍起義之失敗,往日盟友多已魂歸黃土,令梁啟超增添了無數憂思,因此對菊花硯一直念念不忘。1902年,流亡日本數年的梁啟超撰寫《飲冰室詩話》,講到這方菊花硯的來歷。起首即云:“戊戌去國之際,所藏書籍及著述舊稿悉散佚,顧無甚可留戀。數年來所出入于夢魂者,惟一菊花硯。”使梁氏魂牽夢繞的這方硯,是獨一無二、不可復制的絕作,它偶然出現于世間,又如電光一閃,轉瞬即逝,這更令梁啟超感嘆不已:“今贈者、銘者、刻者皆已歿矣,而此硯復飛沉塵海,消息杳然,恐今生未必有合并時也,念之凄咽。”人間的緣分就是這般可遇而不可求。
這時,因參與維新變法而被放還鄉的黃遵憲,又與留居日本的梁啟超恢復了聯系,見其不能忘情于菊花硯,且為之傷感不已,心有所動,遂作書告之曰:
吾有一物能令公長嘆、令公傷心、令公下淚,然又能令公移情、令公怡魂、令公釋憾。此物非竹、非木、非書、非畫,然而亦竹、亦木、亦書、亦畫。于人鬼間撫之可以還魂,于仙佛間寶之可以出塵。再歷數十年,可以得千萬人之贊賞,可以博千萬金之價值。仆于近日,既用巨靈擘山之力,具孟子超海之能,歌《楚辭》送神之曲,緘滕什襲,設帳祖餞,復張長帆,碾疾輪,遣巨舶,載之以行矣!(光緒廿八年八月廿二日)
斯人已去,睹物思人,唯有無限傷懷。十數年之間,梁啟超身邊的盟友及弟子不斷離去,眼見國事日蹙,但他并沒有絕望,而是仍然胸懷奮力之志。
四
江建霞不但有政聲及文名,亦頗有詩名,汪辟疆《光宣詩壇點將錄箋證》,稱其“詩工殊深,風致娟然”;費行簡《近代名人小傳》直接點明其風格是“文學齊梁,詩多側艷”,而僅《江標日記》所存詩歌即多達二百余首。詩詞文賦之外,江建霞亦為當時藏書大家,其業師乃晚清有名藏書家葉昌熾,其所藏金石碑拓,即有六百余種之多。江建霞交往之藏書家,如葉昌熾、汪鳴鑾、王頌蔚、吳大澂、李文田、盛昱、王懿榮、繆荃孫、費念慈、王崇烈、李盛鐸等輩,皆為其學問與藏書上之至交。
自古蘇州出才子。江建霞自是江南才子無疑。然若未出江南,則江建霞亦只能是個才子而已,此類才子夥矣。江建霞之所以為江建霞,乃在于其入湘之后,又沾溉湘人勇猛精進之血性精神。其門生故吏,若蔡松坡、石陶鈞、秦力山等,皆為文武兼備之雄杰。蔡松坡在護國戰爭后死于日本,秦力山參加過唐才常的自立軍起義運動,后脫離康梁轉而奔向孫文之革命派,石陶鈞則自始至終是梁啟超及時務學堂精神的追隨者。石陶鈞在憶及先師時曾想起江建霞對他說過的話:“邵陽先輩魏源,你們得知嗎?讀過他的書嗎?你們要學魏先生講求經世之學。中國前途極危,不可埋頭八股試帖,功名不必在科舉。”江建霞勸告石陶鈞等門生,不必去考科舉,這即是彼時中國科舉廢除之先聲。經江建霞的指引,石陶鈞等人確實沒去考取科舉功名,而是按照江的推薦,去讀校經書院,拜在當時名儒葉德輝門下。然葉德輝思想守舊,在得知其陋行之后,江建霞又毅然讓石陶鈞離開葉德輝,轉而去往江任學政的官署內萱圃居住和讀書,也正是在這一時期,石陶鈞閱讀了大量經世之書,并經江認識了日后對他多有提攜和幫助的譚延闿。然好景不長,就在石入讀萱圃的第三年,江建霞因戊戌變法被罷職。
江建霞被罷職歸吳后,以書畫自遣,其有一方小印章,名曰:“廊廟江湖總圣恩。”可謂其心志之呈現,無論身在廟堂(曾被拔擢為四品京堂候補,署軍機章京,未就職,然屢被光緒召見),還是身在江湖,皆不忘圣恩,其憂國之心昭昭可見。江歸里不久,即以肺疾卒,年僅四十。
江死后,最為悲憤者,當屬唐才常。唐有贊曰:“痛乎往年譚復生(譚嗣同)之哭吳鐵樵也,曰:‘中國遂乃不可為乎!鐵樵而竟死也!甫逾一年,而海內志士又以哭鐵樵者哭復生矣。去年十月,君(江建霞)忽泣告余曰:‘中國遂乃不可為乎!復生而竟死也!又甫逾一年,而海內志士又以哭復生者哭君矣。海內賢達人僅僅有此數,其涕泗幾何,能堪幾哭而堪幾死耶?人或謂去歲若早入都,必與六烈士同死……中國果革政,所以紀念君者,必不后于六君矣。”唐才常將江建霞與因維新變法而死難之戊戌六君子及吳鐵樵等相提并論。而未幾,唐又因自立軍起義而死難,梁啟超又以上述同樣之贊語論列之。英雄豪杰之死難,庶幾相同。
清末革命家馮自由認為“湘省大吏銳意提倡新學者二人:一為巡撫陳寶箴,一則提學使江標”,可謂的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