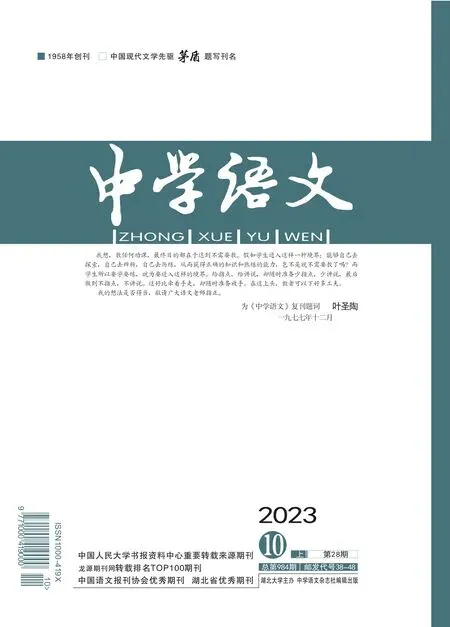語文課程育人途徑芻議
鄧維策
在對語文課程目標的認識中,有一種普遍的觀點:語文要進行人的教育,進行道德的、思想的、人格的教育。“語文教育不僅要進行雙基教學,文化素質教學,還要進行人文精神教育,執著于人類精神文明的終極追求,立足于學生的人文情懷培養,理解人、尊重人、寬容人,注重人性的完善和對自由精神、自由意志、自我實現的追求,注重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心靈溝通并致力于真、善、美的人類終極追求。”[1]童慶炳認為,“必須從‘人的建設’的高度來定位語文教學的觀念”,“語文教學的‘元問題’是我們要建設什么樣的人的問題,是通過語文教學使學生對自身的本質真正占有的問題”[2]。于漪認為,“學語文不是只學雕蟲小技,而是學語文學做人。語文教育就是教文育人。語言文字是文化的載體與結晶,教學生學語文,伴隨語言文字的讀、寫、聽、說訓練,須進行認識教育、情感教育和人格教育”[3]。
這一類的主張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文以載道”思想源自《子夏易傳·系辭上第七》,經過陸機《文賦》、劉勰《文心雕龍·情采》的闡釋,到韓愈大力倡導,至程朱理學的加強鞏固。[4]他們重視的是語言的內容,語言的形式服務于內容。這種“道”是一種特殊的內容,是一種統治思想。在清末以前,為統治需要而進行的語文教育本質上是政治教育。
語言科學告訴我們,語言不僅僅有內容,同時有形式,語言是內容與形式的統一。語言是音義結合的符號系統,所指和能指分別代替概念和音響形象。我們應當從語言的內容與形式的統一來認識語言。索緒爾觀察整個語言活動,描繪了語言循環圖式(見圖1)。

圖1 索緒爾的語言循環圖式[5]
在對語言進行專門研究時,索緒爾說:“語言符號是一種兩面的心理實體。”他描繪了語言的符號圖式(見圖2)。

圖2 索緒爾的語言符號圖式[6]
他進一步說:“我們建議保留用符號這個詞表示整體,用所指和能指分別代替概念和音響形象。”[7]對符號圖式的解釋見圖3。

圖3 符號圖式
“在法語里,‘判斷’這個概念和juger 這個音響形象相聯結;一句話,這就是意義的圖解。”[8]在漢語里,“判斷”這個概念的能指是“pànduàn”。
能指與所指是語言的結構,語言是能指與所指的統一體。“語言還可以比作一張紙:思想是正面,聲音是反面。我們不能切開正面而不同時切開反面,同樣,在語言里,我們不能使聲音離開思想,也不能使思想離開聲音。”[9]單純從所指或能指來認識語言,都是片面的。特別強調語文的育人功能,正是從語言的所指或內容方面提出來的,與“文以載道”思想如出一轍。若我們沒有在語言的能指和所指的統一中認識語言的價值,出發點就已經偏離了“語言”的概念,這種觀念下的語文教學不是為語文的教學。
我國把教育目標分為三個層級。第一級是“教育目的”,陳述教育方針或培養目標,由政府或國家制定,其特點是抽象、籠統,關注“應然”狀態。第二級是“課程目標”,陳述具體課程的目標,由學科專家制定,其特點是從“抽象”逐步過渡到“具體”。第三級是“教學目標”,陳述一節課或本次活動的教學目標,由學科教師制定。[10]教育目的是所有教育工作者的出發點和最終歸宿,是所有課程的共同目的,課程目標“不是教育目的或培養目標的簡單推衍”,“教育目的都要以課程為中介才能實現。事實上,課程本身就可以被理解為是使學生達到教育目的的手段”。[11]我們的課程對人的教育是一個間接過程。我們的教學策略應該讓學生的精神沉浸在語言材料中,用語言來錘煉學生的精神,讓學生的精神健康成長起來。精神的核心是思維。人要在聽、說、讀、寫的活動中具體地進行思維訓練,在思維科學的指導下設計問題,用規定的思維方法來回答,比如,下定義、解釋、分析、假設、比較、推論等。人的精神的本質是個體的自我意識,當“我”在運用思維方法進行思維的時候,下定義、解釋、分析等便是“我”的思維,“我”的思維得到了具體的思維形式的訓練。換言之,在思維訓練中,“我”的思維便顯露出來,思維不單單是一個結果,而是連同結果的過程。這說明,“自我意識”即人的精神應當在教學過程中培養起來。新的教育目標分類學把作為客體方面的知識與主體方面的認知活動分開,知識包括信息領域知識(陳述性知識)、心智過程領域知識(程序性知識)和心因性動作過程領域知識;認知活動包括自我系統、元認知系統、認知系統。[12]漢語課程為認知活動提供內容,認知活動在三個層次上對語文提供的知識分別進行加工處理。在此過程中,自我系統、元認知系統、認知系統得到了改善、發展,從而改善、發展人的認知能力,實現育人的目標。
語言也是一個獨立的科學系統,漢語課程是一門獨立的課程。語言是音義結合的符號系統,不依賴于物理、法律等,是獨立存在的符號系統。這個符號系統持續地存在于人類社會,新事物的產生或舊事物的消亡僅僅增加或者減少了個別的詞語,音義結合的符號系統本身并沒有改變。即使像莎士比亞這樣的語言大師,像索緒爾這樣的語言理論家,也改變不了語言的本質。語言是客觀的、自主的、能動的。我們固然可以根據情境從“瓦片掉下來了”“掉下來了,瓦片”兩個句式選擇其一,賈島選擇“推”或者“敲”,但這何嘗不是不同的語序或語義在與我們對抗呢?一個句子、一個詞是客觀的、獨立的、能動的,我們必須尊重它,選擇與我們的主觀的、特殊意味一致的句式或詞語。一門學科同樣是客觀的、獨立的,有自主性和能動性,我們必須尊重它,提出與學科的結構和發展方向相一致的教育目標。“進行人的教育,進行道德的、思想的、人格的教育。”這種主觀的“我認為”的教育目標,超越客觀的學科,無視學科的獨立存在,是在扭曲、排擠這門課程,這也說明我們的課程并沒有真正獨立。“進行人的教育,進行道德的、思想的、人格的教育”,這種口號標高旨遠,作為課程目標,很能夠誘惑人,但若沒有扎實的課程知識和能力來支撐,就只能是獲得美好聲譽的旗幟。
語言科學要求我們,從整體上把握“語言”;課程論要求我們立足學科教育,學科教學活動就是貫徹國家的教育目的的具體途徑。“實體性的東西,堅定不移的東西,才是特殊目的的負荷者,并可以促進和實現這些特殊目的。人們不必將特殊目的放在第一位,但是那最優良的東西卻能促進特殊目的的實現。”[13]育人的目的,是建立在具體的語言能力的培養上,通過具體的課程內容,在達成課程目標的過程中實現的。我們的課程如果脫離了客觀對象,不把內容與形式統一起來,整體地把握對象,而是直接進行道德的、思想的或人格的教育,必然帶來“偽語文”的教學。因此,我們應該回歸漢語教育,以培養理解和表達的語言能力為課程的總目標,在漢語教育中培育人的精神。這樣的漢語教育才能夠扎扎實實地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