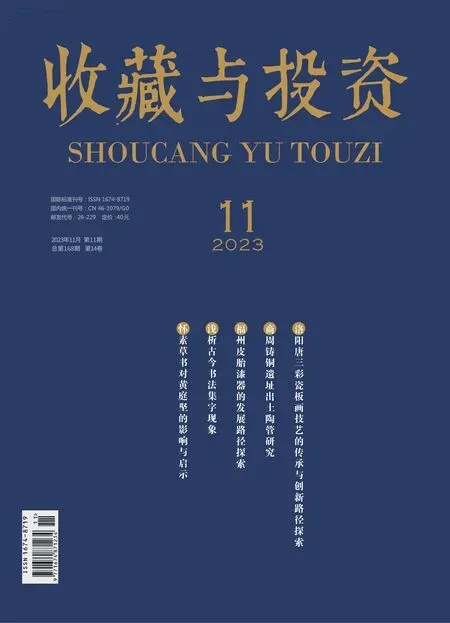淺析古今書法集字現象
蘇 冰(沈陽師范大學,遼寧 沈陽 110034)
集字是書法學習的一個有效手段和必經過程,那么,集字對于書法學習有何意義?集字是怎樣產生發展的?本文試圖展開關于書法集字問題的討論研究。
一、書法集字的意義
書法集字是一種集古代法帖中的文字進行篩選組合的一種書法學習方式,書學者既可以通過集字對名家名帖進行欣賞,也可以為自己的書法創作集成書寫模板。縱觀諸多書法學習者的學書歷程,不可否認,集字現象是客觀存在的,是構建在臨摹與創作之間的一架橋梁,是書法學習者從臨摹過渡到創作的主要途徑,也是書法學習的一個有效手段,對于傳承古代優秀書法作品和充實現代書法學習的意義彌足珍貴。
對于書法學習者來說,集字是一個有效且無法繞開的學書方法,集字的過程也是學習的過程,在選擇所用的文字時,可以領略自己不熟悉的結字方式,開闊眼界。書法集字的意義還在于通過集字方式而形成的經典集字佳作。自古以來,諸多集字書法作品都是書法學習者進行欣賞和學習的重要范本,為書學者的集字創作提供了參照,且對前人精妙書跡的傳承與弘揚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集字既能引導書學者們尊重傳統繼承傳統,亦能啟發書學者們去開拓創新。
集字作為中國書法發展歷程中一種特有的現象,從集字大興的唐代到看重碑刻集聯的清代再到電子軟件集字的當代,集字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書法學習中均有著重要意義。
二、書法集字的歷史發展
考察中國書法史,“集字”方法在不同書家的學書過程中都有著特殊且重要的地位。那么集字是怎樣產生并發展的?在書法史中不同時期關于集字的觀念認識有何區別?
(一)集字出現的南朝
書法史中關于集字的記錄最早出現在南朝,梁朝的《集王千字文》是目前可知的最早書法集字作品。唐代張彥遠《法書要錄》卷三引武平一《徐氏法書記》記載:“梁大同中,武帝敕周興嗣撰《千字文》,使殷鐵石模次羲之之跡,以賜八王。”[1]
史書記載南朝梁武帝蕭衍命殷鐵石摹拓王羲之不同的字一千個,命周興嗣將這一千字編成有韻之文,后依據周興嗣之韻文將這些書法集字拼成《千字文》,作為王室子嗣識字和書法學習的教材。這種集字是先有字后依字撰文,雖然避免了無字跡可集的問題,但依字撰文對書者的文化涵養要求極高。此時集字的主要目的是提供范本以供王室欣賞臨習,主要是集王羲之字跡,一方面是因為王羲之的書風更便于日常書寫,在具有欣賞價值的同時具有實用價值;另一方面是由于君王的喜好,梁武帝蕭衍的個人審美比較側重于鐘繇,而在當時鐘繇書跡已經不可得,進而師法書法造詣亦極深的王羲之。
隨著朝代的不斷更迭,《集王千字文》原本已失傳,我們可以從存世的智永《真草千字文》(圖1)看其遺韻,王羲之的七世孫智永禪師在永欣寺精心臨摹八百余本《千字文》用以贈予江南各寺院收藏臨習,廣為傳播王羲之書法,其間或有部分《千字文》散于民間,普通人亦能一睹王羲之書風,這都為后來王羲之書風的大盛奠定了基礎。

圖1 智永《真草千字文》
(二)集字大興的唐代
隨著時代的發展進步,在社會安定、政治昌明、經濟繁榮、文化輝煌、藝術多元化的唐代,詩歌、書法、繪畫等方面均得到了空前發展,各領域出現了諸多飽學之士和不朽佳作。此時期書法領域有大量欣賞追摹王羲之書法的人,促進集字學書大興,集王字者前仆后繼,集字的佳作層出不窮。
多元繁榮的唐代社會對書法極度重視,參與科舉者重以書學為長、儒釋道三家書跡傳譯經卷、文人墨客以書藝會友且書畫收藏之風盛行。王室貴族對書法的重視對書法的發展有著重要作用。眾所周知,唐太宗對王羲之的書法極度崇拜,不惜重金尋求王羲之真跡,使得大量真跡被朝廷內服收藏,而那些青睞王氏墨跡的普通志士就難以一睹名家真跡,因而促進了唐代以集王字為主的集字作品不斷出現,如懷仁《集王圣教序》、僧大雅集《興福寺碑》、唐玄序集《新譯金剛經》等,其中對時人及后世影響最大的非《集王圣教序》(圖2)莫屬,可以稱其為唐代集字的巔峰。宋《宣和書譜》云:“昔太宗作《圣教序》,世有二本,其一褚遂良書,一則懷仁書……模仿羲之之書,必自懷仁始。”[2]《集王圣教序》為時人及后人臨摹王羲之筆跡提供了新的范本,促進了王羲之書跡的保存與流傳。

圖2 懷仁 《集王圣教序》
懷仁《集王圣教序》的集字方法是依文集字成篇,難在集字,沒有原字的造字、重復字的選擇、大小字的縮放、字里行間的連貫呼應皆是集字之難處,但此作字字精雅飄逸,款款相映成趣,這與懷仁自身深厚的書學造詣及其嚴謹務實、堅持不懈的態度密不可分。也正是如此,此碑才如此成功。此作不僅在唐代影響很大,直至宋明乃至當代,懷仁《集王圣教序》的地位也是無法動搖的。
(三)集字衰落演變的宋元明
宋代至明末清初時期,文人墨客對唐代單集一家書跡而成的作品青睞熱度下降,由“集字”學書逐漸轉變成“集古字”“集古”學書,致力于臨習名士前人經典碑帖的深厚意韻,集古出新,在學多家之所長后集眾法于一身并加以融會貫通,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書寫風格。
1.集字的演變—集古
宋代刻帖之風興起,文人墨客可以一睹深藏內府的諸多名家真跡原貌,隨著學書者書學閱歷的增加,開始致力于臨習前人經典碑帖,領悟經典意韻,借古開今,集古出新。
北宋書家米芾可謂是“集古”之大成者,米芾在其《海岳名言》中云:“壯歲未能立家,人謂吾書為集古字,蓋取諸長處,總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見之,不知以何為祖也。”[3]米芾學書初重臨摹學習古代名家書跡,集古眾家之長,通過對古人古法的揣摩臨習,深入理解古人用筆、結體、布局及氣韻等技巧,在集古學古過程中不斷思索積累,他集古不泥古,經過長期艱苦的集古積累,終于苦盡甘來,晚期形成自己獨特的書風,“既老始自成家,人見之,不知以何為祖也。”[4]
米芾的成功在于集古出新,這與唐代的集字是不同的,唐代集字注重“集”,是幾乎原封不動地照搬王羲之書跡集成,整體連貫的氣韻欠佳,而米芾集古則是通過精準臨摹掌握古跡以助自身書風的形成,臨習的同時有著自身情感的表達,富有氣韻。
2.集古與復古交織下的元明
元代趙孟頫承接了米芾“集古”學書的方式,重視學習古人法度并融古出新,提出的“復古”思想將書法回歸晉唐思想推向整個元朝書壇,力推“二王”,使得“二王”書風幾乎籠罩了整個元代,可見當時的書壇復古書風之盛行。趙孟頫在學習王羲之的書法過程中悟出學書既要潛心學習古人之法,又要開拓創新的道理,其在《定武蘭亭十三跋》中有言:“學書在玩味古人法帖……書法以用筆為上,而結字亦須用工。蓋結字因時相傳,用筆千古不易。”[5]在趙孟頫看來,學書要學古又要因時而變,這與米芾的集古思想有異曲同工之妙。
趙孟頫的書風及復古思想對明代文人書家的影響是深遠的,明代前期書法以人數眾多的臺閣體為代表,書風雖受元代影響推崇趙孟頫書風,扼制宋人取意書風,加之統治者的喜好,此時期書法風氣趨于程式化,書風大多平庸無味。以吳門書派為代表的明代中期,摒棄了臺閣體書風,提倡書法集古學書,上追唐宋名家筆法神韻。晚明時期的書法注重個性解放,重個人主觀情感意識的抒發,已經開始出現“臨創結合”的“集古”學書方式,代表書家董其昌、王鐸二人同為集古書學之大成者,熱衷于臨摹學古后進行個性創作,彰顯新的時代風氣。
自唐代以來至明末清初,在唐代大興的“集字”學書方法逐漸演變成更為靈活豐富的“集古”學書,書家們集古學古不泥古,在集字集古的基礎上求變創新,推動著中國書法的繁榮發展。
(四)集字形式轉化的清代
到了清代金石學復興,有識之士不再單一地追求以“二王”為中心的文人尺牘書法,以取法秦漢、復興篆隸為標志的書法變革運動逐漸展開。與此同時,文學領域楹聯興盛,集字與楹聯二者珠聯璧合,相得益彰,書法“集字楹聯”的形式備受文人書家喜歡,此時的碑刻集聯盛行之風不亞于唐時期的集王字之風,甚至似有超越之意。
“集字楹聯”的出現代表著集字學書形式的轉化,豐富了集字的內涵與形式,既有集字形式又有集古諸家,是集字學書與集古學書相融合的產物。清代文人書家鐘愛“集聯”。存世的集聯書法作品較為豐富,從中既能看到傳統經典法帖的古意,又能看到深厚的文化內涵,為后世學者研究奠定了豐厚的基礎。
(五)軟件集字的現代
隨著書法教育的普及和電子技術的快速發展,集字軟件開始出現并日益完備,為書學者的學習提供了便利的條件。集字已經不再受紙質法帖限制,可根據自己想要達到的書寫效果進行有選擇地集字,既可集一家書亦可集多家書,極大地擴充了集字選擇范圍,使得書寫者在集字的過程中可方便地查看所集文字的多種書寫形態,查看的同時有利于拓展并豐富書寫者的文字儲備。
除此之外,集字軟件集字十分方便快捷,只要輸入書寫內容,就可根據自己的喜好選擇章法形式與書體,簡單操作后一幅簡單的書法作品小樣就完成了,如有不滿意之處還可多次修改以作參考,極大地方便了書寫者的書寫創作。
三、結語
集字在書法學習過程中起著重要作用,是書法學習者從臨摹到創作的一個有效手段和必經過程。臨摹是創作的基礎,集字是臨摹的生發,不變的生發是創作前的突破,無論是臨習集字法帖還是進行集字創作都對書學者的書法學習與創作起著積極作用,我們應該發揚當前集字優勢,在尊古思古的基礎上創新,促進當代書法更好地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