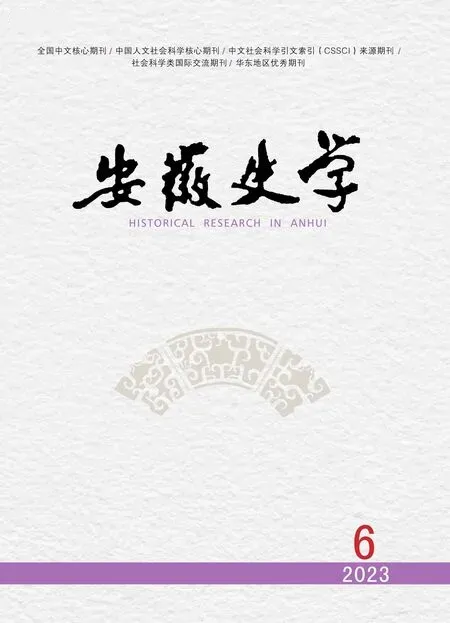蘇聯社會組織管理與發展芻議(1917—1930)
黃立茀
(中國社會科學院 世界歷史研究所,北京 100101)
20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蘇聯高度集中政治體制逐漸形成與確立。社會組織管理體制作為蘇聯政治體制的組成部分,實現了在憲法框架下部分自治向蘇共主導型體制的轉變。在蘇聯社會組織管理體制逐步構建與確立的背景下,社會組織的類型、概念、分類、成員的社會成分與領導機構成員的政治成分發生了哪些變化?這些變化與社會組織管理體制的確立與運轉有何關聯?轉變的背景何在?本文嘗試運用蘇聯歷史解密檔案與解密檔案集,1920年代出版的法令與命令匯編,1920年代黨的工作者指南中收錄的黨的文件,蘇共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全會決議匯編,1930年代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法令與命令匯編,1920年代、1930年代出版的相關雜志、學術著作,俄羅斯權威學者的研究成果等,對這一問題進行初步的探討。
一、十月革命以后至30年代初期社會組織管理體制變化與社會組織發展概況
十月革命以后,蘇維埃政權接受了沙俄時期社會組織的遺產。沙俄時期,社會組織得到了長足的發展。18世紀下半葉至20世紀初,歐洲啟蒙運動、俄國廢除農奴制改革、1905—1907年俄國第一次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等重大歷史事件,激發了社會自治積極性與政治積極性,俄國社會組織萌芽并迅速發展。20世紀初,社會組織的活動已涉及到各個階層、各個群體的利益保護、學術發展、收藏、慈善,也出現了自稱政黨的政治性的社會組織。
十月革命以后至20世紀30年代初,蘇維埃政權不斷探索對社會組織的管理,在此期間頒布實施了三個重要的法令文獻,社會組織管理與發展大體劃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1917年10月至1922年7月,對舊俄社會組織區別對待,進行臨時應急管理。
在該階段,根據舊俄社會組織對蘇維埃政權承認/反對的態度,新政權采取注銷/允許續存區別對待的方針。截至1920年代初,大部分舊俄國的社會組織不復存在。在該階段,受到國內戰爭干擾,蘇維埃政權未頒布關于社會組織管理的專門法令,地方上多頭機關注冊,社會組織自流發展,社會組織的管理處于無序狀態。(1)詳見黃立茀:《新經濟政策時期蘇聯社會組織管理體制的初創與確立》,《俄羅斯研究》2012年第3期,第103—125頁。
第二階段,從1922年8月至1924年4月,草創憲法與法律框架下社會組織自治的較為寬松的管理體制。
新經濟政策初期,許多反蘇知識分子團體利用社會組織多頭注冊的漏洞獲得注冊,反蘇活動活躍。規范社會組織管理,杜絕反蘇知識分子團體的活動刻不容緩。1922年8月3日蘇維埃全俄中央執委會(ВЦИК)與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人民委員會(CHK РСФСР)通過第一個社會組織管理的法令《關于不以營利為目的的協會與聯盟建立和注冊的程序與對其進行監督的程序(О порядке учреждения и регистрации обществ и союзов,не преследующих цели извлечения прибыли,и о порядке надзора над ними)》(以下簡稱《協會與聯盟建立和注冊的程序與監督的程序》)的決議(2)Собрание узаконении и распоряжении 1922г.30 августа,№ 49,С.622.,確定了遵守蘇聯憲法與法律為注冊的標準,規定了內務人民委員會為唯一的注冊機關。
該法令與沙俄時期管理社會組織的思路大體一致。1906年3月4日,尼古拉二世簽署《致參議院關于協會與聯盟暫行規則的上諭》(Именной высочайший указ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ующему сенату о временных правилах об обществах и союзах)(3)https://constitution.garant.ru/history/act1600-1918/5205/?ysclid=lexotlywt4280035419.,其第一條“確定下列協會與聯盟暫行規則”中社團禁止行為的第6款,規定了禁止社團從事行為的3條負面清單,第一條就是禁止違法。(4)“社團禁止:1.以違反社會道德或違反刑法所禁止的行為為目的、或以威脅社會安定與社會安全為目的;2.領導機構或領導人在境外,且社團具有政治目的。”從這一條款看到,沙俄政府禁止社團從事三方面的行為:1.禁止違法;2.禁止違反社會公德和威脅社會安定與社會安全;3.禁止社團跨境且具有政治目的。
蘇維埃政權1922年8月3頒布的法令大體上繼承了1906年法令的這個管理思路,而且禁止的條款更少。這一相對寬松的管理法令,使社會組織大體上能夠自主自治,給予社會組織發展的寬松空間。社會組織發展進入“黃金時代”。
第三階段,從1924年5月至1930年8月,社會組織管理思路和管理體制向“應該做什么”轉變,蘇共主導型社會組織管理體制確立。
1925年蘇聯經濟恢復到戰前水平。聯共(布)十四大提出工業化方針。是年初,斯大林對國際形勢做出“戰爭的爆發不可避免”的判斷,并做出應準備應付一切,加強國防建設的結論。(5)1925 年 1 月19日,斯大林“在俄共(布)中央全會上的演說”中分析國際形勢時指出:“戰爭的前提日益成熟而使戰爭的爆發不可避免(當然不是明天不是后天,而是幾年以后)。”“由此應該得出結論:要準備對付一切,要準備好自己的軍隊,要供給軍隊鞋子和衣服,要訓練軍隊、改進技術裝備,要改進化學部隊和空軍,要把我們紅軍的水平普遍提到應有的高度。這就是國際形勢要求我們做的事。”《斯大林全集》第7卷 ,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 13—14頁。基于此,蘇維埃政權確立了重工業優先,建設備戰型經濟的發展戰略。為了籌集工業化資金,實行對農民的“貢賦”政策。農民因不滿農業稅過重和工業產品高價格的剪刀差,加之1924—1925年由于旱災嚴重歉收(6)Объяснительная записка к единому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му бюджету СССР на 1924-1925 бюджетный год (октябрь 1924 г.- сентябрь 1925 г.Часть 2.С.622,轉引自趙旭黎:《1924—1925年間蘇聯的農村危機與政策調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15 期,2022年3 月,第1—50頁 。,農村出現騷亂、沖突等局部動蕩。截至1925年初,國內有22個省建立起呼吁保護農民利益,客觀上具有政治性的農民聯盟。(7)Совершенно секретно:Лубянка—Сталину о положении в стране 1922-1934гг.Т.2 ,М.: Наука,2003.C.304.為了應對農村的局部動蕩,蘇維埃政權一方面采取“面向農村”減稅等經濟舉措,農村局勢很快得到扭轉;另一方面,聯共(布)中央開始改變社會組織管理思路,果斷地從“禁止做什么”,向“應該做什么”轉變。
1924年5月23—31日聯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會召開,會議通過了“關于黨的建設的當前任務”的決定,第一次明確指出黨組織要成為社會組織思想和政治的領導。(8)《蘇聯共產黨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匯編》第2分冊,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22頁。這為社會組織管理體制向蘇共主導型轉變一錘定音。為貫徹這一精神,聯共(布)中央制定包括削減所謂重復建立的社會組織的較為具體的管理方針,在黨的正式官名冊中任命100名干部到群眾性組織擔任領導工作。根據削減組織數量的方針,1928年2月6日,蘇維埃全俄中央執委會和俄聯邦人民委員會通過關于社會組織管理的第二個重要文件《關于批準不以營利為目的的協會與聯盟之條例》(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Положение об обществах и союзах,не преследующих целей извлечения прибыли)(以下簡稱《批準協會與聯盟條例》)。這個條例規定:廢止1922年8月通過的關于社會組織的法令與法令細則;重新審核1922年被確認合法注冊的社會組織的章程,并決定是否準予這些組織重新注冊。該條例最重要的變化,是規定了憲法與法律之外新的準入條件,包括對重復建立的社會組織拒絕予以批準注冊。這次重新登記的結果,便是多數1920年代活動的自主社會組織被注銷,幫助政權型組織占據社會組織的主導地位。
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為了應對不斷緊張的國際形勢,蘇聯建成中央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社會組織管理體制是這一體制重要的組成部分,也做出相應的調整。1930年8月30日通過關于社會組織的第三個重要法令《關于自愿協會與聯盟(同盟、俱樂部、協會、聯盟)之條例》《Положение о добровольных обществах и союзах(объединениях,клубах,ассоциациях,федерациях)》(以下簡稱《自愿協會與聯盟條例》),該條例明確地將社會組織的宗旨定格在促進“社會主義建設以及促進鞏固國家國防”(9)詳見黃立茀:《新經濟政策時期蘇聯社會組織管理體制的初創與確立》,《俄羅斯研究》2012年第3期,第103—125頁。的框架內。該條例的頒布和實施,標志著蘇共主導型社會組織管理體制確立,社會組織管理思路徹底完成向“應該做什么”的轉變。社會組織從原來主要是保護群體利益、發展個人興趣等,轉向促進實現國家戰略。該條例的實施,形成幫助政權型組織一統天下的社會組織體系。
二、 反映管理體制變化:社會組織稱謂顯著調整
十月革命以后至20世紀30年代初期,隨著社會管理體制的轉型,在若干與社會組織相關的重要文件中,對社會組織概念的稱謂進行了相應的調整。
在第一階段,較多沿襲沙俄時期對社會組織的稱謂。十月革命前,強調社會組織的私人性和組織性,使用小組(кружки)、私人團體 (частные общества)(10)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СССР Институт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и права.Добровольные общества при социализме.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1976.С.8.、會議(собрания)、聯盟(Cоюзы)等概念稱謂非國家的社會團體。1906年3月4日,沙皇尼古拉二世簽署《致參議院關于協會與聯盟暫行規則的上諭》,與國際通用的社會組織概念進行接軌,強調社會組織的非營利性,出現了“不具有營利目的的團體(общества,не имеющие задачею получение прибыли”)(11)1906 г.,марта 4 Именной высочайший указправительствующему сенату о временных правилах об общества и союзах.https://constitution.garant.ru/history/act1600-1918/5205/?ysclid=lexotlywt4280035419.的表述。
十月革命以后至1920年代初,由于社會組織在多頭機關注冊,缺乏統一的文件,社會組織概念很不統一。在蘇維埃全俄中央執委會(ВЦИК)與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人民委員會(CHK РСФСР)的首批文件中,使用了“協會(Общество)”、“聯盟(Cоюз)”的概念。(12)Ильина И.Н.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России в 1920-е годы.Москва 2000.С.35.同時,也注意了社會組織的自愿性特點,使用“自愿小組(Вольные кружки)”、“自愿協會(Добровольные общества)”等稱謂。
在第二階段,一方面繼續使用舊俄時期的概念,另一方面開始凸顯社會組織階級的色彩和為蘇維埃政權服務的目標。新經濟政策初期,蘇維埃政權借鑒了舊俄對社會組織的界定。1922年,官方開始使用不以營利為目的的協會與聯盟(общества и союзы,не преследующие целей извлечения прибыли)的表述,并且出現在新經濟政策時期第一個關于社會組織最主要的法律文件《協會與聯盟建立和注冊的程序與監督的程序》的決議中。與此同時,鑒于蘇維埃政權是勞動人民的政權,該時期對社會組織概念表述亦表現出鮮明的意識形態色彩。突出了社會組織是“勞動人民”團體的階級屬性:1924年,在聯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會“關于黨的建設當前任務”的決議中,首次使用了“勞動人民自愿團體(Добровольные общества трудящихся)”(13)КПСС в резолюциях и решениях съездов,конференций и Пленумов ЦК.Т.3.М.:1984.С.215.的概念。后來,這一概念繼續使用,并且在法律上得到了鞏固。新經濟政策時期,為了配合完成新政權的任務,創立了新型的社會組織,隨著這一組織形式的迅速發展,出現了相對應的概念。1920年代,官方使用了“群眾性組織(Моссовые организации)”的概念,主要指“消滅文盲”協會(ОбществоДолой неграмотность)、幫助革命士兵國際組織(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омощи борцам революции,МОПР) 、兒童之友協會(Общество Друг детей)、城市對農村助導協會(Общество шевства города над деревней )、《國防與航空—化學建設之友協會聯盟》(Союз Общество друзей оборны и авиационно- и химического стройтельства,Осоавиахим)等。這些組織之所以被稱為群眾性組織,是因為其成員的數量通常以數百萬乃至千萬計。同時,由于這些組織大多是在黨的支持下成立和活動的,其宗旨是協助執行蘇維埃政權的方針,對這類組織又出現了更新的表述:1928年,在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НК РКИ)給內務部關于不以營利為目的的社會組織注冊和對其活動進行監督的一封信件中,直接將群眾性組織(Моссовые организации)稱為“幫助蘇維埃政權團體(Общества содействия Советской власти)”。(14)ГАРФ.Ф.Р-393.Оп.81.Д.95.Л.185.鑒于這一稱謂最貼切地反映了蘇維埃時期新型社會組織與通常意義上非政府組織的區別,在蘇聯解體以后,俄羅斯學者一般使用“幫助蘇維埃政權組織”,有時也用“群眾性組織”的術語來稱謂。
第三階段,以憲法形式統一規定社會組織的概念。 隨著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高度集中經濟、政治體制確立,社會組織作為蘇聯政治體系重要的組成部分,其為蘇維埃政權的方針服務已經被有關文件規定下來,無需表現在稱謂上。因此,1930年8月30日通過的《關于自愿協會與聯盟(同盟、俱樂部、協會、聯盟)之條例》中,直接使用了“自愿協會與聯盟”的概念。
1936年通過的蘇聯憲法(根本法)《Конституция(Основной закон Союза Советских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Республик)》,以法律形式確認了斯大林經濟政治體制。同樣,對社會組織的概念進行了統一的法律規范:用“社會組織(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的術語,取代了之前使用的各種帶有不同定語的概念。在憲法第10章第126條中確認,“為了適合勞動者的利益和發揮人民群眾組織上的主動性和政治上的積極性起見,保證蘇聯公民有權結成各種社會組織《право объединения в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организации》(15)Советские Конституции.М.: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1963.С.263.,即工會,合作社,青年組織,體育和國防的組織,文化、技術和科學等組織”。1936年憲法所確認的社會組織的概念,被斯大林之后的蘇聯各個時期延續使用。1991年底蘇聯解體以后,俄羅斯學者仍習慣性地使用這一概念。(16)Правовые основы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не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проблемы и направления 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ния,М.:Юриспрудунция,2004 г.C.26.
三、 保障集中管理:社會組織分類做出重大改變
十月革命后,在嚴厲取締敵對、或不利于新政權的社會組織的同時,蘇維埃政權立法,確定了人民有建立社會組織的權利:1918年7月10日第五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會議通過的憲法宣布:“保障勞動者享有真正的結社自由”。(17)Советские Конституции.Справочник.М.: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1963.С.134.這一法令奠定了蘇維埃社會組織成立與發展的法律基礎。
1918—1920年的國內戰爭時期,殘酷的戰火熔斷社會組織發展的進程。國內戰爭結束,轉入新經濟政策以后,蘇維埃政權在各個社會領域的工作逐步步入正軌。
1922年8月3日關于社會組織管理的第一個法令《協會與聯盟建立和注冊的程序與監督的程序》的決議頒布實施以后,社會組織發展迅速。根據最早的統計數據證實,1922年底僅有49個注冊的社會組織(18)ГА РФ.Ф.Р-393.Оп.1с.Д.97.Л.10.,而到1928年初,注冊的社會組織增加了92倍多,達到4577個。(19)Власов Ю.Добровольные общества как форма советской демократии // Советское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1929.№4.С.64.1928年1月1日內務人民委員會統計部報告的數字略有出入,1928年社會組織的數字是4480個。(20)ГА РФ.Ф.Р-393.Оп.81.Д.95.Л.18.
新經濟政策時期,社會組織不僅數量增長快,而且類別豐富。政府從管理的角度出發,先后在1924、1926、1928、1930年四次對社會組織進行分類。隨著社會組織管理體制的轉型,社會組織分類方法及在相關分類方法框架下社會組織的類別呈現出較大的變化。
(一) 第一次分類,按層級、地區、職能劃分,共27類(1924年4月)。
1924年進行了第一次正式分類。是年4月,內務人民委員會委員А.Г.別羅巴拉多夫(БелобородовА.Г.)呈遞斯大林關于1922—1923年在俄聯邦內務人民委員部注冊的社會組織和聯盟的報告,將社會組織劃分為全俄和地區兩大部類。在兩大部類之下,按職能進行了具體分類。
全俄羅斯的社會組織主要包括——科學的、文化教育的、文學的、藝術的、宗教—哲學的、民族的、運動的、科學—工業的、農業的、技術的、幫助與互助的、法律的、反宗教的、宗教的、其他各種的(разные),計15類。
地區的社會組織主要包括——科學的、醫學的、法律的、方志的、工程師和建筑師協會、保護健康協會、畫家和作家聯合會、文化和教育的、慈善的、世界語、事物的聯合體(деловые объединения ) 、其他的(прочие),共計12類。(21)ГА РФ.Ф.Р-393.Оп.1с.Д.97.Л.10 10 об.
全俄和地區社會組織共計27類。
(二)第二次分類,執行削減現存組織數量的方針,縮減與意識形態相關的和劃分過細的類別,從27類縮減到19類(1926年4月)。
1924年官方對社會組織的分類比較細。如此分類比較瑣碎,增加了注冊和管理的難度。1925年2月16日聯共(布)中央委員會組織局通過一個標志性的文件——“關于自愿群眾性組織”的決議,制定了關于黨全面領導社會組織的一系列重要而具體的規定。規定之一,是要切實地以各種方式削減現存組織的數量,因為社會組織“出現平行重復的現象”。(22)Российска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Справочник партийного работника.Вып.Пятый.(1925 г.).М.:Госиздат,1926.С.С.291.這一規定說明,黨要將社會組織控制在一定的種類和數量之內,與這一方針相聯系,1926年的分類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
1926年4月內務人民委員會發給聯共(布)中央委員會的報告簡化分類,將原來全俄羅斯的15類縮減到9類:科學的、文學的、藝術的、技術的、民族的、幫助與互助的、幫助政權的、文化教育的、農業的。同第一次分類相比,撤銷了與意識形態密切相關的4類。(23)即:宗教—哲學的、法律的、反宗教的、宗教。同時,認為科學—工業類與科學類平行,前者被撤銷。由于出現了幫助政權的新型組織,在分類中增加了這一新的類別。
地區的分類從12類縮減到10類——科學的和科學—技術的、幫助與互助的、幫助政權的、文化和教育的、音樂—藝術的、文學的、農業的、運動的、事物俱樂部、研究國際語言的。(24)ГА РФ.Ф.Р-393.Оп.2с.Д.1752.Л.20.雖然類別數字變化不大,但是類別內容變化較大:取消了8類,包括原來劃分過細的6種職業興趣類(25)即:醫學的、法律的、方志的、工程師和建筑師協會、保護健康協會、世界語協會。和其他類。由于國家開始建立社會保障制度,不再對慈善類組織注冊,取消慈善類。增加的類別中,與全俄層級一致,增加幫助政權類、幫助互助類。還增加音樂—藝術的、文學、運動、研究國際語言類。
第三次分類,取消全俄與地區的層級劃分,從19類精簡到9類(1928年1月)。
在1928年1月1日的統計報告中,社會組織的種類進一步收縮,分類方法出現重大變化:取消全俄與地區這一層級別的劃分,將所有社會組織按職能劃分為9種:科學的和科學—技術的、幫助與互助的、文化—教育的、音樂—藝術的、文學的、農業的、群眾自愿的、運動的、民族的。(26)ГА РФ.Ф.Р-393.Оп.81.Д.95.Л.1,19.這次分類方法的改變在社會組織管理權向中央集中方面意義重大。它標志著原地區性的組織須加入全國性同類別的組織系統,以全國性組織地區分支的形式存在。如此分類,便于國家對社會組織按領域劃分,進行集中、垂直的管理。
第四次分類,全國統一按職能和社會領域劃分,從9類降為8類(1936年11月)。
1928年1月1日的統計報告中將所有社會組織劃分為9種,這種分類一直保持到1930年代初。在1930年代社會組織管理完成向蘇共主導型轉型之后,社會組織的分類以憲法形式固定下來。在1936年11月25日—12月5日召開的全蘇蘇維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會通過新憲法,其第10章第126條規定:“為了適合勞動者的利益和發揮人民群眾的組織上的主動性和政治上的積極性起見,保證蘇聯公民有權結成各種社會團體,即工會、合作社、青年組織、體育和國防的組織,文化、技術和科學等團體。”(27)姜士林、陳瑋主編:《世界憲法大全》上冊,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89年版,第1062頁。從這些內容可看出,1936年憲法根據職能和社會領域劃分,將社會組織分為8種。整個蘇聯時期,如1956年頒布的憲法大體沿襲了這一分類。(28)《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憲法(根本法)》,法律出版社1957年版,第23頁。而1977年憲法沒有對社會組織進行具體分類。(29)姜士林、陳瑋主編:《世界憲法大全》上冊,第1028頁。蘇聯時期,學者大體上根據1936年憲法的分類對新經濟政策時期的社會組織劃分類別,但是依研究對象的需要,有時將不同社會領域的組織合并統稱為自愿協會與聯盟,作為社會組織的一個大類別,與其他類別的組織相并列。即將社會組織分為4種:自愿協會與聯盟、工會、合作社、青年組織;有時為了研究方便起見,根據活動領域將社會組織細分為6種——科學協會、創作聯盟與協會、文化教育協會、國防運動協會與聯盟、互助與社會幫助協會、政治聯合協會,再加上工會、合作社、青年組織,共計分為9種。Коржихина Т.П.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в СССР .Материалы к источниковедению и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и.М.:РГГУ,1992.
四、受管理體制變化影響:不同類型組織的比例逆轉
由于蘇維埃政權1924年以后對自愿性組織發展開始采取限制的方針,不同類型社會組織的數量發展呈現很大的變化,請看以下的數字。

表1 1924—1928年各類社會組織發展動態 單位:個(30)Власов Ю.Добровольные общества как форма советской демократии // Советское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1929.№4.С.65.
從上表看到,以1924年為界,自愿性組織與群眾性組織占全部社會組織的比例,發生明顯的逆轉。1924年,學術團體(科學與科學技術,227個)占全部社會組織(545個)的比例為41.6%以上。而到1928年,下降為占全部組織的9.6%(441個/4577個)。群眾性團體1924年幾乎為0,1925年約為3.4%(24個/698個),1928年增長為40%(1836個/4577個)。1924—1928年,全部組織增加了7.4倍(4577個/545個),其中,自愿性社會組織(科學與科學技術、幫助與互助、文化—教育、音樂—繪畫—文學、農業、運動、民族及其他類)團體增加了4倍(2741個/545個),而增加最快的是幫助政權的“群眾性團體”類,增加了75.5倍(1836個/24個)。
從時間段看,社會組織增加速度最快的是1927—1928年,1928年比1927年增加了3368個組織,是1927年數量(1209個)的近2.8倍。在這1 年間,增加最多的還是群眾性團體,增加1752個,比1927年增加了20.8倍(其他類增加901個,幫助與互助增加437個)。
從這個統計數據我們看到,在1925年以后,增加速度最快的是幫助政權型社會組織。由于這些組織單個規模大,組織數量的迅速增長,使得這類社會組織在社會上影響迅速增長,決定了新經濟政策下半期社會組織的整體面貌,體現了社會組織的轉型。
五、 保障新的宗旨:社會組織成員與管理成員政治成分變化
新經濟政策時期社會組織成員的政治成分,體現了新舊社會相交替的特點:一方面,1920年代絕大多數社會組織中無黨派成員占絕大多數——說明這一時期尚脫胎于舊社會不久,仍保持著舊社會的痕跡;另一方面,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亦占有一定的比例,凸顯出蘇俄是共產黨掌握政權的新社會。根據1926—1927年的數據,幫助革命戰士國際組織中無黨派占71%,聯共(布)黨員和候補黨員占16%,共青團員占13%;(31)Власов Ю.Добровольные общества как форма советской демократии // Советское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1929.№4.С.31.世界語聯盟中聯共(布)黨員占15%(32)РЦХИДНИ.Ф.17.Оп..85.Д.22.Л.2.,蘇維埃電影工作者協會中,無黨派占60%,聯共(布)黨員占35%,共青團員占5%;(33)Коржихина.Т.П.Извольте быть благонадежны!С.230.在掃除文盲協會列寧格勒分會中,1929年共產黨員僅為2%,共青團員占10%。(34)Отв.ред.Купайгородская А.П.Добровольные общества в Петрограде Ленинграде.С.29.當然,也有一些協會,如在列寧格勒無產階級旅行者協會中,共產黨員的比例較高,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占到45%;(35)Отв.ред.Купайгородская А.П.Добровольные общества в Петрограде Ленинграде.С.172.1926—1927年,在戰斗的無神論者聯盟中聯共(布)黨員占54%,無黨派占46%。(36)Олещук Ф.Н.Х лет Союза воинствующих безбожников СССР,М.: ГАИЗ,1936.С.31.
新經濟政策時期在社會組織的領導機構——社會組織理事會中,共產黨員的比例高于整個組織成員中共產黨員的比例。1925年全俄羅斯與地方社會組織領導機構成員政治成分比例如表2。

表2 1925年全俄與地方社會組織領導機構(理事會)成員政治成分(37)ГАРФ.Ф.Р-393.Оп.2с.Д.1752.Л.20.
從表2可以看到,社會組織領導機構成員政治成分有以下特點:
第一,在全俄性社會組織中,文化—教育類和幫助政權機關類組織領導機構中黨員的比例最高,達84—100%。
第二,地方組織中,理事會中黨員比例有所降低,但是黨員比例最高的亦是幫助政權機關組織和文化教育類組織:前者理事會中黨員比例為67.7%,位列第一;后者為59%,位列第二;事務俱樂部位列第三,為57.7%;此外,運動類組織和幫助—互助類組織比例也比較高,分別達到56.6%和44.2%。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無論全俄社會組織還是地方社會組織,其理事會成員政治成分均有一個特點:愈靠近教授知識和進行文化教育類的團體以及幫助政權類組織,領導機構中黨員的比例愈高。
第三,理事會中黨員比例最低的,基本是自然科學類的組織。如全俄科學類組織理事會黨員比例最低,為11%。地方社會組織中,科學與科學技術、農業、音樂—繪畫和文學及其他類都在理事會黨員比例最低的方陣中。
由于1924年聯共(布)十三大通過黨組織要成為社會組織思想和政治領導的決定,1924—1927年的3年間,理事會中黨員比例逐年上升。1924年7月1日這一數據為19.3%,1925年1月1日為26.9%, 1926年1月1日為33.1%,1927年1月1日為33.2%,3年間理事會中黨員比例增加了72%。(38)ГАРФ.Ф.Р-393.Оп.81с.Д.95.Л.19.這一數據表明,黨對社會組織領導的力度在逐年加大。
結 論
綜上分析,嘗試對十月革命以后至20世紀30年代初期社會組織管理與發展得出三點結論。
第一,新經濟政策初期,社會組織管理大體上繼承沙俄時期規定“禁止做什么”的管理思路,社會組織更多具有自治的特點。十月革命以后至新經濟政策初期,蘇聯高層領導對怎樣管理社會組織還在探索之中,因此,沿用了舊俄時期的管理思路。主要體現在兩點上。一是,當時對社會組織的稱謂尚沿用沙俄時期“非盈利團體”的中性定性。其次,關于社會組織注冊條件。蘇維埃政權1922年8月3日頒布的法令與1906年3月4日尼古拉二世簽署的《致參議院關于協會與聯盟暫行規則的上諭》中的管理思路類似:只規定社團“禁止做什么”,而且禁止的條款更少——規定了禁止社會組織從事違背蘇聯憲法與法律的條款。
第二,1922年8月—1930年,蘇維埃政權先后頒布實施三個關于社會組織的法令,推動社會組織管理思路從“禁止做什么”向“應該做什么”轉變;管理體制從憲法與法律框架下自治向蘇共主導型轉變;社會組織宗旨從主要關注個人、群體向助推實現國家戰略轉變。在這一轉變的框架下,關于社會組織的稱謂變化,凸顯無產階級階級性、幫助政權性,標志著已經形成新的社會組織體系;社會組織分類方法變化,組織類別減少,區域層級取消,構建了便于國家集中、垂直管理的社會組織體系;社會組織成員和理事會成員中共產黨員增加,幫助政權型組織成為社會組織的主體,這兩個變化為社會組織發揮幫助政權的功能提供了政治領導保障和組織保障。簡言之,至30年代初,蘇共主導型社會組織管理體制和以助推實現國家戰略為宗旨的社會組織發展體系,基本完備。
第三,社會組織管理與發展的變化并非蘇維埃政權憑空構想或從理論教條而來。它是兩個社會體系對立大背景下新生蘇維埃政權艱難求生存與發展的產物,具有客觀必要性與社會主義客觀合理性。
十月革命以后蘇維埃國家走上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然而,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理論上對立,價值觀迥異,戰略目標對立——是存在著結構性矛盾對立的兩個社會體系。(39)當然,除對立以外,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還相互依存。世界自16世紀進入資本主義時代以后,在資本主義國家發軔以蒸汽機,電力,原子能、電子計算機、空間技術、生物工程等分別為主要內容的三次工業革命。資本主義因占據工業技術和高新科技的先機,生產力迅速提高,并積累了巨額的財富,一直是居于主導地位的社會體系。列寧教誨社會主義者,“僅靠摧毀資本主義,還不能填飽肚子。必須取得資本主義遺留下來的全部文化,用它來建設社會主義。必須取得全部科學、技術、知識和藝術。沒有這些,我們就不能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生活”。(參見《列寧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頁。)然而,蘇聯領導人未真正理解列寧教誨的深意,過高估計蘇東社會主義發展水平,低估資本主義自我調節的能力,未認真學習美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與管理經驗,未占領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前沿,經濟與科技落后于美西方,沒有展示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這是蘇東劇變最重要的教訓之一。由于這種對立,從蘇維埃俄國創建社會主義制度之初,西方國家就企圖把蘇俄扼殺在搖籃里,對蘇俄進行武裝干涉、經濟封鎖、外交孤立和政治敵視。在西方國家的武裝干涉被粉碎以后,資本主義世界仍拒不承認蘇維埃政權,而且圖謀趁蘇維埃政權困難之際恢復在沙俄和臨時政府時期獲得的權益。盡管1920年1月16日協約國最高委員會宣布撤銷對蘇俄經濟封鎖,1921年3月以后蘇俄先后與英國、德國、奧地利等12國簽署雙邊貿易協定,但是1921年蘇俄發生大饑荒,19個資本主義國家討論“援助蘇俄渡過饑荒”時,稱蘇俄若償還舊債和發還原外國企業,各國可考慮給蘇俄發放貸款和救援。為救燃眉之急,蘇維埃政權回應,如承認蘇維埃政權,提供優惠貸款,締結和約,可考慮各國的要求,并建議召開國際會議進行討論。1922年4月協約國最高委員會在熱那亞召開歐洲經濟會議,會議以3月份英國專家會議備忘錄的基本原則——歸還沙俄、臨時政府的債務與財政義務、國有化的外國企業一律歸還原主、取消外貿壟斷權、停止共產主義宣傳等苛刻要求,作為討論蘇俄代表團建議的基礎。(40)參見周尚文、葉書宗、王斯德:《蘇聯興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6—200頁。上述要求充分暴露資本主義國家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在政治與經濟上敵視蘇維埃政權的立場。在這一大背景下,蘇俄若想獲得西方貸款和援助就要放棄社會主義的初衷。當然,蘇俄國家拒絕奴役性的條款,選擇依靠自身力量救災和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道路。
20年代中期以后,斯大林做出帝國主義再次對蘇俄進行干涉的戰爭不可避免的判斷和應加強國防建設的結論。鑒于此,聯共(布)十四大確立并開始實行重工業優先的備戰型經濟戰略。此后,蘇聯各個領域圍繞著這一戰略目標調整發展方針和管理體制。20年代末30年代初,蘇聯建成指令性計劃經濟和中央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在此框架下,蘇共主導型社會組織管理體制和以助推國家戰略為宗旨的社會組織發展體系作為政治體制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構建完成。綜上所述,蘇聯社會組織管理與發展的變化并非主觀臆想或憑理論教條而發生的改變,它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資本主義敵視、包圍、威脅中圖存與發展艱難求索的產物。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蘇俄趕超型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形成的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