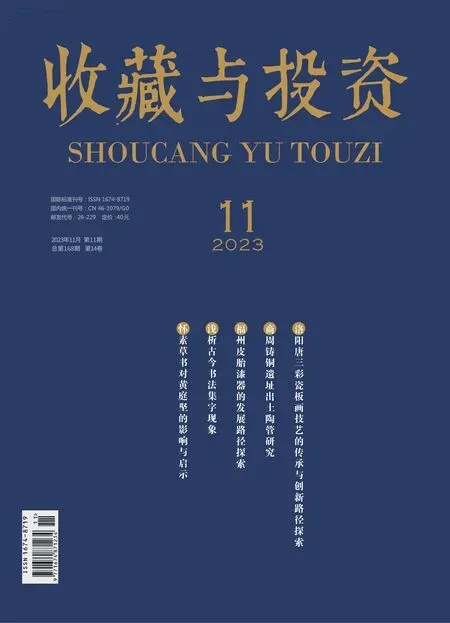信陽地域性繪畫創作中的召喚結構
王召召,康文慧(信陽師范大學,河南 信陽 464000)
一、物質與材料
信陽地域性繪畫采用油畫材料進行描繪。任何人對于客觀自然的感覺都是非常強烈的,但如何采用可支配的手段,使用特定物質材料將非凡的想象力付諸實踐卻不是一般的困難。要想充分地利用油畫與布面材料的肌理和質地,必須同復雜的視覺體驗緊密結合起來。在這個過程中,既要隱藏材料的物質特性,去表達對客觀物象的感覺,諸如色彩、明暗、形狀以及各個視覺元素的邏輯關系,又要避免過于圓滑與確定,如保持油畫質地材料的變化與調整、陌生化客觀視覺印象,但通過油畫顏料可以表達色彩和色調的微妙變化,傳達主觀的視知覺。信陽老城區的形狀是富有韻律的起伏,這是一種動態而非靜態的視覺印象,能將客觀的物質材料通過感性的感覺調配而召喚結構的第一層。
油畫的物質材料必須完全轉換為客觀的色彩塑造,使物質顏料本身創造出視錯覺,感知與自然平行的真實性,這與信陽地域性客觀景象的敏銳和細膩的感受密不可分。信陽老城區的肌理是多樣的,物質材料對不同客觀物象肌理有著不同的表達方式。云舒云卷的天空需要使用較為稀薄的顏料暈染,不同年代建筑物的外表則需要緊密厚涂來展現不同肌理的特色,起伏感觸動著視神經,物質材料在這里被轉換為造型細節。點滴虛化的物質材料可用于表現前景快速移動的物體,為視錯覺進行不斷鋪陳,展現出物象的瞬時性,地面厚實的堆積可以體現延綿的時間(圖1)。物質材料的實與精神世界的虛,通過視錯覺聯系在一起,物質材料正轉化成為現當代信陽老城區人們精神世界的現實環境。

圖1 《信陽地域性繪畫創作》(局部) 20 cm×100 cm 布面油畫 2023 年
二、形式與結構
召喚結構中“形式與結構”對應伊加登對文學作品的“語義單位層”“表現客體層”和“圖式化層面”分類,這需要一種特殊的邏輯思維,即形象思維,包含基形意象、完形意象、群形意象和易形意象四種形象思維。
基形意象在信陽地域性繪畫創作中最基礎的局部形態在各個細節中:信陽老城區線條的質感是豐富的,多山的路面讓原本筆直的道路形成微妙的曲線,深邃的樹木形成了縹緲的邊緣線,纏繞著的濃黑色電線將整個街道連為一體,人們相互之間的信息交流存于這些車流之間,交織成人類情感互動的基礎。畫面中表現的是信陽老城區人來人往和川流不息的運動感,運動感由各種細節構成。圓柱形和三角形松軟的樹木邊緣線,建筑物堅硬的方形構成實體的運動感,前景虛筆所描繪的瞬間形象構成虛體的運動感。基形意象在用筆的選擇方面,素描稿直接作為創作的底稿,經過反復修改形成斑駁變換的街道,天空部分采用硬毛刷拉出垂直厚重的天空肌理,底稿采用黏稠的調色油加上冷色的單色快速區分天空和地面,形成基本的薄厚對比,以表現畫面內容的流動感。待油底半干后進行深入刻畫,反復堆疊不確定性的筆觸與色彩,形成“虛筆”,即“用筆時,須筆筆實,卻筆筆虛,虛則意靈,靈則無滯,跡不滯則神氣渾然,神氣渾然則天工是在矣。夫筆盡而意無窮,虛之謂也”(惲壽平《甌香館集》)。運用虛筆碰撞出偶然的色彩關系,經過視覺的調和形成生成性的色彩。
由兩種以上的基形意象組合而成的完形意象體現在背景的建筑物充當靜的部分,街道上來來往往的行人車輛攪動著畫面,增加了觀看的趣味性。完形意象明暗分布,采用上明下暗的基本分布形式,但又犬牙交互,消失的地平線與平矮的房屋充當暗面的凹陷處、亮面的凸起處。沖出畫面的電線桿、近處的樓房、樹木等是暗面的凸起處、亮面的凹陷處。完形意象線條與形狀的選擇和分布上主動保留垂直方向的線條,用來平衡水平方向的全景式構圖,優化視覺結構。
結構上由完形意象的明暗空間、線條結構的布局組合而成的群形意象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群形意象的疏密關系是完形意象構圖關系中尤為重要的一點。密集處應當塞滿天地密不透風,卻不能毫無章法地堆積,密集處也應當有透氣的孔洞用來呼吸,優化密集處的結構;疏朗處則需空空蕩蕩,但不能空無一物,或增加一些有意味的形式對觀看者進行點化和引導,形成節奏與韻律上的變化。
群形意象之后,需要將感覺經驗通過繪畫技術轉換成繪畫藝術,只有隨著構思的發展和深入轉化為異形意象思維,才能實現信陽地域文化的藝術價值,將感覺經驗轉化為繪畫藝術的技藝,即繪畫的技巧與語言。在構圖上,信陽地域性繪畫探索采用游觀式的橫向全景構圖,將處于不同方向的街道“剪開”橫向觀看,借鑒傳統卷軸式的長卷,減緩觀看的速度,仿佛漫步其中。正如印象派大師莫奈晚期藏在橘園的長卷作品《睡蓮》(圖2)中所描繪的:夢境般的虛筆游蕩其中,產生生命般的共振。這種游離式的易形意象需要通過不斷試錯來達成,需要耗費大量時間和精力細細耕耘。

圖2 莫奈 《睡蓮》(局部) 布面油畫
三、物象與含義
由語言構建起來的象牙塔在畫面的物象面前瞬間消散,但背后的含義十分豐富。物象基于物質材料與形式結構,物象背后的人文含義在信陽地域性繪畫探索中顯得尤為重要,物象的選擇影響著文化含義的呈現,而形體卻是支撐物象表現的基礎,形體通過具體的繪畫物質材料表現出來。畫面由下到上或由上到下,由左到右或由右到左引導著物象背后含義的傳達。
由下至上觀看,即由近至遠,可以感受到速度在畫面里的變化,近處虛幻的形影,展示著快節奏的生活,引出所見之實皆為虛,即運動變化的世界轉瞬即逝,體現出對于時間的直觀表達,相反,遠處的本該虛幻的遠景卻如凝固的時間般永恒(圖3)。在“下”由點、線、面、色彩、用筆、形狀等物象所體現的視覺符號屬于視覺中的繁密,充滿深顏色的實體給人以束縛、稠密和沉重的觀感。視線逐漸向上移動,視覺逐漸得到解放,視覺壓力也得到減輕,物象在上方變得越來越稀疏,這也是人們在無法承受壓力的時候喜歡望向天空的視覺原理,因為明亮而自由的天空給人無拘無束的感覺,釋放下方稠密的視覺壓力。也就是從物體到視覺再到知覺的整體過程,而畫外之音則是文化含義,后者比前者有著更為重要的地位。反過來由上至下觀看,則是由稀疏轉向稠密,開頭的稀疏給人以空靈純凈的感受,而下方的稠密不再只是視覺壓力,而是視覺饑餓后的飽滿,充滿煙火氣的下方轉化為親切與溫暖的意義。由左至右觀看,呈現出連續延綿的物象,人物總體有一個向右的動勢,靜止的建筑物則朝著相反的方向用力。

圖3 《信陽地域性繪畫創作》示意圖
四、意義與意蘊
“寫生家神韻為上,形似次之;然失其形,則亦不必問其神韻矣。”(楊晉《跋畫》)神韻統領著繪畫創作的最高標準,內心便逐漸從世俗欲望中解脫出來,心境越發自由,越能感受到美,越能得到美的享受。美是矛盾的調和(托德亨特,1820年—1884年),這里的調和不是互相抵消、零和博弈,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矛盾統一體,也是主觀意識與客觀對象的完美統一。除了繪畫本體產生的氣韻,創作者“心齋”的形成與鍛煉也尤為重要,也就是創作實踐過程中心態的變化。創作者在創作過程中實現欲望的去除與心境的自由解放后可達到虛靜之道。信陽地域性繪畫創作,應該在虛靜的精神狀態下去深入了解對象所體現的知覺直觀,這需要借助繪畫對象(信陽地域性繪畫創作)與內心的噪音進行主觀上的抗爭,力求達到水面波濤洶涌后的平靜狀態,從而進入澄明之境,也是將主觀意識通過實踐中的繪畫語言物化為客觀對象的心路歷程,在美的觀照狀態下超越日常生活中所帶來的苦惱,即便畫面表現的只是日常生活。
信陽地域性繪畫創作背后呈現的意蘊通過游觀后的苦苦思索,厘清繪畫創作不可言說的神韻內涵,豐富自己的心理定勢。此外,能夠讓心理定勢轉化為實踐才是繪畫理論的最終出路。千言萬語終須凝練為瞬間就能呈現精神本質的視覺圖像。物質材料、形式結構、物象含義與最終的意蘊構成了信陽地域性繪畫創作的召喚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