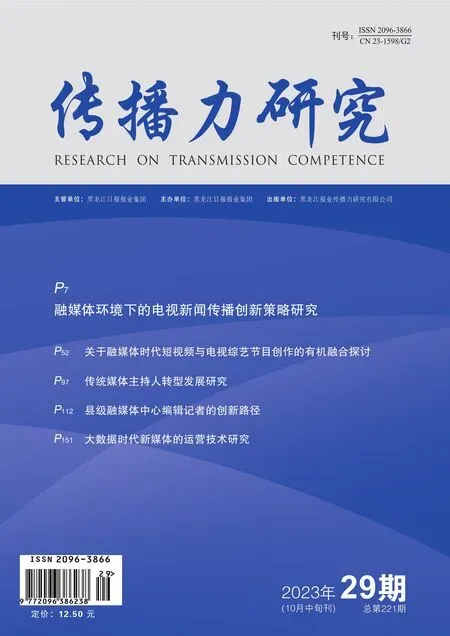試論電影中的“場所”及其空間敘事
◎渠水清
(四川傳媒學院,四川 成都 611745)
一、場所精神與敘事電影
諾伯舒茲在《場所精神——邁向建筑現象學》中寫道:“場所……很顯然不只是抽象的區位而已。我們所指的是由具有物質的本質、形態、質感及顏色的具體的物所組成的一個整體。”[1]他將場所分為自然場所和人為場所兩類。自然場所是人類生存的宏觀環境,人類需要考慮到自然強大力量對于人類的限制;而人為場所是被賦予了更多情感、認知等種種具有功能意義的觀念的混合空間。這種混合空間,是現代人類不可缺少的生存空間,也是被賦予文化價值與意義的空間。
電影藝術發端于工業生產,是人類文明發展和進步的過程中,科技與美學融合的一種新型藝術形式。空間是電影敘事研究的一個重要維度,它不僅是容納故事發展的、可視的真實存在,同樣也可以在電影中作為敘事線索或敘事主體,推動情節發展或升華影片主題。某些人為“場所”蘊含著人類的文化與情感認同,其不僅可以作為電影故事情節發展所依賴的一個背景以及推動電影情節發展的條件,而且還可以喚起觀眾的某種集體意識,彰顯影片的人文關照和情感價值。
二、作為“場所”的故事空間及其影像呈現
(一)《頑主》:造夢場所
電影《頑主》講述的是北京三個無業青年共同開辦了“3T”公司,為人排憂解難,幫人圓夢的故事。“3T”公司承載了一代年輕人的夢,但是在這個夢中,人們只能靠短暫的假象彌補心靈上的缺失,尋求某種心理平衡。影片中“3T”公司是一個極為普通的辦公場所,但是它的理念遠超于這個實在場所之外。青年們的無所事事與玩世不恭,代表了當時部分社會群體的心理。利用“3T”公司解決問題的消費者,也只是把這里當作暫時躲避現實、尋求當下與表面心理安慰的工具。
福柯在《另類空間》中基于“烏托邦”的概念提出了“異托邦”理念。“烏托邦是沒有真實場所的地方,這些是同社會的真實空間保持直接或顛倒類似的總的關系的地方。”[2]54緊接著,他闡述道:“在所有的文化、所有的文明中可能也有真實的場所——確實存在并且在社會的建立中形成——這些真實的場所像反場所的東西,一種的確實現了的烏托邦,在這些烏托邦中,真正的場所,所有能夠在文化內部被找到的其他真正的場所是被表現出來的,有爭議的,同時又是被顛倒的。這種場所在所有場所以外,即使實際上有可能指出它們的位置。因為這些場所與它們所反映的、所談論的所有場所完全不同,所以與烏托邦對比,我稱它們為異托邦。”[2]54筆者認為同樣可將這個概念運用到對《頑主》的探索中。“3T”公司如同投射烏托邦精神的真實存在的“異托邦”,它類似于福柯筆下的“補償烏托邦”,即符合“異托邦”概念的最后一個特征:“與剩余空間相比,它們有一個作用,這個作用發揮于兩個極端之間。或者異托邦有創造一個幻象空間的作用,這個幻象空間顯露出全部真實空間簡直加虛幻,顯露出所有在其中人類生活被隔開的場所。”[2]57在“3T”公司,人們幻想中的場景,通過“人為”策劃,變成了“真實”的事件,所有人一起做夢、一起造夢,在虛幻中得到精神補償。
“3T”公司這種造夢場所,是通過影像中的真實場所來反映和揭示某種幻想空間,將幻想與虛擬投射到現實生活中。在這個造夢場所中,主人公們將顧客的虛擬需求轉化為現實事件,這個類似“投影儀”的空間,用一種“投射”的方式,在真實與虛擬之間往復。
(二)《洗澡》:情感場所
影片《洗澡》的故事發生在北京一個即將被拆除的澡堂。澡堂老板老劉獨自撫養兩個孩子長大成人,大兒子劉大明年少離家做生意,二兒子劉二明智商低下。大明收到二明的簡筆畫信件誤以為老劉去世匆忙趕回北京,又由于二明走失這一事件,大明才意識到父親已漸漸老去。當他延長休假日期后,老劉卻突然去世,澡堂“清水池”也面臨拆除。大明決定將二明帶回南方,一起生活。
澡堂這一場所極具地方特色與時代特色,兼具開放性和私密性特征。進入澡堂的人都是赤裸相見,在同一個水池中沐浴、放松精神,展現真實的自己。影片開篇即對現代的洗澡方式做了大膽分析:洗澡屋坐落于城市的高大樓宇之間,付費后即可進入,單人單間,全自動化,類似于自動洗車場。這種全自動現代洗浴方式與傳統的泡澡、搓背顯然產生了矛盾。狹小的自動洗澡空間可以讓人們節省時間,高效快捷。而在澡堂中,人們既可以享受泡澡、搓澡、按摩的樂趣,同時還可以與他人溝通交流。澡堂在影片中不僅是一個文化符號,而且還是一個情感場所。在這里,私密與開放既是對立的,又是融合的。人們在澡堂中精神變得放松,通過交流宣泄自身情感,化解生活中的矛盾,重拾家庭的溫情,獲得他人給予的鼓勵與信賴。
澡堂本是人們建造起來用于沐浴的場所,然而它的文化功能卻在人們的利用中被更深層次地開發出來。影片拍攝手法平實質樸,顯現出澡堂的空間特性,同時又彰顯出人文特色,為樸實無華的澡堂賦予了多重情感價值。
(三)《看上去很美》:回憶場所
《看上去很美》改編自王朔的同名小說,講述了主人公方槍槍在適應保育院生活的過程中不服管教,聯合所有孩子與李老師抗衡、頂撞唐老師,最終被保育院孤立的故事。在影片的空間呈現中,教室和食堂分別是兩個大型的空間,其他空間為廁所、宿舍以及城墻下的室外游樂場所。臨近保育院的醫院是方槍槍和陳南燕偷偷跑到的最遠的地方。在這里,孩子們的飯食、衣著基本一致,甚至連如廁都要明確規定時間。在保育院阿姨制定的“規則”中,孩子們的表現與發放的小紅花又有所關聯,因而孩子們為了獲得小紅花也會故意做出非凡“成績”。拍攝集體畫面時,影片采用俯拍方法記錄每個孩子的舉動,類似“監控”。方槍槍是老師口中“不聽話的孩子”,渴望小紅花但也不像其他小朋友那樣順從。他策劃了一次小朋友的集體“叛逃”,并試圖將“妖怪”李老師逮住,但是卻很快被李老師“鎮壓”。之后方槍槍更加叛逆,最終被保育院的老師和其他小朋友孤立。
這是王朔帶有自傳性質的作品。保育院作為王朔的回憶場所,并不完全是天真、無邪的樣子,而是一個與世隔絕的小社會,充滿著成人的游戲規則。“地點本身可以成為回憶的主題,成為回憶的載體,甚至可能擁有一種超出人的記憶之外的記憶。”[3]344保育院承載了作者童年的回憶,但選用成年人的敘事視角進行敘述。“當‘空間’已經變成了一個中性的、去符號化的、具有可替代性和可自由支配性的范疇時,人們的注意力就轉向了‘地點’,以及它所擁有的神秘的、非特異性的重要性。”[3]346盡管《看上去很美》的“場所”構建并非具有創傷性,但是它所呈現的某種教育問題是深刻和值得反思的。另外,影片流露出對于自由的渴望,是童年世界也是成人世界所期待的。
三、“場所”與電影的空間敘事
(一)影像中“場所”的虛擬性與真實性
這三部影片中的“場所”,都具備虛擬與真實的雙重屬性。三部影片均為劇情片,以現實題材或小說為依據進行創作與改編。《頑主》的鏡頭以平實的跟、移鏡頭為主,而在虛擬和真實的區分中,對白的玩世不恭與鮮明的時代特色,與虛幻的做夢、造夢行為形成的強烈對比,將一個“造夢公司”變得真實起來。
《洗澡》采用大量全景鏡頭,拍攝澡堂的整體情況,總覽澡堂中人們的動作、語言、神態等。另外,影片中大量跟鏡頭,記錄了父親、大明、二明間的聯系,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著影片節奏,展現人物關系。在澡堂中的仰拍鏡頭呈現出水波折射在天花板的光影,真實的澡堂與虛擬的想象、情感空間,因虛幻的水波紋被模糊了界線。公共場所加強了人們的聯系,私密場所又釋放了人最本真的一面,澡堂便實現了人際關系的聯結。此外,《洗澡》中的澡堂也是反映老劉一家代際關系的場所。代際之地是“賦予某些地點一種特殊記憶里的首先是它們與家庭歷史的固定的長期的聯系。這一現象我們想稱之為‘家庭之地’或者‘代際之地’[3]346。”澡堂是老劉的工作場所,也是一家人生活、成長的代際場所。因此,它不僅是老劉一家,或者身邊的回憶,同時也是北京文化、時代逝去的一種回憶場所。
《看上去很美》采用大量俯拍鏡頭,具有監視、監督之義。鏡頭還會模仿兒童視角,仰拍保育院中嚴厲的老師。影片中的虛構場所,展現的是主角方槍槍一絲不掛地悄悄離開保育院,在雪中的小院散步、撒尿的場景。這種虛擬,也反映了方槍槍內心的反叛與對保育院的抵觸,以兒童視角展現出想要掙脫束縛、逃離牢籠,卻仍被“規則”束縛的無奈狀態。
現實場所的真實與想象場所的虛擬,都構成了對于“場所”的依賴情感。社會環境、文化習俗、長久居住等都是加深場所依賴情感的因素。人類在場所中積淀了深刻的情感,利用光影的方式得以呈現。
(二)歷史空間下的文化象征與場所符號
三部影片中的“3T”公司、澡堂、保育院分別在象征著夢、親情以及回憶。“3T”公司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當時青年人的思維,也象征著他們的生活態度和社會認知。澡堂象征著老劉一家人的生活,凝結著濃郁的親情。片中的澡堂被推翻,也揭示了新舊文化之間的沖突和碰撞,是對于親人逝去、時代逝去以及文化逝去的懷念。保育院則象征著逝去的時光以及某種失去的自由,揭示出保育院中小朋友的“生存法則”,在場所的呈現中體現了對于某個特定時代的回憶與反思。
不難看出,人們對于逝去的文化以及特殊的場所,有一種難解的迷戀與依賴之情。“場所依賴”的概念起源于段義孚于1974 年提出的“戀地情結”,表示人對場所的愛戀之情。“‘場所依戀’這個概念由丹尼爾·威廉姆斯和約瑟夫·羅根巴克于1989 年正式提出,指的是人與場所之間基于感情(情緒、感覺)、認知(思想、知識、信仰)和實踐(行為、行動)的一種聯系,其中感情因素是第一位的。”[4]場所不僅是具象的建筑物,更包含了抽象的人類活動與人類情感。“丹尼爾·威廉姆斯和約瑟夫·羅根巴克于1989 年最早提出了場所依戀的經典二維結構,認為場所依戀包括個體對場所功能上的依戀,即場所依賴和場所認同。個體對地方的功能性依賴,主要是對必要公共設施的需求;情感/象征性意義即通過個體的想法、價值觀、目的、經歷而建立的與該地方相關的個人認同。”[4]在對于場所依戀的刻畫上,電影相較其他藝術類型更能體現所強調和展現的場所的空間感,通過這種全面、縱深的效果,達到對于場所情感的刻畫,是電影的優勢,也是科技的優勢。對于藝術理念與文化觀念的認知,電影無疑是最直觀、最有效的表達方式之一。三部影片中所展現的“場所依賴”,也是對于中國在過渡階段的真實刻畫。人們對于地點的依賴,對于場所的依賴,逐漸變成一種趨勢、一種符號、一種文化標識。
(三)精神空間下的觀眾認同與認知反饋
在《頑主》《洗澡》與《看上去很美》這三部影片中,造夢場所、情感場所和回憶場所,似乎就是一部分人的日常生活片段,成為了反映和引發集體回憶的影視作品。在獲得的這些觀眾認同中,“3T”公司、公共浴池和保育院,它的符號“所指”都指向了集體回憶。而引發這些回憶的這些場所空間,讓人們對其產生了普遍認同與集體回憶,甚至依賴。齊格弗里德·克拉考爾在《電影的本性》中說道:“使迷醉于電影的人忘卻自己的孤獨的東西,并不是一個個人的命運(這也許會使他更感到孤獨),而是人們以不斷變化著的各種方式互相來往和交談的景象。它是在劇情中尋求機會,而不是尋求劇情本身。”[5]在影片中,觀眾通過導演“預設”的視角,循著導演鋪設的觀賞“軌跡”,通過電影反映的不同的故事,引發出某種同樣的情感或者思緒。這種情感的生發,是因為其中都暗含著對于這些回憶“場所”的依賴。
電影與其他藝術形式最大的區別就是利用運動的畫面來講述故事。三部影片中所展現的場所都帶有鮮明的文化特色與時代印記。當我們對這些場所產生依賴之情時,無疑是對于某種社會氛圍以及文化氛圍的回憶與依賴。這些場所暗含著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多重元素,諸如人際關系、代際關系、成長因素、生存因素等,這些元素結合使得影像中出現的特定“場所”成為不可替代的文化代表物或者情感寄托地。
四、結語
將“場所”這一具有地理學意義的概念運用到對電影的分析和解讀中,是對于電影空間解析的另一種視角。而通過“場所”來敘述故事,無疑是電影闡述文化現狀與社會現狀的一種新的方式與路徑。“大多數研究認為,人們對場所產生依戀是為了促進社交關系和集體認同感,而不是來自于對環境的物質特征的認知,因此并不將場所的物質特征視為影響場所依戀的重要因素。”[11]從“場所”角度介入對于影視藝術的研究,發展對于文化的多元思考,是對于“場所”內涵的光影藝術解讀,同時也是補充電影敘事方式的一種新的形式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