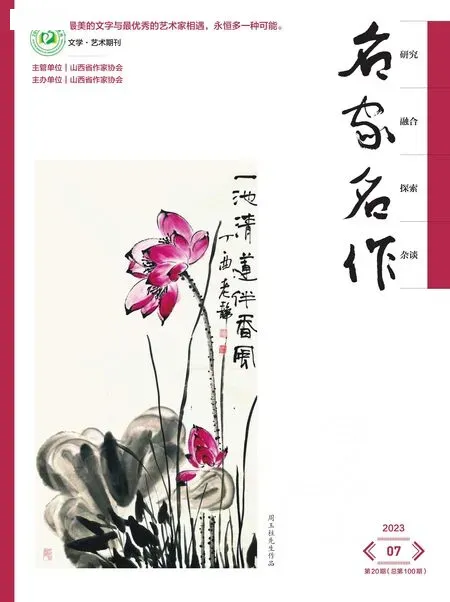抗戰時期延安木刻版畫插圖發展研究
何 婕
一、 延安木刻版畫的發展背景
抗日戰爭時期,國內工業生產和商品經濟遭到嚴重破壞,人民的生存面臨著極大的壓力,動蕩的社會局面再一次使中國的藝術發展陷入了困境。在物資匱乏的戰時環境下,延安等敵后根據地的文藝事業仍在黨施行的開明文化政策下取得了迅速的發展。根據地自由、開明的學術氛圍更吸引了無數愛國青年和文人志士懷揣著愛國熱情奔赴而來。來到延安的文藝家們在音樂、戲劇、美術等方面都產出了很多的碩果,毛澤東同志在1942 年的延安文藝工作者座談會上就曾提及根據地的文藝盛況:“我們的整個文學工作,戲劇工作,音樂工作,美術工作,都有了很大的成績。這些文藝工作者,有許多是抗戰以后開始工作的;有許多在抗戰以前就做了很多的革命工作,經歷過許多辛苦,并用他們的工作和作品影響了廣大群眾的。”[1]由此可見,當時根據地文藝人才之多、文藝事業之繁榮。
而木刻版畫也是根據地文藝創作成就最為顯著的領域,在此誕生了古元、彥涵、王琦、焦心河、羅工柳、張映雪等一大批著名木刻藝術家。這些木刻藝術家們在極其艱苦的戰時環境下,仍堅持著木刻版畫的創作,躍身成為抗日救亡文藝陣線里的主力軍,不僅在“民族化”“大眾化”的創作道路探索出了富有民族特色的木刻版畫風格,將中國的木刻版畫藝術推向了高峰,還以簡單、明快、富有戰斗力的木刻版畫作品鼓舞、喚醒了無數中國人民堅持抗戰的必勝信念。
二、 木刻版畫流派與插圖應用
抗日戰爭爆發以后,文藝家們紛紛拿起自己的文藝武器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當中,“抗日救亡”“拯救國家”“拯救民族”等愛國思想成為這一時期文藝家們創作的主題旋律。這一時期的木刻版畫家們以藝術家和革命戰士的雙重身份站上了歷史的舞臺,他們一方面以木刻刀作為藝術武器,為思想教育和抗戰宣傳發揮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他們的作品是一種珍貴而具有代表性的藝術表現形式,其表現手法獨樹一幟,生動刻畫了抗戰時期人民生活、人民形象、人民精神面貌。
(一)新興木刻版畫風格
諾貝爾文學獎女作家賽珍珠在1945 年出版的《從木刻看中國》版畫集收錄了李樺、王琦、古元、沃渣、荒煙、劉鐵華、汪刃鋒等人在抗戰時期的木刻版畫作品。他們這些作品不僅成為中國革命歷史的見證,甚至極大地鼓舞了世界反法西斯人民反抗壓迫的決心,作者賽珍珠在書中就以“木刻幫助中國人民進行戰斗”來高度形容木刻版畫在抗戰中起到的重要作用。而木刻版畫之所以能被視為一種有力的藝術武器,與其革命性、藝術性的特點是分不開的。這也是因為木刻版畫在視覺上有著強烈的感染力,能夠以明暗對比渲染出壯闊的革命場景,與抗戰時期愛國藝術家渴望宣傳抗戰、救國的訴求不謀而合,因而備受藝術家青睞,成為抗戰時期各類宣傳的常用藝術形式。
實際上,木刻版畫在中國并不是一種全新的嘗試,魯迅在《北平箋譜》的序言中曾提道:“縷象于木,印之素紙,以行遠而及眾,蓋實始于中國。法人伯希和氏從敦煌千佛洞所得佛像印本,論者謂當刊于五代之末,而宋初施以采色,其先于日爾曼初木刻者,尚幾四百年。”[2]可見,我國在古代時就已有了木刻的藝術形式,甚至對西方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但其仍是作為復制型版畫來使用。在隨后的發展中,中國的傳統木刻由于與現實生活隔絕,由于畫、刻、印的分開,缺乏獨立的創作意識,逐漸失去生命力[3]。20 世紀30 年代時,魯迅洞察到了木刻版畫蘊含的藝術潛能,便開始大力推進新興木刻版畫運動,把許多西方版畫家的作品介紹到中國,使人們看到了木刻版畫所蘊含著的新的可能性。在轟轟烈烈的新興木刻版畫運動的影響下,一八藝社、平津木刻研究會、MK 木刻研究會等木刻創作協會如雨后春筍般涌現,魯迅創立的木刻研習會更是為這一時期中國培養了一大批杰出的新興木刻家,如李樺、陳煙橋、鄭野夫、黃興波、朱宣咸等人,他們也成為推動當時中國木刻版畫發展的主力。然而,新興木刻版畫更多的是受到當時西方版畫的啟發,因而在表現手法和藝術風格上與西方木刻比較貼近,畫面比較講究明暗光影、刀痕線條、寫實效果、藝術張力,如鄭野夫在1933 年創作《賣鹽》木刻連環畫中就借鑒了麥綏萊勒的創作技法,使畫面黑白語言既簡潔又富于變化,整幅構圖考究,非常注重表現刀刻線條的藝術效果,陰陽線刻交錯,使人能深刻地感受到黑暗社會給人的壓迫。再如張明曹在1939 年創作的《仇》木刻連環畫,也是新興木刻風格的經典之作。張明曹作為新興木刻版畫運動的倡導人之一,善于利用巧妙的黑白對比、律動感的刀刻線條渲染出故事情景,從而引發讀者內心極大的波瀾,具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張明曹的《仇》一經出版便廣受讀者追捧,半年內出版多次,在當時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除此之外,胡一川在早期的木刻版畫創作中也明顯受到當時德國版畫家梅斐爾德的影響,在他1932 年創作的《到前線去》中也可以找到很多西方木刻語言的影子,這幅作品的構圖、刀法、造型上都經過了仔細的考究,巧妙地利用了黑白對比、構圖突出了造型夸張的主體人物,整個畫面既粗獷又大膽,具有強烈的現實主義色彩。
(二)延安木刻版畫風格
面對戰時環境下物資困難的局面,木刻版畫因創作工具簡單、制圖效果快等特點,成了根據地藝術家們常用的美術創作形式。延安的木刻,是在承繼三十年代魯迅先生苦心培育的新興木刻的革命傳統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4]。在中共中央進駐延安后,一些活躍在上海的新興木刻家,如馬達、劉峴、力群等也相繼來到了延安繼續進行文藝創作。這批新興木刻家之中有許多人以魯藝為活動陣地,一邊將新興木刻版畫的創作經驗傳授給青年一代,一邊又創作了許多表現根據地勞動人民面貌和抗戰題材的木刻版畫作品,如馬達的《五月》、劉峴的《鞏固、團結、抗戰到底》、力群的《飲》、江豐的《碼頭工人》、陳九的《血戰臺兒莊》、沃渣的《查路條》、夏風的《小八路》等,這些作品內容都是從根據地生活中取材,非常具有生活氣息,這些新興木刻家們對根據地的木刻版畫事業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置于爭奪話語權以及救亡的語境之下,大眾不僅成為文學所指向的目標,還成為革命依托的對象[5]。國家身處危難之際,藝術肩負著廣泛喚醒民眾抗戰激情的重要任務。然而,中國傳統繪畫審美傾向于平面。取法西歐的陰刻法,用黑白對比組織畫面、刻劃形象的新興木刻,不容易為人民群眾接受[4]。在根據地,許多老百姓卻并不理解新興木刻版畫中的素描語言,有些甚至將這些有著強烈黑白對比的木刻版畫作品稱為“陰陽臉”。由此可見,根據地的欣賞群體與創作者之間存在著審美差異,因而創作者筆下的作品難以激起欣賞群體內心更深層次的共鳴。1942 年5 月,著名的文藝工作者座談會在延安楊家嶺舉行,毛澤東同志在本次會議上正式把題材上表現工農兵、形式上做到老百姓喜聞樂見的審美趣味確定為解放區的文藝發展方向。在此號召下,延安的木刻家們紛紛將目光轉向群眾身上,開始自覺地探索“民族化”“大眾化”的創作形式。他們一邊從群眾的生活中取材,將自己的作品和群眾結合起來;一邊又對根據地群眾所喜愛的民間藝術形式進行研究和改造,期盼用群眾熟悉的視覺語言來對抗戰事業進行宣傳。因此,版畫的表現形式上,延安木刻家有選擇地保留了曾對中國新興木刻革命化有過影響的外來技法,并在適當地融合于陽刻線條造型的中國傳統木刻技法過程中,創造性地形成了具有時代特色和民族風格的木刻藝術[4]。隨后,這種帶有鮮明中國民族品格的木刻版畫風格也被廣泛地運用在根據地的各類書籍插圖和宣傳畫中。
(三)延安木刻風格在插圖中的應用
魯迅曾言:“書籍的插畫,原意是在裝飾書籍,增加讀者的興趣的,但那力量,能補助文字之所不及,所以也是一種宣傳畫。這種畫的幅數極多的時候,即能只靠圖像,悟到文字的內容,和文字一分開,也就成了獨立的連環圖畫。”[6]魯迅認為,插圖能夠補充文字內容,提升閱讀體驗,有著教育大眾的作用,而連環畫便是插圖的一種。連環畫對比單幅插圖來說,其在表現故事主題和敘事上更具感染力,能以多幅連續圖畫來敘述完整的故事情節,因而深受民眾喜愛,連環畫也被延安藝術家看作是對大眾展開文藝宣傳的有力形式。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后,這種具有民族化特點的木刻風格也被延安木刻家們帶入連環畫創作中,使木刻連環畫在群眾中取得了特別廣泛的傳播。如羅工柳和張映雪以趙樹理的小說《李有才板話》《小二黑結婚》為藍本繪制的木刻連環畫,他們從“文藝大眾化”的角度出發,在技法表現上兼顧了群眾的審美習慣,使畫面語言變得更為通俗易懂。在羅工柳繪制的《李有才板話》二十幅木刻連環畫中,羅工柳為避免人物形象刻畫“陰陽臉”的問題,不再大面積地使用明暗對比,而換以民眾習慣的傳統木刻線條來刻畫,整個畫面趨于平面化,顯得更為明快、潔凈。而張映雪為《小二黑結婚》繪制的木刻連環畫雖使用了西方木刻版畫的透視技法和明暗關系的表現刻法,但是也為了照顧群眾的審美習慣,避免在人物臉部使用明暗刀法,因而畫面既有素描的層次感和立體感,又符合民眾的審美心理。彥涵創作的《狼牙山五壯士》木刻連環畫則有著濃郁的中國氣派,其木刻語言堪稱經典,畫面構圖巧妙,人物形象生動,即使在用色單調的黑白木刻中,彥涵仍能把中國畫的意境深融其中,營造出恢宏的畫面感。力群在為《王貴和李香香》《小姑賢·劉保堂》繪制的木刻插圖中,也不再追求寫實效果、繁復的背景,變得極為樸素,換以簡練的線條來塑造人物,整個畫面極具裝飾性。而莫樸、呂蒙、程亞君三人創作的《鐵佛寺》則是在根據地艱苦環境下少見的大型連環畫作品。《鐵佛寺》的木刻連環畫雖由三人分工合作,但整體風格非常統一,他們在《鐵佛寺》的創作上借鑒了民間年畫、剪紙的形式,改變了以往木刻版畫偏重于以黑白塑造人物和背景體積的表現方式,變得更為質樸明快、通俗易懂,有著濃郁的生活氣息。
除此之外,婁霜的《戎冠秀》、彥涵的《民兵的故事》、馬達的《陶端予木刻集》、沃渣的《黑土子的故事》、安明陽的《女英雄劉胡蘭》、古元的《新舊光景》、呂琳的《紀利子》等也是當時根據地廣受歡迎的木刻連環畫作品,這些連環畫大多數都從真實事件和農民日常生活中取材,并且為了貼近根據地群眾的審美習慣,減少了黑色在畫面的占比,多以陽刻線條來塑造人物,變得更為簡潔、洗練,以便于讓作品更加容易被群眾理解和接受,為弘揚抗戰和新文化思想做出了卓越的貢獻,真正讓藝術作品起到了從“大眾化”到“化大眾”的作用,極具教育意義。
三、 結語
歷史已經翻開了新的篇章,但延安木刻版畫對于研究中國插畫藝術發展方向和中國抗戰文化仍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2014 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曾指出我國在文藝創作方面,也存在有數量缺質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現象,存在抄襲模仿、千篇一律的問題,存在機械化生產、快餐式消費的問題[7],并強調“文藝不能在市場經濟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為什么人的問題上發生偏差,否則文藝就沒有生命力”[7],號召新時代文藝創作者仍要“扎根人民”“扎根人民生活”“扎根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可見,“大眾化”“民族化”仍是新時代文藝創作者所急需探索的重要命題。然而,隨著時代的發展,當代的文藝創作者浸潤在多元化的社會環境之中,而商業文化和外來文化對插畫創作者的影響頗深,一些插畫創作者對于“民族化”“大眾化”的追求似乎已經有所遺忘,因而使自己深陷“泛西方化”“同質化”“商業化”等創作困境。而在抗戰時期,延安木刻家通過踐行“民族化”“大眾化”的思想,使他們的作品受到廣大群眾的捧讀和熱愛,正說明了“民族化”“大眾化”思想對于我國文藝事業發展所起到的有效作用。因此,不管時代語境如何變化,堅持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人民的生活中找到設計靈感,仍是新時代插畫創作者打破自身創作困境的最好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