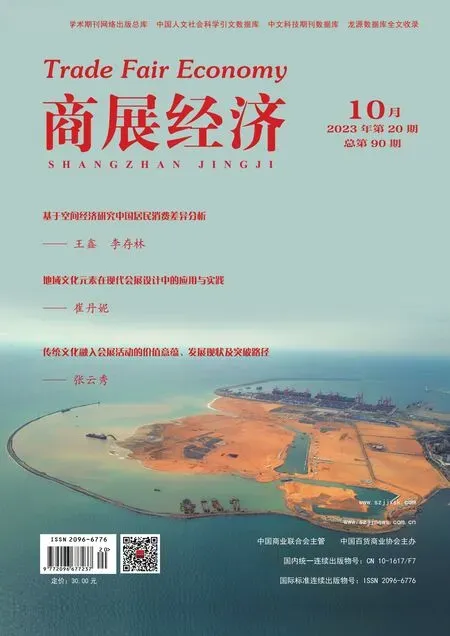關于風險投資、政府補貼與高新技術產業技術創新績效的文獻綜述
劉暢
(桂林旅游學院商學院 廣西桂林 541006)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把創新作為引領經濟發展的第一動力,全面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科技事業發生歷史性、整體性、格局性的重大變化,已成功邁入創新型國家行列。高新技術產業作為國民經濟的先導性、戰略性產業,是衡量一國經濟發展質量是否提高的關鍵產業。
我國的技術創新的確已經比之前有了很大進步,但對一些關鍵領域的核心技術并未掌握,創新基礎相對美國仍有差距,創新能力還達不到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要求。高新技術產業需要大量依靠技術創新,而開展技術創新活動需要大量的資金,同時投資的周期較長,投資的結果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因此高新技術企業常常被傳統金融機構拒之門外,高新技術產業長期面臨創新融資困難、創新投入不足的問題。為此,政府投入了大量資金來補貼高新技術產業的技術創新,以解決創新資金投入不足的問題。同時,風險投資在我國已經發展了30多年,也成為高新技術產業技術創新的重要融資方式。本文通過梳理文獻,探索國內外學者對風險投資和政府補貼對高新技術產業技術創新績效的研究成果。
1 高新技術產業技術創新績效研究
雖然我國的高新技術產業發展規模越來越大,但是存在著缺少核心技術、研發投入低、產品附加值低、盈利能力差等問題。高新技術產業技術創新能力的提高是解決上述問題的關鍵,進而推動我國的經濟發展,提高我國的綜合競爭實力。
在對高新技術產業技術創新績效的研究中,產業創新績效的影響因素一直是研究重點。從企業組織內部來看,影響因素集中于企業規模、所有制、股權結構、公司治理等方面。陳程和劉和東(2012)認為,產權機構和企業規模對高新技術產業技術創新研發效率均有顯著影響;樓旭明和徐聰聰(2020)探討了在智能制造領域,企業規模對技術創新績效具有正向影響,但影響較小;Pavitt和Townsend(1987)則認為,并不是企業規模越大,創新績效就越高,中小企業由于內部結構不復雜,經營方式更加靈活,反而創新績效更高;錢麗等(2019)認為,不同所有制的企業創新能力不同,非內資企業創新績效最高,內資企業創新績效偏低;姚立杰和周穎(2018)提出,企業管理層的能力決定著企業創新水平的高低,高管能力越強,企業創新績效水平越高,企業可通過給管理者股權激勵以提高創新績效,通過股權綁定,管理者將主動做好創新管理及創新戰略安排;朱德勝和周曉珮(2016)通過實證指出,股東持股比例和高管持股比例對企業創新績效均起著正向促進作用,且隨著比例的增大,兩者有替代作用;許曉娜肖宇佳(2023)實證結果,表明董事會正式層級對開放式創新績效和封閉式創新績效均有負面作用,董事會非正式層級對兩者均有正向作用。
影響產業創新績效的外部環境因素主要是政府支持、市場競爭程度、金融市場發展水平、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等。解維敏等(2009)指出,政府補助通過企業R&D支出的中介作用正向影響企業創新研發績效,地區的市場化程度越高,將顯著激勵企業家的創新精神,進而推動地區的創新水平提升,同時上市公司R&D投入受當地銀行業市場化改革和地區金融發展水平的積極影響,而政府干預則會削弱這種積極影響。Fang等(2017)研究發現,一國的知識產權保護得越好,知識產權法律越完善,企業創新的意愿就越強烈,因為能減少其他企業模仿和抄襲,以維持其在市場中的領先地位,同時企業產學研協同越強,企業創新績效水平就越高。
2 風險投資與高新技術產業技術創新的研究
國內外實踐證明,風險投資與高新技術產業的成長和繁榮有著密切聯系,風險投資與高新技術對接后,為高新技術產業帶來了豐富的資金及資源支持,提高高新技術研發效率,促進科研成果市場化。Lerner(2000)以美國20個行業的經驗研究認為,一個行業風險投資參與度的增加能夠顯著提高該行業的專利發明率,進而促進技術創新。硅谷的高新技術企業能在創新領域保持著領先,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當地眾多風險投資給予的資金及資源支持,并且能得到后續更多輪的融資;丁健(2022)認為,風險投資對我國科技創新企業的高質量創新有促進作用,但是對常規創新無影響,風投之所以愿意承受市場及技術風險來投資高新技術產業,是為了獲得巨大的潛在超額利潤;李先江(2008)從信息不對稱的角度分析,認為風險資本比傳統投資機構更能處理高新技術初創企業的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問題,能夠更加吻合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要求;肖珉等(2022)認為,公司風險投資比傳統風險投資有更高的失敗容忍度,同時承載著母公司創新學習戰略意圖,從而更能促進企業的創新。
另一部分學者持有不同的觀點,Caselli等(2009)選取了意大利的74家上市公司,實證表明在風險投資進入企業后,企業會將注意力從創新轉移到其他經營管理指標上,并不能促進企業的技術創新;Atanasov等(2006)利用390個有VC支持的IPO企業的數據,發現風險投資存在攫取創新企業創新思想的情況;夏清華與樂毅(2021)表示,企業的創新投入和產出均與企業有無風險投資背景沒有顯著關系,當存在不同外部調節變量時,也不影響此結論;徐明(2022)認為,政府風險投資與風險投資機構兩者的投資目標難以協調,且更喜歡投資風險較小的企業,對企業創新的負面影響更大;溫軍與馮根福(2018)提出,風險投資的攫取效應大于其增值效應,降低了中小企業的創新水平。
3 政府補貼與技術創新的研究
國內外關于政府支持與創新研發績效關系的討論非常多,目前尚未達成共識,主要的兩類觀點如下:
第一類觀點認為政府支持會提高創新研發績效。Lerner(1999)表示,創新補助可以支持企業尤其是高科技行業的研發創新,能夠獲得政府補助就是企業研發技術能力得到認證的表現,同時能吸引到其他外部投資者;Duguet(2004)通過考察法國年度研發調查的數據,論證了創新補貼會增加法國創新活動私人資金的投入;楊浩昌、李廉水(2019)認為,政府支持有利于促進高新技術產業研發績效的提高,并且這種促進作用主要通過提高技術績效來實現;陸國慶等(2014)論證了政府對戰略性新興產生創新補貼的績效是顯著的,創新的外溢效應也是顯著的;葉祥松、劉敬(2018)證明了政府支持科學研究在長期內對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存在促進作用;莊旭東、段軍山(2021)研究表明,政府支持對產業創新成果轉化具有促進作用,且其影響具有一定的持續性。
第二類觀點則認為政府支持能削弱創新研發績效。Mamuneas 和 Nadiri(1996)表示,雖然政府的創新資助能幫助企業節省成本,但對私人創新投資有一定的擠出作用;黎文靖和鄭曼妮(2016)運用上市公司的專利數據探討產業政策如何影響企業創新行為,發現企業會為了得到政府補助只選擇增加創新的“數量”,而不是提高創新的“質量”,企業的這種應對式尋求政府扶持的方式表明了創新補助的反作用;魏志華等(2015)實證研究發現,政府補助是一把雙刃劍,雖然會緩解企業的融資約束,但容易導致企業過度投資;呂久琴和郁丹丹(2011)通過實證驗證了政府補助對企業研發投入的“擠出”效應,樣本中接近50%的企業研發被政府補助完全或部分擠出。
4 風險投資、政府補貼與技術創新的研究
國內外學者同時研究三者之間關系的文獻較少,大多從企業微觀層面,比如謝光華等(2018)以2009—2015年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實證研究了風險投資如何影響企業配置、政府補貼開展創新活動,發現政府補貼與風險投資對企業創新具有互補效應,憑借其專業的知識技能和管理經驗,風險投資能夠幫助企業有效配置政府補貼資源,增加發明和實用新型專利;楊昀等(2019)以2011—2016年創業板高新技術企業為研究對象,實證研究了風險投資機構對被投資企業利用政府補貼進行研發創新有明顯的監督作用;王慶東、孫雅茹(2021)也以創業板高新技術上市企業為研究對象,認為財政補貼對創新產出質量產生顯著抑制作用,而風險投資行業專長顯著提高高新技術企業創新產出質量,且風險投資行業專長顯著削弱財政補貼對創新產出質量的抑制作用;趙寶芳、陳曉丹(2022)以A股上市企業為樣本,發現企業技術創新水平與風險投資規模及政府創新補貼均呈正相關關系。對于企業技術創新水平的作用,風險投資與政府創新補貼相互促進。
還有學者從單一行業論證了三者之間的關系。周方召等(2013)以中國滬深兩市物聯網行業上市公司為樣本,認為政府直接補貼和稅收優惠及風險投資的參與對物聯網上市公司生產績效均無顯著的積極影響;王昶等(2020)利用2008—2017年中國新材料企業面板數據,探討了風險投資和政府補貼通過提高企業研發投入進而促進新材料企業的技術創新。其中,風險投資的激勵效應更加明顯,但具有短期性,政府補貼的激勵效應則具有滯后性。
5 結語
綜上所述,國內外學者對高新技術產業創新影響因素、風險投資與高新技術產業創新能力、政府補貼與高新技術產業創新能力之間的關系研究取得了長足發展,但目前對作為市場機制的風險投資與作為行政手段的政府創新補貼同時介入是否會產生交互效用的研究尚少。未來,可以研究對不同所有制、不同制度環境或不同企業家特征的高新技術企業影響的差異性,探索更多風險投資及政府補貼對高新技術產業創新績效的作用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