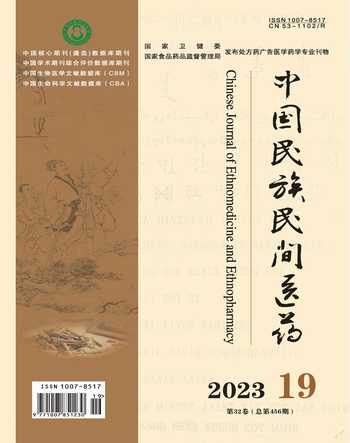“醫戲同源”視域下中醫與戲曲中傳統文化思維的關聯性探討
胡煒圣 邱浪
【摘要】中國傳統文化源遠流長,積厚流光。戲曲與中醫都孕育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土壤,積淀了豐富的傳統文化內涵,故在思維方式上必然存在聯系。醫為仁術,中醫不僅是養生保健治病,更蘊藏傳統文化之道德成分,戲曲不僅是唱念做打,同樣也蘊藏傳統之社會教化準繩。研究中醫與戲曲關聯性,利于理解中華傳統的思維方式內涵,在保護與傳承方面相互借鑒,進而促進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層次傳承與發展。
【關鍵詞】戲曲;中醫;關聯性;傳統文化思維
【中圖分類號】R-05【文獻標志碼】 A【文章編號】1007-8517(2023)19-0001-03
DOI:10.3969/j.issn.1007-8517.2023.19.zgmzmjyyzz202319001
Research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Traditional Cultural
Thinking in Oper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dical Drama Homology”HU Weisheng1QIU Lang2
1. The Second Peoples Hospital Affiliated to Fuji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Fuzhou 350001, China;
2. Xinglin College, Liaoni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enyang 110016, ChinaAbstract: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has a long history and a long history. Both opera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re born in the soil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have accumulated rich traditional cultural connotation, so there must be a connection in the way of thinking. Medicine for benevolence, Chinese medicine is not only health care treatment, but also contains the moral components of traditional culture, opera is not only “singing skills, lines, body, kung fu”, but also contains the traditional social education criterion. The study of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opera is conducive to understanding the connot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way of thinking, and learning from each other in terms of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so as to promote the deep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Keywords:Opera;Chinese Medicine;Relevance;Traditional Cultural Thinking
中國傳統文化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顯露出中華民族之民族風貌與民族特質,蘊釀了中華民族歷史發展中諸多文化思想、形態觀念之總體表征[1]。自秦漢以來,中國傳統文化漸趨融合與發展,構建起自然科學和人文哲學結合之“天人宇宙觀”的理論體系[2]。中華文明在融合與建構的過程中,積淀了中國文化獨有的生存土壤,中醫不僅講求攝生與治未病,更包含了中國傳統的哲學觀念和道德準則。戲曲積累了中華民族長久以來的審美理念與文化習俗,傳遞出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觀念和精神內涵。研究中醫與戲曲的關聯性,加深對彼此探索,對傳承保護中醫和戲曲具有重要意義。文章從戲曲與中醫相似性的淵源出發,研究了戲曲與中醫在對稱性、象思維、程式化等方面相似的思維方式。
1戲曲與中醫相似性的淵源
就中醫與傳統戲曲藝術的關系而言,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講“醫戲同源”。戲曲與中醫能有相似性,來源于戲曲與中醫的同宗同源,巫是二者的來源之一。巫術中祭祀歌舞的部分演化為了戲曲,藥石針灸的部分演化為了中醫。所以二者即使在今日已經完全分離,但在傳統文化的思維方式上,依然可以尋找到關聯性。
1.1戲曲源于巫戲曲“當自巫、優二者出”,為王國維在其所著《宋元戲曲考》中展現的觀點。王國維又依照楚辭漢賦中對巫風盛行的描寫,推斷“群巫之中,必有象神之衣服形貌動作者,而視為神之所憑依”。此記載表明,巫是以歌舞來娛樂鬼神之職業,當時巫所從事之祭祀活動,已然有了戲曲之中人物扮演的成分,即為“后世戲劇之萌芽”[3]。巫所從事的以歌舞來娛樂鬼神的祭祀活動主要有臘祭與儺禮。《周禮》中有涉及方相氏掌管儺禮之記錄:“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師百隸而司儺,以索室逐疫。”方相氏通過儺禮來斥逐疫癘的這一記載,同樣也證實了在儺禮中已經具備戲劇扮演的靈魂。方相氏“黃金四目”,大多數學者揣測為戴面具而致,巫的面具為戲曲臉譜的來源提供了沿革依據,而戴面具所領擁的戲劇性已經被后代人們所公認。
1.2中醫源于巫除了歌舞祭祀敬拜鬼神,巫同時領受了為醫的使命。以此也說巫為祖國醫學起源發生發展的源頭之一[4]。朱子疏解《論語·子路》時言“擊鼓舞趨祈禳疾病曰巫醫”。此時的“巫醫”,不僅掌管祭祀鬼神之職權,更具備了一定診療疾病之能力,具有通神靈與治療疾病的雙重特征。巫者作醫,掌握醫藥知識、從事醫療活動。巫醫同源的推定,還可以文字嬗遞角度考察其中關系。《廣雅·釋話》言:“靈子,醫、覡、巫也。”可見那時的巫與醫都屬靈子一類,醫即為巫。醫巫同源另一依據為“巫”和“工”互訓。許慎釋解“工”字言“工與巫同意”,釋解“巫”字言“巫與工同意”。可見“工”在古代既可為醫,又可為巫,巫醫同源可從中窺測一斑。
2戲曲與中醫的相似性
傳統文化的內涵深邃高遠,匯聚了中國傳統人民歷代以來及不斷積累的生活智慧與價值觀念。戲曲與中醫作為傳統文化的兩大載體,在對稱性、象思維、程式化等方面具有相似性的傳統文化思維方式。
2.1對稱性對稱思維方式,來源于中國傳統的陰陽學說,它是中華本土古典文化的典型思維方式。對稱的事物蘊含著陰陽平衡之美。中國古典哲學的最基本元素陰和陽是對稱的,故而受其影響得戲曲與中醫也可以明顯地看到對稱性。
中醫學的理論建立在中國古典哲學的基礎上,《黃帝內經》把中國古典哲學之中的陰陽學說運用入醫學范疇,使陰陽學說演化為中醫學的基本理論。作為中醫學得以確立的基礎理論之一,陰陽的概念具有明顯的對稱性。《素問·金匱真言論》言:“夫言人之陰陽,則外為陽,內為陰;言人身之陰陽,則背為陽,腹為陰。”這體現了中醫學通常從陰陽這一對稱概念的變化來認識人體內在臟腑聯系的各個方面。同時“陽主升,陰主降;陽主出,陰主入”,人體的生命活動也是由陰陽的升降出入,運動變化而實現的。氣的升降出入,也體現出了陰陽的對立統一。
戲曲亦在舞臺表現上謀求對稱美感,這種思維方式亦來源于陰陽學說的影響。無論是站姿,身段,唱腔,還是在舞臺設計上,都具有對稱性的特色。戲曲站姿講求“子午相”。與其他舞臺劇的正對鏡頭不同,戲曲的子午相為上半身保持正面觀眾,下半身斜向舞臺一方,因下半部分身體始終偏向“子午位”,而被成為“子午相”。一半正對觀眾,一半朝子午方向,有了對抗,形成陰陽;但在對稱同時保持人物動作協調統一,組成整身,就有了陰陽平衡。這是戲曲站姿中陰陽的對稱性。在戲曲身段的對稱性上,京劇《霸王別姬》中,虞姬“勸君王飲酒聽虞歌”的舞劍片段,多次出現繁復的對稱性動作,這種對稱性賦予了虞姬婀娜多姿的體態,讓舞劍更為婉轉纏綿,表現出對霸王的款款深情。除內容外,戲臺的設計也具有對稱性。傳統的戲曲舞臺,必有左右兩扇門,一進一出,是戲曲舞臺上的上場門與下場門,定名上亦是對稱,稱作“將出”與“相入”,借用“將”“相”,有盼成大器之意。
2.2象思維象思維是以直觀、感性之圖像符號等象工具來透露內在規律,采取類比、象征等手段把握聯系,將宇宙自然的規律看作合一的、相應的、類似的、互動的,依托太極八卦、天干地支、河圖洛書等象數符號與圖式構建萬事萬物的宇宙模型,具有顯豁的整體性、全息性[5]。象思維也顯著表現在中醫和戲曲之中。
五行與五臟配屬的規律是《黃帝內經》最具典型意義的象數模型[6]。藏象學說為中醫理論的核心思想,《黃帝內經》依靠中國傳統取象比類思維方法,認識到人體各個臟腑具備以五臟為核心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的關系。同時“圣人治病,必知天地陰陽,四時經紀”,中醫的藏象學說受五行觀念的影響,利用五臟之象與萬物之象相應的觀點,把五臟與四時五行相配,利用五行間生克制化規律來闡述五臟之間的聯系。《靈樞·九宮八風》亦用取象思維之法,以后天八卦定方位,闡發太一游宮規律與太一游宮所致正常、異常的氣候變化,以及八風侵襲人體的不同特點,說明人順應自然之道、與自然和諧統一的重要性[7]。
戲曲里的象思維可以稱之為“虛擬性”。虛擬性是戲曲的重要特色之一。常言“會看戲的看門道,不會看戲的看熱鬧”,此中門道多指對程式動作等抽象化表現形式之意會,是一個象思維的認知過程[8]。戲曲具有的虛擬性,是采取虛無或是用一桌二椅等簡單道具,逼真地表現日常生活的現實情景,依靠類比、象征等手段及演員豐富的生活經驗,凝練實際生活中的意韻,倚托唱戲人的空間顯示力和時間表現力,把觀眾的想象力從舞臺擴展到更為廣袤的時空,在一桌二椅的舞臺上,以人物的取象,生動的表現出“天地日月夜,風云雷電雪”。京劇《白蛇傳》中,僅用唯一一只船槳,通過演員極具表現力的跳板、上舟、隨波搖晃的身段,就表現出許仙和白素貞小青游船借傘,西湖泛舟的場面。
2.3程式化戲曲程式化也是戲曲的一大特色,是用固定的動作標志一定的涵義。戲曲舞臺上的人物動作不是生活中動作之直接摹仿,是在生活動作胚質上歷經粉飾美化與想象施展藝術再塑造,使之演繹成一種規范化之形式。像上轎、坐船、飲酒等,都有一套“口眼手身法”固定程式。程式在戲曲中既有規范性又有靈活性,所以戲曲藝術被恰當地稱為有規則的自由動作[9]。如鷂子翻身,武戲中經常用的串翻身,表現武打的場面為程式化。如史依弘京劇《情殤鐘樓》,越劇《穆桂英掛帥》,婺劇《三請梨花》,蒲劇《白蛇傳》中,武打部分都用鷂子翻身,就是程式化。
中醫在實施辨證論治,“一人一方”同時,也具程式化思維方式。中醫的程式化,是以中醫辨證論治思維與臨床經驗為出發點,圍繞辨證與論治兩個相互關聯的環節構建理、法、方、藥,從而闡明對生命認識的價值觀、診療疾病的方法論與具體遣方用藥之心得的思維過程[10]。中醫學辨證論治的思維方式的淵源為《黃帝內經》,在《傷寒雜病論》中明確并奠定基礎。《傷寒論》中提出了面對疾病“觀其脈證,知犯何逆,隨證治之”的診療之法。“觀其脈證”為辨證之著眼點,“知犯何逆”是立足病機之思維方式,“隨證治之”是面對疾病診療的程式化過程。
2.4貴和尚中貴和尚中是傳統文化的典型思維方式,意在以和為貴,崇尚中庸。中和劈頭于太極陰陽,映現了天人合一時域下和思維的多元互通。 《論語》言“禮之用,和為貴”,強調了“和”是禮儀之邦的生命之魂。傳統文化重申貴和尚中,當中孕育的戲曲與中醫自然也受其陶染。
中國傳統戲曲重視意境美,講求塑造“得其環中以隨成”的圓滿融暢之境,闡揚百姓心中對團圓美滿的精神追求。戲曲珍視“大團圓”之趣,珍攝“如樂之和,無所不諧”的中和之美,映現了中華民族貴和尚中的審美理想境界。如《鎖麟囊》《花為媒》《紅鬃烈馬》等戲曲,都是以大團圓作為結局,戲曲人物的服飾、唱詞、身法等與劇情互施互化,臻至多元和諧,反應了貴和尚中的經典傳統思維方式。
中醫之診病原理與攝生精神同樣存身于貴和尚中。《黃帝內經》傳承與發展了陰陽學說,把“和”的理論運用入醫學范疇,闡發了中醫學天人相失、陰陽失和等的病機理論。《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中對陰陽的描述“陰平陽秘,精神乃治”,表明維系人體氣血陰陽運化勻和,不但能夠保持“平人氣象”,同時也是中醫養生保健和治未病之指導思想。此俱為貴和尚中之典型映像。
3結語
對稱性、象思維、程式化、貴和尚中等作為中醫與戲曲共有的中國傳統文化思維方式,包羅中國人代代積淀的道德追求和精神向往。了解傳統戲曲,探尋中醫與戲曲關聯性,加深對彼此探索,有利于理解中華傳統的文化基因,進而加深對中華傳統的內在思維方式的領悟,進而促進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層次傳承與發展。與此同時,中醫和戲曲如今都面臨著傳承與發展的困境,中醫與戲曲的跨學科研究可使二者在保護和傳承方面相互借鑒,為探尋傳統文化的多樣性傳承方式提供新思路。參考文獻
[1]陳樂平. 儒道醫,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構架──對中醫學在中國傳統文化建構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哲學思考[J].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術季刊,1996,8(3):116-124.
[2]畢思玲,張宇忠. 論象思維在中醫學中的應用[J]. 北京中醫藥大學學報,2016,39(4):277-280.
[3]牟德海,朱立鳴,陸建武,等. 中國傳統文化與中醫學[J]. 亞太傳統醫藥,2016,12(21):8-9.
[4]葛英. 中國戲劇起源于巫覡[J]. 戲劇之家,2002,35(5):17.
[5]沈晉賢. 醫巫同源研究[J]. 南京中醫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12(4):197-201.
[6]王禹. 從思維到漢字象思維的審美特征研究[J]. 藝術科技,2019,32(3):98.
[7]蘇穎. 《周易》“象”思維模式對《內經》理論體系構建的影響[J]. 世界中西醫結合雜志,2008,11(2):67-68,82.
[8]趙鵬飛. 從象思維視角看戲曲與中醫[N]. 中國中醫藥報,2013-12-05(8).
[9]肖婉婷. 試析小旦在粵劇中的表演程式[J]. 南國紅豆,2015,3(2):30-31.
[10]孫光榮. 論中醫臨床的思維模式──中醫辨治六步程式解析[J]. 中醫藥通報,2017,16(4):1-5.
(收稿日期:2023-01-20編輯:劉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