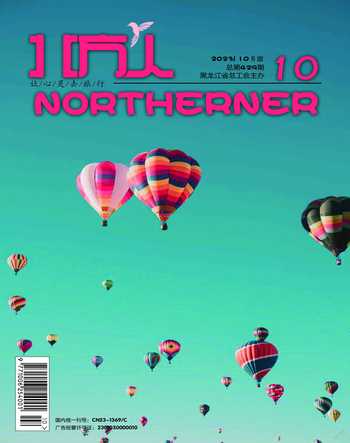感謝饑餓
覃瑞強
如果用兩個字概括我在都安高中的生活,恐怕只有“饑餓”是最準確的,即便是在食物已經非常豐富甚至過剩的今天。因為整個高中階段,饑餓感一直如影隨形地跟著我,是那樣的強烈、那樣的刻骨銘心,以至于如今已經過去四十多年,饑餓的畫面仍不時縈繞在我夢中,讓我半夜被驚醒。
其實饑餓感并非上了高中以后才有。我出生于1963年,那時剛經歷三年困難時期不久,食物極其匱乏。因此自打記事時起,除了逢年過節,餓肚子是司空見慣的事。小學三年級前,我幾乎沒吃過早餐,甚至壓根不知道早餐為何物。好在學校就在村里,上課的時間也不長,每天上午就兩節課,十點鐘就能放早學。這時候,肚子也已餓到極限了。回到家,參加生產隊勞動的大人們剛好收工回來,各自在家準備一天的第一餐飯。由于每年分到的糧食很有限,大人們對這一餐往往都極為節省,一鍋稀飯(多數時候是玉米糊),加上一海碗只有幾星豬油的青菜湯便完事。幾碗稀飯下去,肚子暫時是飽了,但也僅僅飽得了一時,幾泡尿撒完,饑餓感又會陣陣襲來,我們便盼著放晚學。雖說是晚學,其實也才三四點鐘。放完學,還有重要的任務等著我們——放牛或打豬草。因此,即便很困難,大人們也盡量在鍋里留點兒吃的給我們——一碗稀飯或一兩小塊煎餅。菜是肯定沒有了,我常常就拌點兒鹽吃,偶爾能拌上醬油、豆瓣醬之類的,就算人間美味了!煎餅多數是玉米餅,因為少油,常常被煎煳,又干又硬。即便這樣,青黃不接的時候,玉米餅也不常有,而以木薯餅代替。木薯餅氣味較重,難以下咽,往往要放點兒糖才行。那年頭,白糖是稀罕物,不是一般人家能經常買得起的,大人們就用糖精來代替。糖精是一種化合物,甜度是白糖的幾百倍,只需小小的幾粒就能使一張木薯餅變得很甜。有時把握不好,放多了,就會由甜變苦,吃幾口便覺得口干舌燥甚至失去味覺。但為了填飽肚子,哪里還顧得了那么多?
童年階段的饑餓雖說是一種常態,但畢竟都是在家,餓的時候還多少能找到一些食物充饑,因此并沒有餓到終生難忘的程度。而到了離家七十多公里的縣城上高中以后,我常常被餓到眼花腿顫。高一的時候還好一點兒,那時父親剛被確認為游擊隊隊員不久,每月能從公社領到十五塊錢的生活補助。別小看這十五塊錢,對只靠掙生產隊勞動工分維持生計的家庭來說,十五塊錢可以辦很多事,我還能像其他同學一樣,一日三餐都在學校食堂吃。除了早餐基本吃稀飯,中、晚餐統一吃用飯托蒸出來的飯。蒸飯多數是玉米粉加水后蒸制而成,常常硬邦邦的,能把狗砸死,但畢竟可以填飽肚子。高二上學期,一場變故改變了這一切。父親因病去世,使得原本就窮困不堪的家不僅失去了主心骨,還失去了十分寶貴的生活補助,陷入了更加困頓的境地。為了最大限度地節約開支,我停掉了中餐,改為每天早上訂兩份稀飯,先吃一份當早餐,然后再打一份留待中午做中餐。因為早餐是五分錢,中餐是一毛五,這樣每天能省下一毛錢。當時正值青春期,學習又緊張,身體的消耗很大,一份稀飯支撐不到下午就消化殆盡了。要是下午沒有體育課,忍忍還能扛下來,要是有體育課就難以堅持了。有次體育課,老師安排在操場跑步,我剛跑一圈就感到天旋地轉,臉色鐵青,差點兒摔倒。老師問我什么情況,我只得謊稱感冒了。
進入高三,在外地工作的哥哥加大了對我的支持,每月多給我寄幾塊錢的生活費,我才逐漸從這一窘境中走出來,但畢竟學校食堂的菜油水少、分量不足,饑餓感仍揮之不去。每到周末,我都想方設法到校外改善生活,有時到同族叔叔家,有時到遠房表姐夫家,有時到同學家,就為蹭吃一餐肉食。更多的時候,則是一個人走到兩三公里外的飲食店,買上一兩個菜心包子,狼吞虎咽地吃完,再趕回學校。
那時除了肚子的饑餓,還有一種饑餓,就是對知識的饑渴。我們這一屆是“文革”后首屆通過中考考上都安高中的,算得上全縣同屆的尖子生了。但也僅僅是矮子里面拔高個兒而已,成色顯然不足。因為小學、初中階段,我們基本都是半工半讀,學習的時間本就不多,加上鄉村學校師資力量薄弱,根本學不到多少知識,基礎差是普遍現象。特別是英語,上了高一才從二十六個字母開始學起,學得非常吃力。于是很多同學都偷偷自習,惡補功課。晚自習后,學校只留給我們四十多分鐘的洗漱時間,十點半準時熄燈。有些同學便點起自備的煤油燈熬夜學習。有時,被夜巡的老師同學發現,不得不滅燈佯裝睡覺,猜測夜巡者已走遠,又重新點起。而夜巡者每晚都要巡查幾遍,熬夜補習的同學難免被三番五次地警告批評,直到半夜兩三點鐘才睡。
學校、老師當然了解同學們底子的薄弱和對知識的渴望,因此千方百計幫助我們。除了教材,還到處收集課外資料和練習題給我們。那時沒有電腦打印機,收集來的課外資料和練習題基本由大家都叫他“藍工”的干事負責刻蠟紙和油印。他是個身材矮小的中年男人,性格溫和,一件已洗得發白的藍色中山裝和鴨舌帽好像一年四季都沒怎么換過。盡管工作繁雜,待遇不高,還常要加班加點,他卻從無怨言。我無法知道同學們從他親自刻板油印的資料當中收獲多少,但我相信很多同學都從他身上看到了一種精神。
臨近預考(當時高考分預考和正式考試,只有預考過了才能參加正式考試),我感到時間越來越不夠用,又不想像有些同學那樣偷點煤油燈或偷跑到隱蔽角落的路燈下熬夜學習。于是每天吃完晚飯到上晚自習前這段時間,我都邀上一兩個成績比較好的同學到校外的田埂散步。說是散步,實際上是帶著需要記憶的語文、英語、歷史、地理、政治的課本或資料,然后互相問答。一段時間過后,我發現這真是一個好方法,既能增加學習時間,又能活動腿腳,還能欣賞美麗的晚霞,可謂一舉多得。
1981年7月,歷經三年的苦學,我順利參加完高考,并以360多分的成績上了一本線。本以為可以就此跳出農門告別饑餓,不想卻栽了個大大的跟斗。那時高考是先估分再填報志愿,因此,極易因估分不準而出現實際分數與填報志愿差距較大的情況。雖然我的估分和實際分數相差不算太大,也達到了第一志愿的調檔線,但終因沒被錄取又未及時退檔而錯過了第二志愿,鎩羽而歸。這對我是個巨大的打擊,幾乎把我擊垮!我頹唐消沉了兩個月,之后與鄉親們一起挑土、抬石頭,干苦力活,一陣接著一陣的饑餓感終于喚起了我心底的不甘,我不能就這樣自暴自棄,我要振作起來,明年再考!
就這樣,在同族叔叔的幫助下,學校讓我在1982年春節過后回到都高插班補習。此時,距離預考只有不到三個月的時間,我必須加倍努力才能把損失的時間奪回來。當時的班主任和科任老師都盡力幫助我跟上班級復習的進度,讓我很快找回了自信。功夫不負有心人,我終于考出了出色的成績,考上了理想的大學。
對我來說,饑餓是一場經歷,也是一場苦難。它使我受到折磨,受到煎熬。然而,它何嘗不是一場歷練、一筆財富?它使我知道自己所缺、自己所需,它讓我變得隱忍、堅強,并明確目標,勇毅前行。因此,即便痛恨饑餓,我還是要說——感謝饑餓。
(摘自2023年第6期《海外文摘·文學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