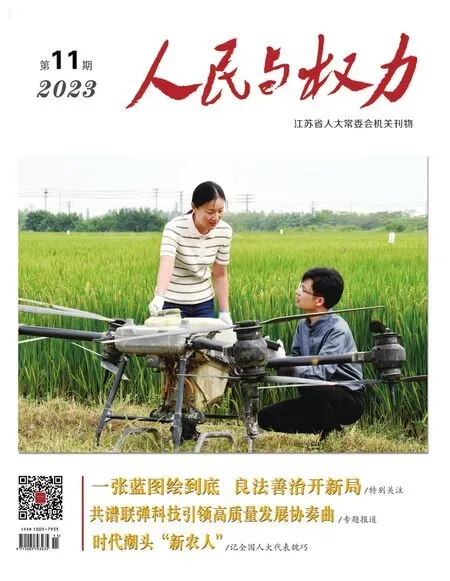江南,美食如汛
☉葉正亭

江南,魚米之鄉,物產豐富,美食如汛!
我很喜歡“汛”這個字。五十年前,江蘇作家艾煊寫過一個名篇,又結集出過一本集子,就叫《碧螺春汛》。用“汛”字好啊,點出了江南水鄉美食特征,如水、如汛,美食猶如太湖水、長江浪,一波一波推著斗轉星移。
江南美食是有季節信號的。早春時節,江南上空升起兩顆信號彈,一紅一綠,紅的是醬汁肉,綠的便是青團子。江南美食的春季篇章就此拉開序幕了!
江南人一年吃好四塊肉。春吃醬汁肉,夏食荷葉粉蒸肉,秋季品扣肉,冬天嘗醬肉。
江南人一年吃好四個糯米團。春天的青團子,夏天的炒肉團,秋天的南瓜團,冬天當然是粢毛團。
江南人一年吃好四塊糕。春吃撐腰糕,二月初二“龍抬頭”,江南女人要吃塊撐腰糕;夏食神仙糕,四月十四“軋神仙”,江南人爭食神仙糕;秋高氣爽,九九重陽登高日,江南人吃塊重陽糕;冬日盼春節,江南人最是思念糖年糕。
江南人一年吃好四碗面。春天吃素面,常以常熟的蕈油、東山的紅油香椿做澆頭。熱天吃楓鎮大面,白湯、香蔥,清清爽爽。秋天吃碗陽春面,燜肉、爆魚雙澆頭。冬天當然是奧灶面,紅紅火火,暖到心窩。
美食如汛,令人思念、牽掛。我個人一年之中有四次“激動時刻”。第一次激動是碧螺春汛,春分起,清明止,必到洞庭東、西山走一走,向茶園的采茶女、炒茶師傅問聲好,體驗一下采茶,并為炒茶的大灶加燒一把橘樹梗。每年的碧螺春汛,我都會買一個透亮的玻璃杯,為自己泡一杯新茶,只嘗那碧綠茶湯中“淡淡的果香味”。第二次激動是“小滿枇杷半坡黃”。開車至太湖一號公路口,有個很大的廣告牌,寫著“世界枇杷問中國,中國枇杷在東山”。話說得有點滿、有點牛,卻也是不爭的事實。我只是建議把最后三個字改為“東西山”,東山的白玉枇杷美,西山(洞庭鎮)的青種枇杷也不差。第三次激動是雞頭米上市。江南有水八仙,茭白、紅菱、茨菇、莼菜、水芹、荸薺、蓮藕、雞頭米。雞頭米上市之時,我總會到太湖邊水八仙種植基地,去看一看采摘的過程,到古城老街看一看農民邊剝邊賣的場景。選準價廉米美者,果斷下手,買回一年的存量。第四次激動是大閘蟹上市。每年的這個時候,我都會寫一篇重復的文章——一只大閘蟹六不吃,道一道吃蟹的注意點,因為并不是每一個江南人都會吃大閘蟹的。
美食如汛。千百年來,在歲月流淌中,留下了許多俚語、食諺,比如:立夏見三鮮,端午食五黃;小滿枇杷半坡黃,夏至楊梅漫山紅;明前螺螄賽吃鵝,小暑黃鱔賽人參;四月十四軋神仙,冬至夜要喝冬釀酒……各類媒體也會按“不時不食”的規律,適時地講述一個個美食故事,比如:康熙皇帝與碧螺春茶;乾隆皇帝食“豆瓣湯”;于右任誤將“斑肝湯”寫成“鲃肺湯”;張翰為“莼鱸羹”而辭官回鄉……
年年都會說,總也說不完,如江南春水,太湖潮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