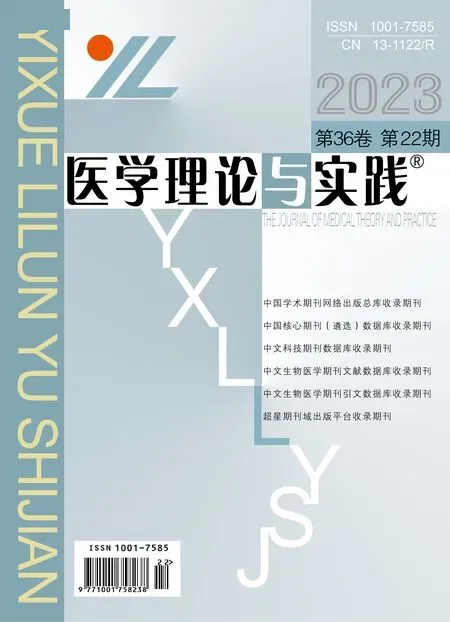宮頸鱗狀細胞癌伴淋巴結轉移患者的TGF-β、uPAR、NLR、FAR、SCC-Ag變化及臨床意義
劉 佩 劉思野 湖南省胸科醫院腫瘤診療中心,湖南省長沙市 40000; 湖南省腫瘤醫院放射診斷中心
宮頸癌中是一種臨床常見的惡性腫瘤,患病類型主要分為鱗癌、腺癌、腺鱗癌三種,其中約80%的患者為鱗狀細胞癌,該病具有較高的發病率與致死率,使女性身心健康與生命安全受到了極大的威脅[1]。研究顯示[2],與淋巴結未轉移者相比,伴淋巴結轉移的宮頸癌患者5年生存率明顯更低。患者預后情況受宮頸癌是否伴有淋巴結轉移所影響,故而在術前準確預測淋巴結轉移對于合理治療方案的確定具有重要意義。由Treg細胞分泌產生的細胞因子為轉化生長因子-β(TGF-β)能夠調節機體免疫應答。近些年新發現的腫瘤標記物尿激酶型纖溶酶原蛋白激活物受體(uPAR)在眾多正常細胞及腫瘤細胞表面中都有發現受體表達,其在腫瘤細胞表面表達明顯高于正常細胞,證明其與腫瘤的發生發展、侵襲轉移及惡性程度密切相關[3]。研究證實炎癥反應與惡性腫瘤存在相關性,患者病發宮頸癌過程中炎癥反應在其中起重要作用[4]。中性粒細胞與淋巴細胞比值(NLR)、纖維蛋白原與白蛋白比值(FAR)能夠反映全身炎性反應,是常用指標之一。在既往研究中發現宮頸癌伴淋巴結轉移時,腫瘤細胞更易向血清中釋放腫瘤標志物,而在眾多腫瘤標志物當中鱗狀細胞癌抗原(SCC-Ag)升高最為明顯,能夠幫助對宮頸鱗狀細胞癌進行輔助診斷,并在判斷預后及監測復發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5]。臨床上有關宮頸鱗狀細胞癌患者的TGF-β、uPAR、NLR、FAR、SCC-Ag與淋巴結轉移相關性的研究報道較少。本文旨在探討宮頸鱗狀細胞癌伴淋巴結轉移患者的TGF-β、uPAR、NLR、FAR、SCC-Ag變化及臨床意義。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21年3月—2022年3月湖南省胸科醫院及湖南省腫瘤醫院接收診治的176例宮頸鱗狀細胞癌患者為觀察對象,根據是否伴淋巴結轉移,將患者分成對照組(淋巴結未轉移,131例)和研究組(伴淋巴結轉移,45例)。患者年齡27~66歲,平均年齡(44.35±5.27)歲;體質量指數(BMI)22~26kg/m2,平均BMI(23.45±1.71)kg/m2。納入標準:(1)所有患者均經檢查確診為宮頸鱗狀細胞癌;(2)患者知曉此次研究的方法、目的等,同意參與;(3)資料完整;(4)未接受過放化療。排除標準:(1)患者合并其他惡性腫瘤;(2)具有免疫系統疾病;(3)嚴重肝、腎功能異常;(4)嚴重精神障礙。
1.2 方法 整理收集的所有患者的診療資料,包括:年齡、BMI、腫瘤最大徑線、人乳頭瘤病毒(HPV)感染情況、FIGO腫瘤分期、細胞分化、脈管浸潤、間質浸潤深度等。分別采集兩組患者晨起空腹肘靜脈血5ml,以3 000r/min的速度離心10min,離心半徑為10cm,將分離出來的血清保存待檢。采用酶聯免疫吸附法分別對兩組患者的TGF-β、uPAR水平進行檢測;根據血常規檢查結果計算NLR,NLR=中性粒細胞總數(109/L)/淋巴細胞總數(109/L);采用免疫比濁法分別對兩組患者的白蛋白水平進行檢測,并采用希森美康凝血分析儀分別對兩組患者的纖維蛋白原水平進行檢測,計算FAR;采用化學發光標記免疫測定法分別對兩組患者的SCC-Ag水平進行檢測。
1.3 觀察指標 采用單因素分析影響患者淋巴結轉移的因素,并采用Logistic回歸分析進行多因素分析,評估TGF-β、uPAR、NLR、FAR、SCC-Ag水平變化對患者淋巴結轉移的預測價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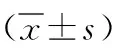
2 結果
2.1 影響患者淋巴結轉移的單因素分析 單因素分析結果顯示:腫瘤最大徑線、FIGO腫瘤分期、細胞分化、脈管浸潤、間質浸潤深度及TGF-β、uPAR、NLR、FAR、SCC-Ag水平與患者淋巴結轉移密切相關(P<0.05)。見表1。

表1 影響患者淋巴結轉移的單因素分析[n(%)]
2.2 影響患者淋巴結轉移的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 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顯示:TGF-β、uPAR、NLR、FAR、SCC-Ag水平升高是影響患者淋巴結轉移的獨立危險因素(P<0.05)。見表2。

表2 影響患者淋巴結轉移的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
3 討論
宮頸癌主要表現為淋巴結轉移與侵犯鄰近組織,其中宮頸癌預后受淋巴結轉移所影響,作為重要危險因素的淋巴結轉移影響著治療決策的制定。通過手術進行淋巴結清掃主要是為了判斷預后及是否需要補充放化療,若經過宮頸癌根治術后病理證實存在淋巴結轉移則需補充放化療,患者在經歷根治術及放化療雙重治療后仍未能改善預后,并且諸如淋巴水腫等相關并發癥增加[6]。現2018年FIGO指南建議,若患者病情經術前影像學提示存在淋巴結轉移則建議首選治療方式為全程放化療[7]。因此若想制定科學高效的治療決策則需準確有效地對宮頸癌淋巴結轉移進行預測評估。
本文通過單因素分析結果顯示:腫瘤最大徑線、FIGO腫瘤分期、細胞分化、脈管浸潤、間質浸潤深度及TGF-β、uPAR、NLR、FAR、SCC-Ag水平與宮頸鱗狀細胞癌患者淋巴結轉移密切相關;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發現:TGF-β、uPAR、NLR、FAR、SCC-Ag水平升高是影響患者淋巴結轉移的獨立危險因素,可對臨床治療方案的制定有一定參考價值。
Treg細胞分泌產生的細胞因子TGF-β與多種免疫細胞作用密切相關,能夠調節機體免疫應答反應,有效參與到宮頸癌的發生發展當中,可作為宮頸癌輔助診斷的標志物[8]。有研究顯示[9],宮頸癌患者血清TGF-β水平呈高表達,且隨病情加重而上升。本文結果顯示,宮頸鱗狀細胞癌伴淋巴結轉移患者的血清TGF-β水平明顯高于淋巴結未轉移的患者,且TGF-β水平升高是影響患者淋巴結轉移的獨立危險因素,說明TGF-β水平可以作為預測宮頸鱗狀細胞癌患者是否伴有淋巴結轉移的有效指標。近年來發現的多功能受體uPAR與腫瘤侵襲轉移密切相關,其與尿激酶型纖溶酶原蛋白激活物(UPA)結合形成復合物后能夠傳導信號并激活通路,傳導通路激活后促使腫瘤細胞骨架重排引發侵襲等行為[10]。本文結果顯示,宮頸鱗狀細胞癌伴淋巴結轉移患者的血清uPAR水平明顯高于淋巴結未轉移的患者,且uPAR水平升高是影響患者淋巴結轉移的獨立危險因素。原因可能在于血管內皮細胞在周圍組織中通過腫瘤中uPAR的蛋白水解作用形成新生血管,uPAR借此經血管淋巴管進入血液當中致使血清中uPAR的表達水平增高[11]。這表明血清中uPAR的高表達能夠充分反映宮頸癌對周圍組織的轉移侵襲,將uPAR表達水平作為反映淋巴結轉移和宮頸癌侵襲程度的生物學指標有利于針對性臨床治療方案的定制。
炎癥反應參與到腫瘤的發生發展、侵襲、轉移和預后當中,其病理機制使得患者機體出現免疫力下降,淋巴細胞減少。中性粒細胞升高能夠通過產生可溶性因子、蛋白酶來加快腫瘤生長,產生血管生長因子促進瘤血管生成,并且能夠抑制效應T細胞和NK細胞發揮細胞功能,進一步促進腫瘤的生長與轉移;淋巴細胞計數降低表明人體免疫功能下降,對腫瘤的監視抵抗作用下降,使腫瘤轉移更為輕松[12]。因此,機體腫瘤相關炎癥反應與抗腫瘤免疫水平的動態平衡狀態可通過NLR清晰反映出來,機體炎癥反應增強則NLR升高,且淋巴細胞參與的抗腫瘤免疫功能降低。FAR是新型的炎性標志物及潛在預測因子,不僅能夠反映全身性炎癥反應,同時還被應用于多種實體腫瘤預后評估中。纖維蛋白原發揮介導細胞相互作用,控制腫瘤細胞活性并促進腫瘤基質的形成,同時能夠與生長因子相結合加速腫瘤組織的血管生成,導致腫瘤生長和轉移[13]。白蛋白參與全身炎癥反應,其水平降低引發機體免疫系統削弱,進而導致腫瘤相關炎癥反應增強,細胞因子進一步增加促使腫瘤加速發展,對惡性腫瘤患者預后產生不良影響[14]。本文結果顯示,宮頸鱗狀細胞癌伴淋巴結轉移患者的NLR、FAR明顯高于淋巴結未轉移的患者,且NLR、FAR升高是影響患者淋巴結轉移的獨立危險因素,說明NLR、FAR可用于臨床預測宮頸鱗狀細胞癌患者是否伴有淋巴結轉移,對針對性治療方式的選擇有參考價值。
SCC-Ag是檢測宮頸鱗癌最常用的腫瘤標志物,惡性鱗狀上皮細胞進入血液循環的方式為通過分泌大量SCC-Ag,以此為基礎引起外周血中SCC-Ag濃度升高,臨床對相關疾病的輔助診斷、病情檢測和預后評估便是通過檢測血清中SCC-Ag水平,但其對淋巴結轉移的預測價值仍存在爭議[15]。李丹等[16]研究提示宮頸鱗癌盆腔淋巴結轉移可用SCC-Ag進行預測,并進一步提出當SCC-Ag為2.65ng/ml時是預測宮頸癌淋巴結轉移的最優截止值。本文結果顯示,宮頸鱗狀細胞癌伴淋巴結轉移患者的血清SCC-Ag水平明顯高于淋巴結未轉移的患者,且SCC-Ag水平升高是影響患者淋巴結轉移的獨立危險因素,可作為預測宮頸鱗狀細胞癌淋巴結轉移的重要指標。分析其原因在于SCC-Ag使腫瘤細胞擴散的方式為通過下調上皮型鈣黏蛋白(E-cadherin)等黏附分子的表達,進而導致淋巴結發生轉移;加之SCC-Ag能夠刺激TGF-β的分泌,而TGF-β以及其下游的β-連環蛋白通路參與早期宮頸鱗癌的淋巴結轉移;SCC-Ag可刺激基質金屬蛋白酶-9 (MMP-9)生成,MMP-9可溶解細胞基底膜以及細胞膜的膠原蛋白-4進一步促進腫瘤細胞轉移以及淋巴結轉移[17]。
綜上所述,TGF-β、uPAR、NLR、FAR、SCC-Ag水平變化對評估宮頸鱗狀細胞癌患者是否伴淋巴結轉移有一定的臨床價值,可作為預測患者是否伴淋巴結轉移的重要指標。TGF-β、uPAR、NLR、FAR、SCC-Ag水平升高是影響患者伴淋巴結轉移的獨立危險因素,臨床檢測患者TGF-β、uPAR、NLR、FAR、SCC-Ag水平對及時采取針對性治療措施有重要臨床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