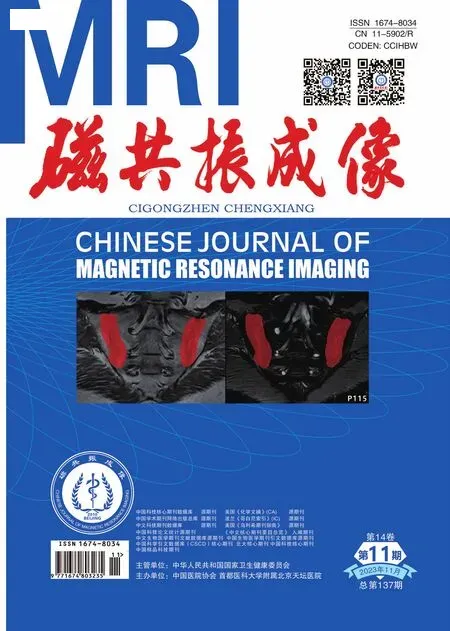腫瘤治療相關神經系統并發癥的MRI特征
何嘉琦,廖偉華,2*
0 前言
近年來,腫瘤的治療方法和模式越來越多樣化,隨著這些治療手段的興起,患者的生存期也不斷延長,同時,與腫瘤治療相關的并發癥也開始被廣泛報道。各種腫瘤治療方法都不可避免地會對神經系統產生不同程度的毒性作用,極大地降低了腫瘤長期生存患者的生存質量。
腫瘤治療相關的神經系統并發癥的發病時間跨度很大,可發生在腫瘤治療后短期內,也可在腫瘤治療數年甚至數十年后發生,且中樞神經系統和周圍神經系統均可受累,對神經系統的影響從早期可逆性的功能改變逐步進展為晚期不可逆性的結構改變,所以,早診斷、盡早進行治療方案的調整是減少神經系統損傷,提高患者生活質量最有效的方法。
MRI 作為一種非侵入性的檢查手段,能從結構和功能層面診斷和評估神經系統的病理改變,為診斷腫瘤治療相關的神經系統并發癥提供客觀證據,從而指導患者的管理和治療。
本文對當前腫瘤治療的常用手段(包括化學治療、放射治療以及免疫治療)可能導致的中樞和周圍神經系統并發癥及其相應的MRI特征進行綜述,并展望未來MRI 檢查在腫瘤治療相關的神經系統并發癥的早期診斷中的重要價值,為以后的臨床以及科研工作提供參考。
1 化學治療
化學治療所產生的神經毒性可影響周圍神經系統和中樞神經系統。
1.1 化療相關性周圍神經病變
化療相關性周圍神經病變(chemotherapy-induced peripheral neuropathy, CIPN)是最常見的周圍神經系統并發癥,大約30%~40%的化療后患者將出現CIPN[1],不同個體的癥狀常有差異,主要為自主神經功能異常及感覺異常,一般來說運動神經及顱神經受累較輕,MRI檢查能夠評估CIPN的病理改變主要包括:(1)背根神經節(dorsal root ganglia, DRG)以及軸突的損傷和凋亡;(2)周圍神經癥狀引發的大腦適應性反應。
大多數感覺相關體征和癥狀來自DRG或其軸突的損傷[1],表現為DRG體積的肥大,且DRG體積的增大程度與化療藥物的給藥劑量呈正相關。已有研究者使用磁共振神經成像 (magnetic resonance neurography,MRN)及電子計算機斷層掃描(computed tomography,CT)測量DRG的體積,在使用MRN對DRG進行形態學評價時發現CIPN 患者平均DRG 體積增加25%(L5)~56%(L4),而在使用CT測量DRG體積時顯示出與MRN測量結果的中等相關性[2-3],這使得使用影像學方法定量評估DRG 的體積從而評估CIPN 發生的可能性及其嚴重程度成為可能。
擴散張量成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g,DTI)因其能夠利用水分子的運動來揭示神經微結構和功能以及能夠提供有關纖維軌跡信息的特點,已開始用于周圍神經系統疾病的評估[4]。已有研究發現經紫杉烷治療前后患者的脛神經在小腿中部和踝關節兩處的各向異性分數(fractional anisotropy,FA)有顯著的降低,這一結果與化療能夠對軸突造成損傷的結果一致[5]。
大腦作為神經系統的中心所在,在CIPN 發病時也會出現一些結構和功能的改變[6]。有研究發現治療后短期內CIPN 患者能檢測到雙側額上回、扣帶回以及左側額中回與額內側回的腦灌注和灰質密度的升高,且升高的程度與癥狀的嚴重程度呈正相關[7]。這就給現如今CIPN以量表為主的主觀診斷方法提供了可靠的功能MRI客觀診斷。
常規MRI 檢查方法在周圍神經病變的檢測中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隨著MRI設備分辨率的不斷提高及檢查方法的不斷更新,越來越多的研究通過直接和間接的方法發現了CIPN 的影像學標志物,從而使得診斷CIPN 并對其嚴重程度進行評估具有可行性。然而由于周圍神經DTI等檢查技術要求較高,目前仍停留在臨床研究階段,需要進一步技術優化以提供臨床應用推廣。
1.2 化療相關的中樞神經病變
化療所致的常見中樞神經系統并發癥主要包括:急性白質腦病、后部可逆性腦病綜合征(posterior reversible encephalopathy syndrome,PRES)、脊髓病[8]。不同化療藥物所致的并發癥不全相同,且同種化療藥物也可能導致多種并發癥的出現。
急性白質腦病的癥狀從輕度認知功能障礙到重度癡呆、癲癇、共濟失調、輕偏癱甚至死亡,主要與化療藥物的代謝產物部分通過血腦屏障導致髓鞘水腫相關[9]。MRI特征為雙側大腦深部白質纖維束走行區域對稱的擴散受限改變,液體衰減反轉恢復(fluid attenuated inversion recovery, FLAIR)序列上呈高信號(圖1),病變部位表現為高灌注,其中,擴散加權成像(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DWI)、FLAIR信號強度及表觀擴散系數(apparent diffusion coeffecient, ADC)降低的百分比與白質腦病的預后相關[10-13]。在少數情況下,急性白質腦病可發展為壞死性白質腦病,這種改變是化療藥物導致的神經元凝固性壞死,為不可逆改變,MRI 上表現為出現在T2WI 高信號區域內的強化灶[8]。通常情況下患者的臨床和影像學異常表現會在停用化療藥物后出現顯著改善,甚至完全消失,且目前暫無研究表明再次引入同種化療藥物急性白質腦病會重復出現[14]。在行免疫治療后急性白質腦病亦可發生,兩者的臨床和影像表現基本相同,但免疫治療相關的急性白質腦病較化療相關性急性白質腦病在停藥后有著更佳的預后。

圖1 男,38歲,乙狀結腸癌患者,第一周期化療(方案:XERLOX)開始后一周突發全身抽搐,雙眼向上凝視,言語不能。顱腦MRI提示雙側對稱的沿白質纖維束走行的T2WI及液體衰減反轉恢復序列高信號(1A~1D)并擴散受限(1E~1H)(圖源:中南大學湘雅醫院影像歸檔和通信系統)。Fig.1 Male, 38 years old, patient of sigmoid colon carcinoma, suddenly presented a general convulsion one week after the onset of treatment (Regimen:XERLOX), with eyes staring upward and speech inability.MRI shows bilateral and symmetric high signal intensities on T2WI and fluid attenuated inversion recovery sequence (1A-1D), and restricted diffusion (1E-1H) along the fibre tracts of the white matter (Source: Image archiving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 of Xiangya Hospit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后部可逆性腦病綜合征(posterior reversible encephalopathy syndrome, PRES)是一種臨床影像學綜合征,典型癥狀包括頭痛、嘔吐、意識模糊、癲癇發作和視力異常等[15]。其機制主要為化療藥物導致的腦血管自身調節機制紊亂或內皮功能障礙所導致的血管源性腦水腫及化療藥物本身導致的細胞毒性腦水腫,后循環由于缺乏交感神經的支配而更易受累[16]。其MRI 特征為大腦半球后部區域(頂、枕葉等)局灶性的T2WI 及FLAIR 高信號[17](圖2),病變主要累及皮層及皮層下腦白質,少數情況下也可累及深部白質[18]。PRES 的發病部位被描述為三種放射學模式:頂-枕模式(病變分布在大腦后部區域)、分水嶺分布模式(病變主要涉及大腦前動脈和大腦中動脈支配區域的分水嶺區)以及非典型分布模式(包括小腦和腦干在內的其他區域)[19]。目前,PRES 病變區域的灌注情況仍存在爭議,一項使用動脈自旋標記(arterial spin labeling, ASL)對PRES 腦灌注改變的研究發現,在FLAIR信號異常即血管源性腦水腫出現之前就已可出現過度灌注的表現,且過度灌注恢復正常先于FLAIR 異常信號消失[20]。擴散受限提示嚴重血管源性水腫已發展到不可逆的細胞毒性水腫,此情況通常與預后不良相關[21]。通常,在停用化療藥物后,腦部的異常信號能完全恢復正常。

圖2 女,10歲,骨肉瘤患者,第二療程化療(API方案)的第4天出現頭痛、嘔吐、煩躁、顏面部和四肢抽搐、意識障礙。顱腦MRI提示左側頂葉片狀T2WI和液體衰減反轉恢復序列高信號(2A~2B),無明顯強化(2C)。2個月后復查顱腦MRI顯示原有病灶消失(2C~2D)(圖源:中南大學湘雅醫院影像歸檔和通信系統)。Fig.2 Female, 10 years old, patient of osteosarcoma, presented with headache, vomiting, irritability, facial and limb convulsions, consciousness disorder on the fourth day of the second cycle of chemotherapy (Regimen: API).MRI shows the signal intensities on T2WI and fluid attenuated inversion recovery sequence(2A-2B) without enhancement (2C).A follow-up MRI 2 months later suggests that the original lesion disappeared (2C-2D) (Source: Image archiving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 of Xiangya Hospit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脊髓病主要與鞘內注射化療藥物相關,病變發展從脊髓側索和后索的空泡變性到脊髓的橫貫性損傷不等[22],癥狀主要為與脊髓病變平面一致的感覺和運動的異常,并最終發展為截癱[23],此類患者通常需要進行腦脊液檢查以排除腫瘤細胞對脊髓的侵犯。MRI 檢查早期不會出現脊髓內的異常信號,隨后矢狀位圖像上出現長節段脊髓內的T2WI高信號以及脊髓腫脹,軸位示脊髓后索受累為主,增強后部分可有強化[23-26]。鞘內注射化療藥物還與姑息性放療時導致的脊髓變性劑量閾值的降低相關,其將增大發生脊髓病變的可能性[26]。
化學治療相關的中樞神經系統并發癥通常在停用化療藥物后可逆,因此,當出現相關臨床癥狀時,推薦患者行MRI檢查以明確并發癥存在與否,并指導臨床盡早進行治療方案的調整。
2 放射治療
放射治療已廣泛用于頭頸部原發及轉移腫瘤的治療,約有33%的患者在放射治療后會發生神經系統并發癥。放射治療誘導的神經系統并發癥主要累及中樞神經系統,周圍神經系統受累則較為少見。根據出現的時間,此類并發癥可分為急性(放療后數天或數周內發生)、早遲發型(放療1~4個月后發生)和晚遲發型(放療6個月后發生)[27],通常急性和早遲發型主要以神經功能改變為主,在常規MRI檢查中通常為陰性表現,晚遲發型則會出現相應的MRI檢查陽性表現,主要包括腦白質病、放射性壞死、腦血管并發癥和放療后卒中樣偏頭痛發作(stroke-like migraine attacks after radiation therapy, SMART)綜合征。
2.1 腦白質病
放療后腦白質的病變和腦白質體積的減小通常與智力和認知功能的降低相關,其產生原因包括血管損害、脫髓鞘和直接神經元損傷[28-29]。MRI 表現為進行性發展的腦白質異常信號,病灶自放射野向其他腦葉或沿側腦室向對側腦組織延伸,隨后逐漸融合,表現為腦室周圍白質的對稱性FLAIR 高信號,病變部腦組織可有萎縮,晚期通常會發展為廣泛的交通性腦積水和腦萎縮,皮層下的U型纖維、顱后窩、基底神經節和內囊通常不受累。已有研究發現,放療時使用海馬回避能夠明顯降低認知障礙的發生[27,29-30]。
2.2 放射性壞死
放射性壞死是由于放療后照射野內腦組織血管內皮的損傷和組織的凝固性壞死從而出現影像上類似腫瘤進展的表現,影像表現為照射野增強掃描后“肥皂泡樣”“瑞士奶酪樣”強化灶,以及強化灶周圍T2WI高信號水腫帶[29],傳統的結構MRI上幾乎無法與腫瘤進展進行鑒別,而當行磁共振灌注成像檢查時,壞死區域由于血管分布減少和血管通透性增加,表現為較低的相對腦血容量(relative cerebral blood volume, rCBV)和較高的信號強度恢復百分比(percentage signal intensity recovery, PSR),且PSR 的敏感性比rCBV 更高[31]。在磁共振波譜分析(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 MRS)中,與腫瘤進展相比,放射性壞死灶內N-乙酰天門冬氨酸(N-acetyl aspartate, NAA)峰、肌 酸(creatine,Cr)峰及膽堿(choline, Cho)峰值均降低,并表現出相對較低的Cho/Cr和相對較高的Cho/NAA,脂質峰和乳酸峰在兩者均可出現[32](圖3)。

圖3 女,38歲,膠質母細胞瘤患者,術后放療。復查顱腦MRI發現術區邊緣強化灶(3A,箭),強化區域相對腦血容量減低(3B,箭),磁共振波譜分析提示病變區域(3C)較正常腦組織(3D)諸峰值均有減低,以及較低的NAA/Cr比值和較高的Cho/Cr比值。隨后多次復查術區旁強化灶及周圍水腫帶無明顯變化,最終診斷為放射性壞死(圖源:中南大學湘雅醫院影像歸檔和通信系統)。NAA:N-乙酰天門冬氨酸;Cr:肌酸;Cho:膽堿。Fig.3 Female, 38 years old, patient of glioblastoma, accepted radiotherapy after surgery.A follow-up MRI shows a newly enhancement at the edge of surgical area(3A, arrow), with a lower relative cerebral blood volume (3B, arrow).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 shows the lesion (3C) has a decrease in height of all peaks,lower NAA/Cr and higher Cho/Cr comparing with the healthy region (3D).After several follow-up examinations indicated a stable lesion, she was final diagnosed as radiation necrosis (Source: Image archiving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 of Xiangya Hospit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NAA: N-acetyl aspartate; Cr: Creatine;Cho: Choline.
有研究發現,在使用放射治療聯合PD-1 抑制劑治療黑色素瘤腦轉移的患者時,其放射性壞死的發生率是單純放射治療的2.4倍,這可能與放射治療破壞血腦屏障并可作為免疫誘導劑加劇正常腦組織的免疫毒性相關[33-34]。
2.3 腦血管并發癥
腦血管病變在頭頸部腫瘤放療后的患者中普遍發生,一項基于7 T MRI對放療后微出血的研究中發現,100%的頭頸部腫瘤患者在放療后1年或更長時間檢測出至少一個微出血灶[35]。放射治療主要影響腦內的動脈和毛細血管,而對靜脈的影響通常較小[32]。主要機制是輻射導致的血管內皮的炎癥損傷,進而出現粥樣硬化斑塊形成、血栓形成等血管壁的改變[36],導致放射野內的血管的閉塞、動脈瘤形成甚至破裂出血,進而出現微出血灶、腦白質病、卒中(缺血性或出血性)、煙霧綜合征或腦血管畸形(包括海綿狀血管瘤、毛細血管擴張和動脈瘤)等[32]。當病變表現為微小血管的損傷時,磁敏感加權成像(susceptibility weighted imaging, SWI)通常能更敏感地在照射野內檢測到低信號的出血改變[37]。磁共振血管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angiography,MRA)和數字減影血管造影(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 DSA)是評估放療后血管情況的金標準,當病變累及較大血管時,還可以對血管壁進行評估。一項對42例單側腮腺腫瘤放療后患者雙側頸動脈管壁厚度的超聲評估發現,治療側的頸動脈管壁厚度增加有顯著性,且這種改變與腦血管意外的發生率增加有關[38]。而高分辨力血管壁成像(high resolution vessel wall imaging, HR-VWI)對顱內血管壁改變的敏感度更高,能夠更準確地檢測到放療后顱內血管壁的改變。
2.4 SMART綜合征
SMART 綜合征是一種罕見的遲發性并發癥,通常在放射治療數十年后發生,臨床上以偏頭痛為前驅癥狀,隨后發展為局灶性神經功能缺損,其MRI 表現通常較為典型,為與局灶性神經功能缺損相關腦區一致的明顯短暫性、可逆性腦回狀皮質增厚、強化,伴有或不伴有軟腦膜的強化,然而皮質增厚及強化程度達到峰值時,相應部位的灌注卻無明顯增高,這一特點可作為SMART 綜合征與腫瘤復發的鑒別點[39]。顳葉,其次是頂葉受累較為常見,且臨床癥狀的持續時間長短與高齡、顳葉受累及擴散受限相關[40]。通常,在受累腦區的皮質完全壞死之前,該并發癥導致的神經功能缺損是可逆的[30]。除此之外,SMART 綜合征、圍發作期假性進展(peri-ictal pseudoprogression, PIPG)及放療后急性晚發性腦病(acute late-onset encephalopathy after radiation therapy, ALERT)綜合征三種疾病實體由于影像學上表現類似,故合稱為放射治療引起的延遲性復發-緩解神經系統綜合征,三者主要的區分在于臨床表現的部分差異,但不一定每一次的臨床癥狀發作都伴隨著影像學的改變[32]。
放射治療相關的神經系統并發癥通常在進入晚遲發反應期才會出現典型的MRI特征,而此時神經系統的損傷已不完全可逆,所以,如何使用更精密的檢查儀器以及更先進的檢查方法尋找潛在的MRI 檢查標志物以在早遲發反應期甚至急性期對放射治療后神經系統并發癥進行診斷以及進行治療方案的調整成為當前研究的方向。
3 免疫治療
臨床目前常用的免疫治療方法包括嵌合抗原受體T 細 胞(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T cell,CAR-T)免疫療法和免疫檢查點抑制劑。
3.1 CAR-T療法
使用CAR-T療法的患者中有60%以上會出現神經系統的并發癥[41],該并發癥稱為免疫效應細胞相關神經毒性綜合征(immune effector cell-associated neurotoxicity syndrome, ICANS)。其產生的主要機制為血腦屏障的破壞從而導致炎性細胞因子和白細胞經腦脊液浸潤[42]。臨床表現從輕度意識模糊到失語、癲癇發作、腦水腫伴昏迷,甚至死亡[43]。美國移植和細胞治療學會(American Society for Transplantation and Cellular Therapy, ASTCT)根據患者的神經系統的癥狀將ICANS 分為4 級(表1)[41]。在顱腦MRI 檢查中,ICANS 1~2 級通常表現為陰性,隨著級別的升高,ICANS 逐漸表現為大腦深部結構的局灶性血管源性水腫,受累嚴重的部位可見T2WI 低信號的微出血灶,更高級別的ICANS可表現為整個大腦半球的血管源性水腫,增強掃描時可在FLAIR高信號區內發現與血腦屏障破壞相一致的強化灶,并可見到非特異性的軟腦膜的強化,嚴重者會出現大腦皮層的擴散受限。當患者臨床癥狀消退后,腦MRI異常可完全恢復正常[44-45]。

表1 ASTCT ICANS共識分級Tab.1 ASTCT ICANS consensus grading
3.2 免疫檢查點抑制劑
目前已投入臨床使用的免疫檢查點抑制劑包括:程序性死亡受體-1(programmed death-1, PD-1)抑制劑及其配體(programmed death-L1, PD-L1)抑制劑和細胞毒T 淋巴細胞相關抗原-4(cytotoxic T lymphocyte-associated antigen-4, CTLA-4)抑 制劑,其作用機制為抑制免疫檢查點分子抑制免疫細胞功能的作用,從而提高機體免疫細胞抗腫瘤的能力,然而檢查點抑制的作用很少局限于腫瘤微環境,PD-1/PD-L1和CTLA4在各種組織類型中廣泛表達,下調可引發廣泛的自身免疫毒性,從而導致免疫相關不良事件(immune-related adverse events,irAEs)的發生。irAEs 可累及全身多個系統,神經系統受累較為少見,稱為神經免疫相關不良事件(neurological immune-related advert event, NAEs),發病率約為1%~5%[46],包括中樞神經系統不良反應和周圍神經系統不良反應兩種類型。
中樞神經系統不良反應主要包括:腦炎、腦膜炎、脊髓炎和垂體炎,其中腦炎表現為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治療后出現的顱腦MRI 單側或雙側T2WI 或FLAIR異常信號,伴有或不伴有強化,病變部位在PET上表現為高代謝,分布以邊緣系統、皮層及基底節區常見[47](圖4)。顱內異常信號對激素治療敏感,分布和信號特點通常不具有特異性,診斷需結合腦脊液抗體檢測。腦膜炎主要表現為腦膜的強化。垂體炎表現為垂體增大。

圖4 男,64歲,非小細胞肺癌患者,行度伐利尤單抗治療后出現頭暈、頭痛、步態不穩等癥狀。顱腦MRI提示腦室周圍、皮層下和深部腦白質T2WI及液體衰減反轉恢復序列高信號(4A~4B),無強化(4C)。經甲潑尼龍注射及血漿置換后癥狀好轉(圖源:中南大學湘雅醫院影像歸檔和通信系統)。Fig.4 Male, 64 years old, patient of non-small cell lung carcinoma, presented with dizziness, headache, and unsteady walking after the treatment of tremelimumab.MRI shows T2WI and fluid attenuated inversion recovery sequence (4A-4B)hyperintensities at the periventricular, subcortical, and deep white matter, with no abnormal enhancement (4C).His symptoms relieved after methylprednisolone injection and plasma exchange (Source: Image archiving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 of Xiangya Hospit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周圍神經系統不良反應主要包括:格林-巴利綜合征(Guillain-Barré syndrome, GBS)和肌無力綜合征,現有的MRI 檢查方法對該類疾病的診斷效果欠佳。
需要注意的是,NAEs 的診斷是一種排除診斷,在作出診斷前需排除腫瘤轉移、副腫瘤綜合征等導致腦內異常信號灶的其他可能原因。所以,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以確定其特異性的影像標志物。
4 小結和展望
癌癥的各種治療方法不可避免地會產生不同程度的中樞神經系統和外周神經系統的多種并發癥,這些并發癥在早期通常可通過停藥或一定的治療手段有效逆轉,而到達晚期,特別是神經細胞發生不可逆的結構改變后,治療效果通常不佳,因此,如何在影像學上早期識別此類治療相關的神經系統并發癥并對神經系統功能進行保護以最大程度改善患者預后至關重要。
腫瘤治療相關神經系統并發癥的診斷仍面臨著諸多挑戰,現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回顧性研究及個案報道,與并發癥相關的診斷和治療指南較為缺乏,這就需要未來大規模前瞻性的研究及臨床-病理對照研究來進行改善。未來的研究也將使用更精密的檢查儀器(如超高場強MRI)、更新穎的檢查方法(如磁共振功能成像)聯合臨床及病理來尋找更敏感的MRI 標志物,以盡可能早地在出現不可逆的神經系統損傷前對其進行診斷并指導臨床治療。
作者利益沖突聲明:全體作者均聲明無利益沖突。
作者貢獻聲明:廖偉華提出本綜述選題和方案,并對本綜述的重要內容進行了修改,獲得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的資助;何嘉琦起草和撰寫本綜述,收集并描述本綜述內呈現的典型病例;全體作者都同意發表最后的修改稿,同意對本研究的所有方面負責,確保本研究的準確性和誠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