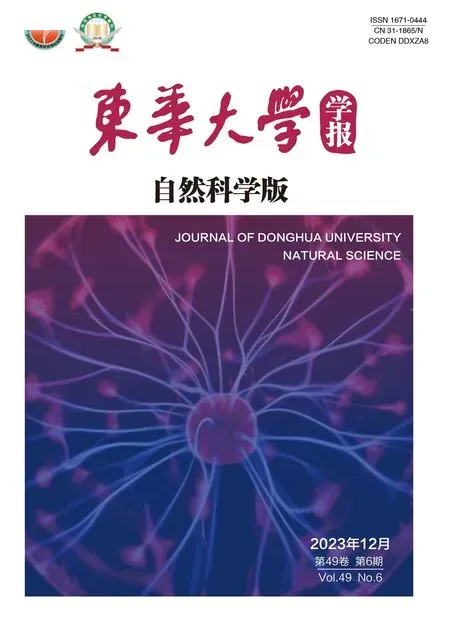典型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在土氣交換中的結構多樣性特征
丁家新,沈忱思,劉樹仁,徐晨燁,3
(1.東華大學 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 上海 201620;2.浙江樹人大學 交叉科學研究院,杭州 310015;3.上海污染控制與生態安全研究院, 上海 200092)
持久性有機污染物(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POPs)是一類具有環境持久性、生物累積性、高毒性并能長距離遷移的化合物[1]。通過“蚱蜢跳效應”,POPs污染物在環境介質中不斷發生“揮發-遷移-沉降”行為并在全球遷移[2]。目前,深海、極地、高海拔地區均檢出POPs[3]。由于這些污染物分布廣泛,且具有三致效應和內分泌干擾作用[4],因此其在環境中的分布、遷移及歸趨倍受關注[5]。
土氣交換是認識POPs生物地球化學循環的重要途徑(見圖1)。土壤是一種固、液、氣三相多孔非均勻的復雜系統,流動性較差,對POPs有一定的吸附作用,可成為POPs的“匯”;但由于大部分POPs仍然具有一定的揮發性和遷移潛力,土壤又會成為二次排放的污染“源”[6-7]。大氣則是POPs的重要遷移途徑。進入大氣后的POPs與顆粒物結合,通過干、濕沉降再次進入土壤,土壤再次成為污染“源”。由此,POPs在土壤和大氣中的賦存、溯源及其在土氣間的交換行為直接決定了污染物在環境中的遷移和歸宿。隨著分析技術深入到污染物的立體化學結構,研究者們發現多種POPs具有異構體特征且表現出選擇性的環境行為[8-9]。此外,采樣技術、環境要素、污染物的理化性質等均會影響POPs的土氣交換行為[10-11]。因此,探索POPs及其異構體在土壤與大氣之間的交換規律,有利于污染物的溯源,以及預測污染物的歸趨模式和計算交換通量。本文從采樣技術、逸度模型、土氣交換方向及通量、影響因素4個方面對典型POPs在土氣交換過程中表現出的結構多樣性特征進行綜述,以期為后續的研究提供參考。

圖1 土氣交換示意圖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soil air exchange
1 土氣交換過程中的采樣技術
POPs在土氣交換過程中的采樣技術分為主動采樣技術和被動采樣技術。土壤主動采樣技術通過直接采集環境樣本,提取目標污染物并計算其含量[12]。空氣主動采樣技術通過不同流量的采樣器采集污染物實現監測,空氣主動采樣器一般由收集器、流量計和抽氣動力系統3部分組成[13]。土壤被動采樣技術則是基于分子擴散或滲透原理,從環境介質中選擇性地吸收富集POPs,再通過分配模型計算土壤中POPs的含量[14],即利用土壤有機質與被動采樣材料之間的分配平衡進行分析計算。例如,Liu等[15]利用低密度聚乙烯(LDPE)膜進行被動采樣,吸附表層土壤中的多環芳烴(PAHs)。空氣被動采樣技術大多使用聚氨酯軟性泡沫(PUF)采樣器進行采樣。該采樣器的工作原理可靠,運輸和安裝成本低廉,因此應用最為廣泛[16]。近年來有許多研究將樹皮作為空氣被動采樣器。相比傳統的大容量活性空氣采樣器和PUF采樣器,樹皮的含脂量高,比表面積大且對空氣中污染物具有惰性[17-20],采樣更容易,且成本更低。因此,樹皮被視作評估大氣POPs污染賦存的環境基質。
2 逸度模型
逸度是指污染物脫離某種介質的趨勢。大氣逸度和土壤逸度的相對大小可以表征POPs土氣交換的最終結果。逸度模型首次由Mackay提出[21-22],通過計算污染物在不同介質中的逸度并對兩種介質進行比較,解釋污染物的遷移趨勢和環境行為。根據系統的復雜程度可將逸度模型分為4級,其中3級逸度模型應用最為廣泛[23]。該模型假設靶區域為穩態非平衡流動系統,結合地理、氣候和環境因素,根據質量守恒定律構建平衡方程以計算POPs的相間遷移量,能夠明確土壤和大氣的“源”“匯”關系[22,24-25]。模型參數包括污染物的理化性質、環境條件、污染物排放系數、介質間遷移系數和平流輸入濃度等。
逸度模型的結果用逸度分數(fugacity fraction,f)表示。f=0.5表示污染物在土氣之間達到平衡;f>0.5表示污染物從土壤凈揮發;f<0.5表示污染物向土壤凈沉降。考慮到參數選擇的不確定性,一般認為:0.3
fs=(csRT/0.411φom)Koa
(1)
fa=caRT
(2)
f=fs/(fs+fa)
(3)
式中:ca和cs分別為污染物在大氣和土壤中的濃度,mol/m3;T為溫度,K;R為氣體常數,R=8.314 Pa·m3/(mol·K);φom為土壤中有機質的含量;Koa為化合物的辛醇/空氣分配系數;0.411為校正因子。
POPs的空氣-土壤交換通量(F)按照式(4)進行計算。
F=(fa-fs)/[RT/K13+L3(RT/B1+H/B2)]
(4)
式中:K13為空氣-土壤傳質系數,K13=3.75 m/h;L3為土壤中的擴散路徑長度,L3=0.05 m;B1和B2分別為空氣和水中的分子擴散系數,B1=1.79×10-2m2/h,B2=1.79×10-6m2/h;H為亨利常數,Pa·m3/mol[26]。
3 土氣交換方向及通量
目前關于土氣交換的研究報道主要是針對傳統POPs,涉及有機氯農藥(organochlorine pesticides, OCPs)、多環芳烴(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 PAHs)、多氯聯苯(polychlorinated biphenyl, PCBs)、多溴聯苯醚(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PBDEs)、有機磷阻燃劑(organophosphorus flame retardants, OPFRs)。現有研究中的新型POPs包括全氟化合物(perfluoroalkyl substances, PFASs)和氯化石蠟(chlorinated paraffin, CPs)。
3.1 有機氯農藥(OCPs)
有機氯農藥是一類強穩定性、強抗降解性的POPs。滴滴涕(DDTs)和六六六(HCHs)是土壤和空氣中普遍存在的OCPs。DDTs及其代謝產物廣泛蓄積于人體和動物脂肪中。HCHs曾是最主要的農藥,其混合異構體包含4種主要成分,α-、β-、γ-、δ-HCH。不同OCPs及其代謝產物在土氣交換過程中表現出不同的機制。
在地中海地區,大多數OCPs的揮發通量遠低于輸入量,即空氣向土壤的凈沉降。Can-Güven等[27]在土耳其安塔利亞農業區的分析結果顯示,93.3%的OCPs的逸度分數低于0.34,僅約2.64%的OCPs的逸度分數高于0.66。這表明OCPs的污染主要來自空氣,凈沉積則是土氣交換的主要方向。在巴基斯坦及印度河流域的農業區,約20%的OCPs自土壤向到大氣凈揮發,導致當地棉花產區的土壤成為OCPs進入大氣的二次排放源[28-29]。此外,在巴基斯坦南部的海得拉巴市、東北部的旁遮普市,OCPs也呈現凈揮發的趨勢[30]。這一趨勢在印度東部的加爾各答、西部的孟買和果阿邦,以及南部的金奈和班加羅爾地區表現得更為明顯,這些地區OCPs的逸度分數的中位數均高于0.5[31]。
在意大利貝內文托省及尼泊爾加德滿都,p,p′-DDT及p,p′-DDD均傾向于沉積在土壤中(f=0.3)[32-33]。在巴基斯坦及印度河流域集水區,p,p′-DDD、o,p′-DDT的逸度分數為0.30~0.59,即空氣向土壤的凈沉降,而農業區的逸度分數變化較大(0.12~0.94)[28-29]。尤其在巴基斯坦南部的海得拉巴市、東北部的旁遮普市,p,p′-DDT及p,p′-DDE的逸度分數接近0.9[30]。對于DDTs異構體而言,湖北省鴨兒湖附近總DDTs的平均逸度分數小于0.5,但p,p′-DDT(f=0.55)、o,p′-DDT(f=0.42)和p,p′-DDE(f=0.26)有所偏移,揮發、平衡、沉積特征的情況同時存在。在安徽黃山、青藏高原西南部、青藏高原長塘草原南部、新疆哈密地區,p,p′-DDE、o,p′-DDE和o,p′-DDT和p,p′-DDT的逸度分數均小于0.5,存在明顯的凈沉積現象[34-36]。綜上所述:o,p′-DDT和p,p′-DDD在大部分研究中表現出從空氣到土壤的凈沉降趨勢;p,p′-DDT和p,p′-DDE則在南亞地區表現出強揮發性,而在中國中西部地區,沉降/平衡的趨勢較為明顯。
與DDTs不同的是,HCHs表現出明顯的異構體差異。在意大利貝內韋托省及尼泊爾加德滿都,大部分γ-HCH(f=0.7)和β-HCH(f=0.8)表現出向大氣揮發的趨勢[32-33]。同樣的結論在匈牙利平原的研究中也報道過,土壤是大多數OCPs的“源”,只有γ-HCH表現出凈沉降[37]。而在中國中部湖北省鴨兒湖,除γ-HCH在少數采樣點揮發外,α-HCH、β-HCH和γ-HCH在其他點位均發生凈沉降[38]。在鄂贛交界金沙地區、安徽黃山地區,α-HCH(f=0.78)凈揮發,而γ-HCH(f=0.4)處于平衡或凈沉積狀態[39-40]。在青藏高原的羌塘草原地區,夏季的α-HCH、γ-HCH和o,p′-DDT的沉積通量分別為1.22、0.38和0.71 pg/(m2·h),冬季的沉積通量分別為0.23、0.10和0.37 pg/(m2·h)。此外,研究[36,41-42]表明,在長三角地區,新疆哈密,青藏高原的紅原縣、黑水縣、紅原縣、阿壩縣,α-HCH、β-HCH、γ-HCH和δ-HCH的逸度分數均高于0.7,即HCHs從土壤中向空氣凈揮發,土壤則成為HCHs進入大氣的二次排放源。Niu等[18]將樹皮作為大氣有機物的被動采樣器,研究了我國農田土壤及周邊樹皮中的HCHs的土氣交換行為,結果在樹皮中檢測出了HCHs的4種異構體。綜上所述,α-HCH和β-HCH在我國中部地區呈沉降趨勢,而在西部及長三角地區,以從土壤中揮發為主。
3.2 多環芳烴(PAHs)
多環芳烴是一類具有多苯環結構組成的有機污染物,主要存在于化石燃料、汽油、柴油、瀝青中,目前16種PAHs被USEPA(美國環保局)篩選為優先控制污染物,包括低相對分子質量(2、3個芳香環)及高相對分子質量(≥4個芳香環)PAHs[43-45]。多數PAHs會吸附在空氣顆粒物上,低環PAHs則較多存在于氣相中。Degrendele等[37]研究發現,在匈牙利平原,土壤是PAHs再排放的來源,其中單個PAH的氣態通量為-8.26~379 pg/(m2·h)。在伊茲密爾的郊區和城市現場、Aliaga和Kocaeli工業區中,較低分子質量(M<178 g/mol)的PAHs逸度分數普遍大于1,以氣體吸收為主,而較高分子質量的PAHs(M>200 g/mol)則以干沉積為主,其中Aliaga和Kocaeli工業區平均PAHs干沉降通量分別為(8 160±5 024) ng/(m2·d)和(4 286±2 782) ng/(m2·d)[46]。總體而言,在地中海區域,低環的PAHs(如菲、芴、熒蒽等)的濃度在環境空氣中占主導地位。此外,一項2007—2008年針對我國京津偏遠地區和城市的調查發現,PAHs年空氣-土壤交換通量中位數為42.2 ng/(m2·d),其中苊烯和苊占了總通量的一半以上,城市村莊的逸度分數較大,表明城市PAHs從土壤到空氣的傾向高于農村和偏遠地區[47]。在上海某公園,菲和氟蒽的空氣-土壤交換通量分別為13.3~43.6 ng/(m2·d)和0.19~1.62 ng/(m2·d)[15]。中國杭州板山鋼鐵工業園區[48]、湖北大九湖[7]、青藏高原[49]、長江中下游(安徽段)[45]、武漢鄂州地區[50]、珠江三角洲周圍[51]、大連地區[44]、上海地區[15]的研究都表明,PAHs的逸度分數通常隨其相對分子質量的增加而降低。低相對分子質量PAHs在土壤中飽和,逸度分數大于0.7,趨向于重新揮發。土壤是PAHs(如萘、苊烯、蒽、菲等)的二次“源”,而大多數高分子相對質量PAHs的逸度分數均小于0.4,土壤是這些PAHs的“匯”(如苯并[b]熒蒽、苯并[k]熒蒽、芘等)。中低相對分子質量PAHs更有可能在大氣和土壤之間建立動態平衡。大連市PAHs的氣態沉降以2、3環PAHs為主,顆粒態沉降以4環PAHs為主,顆粒態5、6環的沉降通量明顯高于其氣態沉降[44]。亞洲五國的研究中,大部分區域土壤依然是5、6環PAHs的“匯”,而3、4環PAHs接近土氣平衡[52]。例如在印度阿格拉市的4個地點的調查中,萘作為一種低相對分子質量PAHs,呈現出從土壤中揮發的趨勢,而中等相對分子質量PAHs(萘、菲和蒽)和高相對分子質量PAHs(熒蒽和)未表現出這種趨勢[53]。
3.3 多氯聯苯(PCBs)
多氯聯苯是一組聯苯苯環上的氫原子被氯原子取代而形成的多氯代芳烴化合物,根據取代數目及位置的不同,理論上存在209種同系物[54]。大氣中PCBs主要來源是污染土壤的揮發或直接排放,進入大氣后PCBs以吸附態和氣態存在。研究表明,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2、3環PCBs從土壤到空氣凈揮發,4、6環PCBs更易發生凈沉降,在土壤中累積[55-56]。調查發現,在布拖爾和穆達尼亞地區[57],3、4環PCBs從土壤揮發至空氣,而高相對分子質量同系物(5-CBs)從空氣沉降到土壤,其中在布拖爾區域平均通量為(-2 145±390) ng/(m2·d),在穆達尼亞區域平均通量為(9±17) ng/(m2·d)。在布爾薩烏盧達格大學附近,PCBs從土壤揮發到空氣[43,58-61],凈通量為-0.2~3.0 ng/(m2·d)。在伊斯坦布爾Yavuzselim附近,PCBs的多數同系物從空氣沉降到土壤,凈通量為-0.5~1.2 ng/(m2·d)[62]。在歐洲其他地區,例如匈牙利平原,土壤是PCBs的“源”,單個PCB的氣態通量為-6.440~0.994 pg/(m2·h)[37]。研究表明,在南亞地區如印度全國典型城市[53]、尼泊爾加德滿都[53],土壤都是低相對分子質量PCBs二次排放源,較輕的PCB-28和PCB-52會大面積凈揮發。城市活動是巴基斯坦旁遮普PCBs污染的主要來源,PCB-28和PCB-52的逸度分數分別為0~0.7和0.2~0.5。其他同系物,如PCB-101、PCB-138、PCB-153和PCB-180,呈接近平衡或從土壤到空氣的揮發的趨勢[33,63-65]。對于PCBs衍生產物的土氣交換規律鮮少報道,僅博卡拉和比爾貢的調查顯示PCBs的硝化/氧化衍生產物3-NDBF、4-NBP等土壤-空氣逸度分數遠高于0.7,呈現出從土壤凈揮發的趨勢[65]。
此前在中國開展的大范圍城市PCBs土氣交換研究的結果表明,2008年所有PCBs同系物都是從大氣沉降到土壤,2013—2014年,PCB-28和PCB-52從土壤到大氣大面積揮發,展現出土氣交換方向的改變[66]。一項模擬研究[6]認為2005年1—3月和10—12月中國大部分地區PCB-28從空氣到土壤凈沉降,而同年4—9月,低分子量PCBs從土壤中向空氣凈揮發。2012年3月至2013年3月在鄂贛[67]和安徽南部[68],PCBs的逸度分數呈從低氯化PCBs到高氯化PCBs下降的趨勢,其中鄂贛地區的PCB-28、PCB-52、PCB-101、PCB-118的逸度分數均值分別為0.56、0.50、0.26和0.12,表現出低氯化PCBs的平衡/凈揮發以及高氯化PCBs的凈沉積[39,68]。一項西藏地區的研究結果顯示,PCB-28,PCB-52更具流動性,易發生土氣交換,同時土壤可能是潛在的二次來源[34]。總體而言,低相對分子質量的PAHs及PCBs普遍向大氣揮發,而土壤是大部分高分子化合物的“匯”。
3.4 多溴聯苯醚(PBDEs)
多溴聯苯醚因苯環上溴原子取代數目的不同而有209種同系物,命名為BDE-1至BDE-209[69],具有難降解和親脂性強的特點,其中四溴、五溴聯苯醚應用最為廣泛。多項研究表明,我國大氣和土壤環境中的PBDEs交換沒有達到平衡,兩相之間的傳遞以大氣向土壤傳輸為主,低溴代組分更接近土氣交換平衡,隨著溴原子相代數目的增加,大氣向土壤的傳輸能力逐漸增強[37,70-71]。在黑龍江省典型工業區,混合土壤中PBDEs主要源于商用十溴聯苯醚和商用五溴聯苯醚,逸度分數均低于0.5,以大氣沉降為主[71]。在中國中部金沙地區,BDE-209的平均干粒、濕顆粒、濕溶沉降通量分別為(210±290)、(80±120)、(160±290) pg/(m2·d)。PBDEs的凈空氣-土壤氣體交換通量為(-16±13) pg/(m2·d),空氣-土壤界面的氣體交換通量明顯低于沉積通量,僅占總沉積通量的2.5%,這意味著大氣沉積是多溴二苯醚進入土壤的重要輸入途徑[70],土壤是多溴二苯醚的重要“匯”。高溴化多溴二苯醚的顆粒沉積和低溴化多苯醚的濕溶解沉積及土壤中多溴二苯醚的再揮發不顯著。在中國的一個電子廢物回收站以及匈牙利平原土壤中,多溴二苯醚土壤-空氣交換的估計方向表明,溴化程度較低的多溴二苯醚(如BDE-28、47和100)通常從土壤蒸發到空氣中,而溴化程度較高的多溴聯苯醚在土壤和空氣中處于平衡狀態。其中匈牙利地區土氣交換通量為0.004~1.320 pg/(m2·h)[37,69-72]。可以看出溴化程度較低的多溴二苯醚的流動性更大,在土壤和空氣界面的氣體交換通量明顯要少于沉積通量,而溴化程度較高的PBDEs多處于平衡/沉積狀態。
3.5 有機磷阻燃劑(OPFRs)
有機磷阻燃劑經常被用作添加劑加至材料中,其具有揮發性,可在人體和環境介質中遷移富集。按照磷酸分子的取代基的不同可分為烷基磷酸酯、芳香磷酸酯和鹵代磷酸酯[69]。對于OPFRs來說,有機磷酸酯(organophosphate esters, OPEs)的大氣沉積會影響磷的自然循環,特別是在土壤貧瘠的環境中會影響生態系統的結構和功能[73-75]。多項研究表明OPEs主要從大氣向土壤沉降而非揮發,大氣是土壤中OPEs的主要來源[71,73,76]。一項我國南方亞熱帶城市——南寧市的水稻田研究結果顯示,土壤是環境中OPEs的“匯”,通過土氣交換向水稻田輸入的OPEs通量平均值為396 ng/(m2·d)。一個生長季(100 d)累積輸入通量約為171 μg/m2,土壤提供的OPEs通量約為86.3 μg/m2[77]。大連一項研究發現,磷酸三正丁酯(TNBP)、磷酸三(2-氯乙基)酯(TCEP)的逸度分數均大于0.6,呈現凈揮發;而磷酸三(2-氯丙基)酯(TCIPP)、磷酸三(1,3-二氯異丙基)酯(TDCIPP)、磷酸三(丁氧基乙基)酯(TBOEP)、磷酸三異辛酯(TPHP)、2-乙基己基二苯基磷酸酯(EHDPP)、磷酸三異辛酯(TEHP)、三苯基氧磷(TPPO)和磷酸三甲苯酯(TMPP)的逸度分數均小于0.25,表現為凈沉降。TCEP的揮發通量最高,為1 100 ng/(m3·d),而TCIPP的沉積通量最高,為171 ng/(m3·d)[73]。不同的是,尼泊爾4個主要城市地表土壤中幾乎所有TNBP、TCEP、TCIPP、TDCIPP、TPHP、EHDPHP、TEHP、TMPP的逸度分數均接近1,表現出絕對的揮發[72]。研究發現,南亞地區的土壤是OPFRs的二次排放源,TNBP和TCEP相較于其他有機磷阻燃劑而言揮發趨勢更高,而TMPP、TBOEP在各地的研究中以凈沉降為主。
3.6 全氟化合物(PFASs)
全氟化合物是一類廣泛用于工業和商業產品的有機化合物,常被用作表面活性劑、消防泡沫和食品包裝上的耐油脂涂層[79-80]。根據其結構特征可分為全氟羧酸類、全氟磺酸類、調聚氟酸和側鏈氟化聚合物及新型全氟化合物替代品[81]。基于多介質三級逸度模型(Level Ⅲ),崔曉宇等[82]考察了全氟辛烷磺酸(PFOS)在深圳多介質環境中的遷移規律,結果表明,氣相到土相是PFOS相間遷移的主要途徑,遷移量(33.6 mol/a)占PFOS總遷移量(104 mol/a)的32%。在大連地區,PFOS大氣到土壤的沉降(2.46×103mol/a)是其主要的遷移過程,占相間總遷移量的45.09%,可見土壤是中國大連PFOS的主要的“匯”[83]。

表1 不同地區PBDEs和OPFRs土氣交換特征Table 1 Soil-air exchange characteristics of PBDEs and OPFRs in different regions
3.7 氯化石蠟(CPs)
氯化石蠟具有熱穩定和耐燃性,通常用作增塑劑和添加劑,一般分為短鏈(SCCPs)、中鏈(MCCPs)和長鏈(LCCPs),碳鏈長度分別為10~13、14~17和18~30。SCCPs具有持久性、強毒性,能夠進行長期的大氣運輸和生物積累[84]。研究[11]表明,在浙江省舟山某造船廠附近,除C10Cl10和C10Cl7表現為凈揮發(f>0.7)、C10Cl5,10和C13Cl5-9表現為平衡狀態(f=0.3~0.7)以外,其他SCCPs和MCCPs的逸度分數均低于0.3。該區域的CPs以沉積為主,SCCPs的土氣排放通量為7.9~102 ng/(m2·h),顯著高于MCCPs[2.2×10-3~5.6×10-2ng/(m2·h)]。總體而言,具有更多氯原子和更長碳鏈的CPs流動性更小,主要傾向于從空氣中沉積到土壤中[11]。
4 影響因素分析
影響POPs土氣交換方向的因素有很多,包括環境溫度、季節變化、土壤性質和植被覆蓋程度等。環境溫度能改變POPs在環境介質中的分配系數。研究表明,土氣交換方向取決于目標污染物土氣分配系數(Ksa),溫度越高,Ksa越低,此時氣態污染物更傾向于從土壤向大氣擴散[58,85]。例如,在夏季高溫時期,賦存在土壤中的PAHs、OCPs易揮發到大氣中形成二次排放[7,31,41]。其次,環境溫度會影響化合物正辛醇-水分配系數Kow、正辛醇-空氣分配系數Koa。當Koa較大時,化合物通常逸度分數較小,難以從土壤向大氣中揮發[86]。
POPs的土氣交換行為還受季節變化的影響,部分POPs的逸度分數呈春夏季變大、秋冬季變小的趨勢。例如,在江漢平原等地,DDTs部分代謝產物的逸度分數在春夏季均接近或大于0.5,在秋冬季節普遍小于0.5[87]。夏季土壤一般為中低相對分子質量POPs的“源”,而冬季土壤為“匯”,而中等相對分子質量的化合物在周期性季節變化中,受大氣濃度、濕度和溫度的影響,通常表現出截然不同(平衡、沉積或揮發)的趨勢[62,87-88]。
土壤理化性質(包括土壤的濕度、有機質含量等)對POPs土氣交換過程的影響較大。濕度的影響主要表現為POPs從土壤顆粒中解析,擴散遷移至間隙水,再基于水氣界面交換揮發到土壤上方空氣中,最后通過與近地面空氣的氣體交換進入大氣中。濕度主要影響整個弱/非極性的化合物吸附過程的難易程度[89-91]。此外,土壤中的有機質大部分為腐殖質,且水溶性和親脂性不同,這導致有機物主要被土壤選擇性地吸附[92]。巴基斯坦、中國青藏高原地區的研究表明,有機碳和黑碳含量對PCBs及OCPs的土氣交換有很大影響[34,48]。具體而言,穩定的含碳吸附劑大量存在于土壤中,導致化合物在土壤中更易獲得保留。有機碳是控制森林土壤中POPs積累的關鍵因素,而在中高緯度森林的土壤中,較高濃度的有機碳發揮了攔截作用,進而削弱POPs向外界傳輸的能力[29,34]。
多項研究[18-19,45,93]表明,植物的葉片和表皮組織能夠吸附大氣中POPs,對POPs有顯著的吸附截留作用。POPs氣態交換可在大氣和植物的葉片、樹皮之間進行,同時也有部分POPs通過大氣沉降積累到植物表面[15,91]。研究指出,樹皮可以作為有機污染物(OCPs、PAHs、PCBs、PFASs)的空氣被動采樣器[20,94]。Jin等[17]對樹皮中的PFASs進行分析,結果顯示,PFOA和PFOS的異構體分布特征在大氣運輸和在樹皮中沉積時保持一致,表明樹皮組織能夠很好地攔截吸附氣態污染物。此外,植被覆蓋類型會顯著影響POPs的土氣交換趨勢和結構化特征[85]。如Liu等[93]研究發現,中國紅松皮中脂質含量越高,C5~C7的全氟磺酸類化合物濃度越高,而加拿大楊樹皮中長鏈同系物(C原子數≥7)的比例較大。Wu等[45]評估了長江中下游PAHs空氣-樹皮分配情況,結果顯示,生長較為緩慢的樟樹比生長較快的樹種能夠更好地截留大氣中PAHs。
5 總結與展望
從采樣技術、逸度模型、土氣交換規律以及影響因素4個方面總結了典型POPs的土氣交換行為。總體上POPs分布廣泛,高相對分子質量化合物受土壤大氣溫度影響較小,傾向于在土壤中沉積。而中低相對分子質量/高揮發性化合物受地理自然環境因素的影響較大,在沉積與平衡/揮發之間呈季節性變化的趨勢。南亞地區由于歷史排放或新規模化使用,OCPs、PAHs、PCBs土氣交換通量相比歐洲地中海區域、東亞地區更強,當地土壤普遍是污染物的二次排放源。近年來對POPs土氣交換過程的影響研究已經取得一定進展,但以下方面還需進一步研究。
(1)針對單個異構體或者衍生物的交換通量鮮少報道。了解異構體及衍生物的土氣交換規律,有利于更好地對污染物進行歸趨預測并總結結構化特征。此外,單一采樣只能反映采樣期內的土氣交換規律,環境條件如晝夜溫差等都會影響研究結果,需開展更廣泛的周期性研究。
(2)需研究全球各地區不同POPs的結構性富集特征,這對了解和評價POPs的選擇性環境分配和全球歸趨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