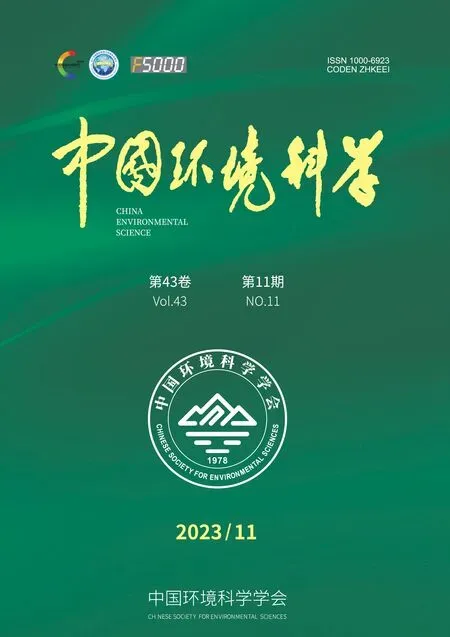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政策有效性評估研究——以江蘇省為例
吳文菁,劉苗苗,馬宗偉,方 文,楊建勛,畢 軍
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政策有效性評估研究——以江蘇省為例
吳文菁1,2,劉苗苗1*,馬宗偉1,方 文1,楊建勛1,畢 軍1
(1.南京大學環境學院,污染控制與資源化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江蘇 南京 210023;2.深圳市環境科學研究院,廣東 深圳 518000)
為了對我國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政策在實施過程中能否提升企業環境合規表現提供實證證據,基于江蘇省2281家企業投保信息和環境違規數據,構建雙重差分模型,檢驗分析政策有效性及其影響因素和機制.結果表明, 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在提升企業環境合規方面具有有效性,但政策效果受到企業環境風險等級、所在城市的調節作用:高環境風險企業提升合規表現的成本遠高于削減風險后能夠減少的保費,因而政策效果相對較弱;城市風險查勘服務質量越高,政策提升企業合規表現的效果越好.研究為提高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政策的有效性提供了實證支撐.
環境污染責任保險;雙重差分法;環境風險防控;有效性評估;企業環境合規
2006~2015年期間,我國共發生5213起環境事故,平均每年發生的環境事故多達500多起[1].近兩年,江蘇響水“3×21”特別重大爆炸事故、黑龍江伊春鹿鳴礦業有限公司“3×28”尾礦庫泄露次生突發環境事件等,嚴重威脅我國生態環境和居民生命財產安全[2-3].因此,高效防范企業環境風險已成為生態文明建設的重大挑戰.
為應對企業環境風險的挑戰,我國引入環境污染責任保險這一市場工具[4-6].2020年,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以立法的形式規定了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在危險廢物行業的強制性.目前,我國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正在經歷由自愿試點到強制推廣的關鍵時期,執行力度逐步增強,保險的行業覆蓋范圍也不斷拓展.
在理論層面,環境污染責任保險通常被賦予分擔損害的經濟賠償功能和預防減少企業環境風險的社會管理功能.一方面,環境污染事故損害數額巨大,賠償往往超過企業的支付能力,使得企業破產、受害人難以得到有效賠償,政府最終承擔了最后責任人的角色[7].環境污染責任保險預期通過集中資源共同承擔經濟損失和賠償,達到資源的效率優化.另一方面,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基于被量化和差異化的風險計算保費,并提供風險管理服務,預期將激勵和幫助被保險人采取預防措施提升其環境合規表現,實現降低風險的社會管理功能.
在我國的實踐中,環境污染責任保險被主管部門作為輔助風險管理的市場工具,更加強調其激勵企業環境合規、降低和預防風險的社會管理功能,并通過各種政策文件突出風險勘查服務的重要性.原環保部與保監會《關于開展環境污染強制責任保險試點工作的指導意見(環發〔2013〕10號)》中提出“健全環境風險評估程序”,鼓勵保險經紀機構提供環境風險評估和其他有關保險的技術支持和服務.同時“建立健全環境風險防范機制”,明確規定各方在環境風險防范工作中的相應責任,要求保險公司做好對投保企業環境風險管理的指導和服務工作.此外,《環境污染強制責任保險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也強調“環境風險評估報告是保險合同的組成部分”,將風險評估與排查服務作為保險公司的責任和義務.
盡管我國一直強調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政策激勵企業環境合規、降低企業風險的作用,但是關于這項政策有效性的爭議卻從未間斷.近年來,學者們從政策與法律的對接、保險產品設計、技術流程和標準完善等角度剖析了我國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政策的問題,并提出了對策建議[8-11].但是,這些研究多是基于專家經驗、文本分析等定性方法的觀點類研究,側重于定性地討論政策設計和實施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和不足,較少關注政策實施效果的量化評估.例如,Feng等[12]根據實際案例,以無錫和重慶作為研究對象,比較了在中國地方試點的強制和自愿的兩種承保模式,得出目前我國強制環境污染責任保險的推廣和實施效果勝于自愿環境污染責任保險的結論.僅有少量研究開展了政策實施效果的定量分析,但是側重于政策實施對企業經濟表現的影響[13].尚未有量化的實證研究檢驗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政策實施在提升企業環境合規表現、降低風險方面的有效性,也難以識別出影響政策效果的核心因素.
因此,本研究針對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政策實施的有效性問題,以江蘇省13個市的2713家企業為研究范圍,基于問卷調研以及公眾環境研究中心(IPE)發布的企業環境違規記錄數據,構建雙重差分模型檢驗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政策是否能夠激勵企業提升環境合規表現.此外,結合交互項檢驗和分組檢驗,進一步探究政策有效性的影響因素和機制.本研究在科學評估政策實際效果的基礎上,幫助決策者科學合理地設計和改進新時期的政策,保障我國環境污染責任保險順利度過自愿試點到強制推廣的關鍵時期.
1 理論基礎與研究假設
為構建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政策有效性評估的實證模型,本研究首先對江蘇省無錫市的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政策實施情況進行了調研和分析.一是因為無錫市是全國最早推廣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政策的地區之一.2009年5月,無錫市下發《關于開展環境污染責任保險試點工作的指導意見》,試點工作有序開展;同年10月,無錫市被環保部列為全國試點城市,首批18家企業投保;2011年,無錫市印發《無錫市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實施意見》,要求太湖流域一級保護區范圍內存在環境污染風險的所有工業企業以及化工、使用危險化學品的企業,危險廢物經營、處置企業,冶金、鋼鐵等多個行業企業參加環境污染責任保險.2015年,無錫市參保企業涉及化工、危廢處置、鋼鐵、印染、污水處理等多個行業,參保覆蓋面積逐年擴大,累計投保4164家、承擔責任風險41億元[14].二是因為“無錫模式”已嵌入我國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政策的頂層設計.長期以來,無錫市堅持打造“基于環境風險管理的環責險第三方評估模式”,為擬投保企業和續保企業提供專業的環境風險現場勘查與評估服務,幫助其根據“環境體檢”的結果進行整治和改進.截至2015年底,無錫市在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工作中對3000多家企業進行了環境風險現場查勘與評估,幫助企業排查出較大環境安全隱患3303個,出具報告3000余份[14].“無錫模式”通過企業參與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構建起企業、保險公司、第三方風險評估機構三者的合作關系(如圖1所示).2017年,無錫市應邀參加國家《環境污染強制責任保險管理辦法(草案)》編制,第三方風險評估模式已成為我國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

圖1 企業、保險公司、第三方機構作用關系
在“無錫模式”下,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政策可能通過兩種路徑影響企業的環境風險管理水平.第一,保險公司根據企業環境風險對保險費率進行差異化厘定.投保企業受到保費的杠桿作用,依據保費厘定標準整改自身風險隱患,以期降低保費支出[15].然而,當前數據和技術方法尚不能支撐企業環境風險的精準量化,導致保費范圍相對固定,難以激勵企業提升環境風險管理水平[16].第二,保險公司被賦予了一定的監管責任和義務,通過聯合第三方風險評估機構,定期提供專業的風險查勘和評估服務,幫助和監督企業解決可能導致風險事故的環境和安全隱患[17].投保企業在專業指導和監督下,出于減少環境不合規伴隨的生產中斷損失的考慮,有動機對自身風險隱患和違規行為進行整改,從而降低環境風險.該路徑已經得到了落實和推廣.基于上述分析,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政策降低企業環境風險最直接的體現是促進企業提升環境合規表現.據此,本研究提出:
假設1: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政策將促進企業環境合規,從而降低環境風險.
此外,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政策對企業提升環境合規表現的促進作用會因企業實施環境管理驅動力的差異而有所不同.企業實施環境管理的驅動力分為內部和外部兩種類型[18].內部驅動力由公司內部動機產生,包括組織能力、動態能力、吸收能力、企業戰略和管理意識等[19].出于利己動機(例如成本節約、資源獲取、風險規避)的一系列有利于提高企業競爭優勢的因素都可能成為企業進行環境風險管理的重要內部推動力[18,20].來自外部的驅動力可以分為三個方面,即政府驅動力、市場驅動力和社會驅動力,例如來自政府法規、社會合法性和利益相關者的壓力.這些驅動力在促進企業環境管理方面非常重要.
從內部驅動力的角度出發,投保企業改善環境合規的動機之一在于其根據專業的風險查勘和評估服務提供的建議對自身風險隱患和違規行為進行整改,可以減少環境不合規伴隨的生產中斷的損失.然而,對于環境風險較高的投保企業而言,進行自身風險隱患和違規行為整改會產生高昂的成本,甚至超出環境合規規避的生產中斷的損失.同時,目前相對固定的保費范圍和有限的賠償額度既無法通過降低保費彌補削減風險的成本.因此,與環境風險較低的投保企業相比,環境風險較高的投保企業出于僥幸投機的心理實施環境管理的內部驅動力會減弱.據此,本研究提出:
假設2: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對企業環境合規的促進作用在高環境風險的企業會受到抑制.
從外部驅動力的角度出發,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政策所產生的政府和社會驅動力將成為影響企業實施環境管理的兩大外部驅動力.對于無錫市企業而言,在“無錫模式”的引導下,政府推進政策、同行參與投保以及第三方評估模式帶來的政府和社會監督都營造了更加積極的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政策環境,驅動企業更加積極地實施環境管理.據此,本研究提出:
假設3: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對企業環境合規的促進作用在無錫市會得到強化.
2 研究設計
2.1 研究方法選擇和范圍界定
2008年起,環境污染責任保險試點在江蘇省內逐步鋪開,本研究將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政策的實施視為準自然實驗,結合面板數據結構、試點性政策特征等特點,構建雙重差分模型,通過計算政策實施前后處理組和控制組之間的差異,反映政策對處理組的真實影響,即政策“凈效應”.
選擇江蘇省內的工業企業作為研究對象,包含投保環境污染責任保險的企業和未投保企業.一方面,江蘇省企業在全國的投保企業中占比極大,樣本充足且代表性強.根據原環境保護部發布的公開數據,2014年全國共有4556家企業投保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其中江蘇省1932家,占比達42.4%;2015年,全國共有3780家企業投保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其中江蘇省有2213家,占比達58.55%.另一方面,江蘇省堅持推行環境污染責任保險第三方風險評估的“無錫模式”,也即保險公司在企業投保前后聯合第三方風險評估機構對企業開展環境安全隱患排查,并提出改進建議.“無錫模式”充分體現了我國環境污染保險政策更加強調其激勵企業環境合規、降低和預防風險的社會管理功能的特點,具有研究代表性.綜合考慮江蘇省企業投保時間和數據可得性,本研究的時間范圍為2011年至2020年.
2.2 主檢驗模型構建
為驗證研究假設1,本研究根據企業是否投保將其劃分為處理組和對照組.同時,根據企業投保年份,確定每家企業的政策生效年.考慮到政策效果具有滯后性,因此分別采用企業首次投保年份以及首次投保的次年作為政策生效年.在此基礎上,構建雙重差分模型檢驗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政策對企業環境合規表現的影響,具體如公式(1)所示:

式中:EP為企業環境合規表現,采用企業當年的環境違規記錄數表示.m為個體固定效應;為時間固定效應;postdate為表征政策干預前后的二分變量(時間虛擬變量),即企業政策生效年后為1,否則為0;treat為表征企業是否為處理組的二分變量(組別虛擬變量),即投保企業為1,未投保企業為0;it為其他控制變量;it為其他不可測因素.treat(組別虛擬變量)和postdate(時間虛擬變量)的交互項系數4表示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政策對企業環境合規表現的影響.若系數為正,表示政策對企業環境合規表現的提升具有顯著效果,若系數為負,表示政策對企業環境合規表現的退步具有顯著效果.
2.3 異質性檢驗模型構建
為驗證研究假設2和3,本研究構建了異質性檢驗(包括交互項檢驗和分組檢驗)探究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政策對不同類別企業的影響效果是否存在差異,進而識別影響政策有效性的因素和作用機制.其中,分組檢驗的模型形式與雙重差分主檢驗模型一致,區別在于根據企業環境風險等級、所屬城市兩個異質性檢驗的分組變量對企業分組后分別擬合模型.交互項檢驗模型具體如公式(2)所示:

式中:Group為異質性檢驗的分組變量,具體如表1所示,其他變量含義同上所述.treat(組別虛擬變量)、postdate(時間虛擬變量)和Group(異質性檢驗的分組變量)的交互項系數4表示異質性變量對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政策效果的調節作用.若系數顯著且為正,表示該異質性檢驗的分組變量會抑制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政策對企業環境合規的促進作用;若系數顯著且為負,表示該異質性檢驗的分組變量會強化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政策對企業環境合規的促進作用;若系數不顯著,則表示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政策對企業環境合規的作用不受該異質性檢驗的分組變量的影響.

表1 異質性檢驗分組變量選擇
2.4 數據采集、清洗與分析
為獲取雙重差分模型數據,2020年5~9月,本研究在江蘇省13個設區市開展了企業環境污染責任保險的問卷調查.該調查采用分層隨機抽樣,最終搜集了2713家企業的有效問卷.問卷調查內容涵蓋企業所在城市、所屬行業、上年度營業收入、員工人數、投保年份、企業環境風險等級評價以及對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政策部分實施環節的認知及看法.由于調查問卷設計局限,本研究只能區分2015年以前企業是否投保,但無法區分2015年以前企業投保的具體年份,進而無法確定2015年以前投保企業的政策生效年.因此,在實證分析時,剔除了432家2015年以前的投保企業.最終,共有2281家企業作為有效樣本納入雙重差分建模,其中處理組企業763家,控制組企業1518家.此外,本研究通過企業信用代碼檢索匹配公眾環境研究中心(IPE)發布的企業環境違規記錄數據,獲取了2281家企業在2011至2020年期間每年違規記錄數目.
由表2可知,處理組和控制組在企業規模、所在城市等變量的分布上基本一致,說明樣本選擇不存在明顯偏移.此外,處理組企業的違規記錄數目和高環境風險等級的企業占比要高于控制組.這也符合現實中保險領域普遍存在的“逆選擇”效應,也即違規更多、風險更高的企業會傾向于選擇投保.

表2 樣本描述性統計
注:“非無錫市”包含江蘇省除無錫市外的全部城市.
3 實證結果分析
3.1 主模型回歸結果
表3展示了主模型的回歸結果.模型(1)是以首次投保年份為政策生效年的結果,模型(2)是以首次投保年份的次年為政策生效年的結果.由表可知,投保當年,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政策的實施對投保企業環境合規表現的影響在90%顯著性水平上不顯著;但是,在投保后一年,投保企業環境違規次數下降0.040(95%置信區間為0.001至0.080).這一結果證明假設1成立,也即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政策會促進企業提升其環境合規表現.企業環境違規記錄反映了企業在污染物排放、貯存、處置以及應急過程中的不合規行為,包括違反環境影響評價、“三同時”、重污染天氣應急預案等環境管理制度的違法行為.這些行為將導致企業環境安全隱患增加、環境風險增大.因此,這一結果也意味著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政策會促進企業環境風險降低.但是,政策效果具有1年的滯后期,不會立刻顯現.這種政策效果的滯后性與保險產品的作用機制有關,通常當年購買的保險產品是為未來一年的風險做準備.

表3 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制度有效性基準回歸結果
注:括號內為聚類到城市層面的標準誤差;*、**和***分別代表在10%、5%和1%的水平統計顯著,下同.
3.2 平行趨勢檢驗
滿足平行趨勢假設是雙重差分法的前提,即通過平行趨勢檢驗則表示處理組和控制組在政策實施之前的變化趨勢相一致,由此能夠以控制組的趨勢來推算處理組在沒有受到政策影響下的情況.研究參照Beck等[21]的檢驗方法,將企業首次投保年份作為政策生效年,首次投保前后的年份按照與政策生效年的時間距離分別設定,以政策生效年的前一年作為基期進行平行趨勢假設檢驗.圖2展示了平行趨勢假設檢驗結果.

圖2 平行趨勢假設檢驗示意
由圖可知,企業首次投保前年份的回歸系數不顯著異于0,也即95%置信區間均包含0,意味著樣本數據通過平行趨勢檢驗.這說明在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政策實施前,未投保企業和投保企業的環境合規表現變化趨勢一致.因此,樣本數據情況滿足雙重差分建模的前提條件,可以通過未投保企業環境合規表現的變化趨勢來推算投保企業在沒有受到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政策影響下的情況.
3.3 穩健性檢驗
為檢驗假設1成立的可靠性,本研究通過兩種方式進行穩健性檢驗:(1)更改時間窗口,由于企業首次投保年份為2016至2019年不等,因此將時間窗口原來的2011年至2020年縮短為2014年至2020年進行雙重差分檢驗.此時,若結果仍然顯著,說明主模型回歸的估計結果具有可靠性.(2)假定政策實施的年份提前發生,即選取政策實施以前的年份進行雙重差分.此時,若結果仍然顯著,則表示主模型回歸的估計結果可能出現了偏誤;若結果不顯著,則表示主模型回歸的估計結果具有可靠性.
表4展示了穩健性檢驗結果.其中,模型(3)縮短了時間窗口,政策生效年仍為首次投保后一年;模型(4)、(5)分別將政策生效年提前為首次投保前一年、兩年.由表4可知,模型(3)中表征政策干預效果的交互項系數在99%顯著性水平上顯著,而模型(4)、(5)中表征政策干預效果的交互項系數在90%顯著性水平上均不顯著.上述穩健性檢驗結果均證明了主模型回歸估計結果具有可靠性.這也驗證了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政策會促進企業提升環境合規表現這一發現的可靠性.

表4 穩健性檢驗結果
3.4 異質性分析
表5和表6分別展示了交互項檢驗結果和分組檢驗結果.

表5 異質性檢驗交互項模型結果
表5中的模型(6)和表6中的模型(8)和(9)檢驗了企業環境風險等級是否會改變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政策對企業環境合規表現的促進作用.由交互項檢驗模型(6)結果可知,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政策對企業環境合規表現的促進作用會隨著企業自身環境風險增加而減弱(95%顯著性水平上顯著).分組檢驗模型(8)和(9)的結果也顯示,對于非高環境風險的企業,投保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會導致企業環境違規記錄次數下降0.054(95%置信區間為0.007至0.102);而對于高環境風險的企業,投保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后企業環境違規記錄次數并沒有顯著的變化.兩種異質性檢驗模型的結果相一致,均意味著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政策的有效性對于高風險企業會大打折扣.
如前文所述,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政策通過保費激勵和第三方風險管理兩種路徑促進企業提升環境合規表現.但是,當前數據和技術方法尚不能支撐企業環境風險進行精準量化評估,無法進行差異化的保費厘定,因此目前政策實施中保費范圍相對固定.這意味著高風險企業通過整改風險隱患、提升合規表現獲得的保費激勵十分有限.但是,相較于非高環境風險的企業,高環境風險的企業實現合規的整改成本會顯著增加,遠高于自身風險降低節省的保費.在成本遠高于效益的情況下,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政策通過第三方風險管理促進企業提升環境合規表現的效果就會大打折扣.這也是政策有效性在不同環境風險等級的企業間產生異質性的根本原因.

表6 異質性檢驗分組模型結果
注:括號內為聚類到城市層面的標準誤差,模型(10)中由于所屬城市這一變量僅有無錫市,因此標準誤差聚類變量改為行業類別.
此外,表5中的模型(7)和表6中的模型(10)和(11)檢驗了無錫市特有的政策環境(也即“無錫模式”)是否會改變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政策對企業環境合規表現的促進作用.由交互項檢驗模型(7)結果可知,無錫市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政策對企業環境合規表現的促進作用要顯著強于其它城市(99%顯著性水平上顯著).分組檢驗模型(10)和(11)的結果也顯示,對于無錫市的企業,投保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會導致企業環境違規記錄次數下降0.123(95%置信區間為0.023至0.224);而對于其它城市的企業,投保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后企業環境違規記錄次數則沒有顯著的變化.兩種異質性檢驗模型的結果相一致,均意味著無錫市特有的政策環境(也即“無錫模式”)會強化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政策對企業環境合規的促進作用.
上述異質性可能歸因于“無錫模式”下第三方風險管理服務的高質量監督和高認可度下企業對環境風險的重視和改進意愿的增強.本研究在問卷調查中搜集了企業對其所在城市第三方風險管理服務質量的評價.結果顯示,雖然其它城市在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政策的實施過程中均借鑒“無錫模式”提供了第三方風險管理服務,但是不同城市企業對該服務的認可度存在顯著差異.由表7可知,在所有接受過風險評估與現場查勘服務的無錫市企業中,對該服務高度認可的企業占比為67.53%,顯著高于其它城市的59.66%.這意味著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政策的有效性依賴于企業所在城市提供的第三方風險管理服務質量.只有第三方風險管理服務質量有保證,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政策才能真正發揮提升企業環境合規表現、降低環境風險的作用;否則,政策就會失效.

表7 風險評估與現場查勘服務認可度(%)
4 結論
4.1 根據高環境風險等級企業組別在交互項檢驗中系數為正且顯著,以及非高環境風險等級企業組別在分組檢驗中交互項系數為負且顯著的檢驗結果可知,由于缺乏量化的、差異化的保費厘定,加之相對更高的環境合規提升成本,政策的促進作用在高環境風險企業會被削弱.
4.2 根據無錫市企業組別在交互項檢驗中系數為負且顯著,以及其在分組檢驗中交互項系數為負且顯著的檢驗結果,結合風險評估與現場查勘服務認可度調查結果可知,企業對第三方風險管理服務質量抱有高認可度的城市展現出的政策促進效果更強.
5 政策建議
本研究的發現對我國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政策的健全和完善具有啟示意義.
一是深入推廣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加大政策實施力度,在政策和保險產品設計中強調和突出環境風險防控的社會管理功能,而不僅是經濟賠償功能.在國家層面,逐步完善我國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法律體系的頂層設計,有效對接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明確環境責任原則,而非行為違法原則;在地方層面,開展強制企業名單制定、承保和風險管理服務方案確定、事故責任認定及賠付等方面的模式創新[8],如在政策中明確提出用于風險防控服務的保費比例,并出臺相關保險服務標準對第三方和保險公司進行規范等.
二是發展風險評估技術,優化保險模式,提高保險產品多樣性,多方位覆蓋企業需求.按照目前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模式推廣環境污染強制責任保險、強制要求環境高風險企業投保會造成企業負擔增加,但環境風險防控效果不佳的困境.因此,應當先優化改進現有保險模式,再進行強制推廣.例如,盡快完善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模式,建立健全面向漸進污染和生態環境損害的環境污染責任保險配套技術支撐體系[22-23],在保費厘定上形成差距,從而通過費率的杠桿作用激勵企業提高環境管理水平[16].同時,在強制保險的基礎上結合“高保額、高保障”的商業附加險[8],滿足高環境風險等級企業的“兜底”需求等.
三是強調第三方風險管理服務的質量保障,特別是對高環境風險企業的風險評估與查勘服務進行專業化提升,加強企業對環境責任保險的認可度和信任度[24].例如,在技術層面,針對不同行業企業區別設計環境風險評估方法以保障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公平性和可操作性[22];在產業層面,積極引進相關專業人才,通過專業人才的培養,提高環境風險評估與查勘工作的專業程度等.
[1] Cao G Z, Yang L, Liu L X, et al. Environmental incidents in China: Lessons from 2006 to 2015 [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18,633:1165-1172.
[2] 中華人民共和國生態環境部.2020年中國生態環境狀況公報. 2020.Ministry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Report on the state of the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in China, 2019.2020.
[3] 中華人民共和國生態環境部. 2020年中國生態環境狀況公報. 2021. Ministry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Report on the state of the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in China, 2020.2021.
[4] 曹夏天.環境責任保險制度研究[D]. 南昌:南昌大學, 2018. Cao X T. Study on environmental liability insurance system [D]. Nanchang: Nanchang University, 2018.
[5] Feng Y, Mol A P J, Lu Y, et al.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Liability Insurance in China: In Need of Strong Government Backing [J]. Ambio, 2014,43(5):687-702.
[6] He G, Lu Y, Mol A P J, et al. Changes and challenges: China's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in transition [J]. Environmental Development, 2012,3:25-38.
[7] 李鳳英,畢 軍,曲常勝,等.中國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制度框架分析[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2009,19(4):167-170. Li F Y, Bi J, Qu C S, et al. Framework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liability insurance system in China [J]. China Population,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09,19(4):167-170.
[8] 劉苗苗,朱天元,李若琦,等.我國推進環境污染責任保險的系統性風險及對策[J]. 中國環境管理, 2020,12(2):6. Liu M M, Zhu T Y, Li R Q, et al. Environmental impairment liability insurance in China: development, risks and countermeasures [J]. Chines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20,12(2):6.
[9] 李文玉,郭 權,徐 明.環境污染責任保險的美國經驗及中國實踐[J]. 中國環境管理, 2020,12(2):6. Li W Y, Guo Q, Xu M.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liability insurance: American experiences and Chinese practice [J]. Chines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20,12(2):6.
[10] 彭中遙,鄧嘉詠.論環境污染強制責任險的出路[J]. 中南林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7,11(2):27-32.Peng Z Y, Deng J Y. The improvement insurance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of compulsory liability [J]. Journ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f Forestry and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s), 2017,11(2):27-32.
[11] 郭 權,徐 明,董 穎,等.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基于市場的環境風險管理工具[J]. 環境保護, 2016,44(18):56-59. Guo Q, Xu M, Dong Y, et al.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liability insurance: an environmental risk management tool based on the market [J].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16,44(18):56-59.
[12] Feng Y, Mol A P J, Lu Y, et al.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liability insurance in China: Compulsory or voluntary? [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14,70(1):211-219.
[13] Chen Q, Ning B, Pan Y, et al. Green finance and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of green insurance in China [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21,(1):1-26.
[14] 劉鴻志,王志新,侯 紅,等.將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引入環境風險管理——環境風險管理的無錫經驗[J]. 環境保護, 2017,45(10):28-31.Liu H Z, Wang Z X, Hou H, et al. Introducing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liability insurance into environmental risk management: environmental risk management of Wuxi city [J].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17,45(10):28-31.
[15] Duus-Otterstrom G, Jagers S C. Why (most) climate insurance schemes are a bad idea [J]. Environmental Politics, 2011,20(3): 322-339.
[16] Freeman P K, Kunreuther H. Managing environmental risk through insurance [M]. Springer Netherlands, 1997.
[17] Zhou Y, Bi J. Economic Policies of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in the Taihu Lake Basin, China: Technical and Institutional Aspects from Chinese and German Perspective [M]. 2019.
[18] Zeng S Z, Meng X H, Zeng R C, et al. How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driving forces affect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SMEs: a study in the Northern China district [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11,19(13):1426-1437.
[19] Jiao J, Wang C, Yang R. Exploring the driving orientations and driving mechanisms of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The case study of the China Gezhouba [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20,260:121016.
[20] Liao Z, Xu C K, Cheng H, et al. What drives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A content analysis of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 [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18,198(PT.1-1652):1567-1573.
[21] Beck T, Levine R, Levkov A. Big Bad Banks? The Winners and Losers from Bank Dereg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10,65(5):1637-1667.
[22] 郭 權,徐 明,董 穎,等.環境污染責任保險的發展及對策研究[J]. 中國環境管理, 2016,(6):7. Guo Q, Xu M, Dong Y, et al.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and countermeasures of environmental liability insurance [J]. Chines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16,(6):7.
[23] 李 萱,沈曉悅,黃炳昭,等.我國環境污染責任保險試點"雙軌制"困境與解決方案[J]. 環境與可持續發展, 2015,40(1):5.Li X, Shen X Y, Huang B Z, et al. Environmental impairment liability insurance pilot program in China: current status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J].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5,40(1):5.
[24] Ren G, Shang J. The conditions of China's environmental liability insurance system [J].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2010,180(2):1-4.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liability insurance policy: A case study in Jiangsu Province.
WU Wen-jing1,2, LIU Miao-miao1*, MA Zong-wei1, FANG Wen1, YANG Jian-xun1, BI Jun1
(1.State Key Laboratory of Pollution Control and Resource Rouse, School of the Environment,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2.Shenzhen Academy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Shenzhen 518000, China)., 2023,43(11):6204~6211
Based on the insurance information and environmental violation data of 2281 enterprises in Jiangsu Province, this study constructed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 model to empirically examine the effectiveness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liability insurance policies in improving enterprises'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nd explores the potential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mechanisms. The result shows that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liability insurance effectively improved enterprises' environmental compliance. Still, the policy effect depended on the environmental risk level of enterprises and the cities where they were located: (1) Considering the higher cost of improving compliance performance relative to reduced insurance premiums after risk reduction, enterprises with high environmental risk levels demonstrate a weaker response to the policy; (2) positive effects of the policy tend to be enhanced in cities with high-quality risk assessment and site investigation services. This study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effectiveness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liability insurance policie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liability insurance;difference in difference;environmental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effectiveness evaluation;corporate environmental compliance
X32
A
1000-6923(2023)11-6204-08
吳文菁(1996-),女,福建福安人,南京大學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環境政策分析方面的研究.wuwj@smail.nju.edu.cn.
吳文菁,劉苗苗,馬宗偉,等.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政策有效性評估研究——以江蘇省為例 [J]. 中國環境科學, 2023,43(11):6204-6211.
Wu W J, Liu M M, Ma Z W, et al.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liability insurance policy: a case study in Jiangsu Province [J]. 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23,43(11):6204-6211.
2023-03-13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項目(71761147002,72222012, 72174084)
* 責任作者, 副教授, liumm@nj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