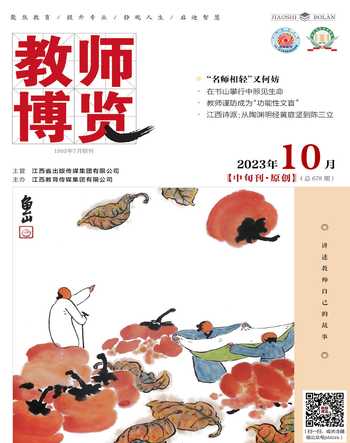好教師要有筆感
孫建鋒
這里的筆感,就是用筆捕獲課堂教學中值得“反思”的敏銳之感。
好教師為什么要有筆感?
若站在林徽因的視角識人,便會發現“只有頻率相同的人,才能看清彼此內心深處不為人知的優雅,懂得你的言外之意,理解你的山河萬里,尊重你的與眾不同”。這種頻率相同,說白了,不就是在彼此對教育教學向好的追求上由對話而創生的志趣與志向?
當然,好教師的標準不是單一的,但即便標準再多,筆感都是好教師應當具備的。
日前,我去聽《一幅名揚中外的畫》的公開教學。課后,我請聽課的老師在評課前先曬曬筆感,然后再“傾心置腹”“盡吐衷腸”。評課的場景與大多數人都經歷過的滿場皆是“大拇指”的好評毫無二致。這種走過場般的心照不宣在人人的意料之中,卻在有效教研的“研”“究”之外。
“一個好教師要珍視評課,珍視的表現之一就是要用筆評課,評出自己的筆感。”我推心置腹地與老師們對話,“筆感不只是用來粉飾教學的,更多的是用來反思、治愈教學的。”
“謝謝大家對我的肯定與鼓勵!”我的話音剛落,執教老師抓住契機展示其筆感,“上了《一幅名揚中外的畫》,我最大的教益就是《一課“三敗”,三敗“覺一”》。”
陌生的標題,一下子抓住了每個教師的心,也包括我。
“人固有自知之明,第六感告訴我,這節課我有三敗:一敗,敗在課上我展示畫卷,從左向右拉開;二敗,敗在課中我專注‘灌輸,學生質疑未有響應;三敗,敗在課題的名揚中外,未探‘揚外證據何在。”她直言不諱,既指出自己的失敗之處,接著又分析敗因:“三敗,敗因何在?一是憑生活習慣,我想當然地像拉橫幅一樣迅速從左向右拉開。其實此畫卷應該放在桌子上,從右向左徐徐展開……”
“這叫循序漸進,又叫開卷有益。”我旋即插話。
“謝謝,領教了!”她接語續陳,“二是專注投喂只是推卸責任的借口。其實學生當堂質疑的什么是‘傳神時,這個問題不在我的預設之中,我不敢接招,不敢與學生對話。”
“好坦誠!”有個老師脫口而出。
“謝謝你的懂得!”她越發坦誠,“三是名揚中外是觀點,課文內容只能證明這幅畫在我國名揚古今,但缺少名揚國外的文本材料佐證。這一方面,我本應該抓住課文證據鏈的缺少,因勢利導把學生引向課外閱讀、上網探究……”
“你都一課‘三敗了,怎么還號稱是最大的教益?”一位戴眼鏡的老師對執教者的“筆感”很有“語感”。
“‘我沒有失敗過,要么贏得勝利,要么學到東西。曼德拉的話不光寬慰我,還開示我。”她回答說,“我贏得了‘覺一。‘覺是指我知道了我知道的,也知道了我不知道的;‘一是指全息的存在。‘覺一,就是體悟到了源頭與本體。在教學上,這個‘覺一意味著‘我在走出故我,我在走向新我。教學自覺的過程是一種全息存在,存在的本身充滿著一系列的追問:我該以怎樣的序列與速度打開我,我該以怎樣的質疑響應我的自我質疑,我該以怎樣的勇氣與藝術進行獨立表達觀點、充分提供證據、合理得出結論的理性思維來思考我的教學……”
“好教師有了筆感,我們才能享受《一課“三敗”,三敗“覺一”》的福祉。它對‘失敗教學的療愈在于,失敗并不代表你一無所獲,它只表明你吸取了一次教訓。”我與執教者和評課者,不,和每一位教師一道分享著名投資大師約翰·鄧普頓的金句:“聰明人從自己的錯誤和失敗中獲得經驗,而更聰明的人則從他人的錯誤和失敗中獲得經驗。”
(作者單位:廣東省深圳市福田區教育科學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