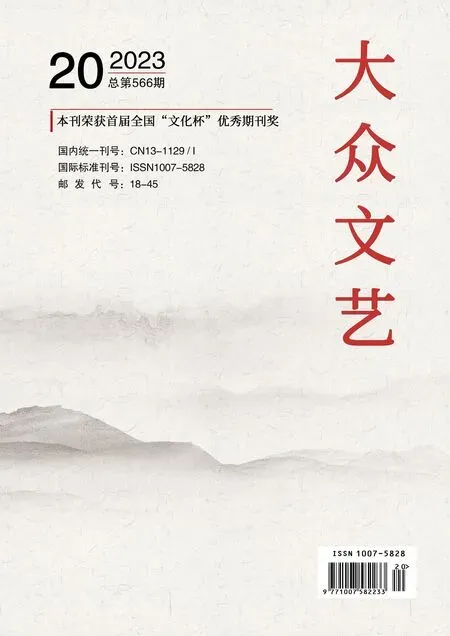民俗文化在舞蹈中的傳承路徑分析*
——以徽州汪滿田村“舞魚燈”為例
王笑寒
(黃山學院,安徽黃山 245000)
民俗文化作為民族歷史的延續與傳承,是民族幾千年來形成的一系列傳統習俗、宗教信仰、文化禮儀等的集合體,利用獨特的文化符號記錄民族的起源、發展與演變。每一個民族有特有的民俗文化,體現出的文化特征反映了民族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審美觀點等,是民族文化身份和認同的象征。當代舞蹈教育作為一種美育活動,是基于主體感性經驗雙向轉換的審美教育活動,在身體審美的表達上滲透著歷史與文化的意義和超越生命的情感體驗,因此在這一角度下,舞蹈關于身體美的藝術涵義決定了其舞蹈教育是關于身體的審美教育,對于當下的舞蹈教育而言,應當充分發揮其美育價值,與美育教育核心接軌,在實現藝術教育、美育教育的共同基礎上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充分發揮其主體性意識。民俗文化在舞蹈教育中的滲透即是舞蹈教育與審美教育的結合,在審美的層次發揮舞蹈教育的整體性價值,進而實現“身心兼備”的開發,在“以舞釋美”“以舞育美”的舞蹈教育教學活動中,讓舞蹈教育回歸身體本位,真正達到個體由自然的身體向社會的身體、文化的身體的超越發展。
一、民俗文化釋義
民俗文化是生活在某一地區的民眾為適應自然環境、寄托情感需求、維持自身生存發展而發現創造、延續傳承并長期留存在現實生活中的一種文化現象。這一文化現象是極具代表性的地域文化的象征,體現著某一民族信仰、人文價值以及社會形態,呈現出集體性和認同性;從更深層次的意義而言,民俗文化具有獨特的凝聚性,是民族這一區域空間內的價值觀念的世代相傳,是民族內成員的情感共鳴與文化自覺,對于整個民族的傳統禮俗形成與延續具有重要價值。
民俗文化在長期歷史發展進程中,呈現出其自身的發展,對于民俗這類詞語,是約定俗成的長期發展中族群形成的文化形態,最早在我國先秦時期就已出現,但是,對于它的釋義并不確定,對于這一歷史存在的專業名詞在當下作為科學用于出現,作為科學用詞,在當下語境下,并不是任意的文化現象,也非簡單意義的文化現象,既不屬于個人,也不屬于短期當下出現的,它是一種集體性行為,在一定時間內的族群的人的行動或語言表現,因此也將集體性、傳承性作為其重要特征,在必要時逐漸形成一種模式。在形態發展尚不完善的社會中,民俗在某種意義上被認定為“約定俗成”的文化,這種身份被強化,對于形態比較發達的社會層次中,民俗被認定是文化總體中的組成部分,即包括婚喪嫁娶、歲時節序的禮儀,又在政治、法律、經濟等部分中被出現,民俗文化依附于這些系統而存在;[1]民俗文化在發展的過程中具有層級區分,尤其是上述而言形態發展較為完善的社會中,文化概括而言具有上層與下層的區別,并且各層次文化都打上了各自的烙印,具有這一文化背景層次人群的特征,但是上層社會中的某些風俗、民俗,與下層社會流行的民俗具有相同性,兩者本源相同,在共同的社會中共同發展,民俗更是歸屬于整個民族的,是民族長期生存中重要的本源文化,在整個民族的傳統文化中占有重要的比重,具有重要的意義。
優秀的民俗文化是文化軟實力治理的重要基礎,對于其思維形態、行為方式產生深遠影響,黨的是十八大以來,“大力弘揚中華優秀民俗文化,構建中華文化傳承體系”已成為重大戰略決策,對于民俗文化的弘揚、自信以及傳承,是文化工程的推進,具有重大的現實與歷史意義。民俗文化的根基在鄉村,當下傳承民俗文化,對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賡續中華文脈發揮價值,民俗文化正式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重要元素的典型代表,民俗文化正是承載著厚重的文化底蘊和歷史積淀,是一個民族的靈魂和根基。文化是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發揮著規范社會成員行為和心理的作用,民俗文化對于規范集體成員行為不僅體現在意識形態方面,在物質層面也起到一定作用,對于社會成員的規范作用,從另一種角度而言,即是凝聚力,在民俗文化中,由于廣泛存在和潛在作用,在團結民族成員凝聚性作用顯得特別重要,這種凝聚并不同法律、法規,利用強制性的手段對于社會成員起到一定的約束作用,民俗文化在于利用無形的手段,將社會成員不約而同地凝聚在一起,社會成員在無形的、近乎神秘的民俗文化中被凝聚,將現在的族群人與逝去的前輩、祖輩連接在一起,甚至將世界各地的族群中聯結、團結在一起。因此,傳承與保護顯得尤為重要,在民俗文化的傳承中,文化本質價值被重新審視,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系統整合,挖掘其在新時代語境下的多元價值。新的歷史背景下,民俗文化發揮其社會價值、藝術價值等多元價值。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民俗文化在傳承與發展中面臨著挑戰,城市化的快速發展帶來了生活方式的巨大改變,傳統的民俗文化逐漸被遺忘,主要呈現出以下現狀:第一,民俗文化被同化,隨著全球化的進程以及信息的快速發展,逐步打開民族之間的信息閉塞,尤其是旅游業的大力開發,傳統的民俗文化受到外來文化的沖擊,其穩定性逐漸較小,民俗文化內容與形式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甚至一些民俗文化逐漸消失;第二,民俗文化逐漸被商業化取代,隨著當前世界經濟增長的趨勢,我國經濟也從改革開放后的快速增長放緩到中高速增長,不僅如此,經濟結構、產業結構以及科技創新面臨著優化與改進,文化產業逐步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增長點,相關政策推動下,我國文化產業市場快速發展,民俗文化成為巨大商機,被取代為旅游資源發揮著其經濟效益,變為具有價值屬性的商品,這一文化屬性現象轉化為商品形式,丟失了民俗性的本源意義,這一方式阻礙了民俗文化的發展,不僅于此,作為社會風俗、思想觀念以及行為方式的集合,隨著傳播技術的發展,互聯網廣泛作用于其中,構建了互聯網背景下的民俗文化經濟新生態,這一時代的沖擊對于開發民俗文化的經濟價值具有推動作用,但是反之民俗文化資源產業鏈的快速發展,民俗文化的特質被弱化,轉化為產業之后變為新時代元素與商業元素的博弈;第三,民俗文化傳承的斷層出現,民俗文化發展需要依靠“技藝”人,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隨著保護經費窘迫、挖掘內涵不力、人才匱乏等問題,年輕人學習與參與逐漸減少,“接班人”出現缺失,[2]不僅如此,當代社會的急劇變革過程中,文化發展的非延續性日益凸顯,原住民大規模的搬遷,導致民俗文化賴以生存的原始土壤被破壞,民俗文化逐漸消失,傳承出現斷層趨向。
二、徽州“舞魚燈”民俗文化傳承路徑展望
徽州汪滿田被列為第五批傳統村落,是歷史悠久的古村落之一。其中在這一地區保留了六百年的歷史民俗“舞魚燈”,是非物質文化遺產,其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世界文化多樣性的體現,是具有重要價值的文化資源,也是歷史的真實見證,是各族人民世代相承、與群眾生活密切相關的各種傳統文化表演形式和文化空間,是中華民族智慧與文明的結晶,“舞魚燈”是徽州人民長期生產生活實踐中創造的豐富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是連結民族情感的紐帶和維系國家統一的基礎。在每年農歷正月十三至十六,以魚燈游村,當地人又稱“舞魚燈”為“嬉魚”,這一傳統又古老的藝術形式,寓意年年有余、風調雨順。汪滿田村“舞魚燈”始于清光緒初年,相傳,朱元璋平定寧越后,派徐達率領部隊北上征服遼,之后派胡大海驅逐倭寇,保護居民平安,在戰局不利之后,胡大海借助風浪游魚的助力化險為夷,得勝上岸,驚喜異常,但是不解潮水由漲變退的原因,詢問當地的老漁民,老漁民說這次潮水突然漲落,是由于鰲魚翻浪幫助,保船只平安出入,這次也是鰲魚幫助大明朝,胡大海將鰲魚助力之事上報朝廷,洪武帝聞之大喜,賜鰲魚龍頭魚身,封安海定神,從洪武二年開始,逢年過節,遇重大喜慶慶典,龍燈在前,龍頭魚身的魚燈在第二,“舞魚燈”因此出自歷史傳說典故。整個魚燈竹扎紙糊,制作流程有四步:第一步是削竹開度,把竹削好,按所需要長度裁剪好;第二步是扎骨架,魚骨架分別有頭架、身架、尾架等,用不同大小的鱷魚安全連扎成魚的軀干骨架,交接處用韌性較強的砂紙糊;第三步是木版印彩紙,用木版刻制魚頭、魚尾、魚身等圖案,涂上牛皮膠,蓋上紅紙粘印后在金粉中拍打,形成金光閃閃的鯉魚身體圖案;第四步是上漿貼紙,在骨架上涂上牛皮膠吧魚鱗紙貼上,魚脊上開一個小口用來點火和放置蠟燭。整體的魚鱗線條以彩繪形式展現,大的長度約七米,高度約三米,共三節,內點燭一百余支,魚嘴有噴火裝置,每個燈需要二十名左右的演員,邊走邊演,小的魚燈僅有一米左右,點三支蠟燭,可隨著手部動作舞動。整個“舞魚燈”具有完整的程式,在入夜時分,嬉魚之前,先點燃火把與燈引,大小魚燈隨著信號逐漸從各自的祠堂魚貫而出,跟隨燈引穿越大街小巷,魚龍舞在整個村莊演繹,游走村口、拜神廟、返回祠堂,汪滿田村的“舞魚燈”是其傳統的文化節日,具有祈福、敬神的功能。夜幕時分,魚燈夜游,敬天地、祭先祖、祈福澤,美好祝愿盡顯其中。
當前,“舞魚燈”的形式隨著傳承與發展逐漸產生變化,但是其最大的特點是不脫離民族特殊的生活生產方式,是徽州人個性、民族審美習慣的“活”的體現,徽州“舞魚燈”在傳承發展的過程中始終將人作為重要元素,保護其傳承過程。每年燈會前,村里六家魚會首先會選出一家擔任“魚頭”,負責組織到每戶每家進行資金籌集、采購材料、安排扎制等各項事宜,且早年的魚燈會一般是有威望的成年人擔任“魚頭”,而現今的“魚頭”則以年輕人為主,跨越各個年齡階層,甚至初中生也可以擔任“魚頭”,據老一輩口述,魚頭表演者的變化不僅可以鍛煉年輕人的主事能力,更重要的是讓魚燈成為人人皆可舞的活動樂事。“魚燈舞”成為徽州人民精神圖騰,亮起的魚燈、舞動的身姿,閃爍著中華傳統民俗的血脈傳承和歷久彌新之文明,詮釋著中華民族代代相傳的共同信仰。當今這一國家非遺項目逐漸被創新,高校、政府、新媒體等都將其各自傳承與發展,“舞魚燈”日益彰顯著民俗文化經久不衰的生命力。
徽州“舞魚燈“這一項給物質文化遺產在發展過程中不斷創新,在徽州古城非物質文化遺產夜市,舞魚燈進行了經濟轉化,“大魚徽州”舞魚燈首演,對魚燈表演形式進行創意編創,魚燈表演形式更具觀賞性,用潮流的方式向傳統致敬,并且以此衍生出魚服秀,延續魚燈制作流程融入創意元素,采用徽州剪紙藝術創作魚服,這一傳統的民俗形式經過匠心傳承,衍生出互聯網產品,結合數字平臺,以徽州“舞魚燈“為原型開發創作立體三維形象,將”舞魚燈“形成文化產品供給,每一位參與者都將感受這一非物質民俗文化遺產技藝背后的細膩與工匠精神,“舞魚燈”在創新發展過程中立足非遺傳承、文旅融合,厚積薄發,深厚的文化內涵被充分挖掘,其傳統文化的知名度、美譽度和影響力被拓展。
徽州“舞魚燈”舞蹈形式與民俗文化融合的展望主要有如下三個方面:第一,內部整合民俗文化資源。相關學者對徽州“舞魚燈”文化有一定研究,但是仍然需要進一步探索其文化淵源、歷史流變以及地緣特征等,從多方面探索新時代徽州“舞魚燈”文化根基,為現代文化新融合奠定基礎,在縱向與橫向整體的基礎上進行分析,進而構建徽州文化共同體,真正將這一文化形式與徽州地區傳統文化淵源相結合,把握民俗文化的基本性質及形態,相關政府、研究機構加大對這一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挖掘以及再開發,注重民間老藝人的輻射作用,不斷加大這一民俗文化形式的影響力,在年輕人中進行普及,延續其人人而舞的文化共同體屬性。第二,外部技術開發創新民俗資源。在內部挖掘其本質的基礎上,也要建立對已有傳統的民俗文化資源地再整理與再傳播,隨著信息時代的發展,大數據、云計算成為主宰生活的方式之一,因此,徽州汪滿田“舞魚燈“應充分借助大數據對其進行全面整理,建立相應的數據庫,便于流傳和傳承,同時在此基礎上,精準傳播,大數據時代互聯網使用者心理需求、行為指向都將被留痕,對于民俗文化的精準分析,可以實現其精準、有效的椽筆,進而形成持續性強、黏度性強的效果,不同地區、年齡段、性別的受眾有不同的需求,建立相應的民俗文化網站,帶動民俗文創產品的研發,滿足精準受眾的民俗文化需求,并且創造相應的平臺,相關愛好者可以進行學習與培訓,激發受眾引起共鳴,也進一步改善民俗文化的斷層問題,突破技藝斷層困境。第三,內外部整合,形成整體性的區域協作,民俗文化在不同的動機下,會產生新的傳承途徑,民俗文化在自身的發展規律中,并沒有按照自身發展規律自然延續,而是形成有意識的、主動的跨越性傳承,隨著社會人群主體的變遷進行變化,因此,在不同的區域建立整體化的區域合作,對傳承人與傳承文化起到一定的保護,實現其主體多元化,將新渠道傳承文化的途徑與原有渠道相匹配,對自然傳承起到一定的積極干預,避免內在本質脫離本體與地域特色,成為新產物,重點始終應把握在民俗文化本源性的基礎上融合現代意義。
三、徽州“舞魚燈”舞蹈傳承中的價值彰顯
徽州“舞魚燈”作為傳統的民俗文化與獨特的舞蹈形式在發展中呈現出重要價值,徽州汪滿田“舞魚燈”民俗文化在歷史發展中,在中華文明的統一性中孕育著其文化的獨特性,實現其創新發展。其價值主要體現在文化價值與藝術價值上。
從文化角度審視,民俗文化在發展過程中實現了文化價值,遺產化是其文化價值的延伸,遺產化指政府將通過行政手段使得具有歷史、文化、藝術、科學性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予以保護的系統性實踐。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出現,對于民俗文化進行了承認與保護,完成了現代民族國家的文化轉型,其文化價值對于中華文化的多樣性,助力構成全民文化認同的最大公約數做出貢獻,對于民族而言,“舞魚燈”蘊藏的文化價值是增強促進中華民族認同的重要文化符號,對于維系整個民族的文化共識具有奠基作用,從一定意義上而言,文化價值會隨著全球化進程,超越地域、國家的界限,實現從地緣、族群到全球、國家的意義轉換。民俗文化發揮的文化價值始終是社會發展與進步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源。
從主體藝術角度審視,民俗文化具有一定的藝術價值,民俗的藝術化指結合聲音、文字、視覺等手段,提煉、加工、再創造的過程,藝術化的延伸是審美價值,民俗文化的藝術價值除具有觀賞性的同時,又具有實用性。民俗藝術的價值最重要在于對于民族精神的核心表達以及多元形式,各種藝術形式都有自身的特點,徽州“舞魚燈”作為集體項目,民族精神的凝聚力充分彰顯,其形式多樣,為徽州民俗藝術的繼承與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典范,藝術價值充分反映藝術的普遍規律,其藝術價值對于其內在本質的挖掘具有重要意義,在其傳承的過程中,具有更長遠的挖掘潛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