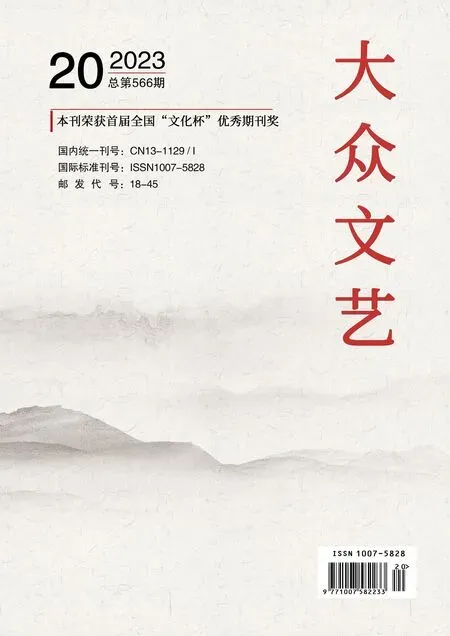徐浩峰電影《師父》中的功利主義迷思
強立橫
(西安郵電大學數字藝術學院,陜西西安 710100)
一、武林之“局”
《師父》是徐皓峰導演武林三部曲的高峰,藝術和商業元素較完美結合,觀影愉悅的同時也觸發思索。故事總體來說是一個“螳螂捕蟬,黃雀在后”的框架。
民國期間,師父陳識為了自己和恩師,也為了重振家業,從廣東北上,要在天津武林開立詠春一派,“以拳法揚名,成敗都快。先報師恩,再整家業”。按天津規矩,開館立足需要徒弟替師父比武正名。陳識一方面“娶師娘”(金錢交易)、住貧民窟掩人耳目,以防止踢館后仇家追殺——將踢館責任推給徒弟,而自己“養女人、有活做、沒野心”;一方面收取、利用徒弟耿良辰為其踢館。按規矩,如果前八家比武成功,第九家是天津武術泰斗鄭山傲。鄭山傲要求陳識教自己詠春刀法,確保自己獲勝,這樣即保住了天津武術的顏面,也可讓詠春開館,但徒弟,要被逐出天津。師父和天津武林達成共謀;開館規矩是武林給陳識下的局,要入行、先入局。陳識接受——“我是一個門派的未來,我要按照規矩來”——也就是把局設給了徒弟耿良辰。一方面,陳識賞識耿良辰的武學潛力,所以拒絕了鄭山傲選派的徒弟;另一方面,耿良辰初遇陳識的理由是貪圖“師娘”的美貌(食色,性也),這讓陳識找到了陷害的合理化理由:“好在是個小人,毀了,不可惜。”
這樣的兩層盤算不料掉入了更大的算計之中:年邁的天津泰斗鄭山傲被軍人徒弟林希文暗算,在攝影機面前敗給了突襲的徒弟,天津武林顏面掃地,也意味著軍界開始接管武林。這樣的局面使得天津武林的“好日子到頭了”,也使得鄭山傲無法出面進行第九場對決,師父的算盤打空了。更糟的是,徒弟耿良辰有被仇家(以鄒館長為首)報仇性命堪憂之危險。這時候師父陳識想挽救已鞭長莫及,耿良辰被鄒館長和軍界聯手暗算——腹里插刀重傷,終因性格耿直為尊嚴狂奔不治身亡……一個正直的武學奇才就這樣在眾人的算計之中成為犧牲品。面對徒弟的血跡,師父終于懺悔,“我不是他師父,我是個算賬的。”隨后在鄒館長的設局算計中,陳識殺掉了林希文替天津武林報了仇(鄒館長表面和林希文聯手,但也想擺脫軍界重回武林的舊時光),但自己也落得和徒弟一樣的替罪羊下場。最后高潮部分,陳識憑借自己的計謀和武力,單挑天津十九家武館,拼殺逃離了天津。“老規矩,逃了就等于死了。事情完了”,“他有女人,會遵守契約。詠春拳絕了。”
二、多維呈現:局中“功利主義”的幽靈
電影中的武林規矩和層層算計令人印象深刻,這些算計與“功利主義”的主題頗為契合。功利主義由英國哲學家邊沁建立,主張用快樂和痛苦衡量人的行為,衡量標準是幸福(快樂)的最大化:每個個體或每個立法者考慮的都是避苦和趨樂。功利原則或者幸福最大化原則成了道德的基礎。幸福的最大化涉及苦樂計算:邊沁建議我們在行動之前,應當計算一下這些苦樂份額的值,這些值取決于快樂的強烈性、持久性、可靠性以及它的臨近性。只要計算結果快樂大于痛苦,快樂有結余,這些結余就會給行為帶來好的趨向。邊沁感興趣的主要是快樂的量的方面:如果兩個行為能夠產生同樣數量的快樂,那它們就是同等程度的善。我們是否真的在做這樣的計算?邊沁的回答是:人們確實在計算,有些計算不那么精確,而有些較為精確:但一切人都在計算(和比較)①[1]。
因此,師父陳識最后會感慨:“我不是他師父,我是個算賬的。”這里有四層計算:其一:師父陳識算計徒弟耿良辰。因為犧牲一個徒弟可以成就一個門派,從詠春門派的角度看,值得。其二:天津武林的規矩也在算計新入行門派。打得過八家武館才能立足,而贏八家的徒弟要被逐出天津。這樣的入行標準(或者行業壁壘)保證了既有武館的利益,也使得新入行者(實力強者)不得不對規矩低頭,成為被收編的一員,可以繼續維持武行“只教招數套路不教真功夫”的“好日子”,從武行的角度看,值得。其三:軍閥看到武館的油水,想要瓜分侵占。林希文從軍人的利益出發,一個欺師滅祖的罪名連帶兩套房產,換得對武行的統治權,值得。最后,鄒館長借刀殺人。除掉了武行的災星林希文,替老泰斗鄭山傲報了仇,鄒館長自己也榮升為天津武林新掌門,犧牲一個外來者陳識,值得。這四層算計看來,功利主義原則被各層面熟練使用,但這樣的“功利世界”,合適嗎?
對功利主義的一種批評來自道德角度:在處理善和快樂問題時,如果只一味強調量的方面,這就不可避免地成為道德相對主義者。為了最多數人的幸福最大化,是否可以放棄或犧牲少數人的幸福呢?邊沁的推理會給出肯定的回答。這就產生了嚴重的不公平,也就是“替罪羊”:功利主義者可以為了大多數人的幸福而允許社會不公平,而少數人的利益被舍棄,成了替罪羊——受難的無辜者。[2]有名的“電車困境”就是這個問題的示例:為了救五個人而害死一個人呢,正當嗎?
這一“替罪羊”批評也符合電影的安排。徒弟耿良辰成了師父開館的替罪羊,師父陳識成了鄒館長借刀殺人的替罪羊,鄭山傲成了軍人統治武林的替罪羊……這樣的生活很難讓人心生向往,因為人人在算計,也預示著人人被算計。自己很有可能掉入下一張網之中,成為“更大利益”犧牲的替罪羊。似乎,功利主義會掉入自己對自己設下的迷局中,難以自拔。
三、人性的矛盾:師父、徒弟、妻子之間的功利主義迷思
《師父》中有兩位師父、兩位徒弟、兩位妻子之間兩兩矛盾,存在著或明或暗的算計,又同時存在著中國的傳統倫理與人性普遍的光輝。
兩位師父將算計擺在了明面上,但又有著“老規矩”優雅的契約精神:鄭山傲設局,陳識北上以天津規矩教徒弟踢館,然后廢徒弟開館入局,報師恩,振家業。《師父》中將傳統武俠電影中踢館的華麗“外衣”脫掉,暴露的是其赤裸裸的手段與工具屬性,而這手段中的“規矩”則充滿了算計與功利性:驅逐徒弟,“老人”留了面子,“新人”扎了根,劃算買賣,甚至為了給足陳識照顧,“徒弟”由鄭山傲親自選,選出來的人被放逐,他認,這在鄭山傲心中是契約精神,是給本質上的功利披上了“優雅”的外衣,但陳識卻有自己的私心。在發現鄭老選的人各方面水平都不行時,認為鄭老不想讓其在天津立足,為了對抗這種算計,他親自選了耿良辰,一個在他心中是個武學天才的“小人”,一個毀了不可惜的人。所以在鄭老算計他的同時,他也在算計著耿良辰。從電影的結尾來看,雙方的算計都沒有達到利益最大化的目標。一方面是因為道德相對主義——鄭山傲為了維護天津武林,“犧牲”陳識;陳識為了詠春的未來,“犧牲”耿良辰——的弊端:冤冤相報;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兩位師父復雜矛盾的人性。耿良辰的天資與剛直的骨氣激發了陳識深處的惻隱之心,在徒弟被天津武林和軍界聯合暗算慘死后,他決心與整個天津武林對立,最終因寡不敵眾而落逃。鄭山傲被軍界的徒弟林希文算計,本在比武表演過程中能反殺,戳瞎徒弟的雙眼,甚至殺死他,但最后關頭鄭老念及情誼卻故意放水“力竭”而倒,天津武林因鄭老的“師徒情”而被軍界吞并。在這里,功利主義追求幸福最大化的量化手段失靈了,因為矛盾的人性與功利主義本身的弱點,讓其蒙上了不確定真理的迷霧。
兩個徒兒,耿良辰與林希文在電影中的每一步行動亦帶有十分明確的目的性。在電影中,林希文作為鄭山傲的徒弟,“武功不好,好處多多”(鄭山傲語)。但恰恰是這個“好處多多”的徒弟用陰謀奸計——買通師父身邊人與武行,共同哄騙師父拍攝比武紀錄片,借“跟隨師父走進歷史”之名,用小人手段打敗師父,外加“施舍”兩處房產,搶走師父一生名譽,并將師父打出歷史。這是蓄謀已久的算計,處處透著“功利主義”原則。然而林武行出身,竟然“忘記”開館儀式里“上門板”的風險,抑或是他已經狂妄到自認一人可以壓服整個天津武行。所以從此可以看出,林副官的敏銳性、斗爭意識與政治智商都是不合格的,他只是依附于軍閥老總的一條得勢之犬,也是軍閥與武行之間利益糾葛的犧牲品,這是純粹私利下林的悲慘結局,可以看成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天道”對“功利主義”的矯正。耿良辰雖然為了看漂亮師娘一眼而拜師陳識,“算計”師父的同時也入了師父的局,但在學拳的過程中耿逐漸拋棄了邪心,死前自白中也呈現了陳識所說的“大才”之相:成長速度異于常人、對愛很忠貞、不畏敵手、熱愛家鄉、尊師重道。但他的“純粹”與“忠誠”卻透露著愚、耿直與莽撞:死前并未察覺軍界對他的利用,面對算計只會“伸”不懂“屈”。這也表示,動機若是鉆營,無論中途是否“浪子回頭”,最終的下場是悲劇,被歷史所淘汰。
鄒館長與趙國卉均是近代中國女子的典型代表。前者是豪門貴夫人,后者是“丫鬟”;但是后者對生活的熱愛要高于前者。兩種女性的活法不同,鄒館長留著男子短發,穿著中性西裝,走路身后跟著一眾隨從,講話霸氣強勢,是天津武行實際的操縱者。她一步步爬上天津武行權力的頂峰,但其手段卻極致的功利與自私——一切為了量化的“幸福”,也就是利益。所以對她來說“好日子過一天是一天”。趙國卉堅守著逛街、螃蟹、丈夫、故鄉還有會來找她的孩子,雖然她與陳識開始于一場利益交換——為陳識開館“打掩護”(她并未察覺),自己得到一筆養老錢。但哪怕陳識最終暴露了自己娶她的目的,但她還是沒有始亂終棄,這是中國傳統女性的特點。前者未必比后者過得好,甚至對她心生羨慕,同樣是“女人需為自己而活”,不能只看表面上的凌厲,“師娘”趙國卉遠比鄒館長從容和灑脫。陳識對小耿的惻隱觸動了趙,所以她打破了自己“不會離開天津”的算計心,一路向南追尋因為徒弟復仇失敗而逃掉的陳識,而鄒館長看到趙國卉的舉動,也可能回想起當年赤誠的自己,所以她放棄了當下對陳識和趙國卉的追殺,“老規矩,逃了就是死了。”,兩位女性身上的矛盾讓“功利主義”陷入了迷思當中,這種不確定性透漏的確實人性中溫暖的光輝。
四、密爾的改良:“功利主義”在《師父》中的破局
為了避免道德相對主義,密爾試圖以質的方式處理功利主義:快樂在種類或性質上互不相同,而不只是有量的不同。“人類有比動物的欲望更高級的官能,而一旦意識到這些官能,人類就不會把任何事情當做幸福,除非其中包括了對那些高級官能的滿足。”感官欲望的價值低于智性快樂(想象力所帶來的快樂),而且,生命的道德價值被建立在我們更高官能的更高快樂的基礎上,這樣,道德性就與幸福成正比。和邊沁不同,密爾認為快樂的量或質是無法量度的:每當我們需要在兩個快樂之間選擇其一時,只有我們對兩種可能都有所經驗,我們才能明智地表達我們的偏好。其實人們并不是計算,而只是一種偏好。其次,功利主義未必就是利己主義,人們應當幫助別人獲得幸福,因為這樣我們也會使自己的幸福得到保證,同時我們也可以憑借社會機構來促進我們對他人的關心。[1]
密爾對功利主義的改良應該說更深刻一些:他將功利和道德劃一也避免了功利主義自身的尷尬;用偏好替代算計,似乎更符合實際。徒弟耿良辰的死并不是沒有意義,在看到留有徒弟血跡的書冊時,師父無言以對,他向茶湯女請求保留那本“血書”,向耿良辰昔日的租書攤深鞠一躬。師父陳識是復雜的,他人性中的道德和良善的一面被徒弟的死激發,勝過了內心算計的一面。徒弟的死激發了陳識正義的偏好,放下了功利,開始熱血的打拼。鄒館長認為人生就是“裝裝樣子”,而丟掉內容的樣子,對陳識來說,不值得裝。
結語
密爾認為:享受快樂的質的方面,正如邊沁強調的量的方面一樣,也是一種經驗事實:“能證明任何一個事物值得欲求的唯一證據,就是人們確實欲求它。每個人只要相信幸福是可以得到的,就會欲求他自己的幸福。”如何加強這種道德確信?密爾指出既有外部約束或動機,也有內部的。外部約束是別人在我損害他人時對我的“討伐”和在我追求幸福時對我的支持,但是密爾認為“內部約束”是最重要的動機,它會讓一個人在違背整體社會責任時產生內疚,這是一種責任感,最初通過教育形成,它“來源于同情心,來源于愛,而更來源于恐懼;來源于一切形式的宗教情感,來源于對童年時代和我們過去一切生活的回憶;來源于自尊,來源于得到他人尊重的愿望,偶爾甚至來源于自卑。”②陳識因為內疚、同情(徒弟),因為愛(愛她的女人趙國卉,也是她最早揭穿陳識的虛偽和自私),因為自尊,或者因為其他種種……終于放下了算計,亮出了刀子。徒弟的理想化,傳遞給了師父,為了求生,為了徒弟,同時也厭棄了之前那個只會算計的自己,最終走向反抗與逃亡之路,著實令人喟嘆。
注釋:
①撒穆爾?伊諾克?斯通普夫.西方哲學史[M].世界圖書出版社,2008:313-323.
②Jonathan Wolff.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Philosophy[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48-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