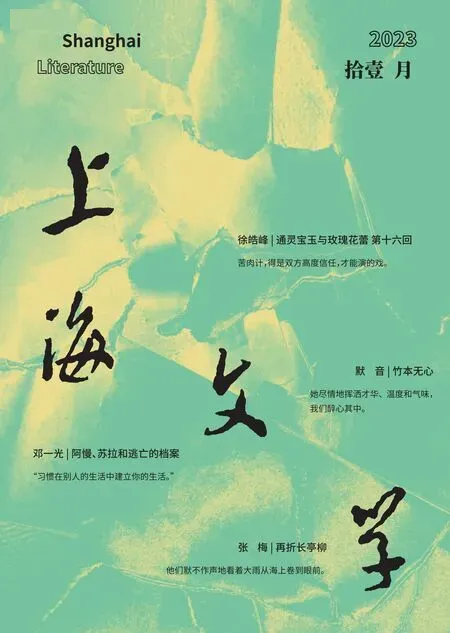他,與在島嶼寫作的他們
宇 秀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兩鄉。
——摘自王昌齡《送柴侍御》
一
溫哥華夏日的傍晚,陽光依然耀目,燦爛卻并不火辣,仿佛人過了盛年現出的溫厚與舒緩。沐浴在如此光芒之下的大自然好似午睡尚未醒來,有一種慵懶空茫的寂靜,等待叩響。
這是大溫哥華三角洲(Delta)一處幽靜的居民區。我的車子停在一棟花木蔥蘢的獨立屋前。說是門前,其實車子停靠的路邊與房屋還隔著長長的斜坡,房子與車庫大門及其后院邊門一字排開,像一幅橫軸展開在斜坡之上。那斜坡則是被我在另一篇文章里稱作“排比句”的長長石階。我曾多次獨自拾級而上叩響屋門,但這次,隨我下車的是一位身著紫絳紅夾克衫的銀發長者,我陪著他一道走上那些步步高升的“排比句”。
長者剛從著名的千古冰川之地洛基山脈(Rocky Mountain)返回溫哥華,去那里可是要有好體力,尤其三天行程,一般人是吃不消的。陪同他的女兒連喊吃力,老父親卻淡淡地說道還可以。想到他剛從大洋彼岸的上海飛來,時差都來不及倒,趕著出席會議和各種活動,然后又馬不停蹄地踏上冰川之旅。畢竟耄耋之年啊,我不由想去攙扶他一把。可他步態矯健,毫無耄老之蹣跚,我若去攙扶就顯得做作了。
到了“排比句”的最后兩三行,屋門拉開走出一位身著淺色休閑西裝、拎著黑色手提包的老人。我太熟悉他的手提包了,那是他每次出門的標配。紅衣長者加快了腳步,我的心跳也不由地加快。為能夠安排這位遠渡重洋的長者,與他一下飛機就念叨著最希望見上一面的人在遠離故土的異邦相聚,我多少難掩激動之情,這或許將是中國當代文學史上值得記載的一刻。
二
二○一七年七月十六日,加拿大華裔作家協會舉辦三十周年慶典與“第十屆華人文學國際研討會”,來自復旦大學的陸士清教授是三十位特邀嘉賓中最年長的,也是世界華文文學研究和教學領域的先行者,更是把臺灣文學引入大陸高等院校講壇的拓荒者和躬耕者。當時,我對大陸的海外華文文學研究知之甚少,在這次跨越太平洋來參會的學者中,陸教授是我唯一認識的一位,而且是從我移民之前的原居地上海來的,親切感油然而生。
在接機大廳,一眼看到走出海關的陸士清教授及其女陸雨。教授斜挎的背包全部移至身前,跟防備小偷割包包的游客一樣。我每每看到這樣挎包,就想起賣五香豆的。這與二○一四年在南昌首屆新移民文學研討會初次見到他大相徑庭。那次會議結束時,代表們在賓館大廳等候離會,每人座位旁都是行李,不少人東倒西歪地在打瞌睡。就在我對面座位上的一位鶴發老先生正興致勃勃地跟我的文友、洛杉磯華文作家葉周先生學玩微信,倆人頭碰頭竊竊私語,形似父子。我聽到葉周壓低的滬語,對方回應的則是蘇南口音普通話。老先生脖頸一條花色絲綢薄巾與鶴發相映,頗有點海派老克勒之風,令我忍不住偷偷抓拍了兩張。盡管當時知道老先生就是復旦大學陸士清教授,但并未借機去認識他,他也根本沒注意到有個偷拍者。而溫哥華機場看到“老克勒”變身“賣五香豆的”,距離感頓消,心里竟涌上“老家來人了”的溫暖。
在去往飯店午餐和餐后送陸氏父女前往住處約有四五十分鐘的車程中,我擔心老人坐了一夜飛機,舟車勞頓會吃不消,但我的擔心是多余的。老先生一路上興致很高,他那口慢條斯理卻又咬字鏗鏘的蘇南普通話,在離開主席臺話筒的零距離閑聊中,讓我恍若回到老家長輩跟前。閑談中,陸教授說希望我能聯系痖弦先生,安排他們見一面。他說,他這次來溫哥華就想,如果能拜訪一下痖弦先生那是最好不過了。原來七年前,二○一○年十月,在武漢召開的“世界華文文學國際研討會”上,痖弦致開幕詞的時候,陸教授就在主席臺上,那是他們的初識。會后,同游神農架,同行的錢虹教授還幫他們拍下一張珍貴的合影。同框里,一個身穿紫絳紅夾克衫,另一位著休閑西裝,兩人的盈盈笑容里蓄滿了陽光。痖弦戴著一頂淺色太陽帽,陸教授則一頭烏發。我看著七年后的陸教授,他的“頂上風景”已徹底由黑變白,心想,痖公(我平時總是這樣稱呼他)因健康原因,已不可能飛越太平洋,陸教授恐怕此后也難得再有機會飛來溫哥華,這對背負著兩岸歷史和當代文學史的同庚老人,這次在溫哥華如能相聚恐怕也是最后的機緣了。
陸教授原以為此番來溫哥華參加這么大的文學活動,自然能夠遇見痖弦。遺憾的是,痖弦并不出席這次活動。因為同一天,臺灣《創世紀》詩刊的前任和現任兩位主編張默和辛牧,率詩刊社一班人馬專程從臺北來溫哥華看望痖弦。對臺灣詩壇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張默、洛夫和痖弦乃《創世紀》“三駕馬車”,叱咤臺灣詩壇數十年。如今老伙計遠道而來,痖公這一天自然是分身無術,無暇他顧。也好,私下的會面如能達成,一定比場面上的相遇更能深入,也更有溫度,但我對安排這場會面并未有十分把握。痖公府上的電話常常是無人接聽狀態,痖公也不用手機微信什么的。平時跟痖公聯系,今天打不通,明天再打,有時他會突然打我手機,并無具體事務,卻總是一通上話就聊上個把鐘,甚至更長。事后我總是自責,這個馬拉松電話是不是累著了老人,興許放下聽筒,他正在揉搓發酸的胳膊呢,但每次通話又不忍主動喊停,聊天內容無一不是圍繞著文學話題。和痖公多年的交往,就那么隨意閑散,像兩朵沒有目的地的云。但這次不同,陸教授在溫哥華的時間有限,除去各種官方活動和陸雨預定的冰川行,他們的會面只有安排在父女倆離境前的一天了。可我還不知道能否及時與痖公取得聯系呢。
我沒把上述顧慮流露給陸教授。雖然當時我并不詳悉他在中國臺灣文學研究與傳播方面的卓著貢獻,但我直覺到一位海峽這邊的研究者和海峽那邊的創作者,兩位前輩文學家在兩岸之外的太平洋西岸的會面,將是中國當代文學史和兩岸文學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話,而促成此一歷史性重逢,義不容辭。盡管陸教授話語不緊不慢,但我聽得出蘊含著一份熱切。在以后幾天的接觸中,愈加感覺到他對臺灣作家、詩人的感情,有一份源于手足之情而又超越私人交際和個體情感的厚重的東西。
近年,臺灣拍攝了一套非常有格調的傳記文學紀錄片——《他們在島嶼寫作》,除了西西、也斯和劉以鬯三位,其余十位均為臺灣作家和詩人。其中斬獲第十七屆臺北電影節紀錄片大獎的《如歌的行板》是以痖弦為傳主的。二○一五年三月,我曾應痖公邀請出席了這部影片在溫哥華的首映式。也是那時,我知道了臺灣拍了這么一套被業內稱為文學傳記影片“標桿”的系列紀錄片,也認識了幾位我原先并無了解的臺灣作家。然而,“在島嶼寫作”的他們,早在一九八一年就被時任復旦大學中文系現代文學(含當代文學)教研室主任的陸士清老師一一請進了國內著名高等學府的文學課堂,如楊逵、賴和、於梨華、白先勇、楊牧、陳映真、余光中、洛夫、痖弦、周夢蝶等等。
在今年與陸教授微信筆談中,在閱讀有關他的各種資料和作品中,我逐漸清晰地看到了一個在歷史風云際會的時代洪流中,審時度勢,抉擇把握方向,而后專注堅定前行的中國學人和文學活動家陸士清,那個我之前感覺的厚重的東西,正是在血濃于水的人性基點上的民族情結,并由此賦予自身的使命感。行文至此,我腦海里突然跳出二○一八年十一月第三屆海外華文文學上海論壇主題,那行醒目地懸掛在開幕式橫幅上的大字:“詩情雅意與時代擔當”。記得在作家書店海外作家與上海讀者的見面會上,陸教授站在那條橫幅下對這句話做了富有激情的闡釋。而上海論壇就是陸教授倡議組織的,這次論壇主題也是他提出的。如今想來,他心頭的“時代擔當”是由來已久了。
從我陸續讀到有關陸士清教授的訪談、報道和各路名家以及他的弟子們記述他的文章中得知,陸教授在港臺文學和世界華文文學研究領域有著不凡的學術生涯,在文壇有著廣泛的人緣,早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兩岸尚未破冰時就開始了與臺灣文學大家們不尋常的交往。但在溫哥華幾天近距離接觸交流中,卻從未聽他談及,倒是不止一次聽他說到自己是普通農家的孩子,貧苦出身,曾經失學務農,日本人侵略時被迫逃難。直到一九四九年春節前,父親悄悄賣掉一畝田,讓他重新就學,期望他以知識改變命運。如今已桃李滿天下的陸教授,想到父親當年的決斷,甚是感恩,也深感自己的幸運。這幸運包括解放后得到考大學的機會,只讀了半年初三的他,以同等學歷的資格考取了復旦,畢業后留校任教,由此重塑了自己的人生。
鮐背之年,陸教授談到自己的學術人生,用兩個字概括就是“專注”。他總結道:“一門學問,持之以恒做下去,不管大小,都會有成果的。”平和低調的話語里道出的是真理,透出的是做人、做學問的最樸素也是最高貴的品質:誠實。當臺灣文學尚未進入大陸學界視野之前,文學研究領域對臺灣文學尚不屑一顧的時候,他如何就掉轉了自己學術研究的方向,堅定地走上了這條獨木橋呢?在本文撰寫過程中,我的疑惑隨之解開。
四十多年過去,陸士清教授與“在島嶼寫作”的那些名家的交往,業已成為他文學研究的第一手資料和創立世界華文文學學科平臺的基礎,并熔鑄在他一部部學術和文學著述中,如《曾敏之評傳》《三毛傳》(合著)、《白先勇小說選》《臺灣小說選講》《筆韻》《王幀和小說選》《血脈情緣——陸士清文選》《品世紀精彩》等等。當榮譽褒獎和各種溢美之詞蜂擁而至,陸教授總是淡淡地說“是時勢和條件,我只是做了一點推動和聯系”。他輕輕一言就把個人的功勞推到了一邊,猶如交響樂激昂熱情的第一樂章轉入第二樂章,舒緩、平靜,讓我想起他晚年回老家張家港微笑著站在油菜花田野里的留影,怡然、平和。
回到二○一七年夏日。
不知該算是我的運氣,還是“陸士清”三個字被繆斯賦予了神力,電話一打過去,就聽到痖公的聲音,好像他就等在電話旁。一如既往的溫潤、富有金屬光澤的嗓音。我問他記不記得復旦的陸士清教授。線那頭立刻答曰:“記得記得。大陸的陸,士兵的士,清廉的清。”沒想到痖公竟把陸教授姓名的三個字拆開來逐一注解,跟著他的注解,我眼前浮現出一幅寥寥幾筆的簡筆速寫畫,倒也符合主人的樣貌和性情。接著,電話里就定下了與陸教授會面的時間。于是就有了本文開頭紅衣長者一路登上“排比句”的那一幕。
三
溫哥華七月的黃昏,落日熔金。
在痖公家門前,兩位老人緊緊握手、擁抱,像是久別重逢的兄弟。相擁的兩位“白頭翁”都笑成了慈祥的“老奶奶”。夕陽的余暉為他們白得不分彼此的銀發,撒上了一層淡淡的玫瑰金。在走下那排長長的石階時,陸教授挽著痖公。雖說同庚,痖公則年長幾個月,他的背明顯駝了,而陸教授從背影看依然挺拔,沒有一點弧度。我抬頭望望天空的云,不知何時好似圍攏過來,如易安居士所稱的“暮云合璧”。我忍不住想說,宋朝的天空還在今天的天上……
我預訂的餐廳是痖公推薦的。碰巧餐廳的經理是我初到溫哥華在一個課堂讀書的同學,自然對我們這一桌照顧有加,菜品也很可口,色香味俱全。
一落座,痖公就從他的黑提包里拿出一份關于建設海外華文文壇設想的打印稿交予陸教授。雖然痖公早已不再寫詩,也早已離開臺灣聯合報系的副刊主編職位,卻非常關注華文文學在海外的建設推廣。這一點,與幾十年專注于臺灣和世界華文文學研究的陸教授,可謂心有靈犀。兩位老人邊吃邊熱烈交談,從大陸的“傷痕文學”聊到臺灣文學及其作家進入大陸,就說到了於梨華、白先勇。
四
一九七五年和一九七七年,旅居美國的臺灣作家、被譽為“留學生文學鼻祖”的於梨華先后兩次到訪復旦。一九七九年她第三次來到復旦,陸教授與她有了深入的接觸與交流,并請她為中文系師生做了“臺灣文學發展概況”的演講,在當時對國內聽眾是非常新鮮的。正如陸教授在於梨華因感染新冠而去世的悼文里所追憶的:“她的精彩講演,為我們中文系師生打開了一扇文學之窗,使我們看到了中國大陸以外的天光云影。”當時的陸士清也從於梨華打開的那扇窗,看到了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版圖上一門有待開發的新學科的遠景。其時,他已經讀過了作為留學生文學代表作的《又見棕櫚,又見棕櫚》和於梨華在上海發表的其他作品,如《收獲》上的長篇《傅家的兒女們》,對她的創作已有相當程度的熟悉。于是就在同年,把《又見棕櫚,又見棕櫚》推薦給福建人民出版社,并積極鼓勵出版社編輯:“如果你們出版了,就創造了歷史。”
小說在翌年九月出版,比瓊瑤小說進入大陸還早兩年(以《我是一片云》在《海峽》雜志刊登為時間點),成為中國大陸出版史上第一部問世的海外華文作家的長篇小說,而陸士清也自然成為創造這一歷史的第一推手。著名文學評論家蔣孔陽在陸士清《臺灣文學新論》序言里指出:“一九七九年,改革開放剛剛起步,在人們對‘左’的一套尚心有余悸,我國大陸文學界絕大多數人對海峽彼岸的文學情況尚茫然無知的情況下,士清同志又鼓起了勇氣,開始介紹和研究臺灣文學。”從這段敘述里也可見,當時舉薦出版海峽對岸作家的作品還是需要勇氣和膽略的,而且陸士清不僅是推薦,更是下了功夫為大陸版的“棕櫚”寫了序。因對原版序作者夏志清先生的尊重,大陸版仍沿用了舊序,但於梨華對新序非常贊賞,不忍割愛,她說:“陸先生對我的作品有更深的理解,我很喜歡,附在書后,成為書的一部分。”既然作者本人把陸序當作書的一部分,那么研究於梨華的“棕櫚”,也就不能繞過“這一部分”了。
於梨華是陸士清在現實生活里最先接觸到的海外華文作家,對于站在人到中年門檻上的他有著不同尋常的意義,給予他對于臺灣文學的具體切實的感性認識,加上之前就讀到的在一九七八年出版的《臺灣鄉土作家選集》和南下廣州暨南大學做相關調研所獲信息,陸教授的臺灣文學選修課便應運而生,復旦中文系因此成為開臺灣文學教學和研究之先河者,陸士清也成為國內最早的海外華文文學“傳道人”。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國內大學中文系基本上還是循規蹈矩地局囿于傳統學科,連當代文學課在內地高校中文系課堂上也只是選修課而已,更別提港臺文學以及海外華文文學了。記得我在內地大學讀到大四的時候,才有機會選修當時在文學評論界名聲鵲起的劉思謙教授的當代文學課,直到大學畢業的一九八四年,對港臺文學的認識也僅止于金庸、瓊瑤、余光中等個別港臺作家。陸教授當年的學生、如今大名鼎鼎的文學評論家陳思和先生在他為《曾敏之評傳》一書所作序言里追述道:“記得是在一九八一年,我還在復旦大學中文系念大四的時候,陸士清老師開設了臺港文學課程,在當時大約也是全國高校里最早開設此類課程的先驅者。陸老師講臺灣文學不僅僅講鄉土派和現代派,還介紹了臺灣在一九五○年早期的軍中作家,講司馬中原和朱西寧的小說創作,這讓我們大開眼界,知道了海峽的另一端還有著多姿多彩的文學創作。后來我在學術生涯里多少也涉及臺港文學的研究,最初的興趣就是陸老師教授予我的。”一九八六年,陸教授招收了以臺灣文學為研究方向的首屆研究生。
在於梨華之后,陸老師在現實里交往密切的臺灣作家當屬白先勇。一九八七年,世界華語文壇杰出的小說家白先勇先生以教授和作家的身份訪問復旦,實現了他闊別大陸三十九年后的破冰之旅,在大陸文壇引起轟動。之后,他的《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孽子》《永遠的尹雪艷》《玉卿嫂》《謫仙記》《游園驚夢》等小說、戲劇和影視相繼風靡大陸,形成了一股“白先勇熱”,而又有多少人知道在這熱潮背后那位最初的“持微火者”呢?
九歲初到上海的白先勇,雖然在這座城市僅僅生活了兩年半,童年的上海印象卻是他文學創作中“所有故事的底色”。這位懷著濃重的上海情結的小說家,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在雜志上看到陸士清論文——《論白先勇的小說技巧》,知道復旦還有人研究他,便生出訪問上海的念頭。陸老師得知此信息后,即征得校領導同意,與白先勇取得聯系,最后促成了白先勇受復旦之邀講學兩個月。在此期間,陸老師陪同他訪問了蘇大、無錫、南大、揚師、浙大、紹興,與他一起和謝晉、吳貽弓討論,將小說《謫仙記》改編成電影《最后的貴族》。同時,客觀上也促成了白先勇的話劇版《游園驚夢》再度登上廣州、上海、香港的舞臺。之后的一九八八年,白先勇邀請陸教授到他執教的美國圣芭芭拉大學做了半年訪問學者,陸教授得以與白先勇深入交流,并對其創作和治學仔細觀察、研究,寫出了多篇研究文章,在文學和治學以外,也建立了篤厚的友情。白先勇在《樹猶如此———紀念亡友王國祥君》一文里曾提到,為了救治重病的摯友,在雜志上看到上海曙光醫院有治療相關病癥的報道,就立刻聯系陸士清教授,飛赴上海,陸教授則傾心傾力,一路陪同為摯友生死而焦慮的白先勇求醫問藥。
陸士清教授在海外華文文學的研究教學中,不僅搭建起了學科領域的平臺,也建設著世界華文文學作家、詩人交流和友情的平臺,這與痖弦先生建設世界華文文壇的理想也是不謀而合的。文學說到底是人學,文學研究的投入也離不開生命情感的注入。除了對時勢的敏感洞察,孜孜不倦的腳踏實地,能夠幾十年如一日關注研究“在島嶼寫作的他們”,則必有一份大愛的情感支撐,這份情感,在陸士清身上是平靜水面之下不懈的涌動。
五
飯桌上談到於梨華,痖公遂問陸教授是否見過聶華苓。陸教授說她來上海時就見過,后來在白先勇邀請訪學期間的一九八八年元旦,又到她美國的家里拜訪過。“哦,那時安格爾還在。”痖公說。痖公曾是聶華苓和安格爾主辦的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最早一批被邀請的華人作家,他曾說聶華苓是他的貴人。
陸教授說,聶華苓和於梨華她們兩個人都是到大陸最早的臺灣作家,也都是很看重自己的根在大陸的臺灣作家。於梨華當初訪問大陸還是壓力很大的,但她也不顧,回去還寫了很多文章。她對故土的赤子之心,無可置疑。
這時,我那位做餐廳經理的同學親自端上一條清蒸鱖魚,魚頭正對著客人。陸教授和痖公禮讓再三,誰也不肯先下箸。我說,鱖魚頭對著貴客,那就陸老師先吧。陸教授便夾起一塊魚肉放進了痖公的碟子里。接著兩人的一段對話,包含著兩岸文化人復雜的家國情愫、世俗人情與彼此尊重。我記錄如下:
陸:你講的一句話,我是非常感動的。那就是在去神農架的路上,你跟我講的一句話,就是說到日本要把釣魚島國有化嘛,你就講“我們溫總理已經申明了這是我們固有的領土”。你講“我們溫總理”,我是很感動于這句話的……
痖:是是是,我們年齡一樣,感情也一樣。
陸:我們都經歷過國家、民族的苦難。
痖:是。《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你看,一個個的場景:江上,烏篷船,船里那個小燈,拉著大車在雪地里奔走……人民的形象都在那里了。“在漆黑的夜晚,我這點在燈下寫的無力的小詩,能為中國增加些許暖意嗎?”(痖弦用他自己的話復述了艾青詩結尾的那一段。早兩年,他提到這幾句是照原文背下來的。)
艾青詩很好……艾青是很有感情的,嗯,手法也很好。但是到了《吳滿有》就比較差了,那個時候,作為詩人的形象就懈怠了。早期的很好。我沒見過他,很遺憾!
六
晚餐后,談興未盡,痖公邀大家到府上坐坐。
痖公的家,儼然是個小型博物館,他在臺北許多年里積攢的各種收藏,與古色古香的家具擺設相得益彰,一進房門就令人目不暇接。痖公讓我幫他泡茶招待客人,陸教授連忙示意不要,我知道他的意思。作為臺灣文學研究專家,在研究對象家里的所見所聞,屬于文學研究的第一手感性資料,何況是在痖弦先生家里?時間寶貴。我便遵從陸教授的示意,隨他們兩位從客廳移步書房。
事實上,痖公的書并不在這里,多在地下室。他曾戲稱自己是“地下工作者”。而這間擺放著寬大書案和若干展示柜的大房間,更像是一個博物館的小展廳,應該是主人比較私密的會客室。一個鑲著玻璃門的博物柜,錯落有致地擺放著各種藏品,正中最大的一格,立著一幀痖公母親黑白照的相架。痖公說,這是母親唯一一張遺照,還是他闊別大陸四十年以后回鄉探親,從堂兄弟手里得到的,而父親沒有留下照片,他對父親的容貌已經記憶模糊了。我想,站在痖公母親像前那一刻,陸老師一定也在想自己的母親,他三歲時母親就過世了。
一陣肅然之后,痖公引陸老師走向房間盡頭的辦公臺。書案一側墻壁上掛著臺靜農的書法對聯“春前有雨花開早,秋后無霜葉落遲”,給充滿文物感的室內平添了一份庭院氣息。另一側頂到天花板的展柜,擺放著锃亮可鑒的各種金屬茶壺,有的造型像古時的鼎。痖公說:“有這么多的茶壺,卻沒讓客人喝一口茶,真是諷刺。”大家都笑了。然后他又問陸老師,“你看上哪個?我送你。”陸老師笑說:“不能破壞文物珍藏的完整。”痖公又說:“我可是很小氣的哦,快選一個,別等我改變主意。”大家更笑了。
從“展廳”出來,痖公得知我女兒在晚餐前剛上完鋼琴課,便指著墻角一臺棕色雅馬哈讓孩子去彈奏,然后請陸教授入座一起欣賞。一曲普列考夫耶夫和一曲貝多芬的奏鳴曲之后,一直跟著琴聲在座椅扶手上輕輕打著節拍的痖弦說,我家這臺世界上最寂寞的琴今天發聲了,并贊“這不是學生的彈奏,有大家氣象”。他問了女兒的名字說,你以后開音樂會一定要通知我,我要買票去看你!隨后就跟陸教授從音樂又談到文學,遂拿出厚厚的一本《眾筆繪華章》贈給陸教授。我知道痖公很看重這本文集,這是他退休移居溫哥華后主持的《世界日報》上的一個文學版面——《華章》的一部作品匯編。書里的每一篇詩文都經他親自審閱。痖公一向在場面上很周全,很注意給身邊人面子。他贈書時特別提示說:“里面也有宇秀的詩。”
臨別,賓主在一面由大小一致的同款小木格筐壘成的隔墻前合影。這面別致的“墻”,三十個小筐里分別存放著主人擔任《聯合報》副刊主編三十年的編輯底稿,以及與作者的全部通信——一封不落地從臺北運過來,包括張愛玲、巴金等耳熟能詳的文學名家的信件,以及痖弦自己回信的復印件。那是一面承載著現當代豐厚的第一手文學史料的“墻”啊。
離開痖公家回賓館的途中,陸教授沉默不語。深藍的夜色在車窗外匆匆后退,襯著車內異樣的安靜。我想,老先生是累了。突然他從前排回頭對我說道:“宇秀,你能不能動員痖弦把他那些信捐給我們上海的巴金紀念館?”
哦,我明白了陸教授離開痖公家之后的沉默。我很理解他身為大陸臺灣文學研究拓荒者的心思和作為一個當代世界華文文學研究者的學術敏銳。可惜,晚了!痖公已經承諾了臺北的圖書館,將全部信件捐給他們,已有專人每天到痖公家整理和輸入電腦。這件我不能幫陸教授達成心愿的事,讓我好一陣遺憾。不過,如今想來無論這些信保存在臺灣,還是在大陸,都是中國文學史的一部分,都是屬于華文文學的財富,就像分藏于海峽兩岸的《富春山居圖》,不管在此岸還是彼岸,終究是一幅必須合璧展示才完整的中國山水。
七
今年三月初,和陸老師微信私聊,我問他:“隔了這許多年,回頭再看您當年開設臺灣文學課,您如何看待自己那段教學歷史?又如何看待臺灣文學在華文文學中的地位?”大約隔了近一個鐘頭,陸老師在微信里做了四點回復:
“一,我當時開‘臺灣文學’課是正確的,及時的。因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臺灣文學當然是中國文學的一部分,關注臺灣文學是我的責任;二,改革開放,臺灣問題有望和平解決,兩岸文化交流,兩岸中國人走到一起是必然的,我們應為此做文化和學術上的準備;三,臺灣新文學中,除去一九四九年后出現過低俗的文化垃圾外,其余部分,都是中國文學寶庫的一部分,包括陳映真為代表的鄉土文學,白先勇為代表的現代小說,洛夫、痖弦為代表的現代詩,林海音為代表的懷想文學等等;四,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中期,因‘文革’破壞,大陸文壇頗為荒涼,而這時臺灣鄉土文學和現代小說、詩歌都發展得很好。我任常務編委編寫《中國現代文學詞典》時,似乎感到,這時段的一些臺灣作家作品,彌補和充實了這段歷史。我把他們和他們的作品收入辭書。”
他平靜的文字里,表達的不僅僅是理性的文學觀點,更有一份民族情感,這份情,具體地落實到了對“在島嶼寫作的他們”的惺惺相惜。說到這里,我忍不住要提及一位在大陸熱度延續長達十五年、且不是靠“觸電”火出圈的作家,她就是三毛。如果你想完整地了解三毛,在走近這位傳奇女作家時,你會遇到“陸士清”這個名字。
一九九一年一月四日,三毛突然辭世,震驚了海峽兩岸、東南亞等世界各地的華語讀者。一九九二年六月,由陸士清、孫永超和楊幼力合著的《三毛傳》出版。雖然在此之前,國內已有四五本寫三毛的書,但這部新的《三毛傳》一經問世,即被海峽對岸的出版界認為是一部更全面、更深入、更準確了解三毛、既有可讀性又具有學術價值的書。臺灣晨星出版社迅速向大陸百花洲出版社購買了該書的版權,于翌年七月三十一日,推出臺灣版《三毛傳》,并且以“第一本關于三毛一生的完整傳述”為封面導語。出版介紹稱這部傳記“從三毛的出生到生命停止,在每個人生階段都有極為詳盡的資料考究。完整地呈現了一個生命的個體在生命歷程所展現的生活觀察,了解三毛,請從《三毛傳》做起點”。臺灣圖書資料部門還買了《三毛傳》兩章———《殞落了,沙漠之星》《透明的黃玫瑰》的版權,以作為對三毛的權威評論收藏。
一個傳記作者,對自己筆下的人物,除了深刻的了解,還必須有一份特別的感同身受,才能使自己的文字富有代入感而打動讀者。很難為情,我尚未讀過這本傳記,但我看到豆瓣上讀者的感言:“是這本,讀完唏噓不已。”另一條留言說:“放下手中的《三毛傳》,久久不能平靜,幾度感懷,幾度落淚。”可見,該書除了學術價值被業界認可,其文學性也深深打動了讀者。
說到當年的陸士清教授為何如此重視三毛的人生和創作,我以為,除了對于三毛創造的“撒哈拉魅力”這一華文文學界重要的文學現象的學術認知,和意識到三毛文字對當代人感情真空一定程度的填補與撫慰之外,更有傳記作家自身內心里的青春激情。讓我暗暗訝異的是,當時的陸士清已年過半百,對于更為年輕人追捧的三毛,他如何也有一股青春的熱情?以他的年歲、個人成長經歷、社會生活環境,如何能對一個在不同社會語境中成長的年輕女作家的心靈世界有細致的體察與同情呢?從表面看,這位嚴肅的年長學者與一位浪漫不羈的臺灣女作家,有很大的反差,然而,與他走近,便可感覺到波瀾不驚的水面之下的湍流。想起一件事,那是他剛到溫哥華的當晚。
那天晚餐后,應陸雨的要求,我和我先生帶他們父女到市中心的英吉利海灣史丹利公園尋找張國榮的長椅,在著名的海灣景點Tea House前。溫哥華“榮迷”們為偶像捐獻的長椅就在這附近面對大海的斜坡上,這里也是“哥哥”生前住在溫哥華時與朋友經常小聚的地方。本來我想陸教授就在車里休息等我們好了,畢竟是八十多歲的老人了,又是長途飛行到達的第一天。沒想到他竟興致勃勃,跟我們一道在夜色下的斜坡草地來來回回地搜尋。那片斜坡閑散地放置著多條長椅,像自然生長在那里的樹木一樣并無規則,我也不能準確地指出哪一個是張國榮的,需要查看椅背上的銅牌,上面鐫刻著逝者的姓名、生卒年月,長椅也是另一種形式的墓地。那晚的月躲在云層后面,夜幕像厚重的黑色大氅,陸老師就跟著我和陸雨在黑暗里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地兜來兜去,直到陸雨用手機上的“手電筒”照見一塊長條銅牌上刻著張國榮的名字、生卒年月,和長達五十字的紀念文——這是我所看到的鐫刻在椅背上最長的文字。陸老師也興奮地湊近細看銅牌上的刻字。忘記當時是誰提議在椅子上坐一坐,我一摸椅子很潮,已被夜晚的露水打濕。
可惜陸教授在溫哥華與痖弦先生重聚的時間有限,不然,如果談及三毛,他們一定會有很多話說。要知道,三毛可是痖弦一手推出的明星作家,當初她的第一篇撒哈拉故事,就是發表在痖弦先生時任主編的《聯合報》副刊上。之后在痖弦的鼓勵下,她與荷西在撒哈拉生活的系列散文連續刊出,她的第一部散文集《撒哈拉的故事》便是這些文章的結集。而后她的《高原的百合花》就是在《聯合報》“三毛中南美之旅”資助計劃下寫成的。痖弦根據報社計劃為三毛設計了一系列演講,觀眾的反響熱烈到瘋狂的程度,令痖弦始料不及,考慮到三毛的安全,不得不喊停。如今想來,很是遺憾那天怎么沒提起三毛的話題。一位《三毛傳》的作者和一位三毛的文學伯樂,在一起談三毛該有多少值得記載的內容呢!
再回到英吉利海灣那晚,一位耄耋老人陪女兒夜尋“哥哥”的長椅,陸士清之外,怕是沒有第二人了。我忽然在陸教授三十年前寫《三毛傳》和陪女兒尋訪張國榮長椅之間感覺到某種聯系:一個學者和文學人的內心青春,總是具有超越各種藩籬的人性力量。難怪《臺港文學選刊》創辦人楊際嵐先生以《歸來還是少年》為題記述陸士清教授,著名詩人學者劉登翰先生則在為陸老師新著《品世紀精彩》序言里,以“青春是一種生命的精神”來形容和總結學界老友。
八
二○一六年秋,在北京第二屆世界華文文學大會高峰論壇,我做了《轉道臺灣的中國新詩——從洛夫、痖弦和余光中看中國新詩的經典傳承》的演講,沒想到與陸士清教授不謀而合。他則說自己的觀點“很高興得到你的認同”。
最近閱讀有關陸老師學術生涯的資料才知道,他早在一九八一年開講“臺灣文學”課程時就相當重視詩。對于痖弦的創作,重點介紹過他的三首詩:《上校》《鹽》《如歌的行板》,著重強調他在詩藝上的探索和作品的社會意義。陸老師把臺灣詩人們“請進”課堂的時間,較流沙河在《星星》詩刊評介臺灣詩人的專欄文章結集出版的《臺灣詩人十二家》,還早兩年。
一九八五年出版的中國首部百科全書詞典《中國大百科全書》,由陸士清為之撰寫“現代臺灣文學”條目,乃是國內辭書第一次上臺灣文學條目。他將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武治純先生所寫第一稿約七千多字擴大到近二萬五千字篇幅,使這個條目實際上成了現代臺灣文學的“史綱”。更可貴的是,在梳理這些條目時,他糾正了以往偏重小說、忽略詩歌的現象,將詩歌擺到了應有的地位,點評了一百一十五位以上的小說家、詩人、戲劇和散文作家的活動和創作。
一九九四年夏,陸士清與上海人民廣播電臺合作了一檔廣播節目,叫作“世界華文文學百家精品展播”,介紹和展播近百位臺港和世界華文作家的作品。每次半小時,由朗誦演員朗誦,每位作家持續一周。我曾看到陸老師當時為這個廣播節目所寫的介紹痖弦那一集的手稿中有這樣一段文字:
“痖弦吸取了超現實主義的技巧和手法,成為臺灣詩壇勇于探索而自成一格的詩人。痖弦不否認文學的社會意義,認為詩人的全部工作似乎就在于‘搜集不幸’的努力上,他在對眾多小人物生存痛苦的描寫中,概括了較為普遍的人生經驗和人性感受,表現出了深厚的同情心和‘人道主義’精神。”
綠方格稿紙里娟秀的字跡,雖然已被歲月吃掉了墨色,但依然可見真情理解的飽滿書寫。當時的陸士清不會想到三十年后的一天,會與自己筆下介紹的詩人在溫哥華擁抱在一起,但他對兩岸文化交流的愿景是充滿期待和樂觀的,正如他在《筆韻》第一編中寫下的題記:“炮聲,遠去了;海浪,傳來兄弟的心跳。”讀到這一句時,我眼前疊化出另一個畫面——
尾 聲
溫哥華七月深夜十點多,微藍的月色清輝灑在大地上。痖弦先生將客人送到門口時,再一次上前擁抱住遠道而來看望他的陸士清教授,動情地說:“世界已經夠寒冷,讓我們用彼此的體溫互相取暖吧!”
當時在場的陸雨事后跟我說:那最后的擁抱,讓人落淚。我則想到王昌齡的兩句詩:“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兩鄉。”這詩的意境,也是陸士清教授四十多年來投身的臺灣文學和海外華文文學研究的學術天空和他的心境的寫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