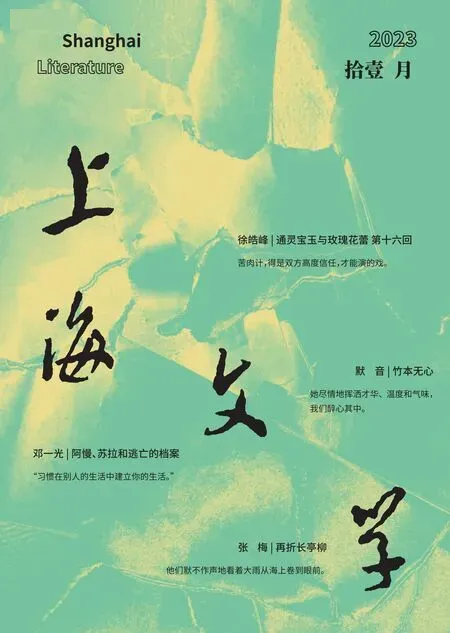末腳位(外一篇)
干亞群
每個月的月底,院長從抽屜取出一張紙,直尺在上面橫橫豎豎,圓珠筆緊貼著拉出一條條線,像木匠彈墨線。之后,圓珠筆順勢倒在院長的虎口,醫生們的名字一個個認真地站到了方格里,你在我上面,她在我下面,擠擠挨挨。
這是考勤表,貼在內科,下面坐著的是院長。每天按上班鈴的是院長,在鈴聲大作中反背著手站在走廊里的也是他。
院長每天在那里劃斜杠,或圈圈,如果是三角形,說明去開會。童醫生偶爾有之。童醫生去鎮里開會從來不算開會,只是去縣計生指導站時,她才標這個符號。劉會計對開會者報銷差旅費,是根據院長的考勤表來發放的。鎮政府的會議一般安排在電影院,童醫生過去也就二十幾步路,根本算不上差旅。
每個醫生有一個編號,我是十四號,下面還有幾排空的,使得我的名字像一棵伶仃草。隨著橫格上的斜杠越來越多,我那棵草如同穿了件編織衫。
這不是我的比喻,是阿榮伯說的。
那天,院長的考勤表出現了三角形,于是,同事們開始串門。我也是,串到了內科,在那里翻舊報紙,聽人聊天氣。阿榮伯忽然說,小干,你怎么成了末腳位?我差不多被他嚇了一跳,不知道我末腳在哪里。阿榮伯指了指考勤表,說,你是正規軍,我們是野戰軍,怎么可以把你的名字放在末腳位?明天跟院長說說,末腳位應該是我。
我知道這是阿榮伯開玩笑,也沒接過話,笑了笑,繼續翻舊報紙。
阿榮伯似乎對末腳位充滿了敵意,一個人在那里痛訴著,考核末腳位,轉正的希望末腳位,家里的地位也是末腳位。
醫院的后面是幼兒園,小朋友正在風琴的伴奏下唱歌。像是有意為之,阿榮伯左一口末腳位,稚嫩的聲音唱一句“娃哈哈”;阿榮伯右一口末腳位,好聽的“娃哈哈”再次飛進醫院。
阿榮伯瞪了一下眼睛,怎么那么煩的。他甚至用手去撩,似乎“娃哈哈”是一張蜘蛛網。
阿榮伯在醫院里已經工作了二十多年,可拿的還是臨時工的工資。每次發工資,他都要咬牙切齒,恨恨地罵幾句,罵聲里“末腳位”一會兒倒過去,一會兒翻過來。
我第一個月去領工資時并不曉得要避開他,所以,他問我拿了多少,我老老實實地回答。他要看我的工資條,我也給了他。
劉會計在邊上又是咳嗽,又是遞眼色,我還誤以為她咽喉炎發作。當她看到我把工資條給阿榮伯時,她咳嗽沒了,眼色也沒了,但臉色變了,變得有點陰郁,一邊嘴里“阿梅阿梅”,一邊起身閃出了會計室。
阿榮伯虎起了臉,原本黃瓜似的臉變成了一根紫茄子,兩只眼睛迅速翻了個白眼,會計室里只剩下我跟他,那個白眼毫無疑問,只有我看到了。我有些尷尬地站在那里,也想跟劉會計一樣借故離開,可阿榮伯一把扯住我的白大褂,非得給我看他的工資條,就像一個病人袒露他的傷口似的。他的工資只有我的三分之二,看得我有些尷尬,臉上的表情可能讓他看出我有些愧疚,于是,他大大方方地放我走,自己一屁股坐在劉會計的位置上,似乎鐵了心要坐到下班。
可是劉會計遲遲沒有出現,她跑到掛號室去對賬了。平時是掛號室的梅姨去她那兒的,一個站著,一個坐著,坐著的人還時不時地指責或批評幾句。但只要阿榮伯去領工資,劉會計就會跟梅姨親近起來,一個站著,一個坐著,坐著的是梅姨,她在劉會計的賬單上指指點點,手不停地推推鼻梁上的眼鏡,神情很嚴肅。
劉會計的消失,仿佛讓阿榮伯覺得面子失得更大。他干脆到各個科室顯身,罵罵咧咧,看到貓,罵門衛老伯腦子不清爽,收留了那么多流浪貓,掄起掃帚去打貓,貓豎起尾巴,沖他嗚啊嗚啊,轉身跳上窗臺,很快不見了蹤影;見地上有垃圾,罵清潔工阿德,拿的是醫生工資,做的是掃地的活,地還掃不干凈,隨手把手里的掃帚扔到了墻根,那里堆著阿德收集起來的紙箱子,嘩啦啦,箱子癱軟到了地上;罵著罵著,突然張大了嘴巴,一個“啊”字很響亮地從嘴里噴出來,隨后他像是停頓在那里,鼻翼抽了幾下,眼皮合上,又打開,嘴唇牽著,喉嚨里似乎有什么東西卡在那里,半響,才“啾”地一聲。
阿榮伯非常情緒化,高興的時候,見誰都是親人朋友。碰到病人配藥錢不夠,他跑到藥房去做擔保,如果藥房不配合,他瞪起眼睛,跟藥房的魏姨背《為人民服務》,念發揚人道主義精神。病人在藥房外尷尬地站著,配,不是,不配,也不是。魏姨急了,一跺腳,說,你借錢給病人不就得了。說完,魏姨沒來由地嘻嘻笑了起來,似乎想沖淡自己剛才所說的話。阿榮伯再次瞪起眼睛,我工資末腳位,哪像你福氣好,一到醫院就是正式工。魏姨的嘻嘻沒有間斷,滾圓的手開始去捉藥瓶。
阿榮伯是赤腳醫生出身,只念了小學,這是他遲遲得不到轉正的一個原因。另一個原因是因為他考核總是末腳位。隨著年歲的增大,他轉正的希望越來越渺茫,比他資歷淺的人,一個個轉了正,工資單上是三位數,似乎一下子稱出了身份,還有地位。考勤表上阿榮伯排在院長的后面,拿的卻是全院差不多最低的工資,比他更低的是阿德與菊嬸嬸夫婦倆,但他們的工資單是另外一張。對此,他一直耿耿于懷。
有次,他借著酒勁,把院長罵了個狗血噴頭。院長指著他的白大褂說,你還像不像個醫生?他一聽此言,干脆脫了白大褂,繼續指著院長的鼻子開罵。
阿榮伯嗜酒,不是秘密。他跟鎮政府的干部斗過白酒,跟派出所的民警賽過黃酒,跟供銷社的柜員喝過啤酒。每次喝酒,他總要跟人劃拳,二相好,五花魁,八匹馬。輸了,不用別人催,自己端起酒碗,咕咚咕咚,酒碗很快見底。贏了,捧起酒碗主動陪輸者喝一半。
喝了酒的阿榮伯心情大好,拍拍鎮政府干部的肩,勉勵他們酒風就是作風,能喝半斤喝一斤,這樣的干部要提拔,能喝一斤喝三兩,這樣的干部要靠邊。也有人捉弄他,說他什么時候提拔。阿榮伯快活地呷一口酒,說,廿七廿八,等待提拔,三七三八,飛黃騰達,四七四八,死蟹一只。我現在是死蟹一只。別人糾正他,是醉蟹一只。他也不生氣,嘻嘻哈哈,手指一會兒張開,一會兒攥攏,喊著二相好,八匹馬……聲音高亢地穿過沉沉的夜色,然后隱隱地傳到醫院。他的一件白大褂貼著墻壁,一動也不動。
阿榮伯還跟他的病人喝。有些先是他的酒友,后來成了他的病人。看病前,倆人先回憶一下喝酒的那些事,一個說,你的酒量在進步,所以身上沒什么大毛病。一個說,你的酒德就是你的品德,跟你喝酒痛快。一個說,下次我們喝酒不要再叫某某了,這人老是嬉調皮。一個說,再也不叫他了,上次往酒里摻水,太沒信仰了。之后,倆人才切入看病的程序。而有些先是病人,后才是酒友。這大多是別人感恩于他,投其所好,請他喝酒。喝著喝著,成了朋友。
阿榮伯有宿醉的習慣,雖然,他上班很準時,甚至比我們早到十幾分鐘,但整個人混沌沌,身上散發一股刺鼻的酒氣。如果心情不錯,他會主動搭訕,看病又看相,說人家印堂發紅,兩耳圓潤,一臉富相。如果情緒低落,就呆呆地坐在那里,半天不見他眼珠子動一下,既像老僧抱禪,又像是失魂落魄。
其實,阿榮伯的病人并不少,尤其是上了年紀的病人,都喜歡找他看病。他有一個特點,凡是找他看病,他總是鹽水一瓶,里面無一例外是激素與抗生素。農村病人哪里懂抗生素濫用這種說法,大多是鹽水一打,病情改善,甚至治愈。在病人眼里,他無疑是醫院里最好的醫生。他最擅長的是支氣管炎,農村人叫“老耗駝”,發作時人上氣不接下氣,喉嚨里像拉破風箱一樣,背高高駝起來。到了他這里,不出三天,氣急肯定得到緩和。但凡找他看過這個病的人,到了別人那里肯定治不好。雖然,我們私下里說他激素用得過猛,可這種病不用激素,確實不會緩解。此外,他還看痔瘡,也不知從哪里得來的偏方,凡是得痔瘡的,他在病人的嘴邊扎幾針,再配一副中藥膏,這藥膏他秘不示人。別人再怎么樣討他的話,也討不到半星點信息。
有次,他酒又喝多了,坐在椅子里打瞌睡。阿其醫生想讓他酒后吐真言,問他藥膏里有什么藥。他歪著腦袋,說,有紅花。阿其醫生又問,還有什么?他睜了一下眼,又合上,說,有維生素C。阿其醫生再問,還有呢?他不響,然后鼾聲大作。阿其醫生繼續問,也問不出所以然。當阿其醫生放棄尋求秘方時,他突然醒了,神清氣爽地看起病來,仿佛剛才他什么也沒說。
病人稱他阿榮伯,同事喊他阿榮伯,連七八十歲的病人也這樣叫他,似乎阿榮伯才是他真正的名字。對此,他似乎也挺滿意,對誰都會擺一擺阿榮伯的架子,比如碰到同事,必須別人先叫他,如果別人不主動,他會斜著眼睛看著你,目光里似乎蠕動著各種蟲子,讓你覺得臉上脖子癢癢的,手不由自主去撓撓,撓著撓著,就撓出阿榮伯。他便滿意地收起目光,高興之余也會親切地拍拍你的肩膀,類似于一位長輩對晚輩的鼓勵與肯定。
我曾好奇地問童醫生,為什么大家都叫他阿榮伯?童醫生說,她具體也不是很清楚,有的說是綽號,他年輕時就喜歡指手畫腳,誰的賬也不買,別人取笑他做人的態度跟老伯伯似的,一叫就叫順口了。也有的說是他輩分高,同樣年紀別人得叫他阿伯,叫久了似乎也就成了習慣。
阿榮伯很少到我們科室里來,來了就喜歡跟我們說生男生女的事。他說,他能從孕婦的脈中切出是男是女。童醫生笑他吹牛。他說,不信試試看。他又說,他能從孕婦的肚子形狀判斷出生男還是生女。童醫生不信。我也不信。他說,我跟你們打個賭。后面的話我們沒有接過去,誰也不愿跟他打這個賭。他的賭注我們知道,可我們誰也喝不來。
有年,醫院里突然改變了考核方式,民主測評的對象引入了病人,還有鎮上的一些單位。結果,阿榮伯的考核數遙遙領先。阿榮伯像是暢飲了十幾碗酒,一整天都笑咪咪的,表揚阿德,肯定門衛老伯,還買了包大重九的香煙,見人就分一支。他還站在屋檐下,跟我們說從現在開始要戒酒了。陽光大團大團地灑在他身上,他臉上的笑容也大團大團。
我們果真有一個星期沒有看到他喝酒。這一個星期他認認真真坐在診室看病,醫院里似乎突然多出了一份安靜,多少有點異樣。
不久,醫院里調他到下面的分院去做院長,那里加上他共三個人。他似乎也很樂意,高興地跟我們道別。到了年底他到醫院里來拿獎金的分配單,結果發現他在三個人當中又是末腳位,其他兩個人是正式工。
晚飯,他是在醫院里吃的。他再次喝得酩酊大醉。院長和阿其醫生左右攙扶著他,搖搖晃晃走出醫院。還沒到醫院門口,他猛地睜開血紅的眼睛,高聲背誦:“當他回首往事的時候,不因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因未腳位而羞恥。”院長糾正一下,儂不是末腳位。阿榮伯大吼一聲,誰說不是末腳位。院長忙說,是末腳位。阿榮伯癱在院長與阿其醫生的肩上。
一彎鵝毛新月,靜靜地臥在西邊,仿佛是天空的末腳位。
偏 方
我在屋子里咳咳咳,知了在外面喳喳喳。
剛開始的時候也就偶爾咳咳,沒放在心上。后來咳嗽的頻率高了,呼吸短促,一說就氣急,如果多說幾句,期間不停地被嗆著,仿佛話在嘴里成了一塊破風箱栓,左右漏風,且無處可逃。
最難堪的是話才說了前半句,后半句就卡在了氣道里。我捂著嘴巴,把頭偏過去,努力不讓咳出來的氣流與唾沫恣意飛跑,但總有閃失的時候。
于是,我成了穿白大褂的病人。
阿其醫生很認真,望觸叩聽,花了十分鐘時間,認為是一般性的傷風,門診記錄本上寫的是感冒。阿其醫生在處方上寫了三種藥,都是口服藥。我拿了處方,道了謝,咳著去配藥、拿藥。
阿其醫生的藥,一種是棕色合劑,止咳化痰,另兩種是抗生素,既可治療呼吸道感染,也可治療尿路感染,做個不恰當的比喻,就像是農藥,噴灑下去總有蟲子會敏感,至于蟲子長在什么部位并不是重點。
我小心地遵守阿其醫生的醫囑,棕色合劑飯前喝,兩顆膠囊與一片白色的藥丸飯后服。飯前服的前提是胃的消化能力好,藥物對它沒刺激。這當然是基于我自身的主觀判斷。阿其醫生只是設置了一個條件。我看的是咳嗽,沒讓他看胃病。
我服了兩天的藥,咳嗽仍在持續,就像延續一場壞天氣,有時陣雨,有時多云,如果不打雷,這天氣將繼續陰晴不定。我的咳聲,從早上一直響到晚上,由診室到食堂,又由食堂到宿舍,把阿其醫生咳得有些臉紅。
坐在阿其醫生隔壁的是外科黃醫生。他原來是赤腳醫生,會包扎,也會扎針,他的嘴里常年叨著一根煙,就是給病人扎針縫傷口,煙灰也是一楞一楞的。或許我的咳嗽咳出了他的使命感,非要給我扎幾針,說是保證把我的咳嗽扎好。我半信半疑。他嘴皮一動,香煙從他的嘴左上角移到了右下角,煙霧趁勢捧住他的嘴唇,使得他的面目有些神神道道。
黃醫生似乎看出我的猶豫,起身把針灸盒拿出來,掏出幾根,用酒精棉球粗枝大葉地擦了幾下,就要往我身上扎。我跳了起來,說什么也不肯。黃醫生一臉的失望,煙灰撲撲地掉下來。
阿其醫生建議我拍張片子,因為他聽出我肺部有羅音。可他一會兒說是濕羅音,一會兒又說是干羅音。我問他到底是什么羅音,他便翻開厚厚的內科學,一邊把聽筒貼在我背部,讓我深呼吸。良久,他說,干濕羅音都有。我說,肺部感染了?他點了點頭,毫不猶豫。阿其醫生又開了兩天的藥,打點滴。我片子也沒拍,怕那X光的射線。
我的靜脈比較飽滿,一針見血。液體隨著輪流管靜靜流進體內,我感覺身體開始慢慢發熱,這是抗生素起的作用。當晚睡得還比較穩,沒怎么咳嗽。我大喜,特意準備了一些好話跑到阿其醫生那兒。黃醫生似乎臉上有些掛不住,不冷不熱地說,當心第二天反彈喲。我說,你這張烏鴉嘴。說完,我有些后悔了。黃醫生的資歷雖然在醫院不算最高,但他畢竟是老同志,說話不該沒大沒小。
第二天我果真咳得厲害了,還發了燒。阿其醫生補了張方子,里面加了一支激素。我是上午十點后打的點滴,這時候病人基本不太有了,我穿著白大褂坐在躺椅里輸液,因不能吹風,就把注射架搬到了走廊里,外面知了扯著嗓子拼命叫,我聽著聽著打起了瞌睡。
等下班鈴聲響時,我撥掉針頭,汗也出來了,人感到有些輕松,但沒什么胃口。撥拉了幾口飯后,我倒了一調羹的棕色合劑,脖子一仰,嘴里泛起澀澀的苦味。
天氣仍熱得出奇,大家直對著臺扇吹。我沒辦法,只好讓臺扇搖頭,吹東吹西。病人來了,我戴起口罩。病人有的說,你傷風了?我說是。有的說你病了?我說嗯。病人也有好奇的,醫生怎么也生病。我覺得好笑,可笑不出來。因為一笑,眼淚汪汪的。
病情出現反復,尤其是晚上更嚴重。我平躺,感覺胸悶,做一個深呼吸非常困難,仿佛吸進去的氣都自顧自地躲在胸腔里,真切體會到英雄氣短的窘迫。我往右側臥,左側的鼻塞倒得到緩解,可咳嗽加重,似乎壓迫到了肺組織。我朝左側躺,像是很多水往左側灌,呼氣時甚至有咕嚕咕嚕的氣泡聲。
阿其醫生又加開了三天的點滴,把頭孢先鋒霉素調整成氨卞青霉素與慶大霉素。后兩種藥我也經常開給病人,尤其是患了婦科炎癥的病人,用三天的肌肉注射量,但得分開打。有次我給病人開了方子,第一天是在醫院打的,后兩天她去村衛生室打,也不知是她自己想減少疼痛的次數,還是村里的赤腳醫生貪方便,青霉素與慶大霉素直接混合成一針,結果病人打出了腫塊,腿瘸了一星期。
我做了皮試,結果自然是陰性,我沒有過敏史。在扎靜脈前,阿其醫生有點心神不定,為要不要再加支激素而躊躇。黃醫生見狀,悠篤篤地說,激素當然要加了,最起碼兩支。說完又動員我扎針。我還真有點動心。可看到他的煙灰突然不爭氣地塌下來,我覺得這不是好兆頭,趕緊咳著離開。
輸了五天的液,病仍黏著我,而且我越來越強烈地感受到水住進了肺泡里,我為它們整夜輾轉反側。
我提不起精神,可一個人躺在宿舍里反而更低落,所以,仍繼續上班。對面的童醫生起初戴著口罩,怕我傳染給她。過了三天,她可能覺得危險期過去了,就把口罩摘了。平時倆人無事時會聊天,我病了,大家一時都沒有說話的興致。
我偶爾把頭靠在椅背上,眼睛無力地望著窗外,那里有數只知了在叫,叫聲密集時仿佛像一陣雨,這時我會感覺到我肺部的水醒了過來,以滲透的方式擠進一個個細胞,攜帶進病菌,在那里遇到抗生素,于是細胞縮水的有之,膨脹的有之,仿佛成了混亂的主題公園。
童醫生在看書,低著頭,風扇把她的頭發吹出一縷又一縷,像是有誰在挑她的頭發。雖然,她把書擱在膝蓋上,還用蹺起來的左腿虛掩著書,可我還是看到了,是本《圣經》。于是,我猜想她的寢室里一定掛著畫有十字架的日歷。每年的年底,童醫生總會抱來厚厚的一疊新日歷,上面還散發著刺鼻的油墨味。新日歷的上半部,似乎年年如此,“只生一個好”后面是漂亮媽媽抱著一個漂亮女娃娃,她們笑容明亮,無懈可擊。童醫生很客氣,見熟人就發,見病人也送。送不完時,她就擱在文件柜上,她女兒有時抽幾張玩,折疊成一只只船。
我喝了五天的中藥。藥方是黃醫生開的。他沒有聞,也沒有切,用極不正確的握筆姿勢寫了一張方子,上面寫了十四味藥,但看著像十四種花:玫瑰花、桂花、芍藥、蒲公英……黃醫生先寫藥名,后才寫劑量,他似乎寫得很艱難,在十克與十二克之間糾結,還涂寫了兩次。他再次把大拇指壓到了食指,像是捻針的手法。
中藥房的麗姨是衛生院臨聘的,前身是赤腳醫生,也替人接生過,在調整村衛生室的醫療點時她被聘到了衛生院。她給我抓藥,那桿細細的藥秤,被她提得行云流水,秤尾高高地翹起來,且手指離秤坨遠遠的。她讓我報藥名與劑量,有時湊到亮處,對著我看秤星。我看得明明白白,她把秤星往外移了。我說,麗姨,你把藥多秤了。她壓低聲音,說,沒事的,這藥可以多幾克。
藥被我浸泡了一刻鐘,漸漸露出花的形狀,浮在水里,也有的沉到水底,像是收集了一個春天的記憶。我把它們倒進鍋里,用草黃色的紙把鍋蓋隔開。經過武火與文火,花被熬成了一碗褐色的湯汁,那里凝聚著花魂,我的病軀將安放它們,而它們用辯證的方法選擇袪,選擇宣。
我的康復,讓黃醫生很得意,說,很靈吧。他既像是討的,又像是問的。
后來,我問黃醫生,那個方子是什么方子?他吹了吹香煙,說,偏方。
我又問,針灸有沒有偏方?黃醫生似乎認真地想了一想,答,也有。
我竊喜。幸好沒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