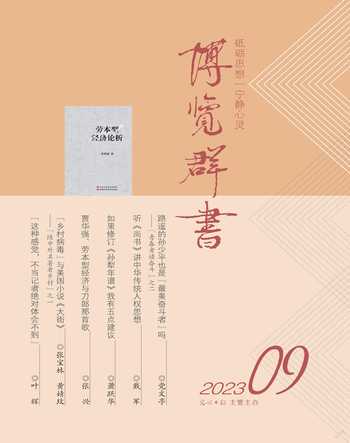如果修訂《孫犁年譜》我有五點建議
蕭躍華
段華編著《孫犁年譜》(人民出版社2022年3月,責任編輯羅少強)消息傳來,我按捺不住喜悅,輾轉聯系求賜簽名本。然后帶著期盼和挑剔的眼光逐字逐句拜讀,深為段華30多年打磨一部書的敬業精神所折服,花了近一個月時間,吭哧吭哧寫下3400多字書評《〈孫犁年譜〉:讀來文字帶芳鮮》。承蒙《光明日報》抬愛,特意安排孫犁誕生110周年的紀念日2023年5月11日刊發,何其幸哉。
我讀書喜歡挑三揀四,邊看邊作記號,如有疑似差錯標注頁碼打印出來,和書評一道呈編著者審定,與姜德明、朱正、鍾叔河、邵燕祥、楊天石、蘇晨等有過互動。這次也不例外。但從未想過有朝一日將疑似差錯公之于眾。《博覽群書》之“錯了嗎”開張營業,總得找到幾個“患者”的病情,作為引玉之磚。我顧不上友誼的小船,請出靜臥電腦中的“病例”,擇其可商榷者羅列如下,為《孫犁年譜》(以下簡稱年譜,引文標示第X頁第X行)的修訂再版提供借鑒。知我罪我,其惟春秋。
序言是閱讀的導航儀、指南針,如果缺項多少會給讀者帶來“摸著石頭過河”的感覺。年譜《后記》述說了成書經過,但《目錄》前缺少提綱挈領的導讀(序言),建議撰寫《凡例》,扼要介紹編纂體例,以千字左右為宜。內容諸如:
年譜遵循知人論世原則,廣泛考察譜主的家庭出身、教育背景、時代際遇、興趣愛好、社會交游、創作理念、文學貢獻等,紀述言必有征。譜主著述標明寫作時間、著述體裁(如小說、散文、評論、書信、書衣文錄等)、刊發何處。年譜初次出現人名,或正文簡介生卒年、籍貫、名號、職業(職務),或當頁腳注。節錄同時代人對譜主的主要社會評價,既反映正面性的,也反映批評性的,不虛美,不隱惡,實錄存真。
年譜正文原則上不特別標識信息來源,重寫初版對新發現未收入《孫犁全集》(以下簡稱全集,引文標示第X卷第X頁第X行)佚信、佚文50多篇(封),糾正全集誤寫、誤植、誤傳60多處等考證文字,不加“按”語徑直表述。這樣版式更疏朗、文氣更貫通,方便讀者閱讀。這些珍貴史料將來另行單獨成文。
年譜采用公歷,以月份作二級標題,以日期標識譜主相關信息。譜主年齡以周歲計算,譜主行文依舊俗用虛歲的未做更改,一歲之差緣于表述方式不同。譜中日期不明的重要信息,置于月末表述;只能確定到季或年的重要信息,置于季末、年末表述。
譜主的后世影響,依據時間順序,譜后單列敘述,主要包括正文未及的相關悼念、紀念活動,著作出版、重要研究成果等。
魯迅《答北斗雜志社問》論及“創作要怎樣才好”說:“寫完后至少看兩遍,竭力將可有可無的字,句,段刪去,毫不可惜。”用此標準衡量,年譜要做的“刪去”工作還不少。
日期重復。第293頁上數5行:“11月30日,致鐵凝信。信末自注:1980年11月30日晚。”第303頁上數第7行:“4月1日,晚,寫作散文《大星隕落》,副題為‘悼念茅盾同志’。文末自注:1981年4月1日晚。”第351頁下數第4行:“9月2日,寫作小說《玉華嬸》。文末自注:1983年9月2日晨改訖。”
前后重復。第296頁下數第7行:“1995年5月15日,孫犁早晨下樓散步感染風寒,從此擱筆。天道如此,此情可嘆!”第525頁下數第7行:“(1995年)5月15日,早上下樓,又感風寒。其后,身體健康狀況急劇下降。從此停止文學創作。”
上下重復。第350頁上數第10行:1983年6月“23日……夜起,地板上有一黑甲蟲,優游不去,燈下視之,忽有詩意。”同日另起一行又寫:“23日,寫作詩歌《甲蟲》。詩前自注:夜起,地板上有一甲蟲,優游不去,燈下視之,忽有詩意,1983年6月23日記。”
書名(標題)重復。孫犁致友人書信大多公開出版發表,反復標示“載《孫犁書札:致姜德明》”“載《孫犁書札:致徐光耀》”“載《孫犁書札:致韓映山》”“載《我與孫犁的深情厚誼》(《羊城晚報》副刊編輯萬振環)”等,令讀者目不暇接。
以上例子不勝枚舉,包括稿件的寫作、郵寄、發表,同一事情書信通報多人等內容重復,可否開動腦筋合并同類項?
另外,“以書信形式寫論文《再談通俗文學——至賈平凹同志》”,“寫作雜文《百花文藝出版社建社三十周年賀詞》”,“寫作論文《〈紅樓夢〉雜說》”,“寫作序言《從維熙自選集序》”等,文章定性不太嚴謹,似有蛇足之嫌,不若直說“寫散文”“寫小說”“寫評論”。某些不便定性的索性直說“寫”什么?如此或許眉清目秀一些,還能節省版面。“從維熙自選集”似應打書名號。
其他如第83頁下數第1行:“《郝家儉賣布》系天津一紡織工人大呂所作短篇小說”。“一”似顯多余。第131頁上數第13行:“這次會議與孫犁有關的事還有一件,是會上周揚作的名為《建設社會主義文學的任務》的報告中提到了他的小說《風云初記》。”“ 是會上”和“的名為”六字似可刪去,抑或直奔主題——“會上周揚作《建設社會主義文學的任務》報告,對孫犁小說《風云初記》先揚后抑”,接著引用周揚那段話。因為背景材料前面已交代得清清楚楚,甚至稍嫌煩瑣了。
年譜從某種意義說是另一種傳記,而作品是考察譜主言行的重要依據,有必要從全集補入這方面的內容。如:
孫犁初到延安寄居騾馬店內,夜晚山洪暴發房屋倒塌,“我被洪水沖倒,棄去衣物,觸及一拴馬高樁,遂攀登如猿猴焉。大水沖擊馬樁,并時有梁木、車轅沖過。我怕沖倒木樁,用腳、腿撥開,多處受傷。”(《〈善闇室紀年〉摘抄》,全集第五卷P191)
孫犁從延安奔赴華北戰場時當毛驢隊長,偷越同蒲線命令:
凡是女同志小便,不準遠離隊列,即在驢邊解手。解畢,由牽驢人立即抱之上驢,在驢背上再系腰帶。由于我這一發明,此夜得以勝利通過敵人的封鎖線,直到現在,想起來,還覺得有些得意。(《牲口的故事》,全集第七卷P33)
讀者熱切期盼孫犁盡快寫出《鐵木前傳》姊妹篇,他也有這個想法:
在風雪天不能出門游散的時候,我就打開了封存幾年的稿件,想有所作為。但是,要想寫《鐵木后傳》,需要重新下鄉。(《津門小集·后記》,全集第二卷P280)
孫犁經魏巍介紹與江西修水的北大才女張保真通信:
發信頻繁,一天一封,或兩天一封或一天兩封。查記錄:一九七一年八月,我寄出去的信,已達一百一十二封。信,本來保存得很好,并由我裝訂成冊,共為五冊。后因變故,我都用來生火爐了。(《書信》,全集第七卷P263)
我以為文人宜散不宜聚,一集中,一結為團體,就必然分去很多精力,影響寫作。散兵作戰,深山野處,反倒容易出成果,這是歷史充分證明過的。(《答吳泰昌問》,全集第六卷P7-8)
文章窮而后工。作家不能貪圖大富大貴。魯迅引用外國人的話說:創作如果要豐收,最好的辦法,是使作家多受苦。生活太幸福,就沒有花兒開放,也沒有鳥兒歌唱了。(《作家與道德》,全集第九卷P151)
我的語言,像吸吮乳汁一樣,最早得自母親。母親的語言,對我的文學創作,影響最大。母親的故去,我的語言的乳汁,幾乎斷絕。其次是我童年結發的妻子,她的語言,是我的第二個語言源泉。(《文集自序》,全集第十卷P475)
孫犁16歲結婚,糟糠之妻不下堂,新中國成立之初受到中國文聯主席大會表揚,成為作家中不換老婆的模范。但他也有感情“開小差”的時候,盡管走得不是很遠。他《和郭志剛的一次談話》自述隱秘之情,自剖感情糾結:
個人私生活方面,我覺著也比較簡單,也沒什么很離奇的戀愛故事,有一些也是淺嘗輒止。隨隨便便就完了。但是,也留下一些印象,這些印象我也不大掩飾它,有時就在一些作品里邊寫出來了,如實地,不是加以夸大。(全集第九卷P87-88)
這些“印象”寫入《保定舊事》《病期經歷》《無花果》《頤和園》《宴會》《石榴》《憶梅讀〈易〉》《記陳肇》等憶舊文,適當引用摘錄,能夠折射出孫犁的真誠和偉大。孫犁說:
人之一生,行為主,文為次。言不由衷,其文必偽;言行不一,其人必偽。文章著作,都要經過歷史的判定和淘汰。(《遼居稿》,全集第九卷P466)
此乃不刊之論。孫犁作品之所以百讀不厭,披露腹心、言行一致是重要原因。
準確性是文章的生命線,它需要知識奠基,認真守門,才能有效防止詞義紛紜現象的發生。這個問題應該引起重視。
第11頁下數第1行:“(1937年)12月下旬,河北游擊軍成立,孟慶山任司令員,侯平(侯世珍)任政治部主任,閻久祥任參謀長。侯邀請孫犁到肅寧。”第12頁上數第2行:“(1938年)春季,受李之璉、陳喬親自至家里邀請,到人民自衛軍政治部參加抗日工作,從此正式開始革命工作。”第190頁下數第8行:“陳喬,河北安新縣洞口人,孫犁在同口教學時二人相識,是陳喬、李之璉親自到孫犁家請孫犁參加革命的。”毛澤東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邀請”或“請”不如“動員”妥帖,“受李之璉”之“受”可刪去。孫犁《吾學錄初編》云:“吾嘗思:如不參加革命,吾亦不能鄉居,不能適應當時舊風俗禮教,必非常痛苦,而不為鄉里喜歡。既不能務農,稍識字即被歧視,此余所習見也。”(第九卷P459)說明他有“主動”參加革命之意。
第30頁下數第4行:“邊區魯迅文學獎金委員會本年第一季度獲獎作品已經評定”。第35頁上數第3行:“魯迅文藝獎金委員會公布年獎,三、四季度獎”。第105頁下數第12頁:“這個劇雖獲斯大林獎金,但歪曲和侮辱了中華民族和中國偉大的勝利”。第350頁下數第5行:“中共天津市委宣傳部開會研究魯迅文藝獎金之事”。如同“魯迅文學獎”和“中國新聞獎”沒有“金”字一樣,上面四個“金”字皆須刪去。“歪曲和侮辱”可能言重了。如果蘇聯方面有意為之,就不會邀請中國作家代表團成員觀看《紅罌粟》。這并非政治問題,而是站位、表達、解讀問題。可否改為“但沒有客觀真實地反映”?
第37頁下數第6行:“(1944年)4月,出發赴延安,經過綏德,到晉綏軍區呂正操司令部,送給呂一部線裝的《孟子》”。“晉綏軍區司令部”不能稱“晉綏軍區呂正操司令部”,可將“呂正操”三字后移,“送給呂正操一部線裝的《孟子》”。這段話來自《〈善闇室紀年〉摘抄》:“晉綏軍區司令部,設在附近。呂正操同志聽說我在這里路過,捎信叫我去。我穿著那樣的服裝,到他那莊嚴的司令部做客,并見到了賀龍同志,自己甚覺不雅。我把自己帶著的一本線裝《孟子》,送給了呂。現在想起來,也覺舉動奇怪。”(第五卷P190)壓縮文字壓出了問題。
第41頁下數第2行:“不久,見到一座天主教堂。窮山僻壤也有此教的侵入。”抗戰勝利,孫犁隨團返回冀中,途經綏德見到這個教堂。《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我黨解放前同樣尊重黨外人士的宗教信仰自由。“侵入”改為“傳入”似合情合理合法一些。
第64頁下數第8行:“土改工作組結束。孫犁回到《冀中導報》。”似為“土改工作結束”或“土改工作組任務結束”。
第127頁上數第2行:“王林晚上來訪。談到方紀寫一篇文章之事(關于有人揭發蘆甸的文章的支持)”。“關于”后落“對”字?
第193頁下數第3行:“托付田間孩子長生的事情。”孫犁請托戰友陳喬,“長生”后加“工作”二字指向明確些。
第307頁上數第12行:“北京市商業局刪改《山地回憶》太多,為此生氣。”“商業局”后應加“干部”二字,這是他的個人編書行為,省卻容易誤解成單位行為。
第351頁上數第10行:“《天津日報》刊登消息:作家孫犁把1500元魯迅文藝獎金全捐贈給天津市少年福利基金會。早晨,新聞聯播也播此消息。”“魯迅文藝獎金”規范表述為“魯迅文藝獎獎金”。后一句指代不清楚。《新聞聯播》晚上播放,《新聞和報紙摘要》早晨播放。節目名稱似應打書名號。
第362頁上數第7行:“詢問《花隨人圣庵摭記》孫犁信中誤為《人隨花圣庵摭記》作者黃(黃秋岳)的生平。”此處似可簡介:黃濬(1891—1937),字秋岳,福建福州人,抗戰初以叛國罪被處決。如此讀者看到第363頁下數第5行:“感謝姜(德明)先后抄錄的黃濬材料,并認為《花隨人圣庵摭記》是下了功夫的。”或不至于把黃秋岳、黃濬錯當兩人。
第424頁上數第7行:“致自牧信。”第432頁下數第9行:“致鄧基平信。”自牧乃鄧基平筆名,兩種稱謂多次交替出現,易給讀者造成兩個人的錯覺,宜用統一稱謂。
《文匯報》筆會、《新民晚報》夜光杯、《羊城晚報》花地和《天津日報》文藝評論、文藝周刊、滿庭芳等副刊名稱,報人一看就懂,外行不一定看得明白。要不要打引號(“筆會”)?或放入書名號內(《文匯報·筆會》)?
年譜42萬字,要求零差錯有些強人所難。但國字號出版社不能滿足于差錯率不超過萬分之一的合格門檻,應該有更高的標準和追求,這方面還有努力空間。
第1頁下數第3行:“孫犁乳名振海,學名樹勛。上有兄姊五人,皆殤。”孫犁《母親的記憶》卻說:“母親生了七個孩子,只養活了我一個。”(全集第七卷第47頁上數第2行)“兄姊五人”當為“兄姊六人”。
第245頁上數第11行:“8月21日,致韓映山信。信末自注:6月21日上午。”“8月”與“6月”誰對誰錯?
第371頁下數第2行:1985年“9月3日,幾名攝影愛好者要去白洋淀采風,行前來拜望。為他們題字一幅:‘白洋淀紀行。孫犁1995年9月3日’”。“1995”當為“1985”之誤,句號可置單反引號內。
第468頁下數第12行:“寫雜作文《我的“珍貴二等”》。”“寫雜作文”當為“寫作雜文”之誤。
第529頁下數第8行:“天道無親,常與慧人——至此,孫犁完美地結束了自己創作的一生。”“慧”乃“善”之誤?《史記·伯夷列傳》引用《道德經》八字:“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老子正說,司馬遷反問:“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孫犁《曲終集》后放下手中武器——筆,徹底告別文壇。這種無奈之舉算不上“完美”。如果健康狀況允許,孫犁生命的最后六七年能留下多少精美文字啊!
我呈段華審定拙稿信中說:
以上乃一孔之見,不乏雞蛋里面挑骨頭的刻薄,權且算是拋磚引玉吧。但心是誠的,出發點是純的,目的是希望年譜再版時(封面黃色裝幀易臟宜改,設計者或許不是真正的讀書人)盡善盡美一些。我問過來新夏先生:“如果我只收藏您一部大作,您推薦哪部?”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近三百年人物年譜知見錄》。”《孫犁年譜》是能夠流傳下去的,您付出多少心血都值得。多聽聽認真看過年譜的同仁意見再動手。
(作者系北京日報社副社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