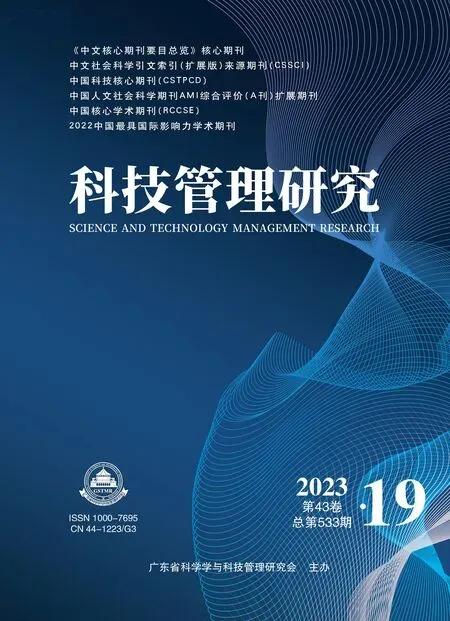中國式創新生態中的企業創新韌性:空間關聯、差異結構與政策組態
夏后學,焦婧瑤
(1.南京工業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江蘇南京 211816;2.江蘇省決策咨詢研究基地,江蘇南京 211816)
1 研究背景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我國發展進入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各種“黑天鵝”“灰犀牛”事件隨時可能發生;要著力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在美“芯片法案”脅迫、俄烏沖突、新一輪科技革命等交織影響下,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安全與穩定遭受嚴重沖擊,企業創新發展環境發生深刻變化,部分領域中小企業面臨嚴峻風險挑戰。在此背景下,構建中國式自主可控創新生態,培育企業特別是民營中小企業創新韌性,塑造企業在復雜環境下的創新能力,已是亟待深入研究且十分重要的現實問題,這在加快形成新發展格局進程中尤為突出。其中,系統梳理我國創新生態發展歷程、科學測度企業創新韌性是研究解決上述問題的基礎性工作。
在物理學中,韌性一般指物體在形變或破裂過程中吸收能量的能力,韌性越強,發生脆性斷裂的可能性越小。至今,不同領域研究學者對韌性的定義存在較大差異。根據劉曉星等[1]、Wang 等[2]的研究,韌性一般指經濟系統抵御外部沖擊的能力以及風險沖擊之后的恢復力;Duan 等[3]、魏建漳等[4]認為,相對組織韌性而言,政策和制度、社會資本、經濟結構等宏觀環境是闡釋韌性形成過程及影響因素的關注焦點;而在Rao 等[5]、Christensen 等[6]看來,韌性是主體或客體在危機、災害等困難處境中的維持能力與應變能力,包括吸收、適應、恢復與變革等維度;根據Jaaron 等[7]、Ambulkar 等[8]、Herbane[9]研究觀點,吸收通常指客體具有的環境變化感知力和抗干擾能力等,適應則是災害發生后企業維持現有經營狀況的能力,而恢復與變革一般指企業遭受外力沖擊時的承壓能力以及沖擊結束后的修復能力;盡管韌性測度體系在不同學科領域尚未達成一致看法,但Merkle 等[10]、Bohnett 等[11]在韌性內涵界定與形成因素方面已有較成熟的研究結論,即一國或地區政策與制度環境、市場體系、資源稟賦、風俗文化等具有“生態”特征的因素對韌性生成具有重要影響,在較大程度上,組織賴以生存的生態體系是孕育組織韌性果實的土壤;梅亮等[12]、Barile 等[13]、曾賽星等[14]認為,如同生物系統一樣,從要素的隨機選擇不斷演變到結構化群落,創新生態系統是在企業、消費者、科研機構、要素、市場、政策等多重因素作用下形成的相互依賴和共生演進的復雜網絡,具有生態位、生態勢、生態圈等屬性。特別是在重大突發事件等沖擊影響下,體制機制、政策、市場體系、數字化基礎設施等本土創新生態外圍結構的完備與穩健,已成為企業等內核主體維持創新的基礎性保障。然而,如何測度一國或地區創新生態孕育的企業韌性水平,進而倒逼具有本土特色的創新生態體系的完備與進階,目前仍是有待研究的新興話題。本文首先從外圍結構與內核主體視角回顧我國特色創新生態演進軌跡,認為創新生態的形成與發展是催生企業創新韌性的必要條件,企業韌性的鞏固與強化推動創新生態結構高水平演進。其次,從風險吸收、維持創新、形變恢復、柔性變革等“質”與“量”視域構建企業韌性測度體系,綜合運用探索性空間數據分析、信息熵、泰爾指數等技術方法,分地區刻畫中國式創新生態中的企業創新韌性,厘清區域企業創新韌性水平、差異結構與政策取向。
2 中國式創新生態躍遷歷程
中國式創新生態的形成和發展,與國家經濟基礎、科技管理體制、市場體系建設、企業改革、互聯網及數字技術應用等密不可分。經政府主導、政府推動、市場導向、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驅動等發展階段,逐漸形成了“內核-外圍”式體系結構,即以企業、客戶、高校院所、科研機構、金融服務部門等為主體的“內核”體系,以及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超大規模市場、新型基礎設施、政策體系、發展戰略等組成的“五位一體”式外圍結構。
2.1 新中國成立之初的艱難探索階段(1949—1977年)
這一時期,為推進我國工業化建設和國防事業發展,國家建立高度集中的中央計劃管理科技體制。在行政力量推動與宏觀調控作用下,科技資源整合機制逐步完善,戰略科技力量不斷強化,我國工業化建設和國防事業發展取得系列重大成就,為統籌發展和安全奠定堅實基礎。創新生態體系中的內核主體由中國科學院、中央部委所屬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及國防研究機構等單位組成,在國防科技攻關、技術裝備研制過程中形成了密切合作,我國創新生態體系中的主體構成與合作模式初步建立,創新生態體系建設開啟艱難探索。
彼時,不同創新主體之間的協調配合有賴于行政指令,科技創新投入和資源籌措主要依靠政府,加之企業等市場主體數量匱乏且技術創新能力有限,與科技創新相關的市場機制如要素市場、產品市場、金融市場建設步伐緩慢,在科技攻關與創新合作方面,高校院所與企業、技術開發與市場幾乎脫離,創新鏈、創新生態圈等創新生態相關組織形態尚未萌芽。
2.2 改革開放以后的發展萌芽階段(1978—1991 年)
盡管這一時期我國經濟體制仍帶有計劃色彩,但改革開放引起的一系列重要變化深刻影響科學技術發展。科技體制改革、專利立法保護、科技發展戰略、要素市場建設等為創新生態體系外圍結構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基礎。黨中央、國務院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和會議決定,以及中共中央《關于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決定》等重要文件頒布實施,進一步清除了阻礙科學技術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市場導向的經濟體制改革加快推進,我國經濟體制亦由計劃經濟逐步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渡。
這時,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作為重要市場主體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科技創新發展更加重視企業技術吸收和開發、科研與市場的銜接等,科技發展計劃覆蓋基礎研究、技術攻關、技術成果商品化等不同方面,推動創新生態體系中的技術鏈、市場鏈、價值鏈涌現,引導和強化企業、高校院所等創新主體合作。我國創新生態體系的內核主體雛形初現,體制機制、法律法規、規劃計劃等外圍結構初步形成。
2.3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生成階段(1992—2011 年)
隨著不同經濟類型的企業數量迅速擴張,以及我國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加入WTO、互聯網應用等有利條件助推,以企業、高校院所、科研機構、客戶等為主體的創新生態體系加速生成。1991 年12 月,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頒布科學技術發展十年規劃和“八五”計劃綱要,指出企業是國民經濟的主體,并從工業與交通運輸業中遴選250多家大中型骨干企業開展技術改造。1993 年11 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作出《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發展生產要素市場、金融市場、技術市場和信息市場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建立并不斷完善。與此同時,鄉鎮企業異軍突起,成為我國“三農”事業發展進程中的一個偉大創舉,進一步豐富了市場主體類型。1997 年9 月,黨的十五大提出,支持和鼓勵企業從事科學研究和技術開發,使企業成為研發投入的主體,并要求有條件的科研機構和高校院所以不同形式同企業合作或進入企業,走產學研相結合道路。同時,繼續鼓勵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建立實施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我國特色創新生態體系內核主體更加多元、合作更為緊密。
進入新世紀,互聯網在全球范圍內的迅速傳播為創新生態體系建設提供了新穎工具,創新發展迎來新機遇。互聯網的應用加快了社會分工和要素連接,創新主體可在更大范圍利用要素資源,創新合作效率得到顯著提升。國家“十五”科學技術發展規劃提出,要形成以企業為主體,高校、科研院所、中介機構、政府部門相互聯動的創新網絡,建立服務中小企業技術創新的支持系統。黨的十六大確立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實施科教興國戰略,推進國家創新體系建設。同時,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逐步建立,客戶、消費者等主體開始深度參與創新,創新生態體系的主體構成發生新變化,創新活動的體系化、協同化、網絡化特征凸顯。
2.4 步入新時代后的全面建設階段(2012 年至今)
2012 年11 月,黨的十八大提出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堅持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建立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我國特色創新生態體系進入全面建設新時代。隨后,黨中央、國務院印發《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從戰略目標、戰略部署、戰略任務等方面明確創新驅動發展“三步走”戰略,要求培育世界一流的創新型企業、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一流的科研院所、發展面向市場的新型研發機構、構建專業化的技術轉移服務體系,新型研發機構、眾創空間、孵化器、技術轉移服務部門等成為創新生態體系建設的新載體、新主體。在新發展理念指引和全面深化改革激勵之下,市場主體活力得到有效激發,為我國經濟長期穩定發展提供了蓬勃動力。2017 年10 月,黨的十九大提出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在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的進程中,要將創新擺在更加突出的重要位置,通過立法的方式不斷優化營商環境,促進市場主體活力迸發。同時,科技管理領域“放管服”改革進一步釋放研發人員、科研單位創新活力。
罕見疫情暴發以來,全球創新發展環境劇烈變遷,從韌性視域塑造企業在不確定情境下的創新能力,是有效應對外部風險挑戰的重要方面。中央和地方密集出臺減稅降費、援企穩崗等系列紓困政策,為我國創新生態體系持續發展提供了重要保障。2020 年3 月,黨中央、國務院出臺《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從促進傳統要素與新興要素發展等方面擘畫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改革,為持續推進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建設奠定堅實基礎。步入新發展階段,面對復雜多變的外部環境及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需要,黨中央、國務院提出加快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印發《關于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從市場基礎制度規則、市場設施、要素和資源、商品和服務、市場監管等方面制定系列改革方案和保障舉措,我國創新生態體系中以市場、要素、體制機制等為主要內容的外圍結構進一步完善。
這一時期,人工智能、大數據、區塊鏈等數字技術的深入應用與迭代演進,以及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的加快推進,深刻影響我國創新生態體系的內核主體構成與外圍結構變遷,推動實現如下方面的進階轉變。一是聚焦企業創新能力和創新生態建設,注重系統性的風險應對。通過全面深化改革、建設統一大市場、優化科技評價體系、實施“雙創”戰略等,營造全社會參與的創新發展環境,以發展共同體、創新聯合體等形式促進主體間協同合作。二是從創新體系分類建設向創新系統集成與體系融合轉變,建設國家科技創新體系。發展國家重點實驗室、高水平大學、新型研發機構、領軍企業等科技力量,促進戰略科技力量互聯互通和科技基礎設施共建共享。三是新一代信息技術推動傳統創新范式向以商業模式創新、營銷服務創新、創新生態圈等為主要內容的新業態轉變,突出資本、勞動力等傳統要素與數據等新興要素在基礎研究、原始創新、關鍵核心技術攻關中的深度融合。四是規劃建設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推動區域創新體系有效銜接,創新發展進入深度參與全球創新治理的新階段。
發展至今,我國特色創新生態體系基本形成企業主導,高校院所、科研機構、消費者、金融服務部門等廣泛參與,上下游銜接的內核主體架構,以及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超大規模市場、新型基礎設施、政策體系、發展戰略等組成的“五位一體”式外圍結構。外圍結構是“內核”主體協同創新的基礎保障,內核主體是推動完善外圍結構體系的重要力量,內核主體與外圍結構緊密結合共同構筑我國特色創新生態體系。其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包括市場經濟體制、分配制度等,是發展特色創新生態的根本遵循;以要素市場、產品市場、金融市場等為主要內容的超大規模市場及其規則體系,為發展特色創新生態體系提供有效供給、需求激勵和空間載體;以人工智能、大數據、區塊鏈、工業互聯網等為核心的數字技術及新型基礎設施,是優化我國特色創新生態環境的有力支撐;企業創新政策、產業創新政策、科技園發展政策等是激發創新生態活力的有效工具;區域協同(一體化)創新、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和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等發展戰略為創新生態體系向上攀升注入強大動力。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世紀罕見疫情、新一輪科技革命等疊加共振,以及一些超預期因素等交織影響下,我國特色創新生態土壤孕育的企業創新韌性果實,為推動高質量發展奠定堅實基礎。
3 企業創新韌性測度體系
3.1 指標體系
早期Holling[15]的研究將韌性定義為系統吸收變化和干擾的能力;Lhomme 等[16]將韌性定義為系統吸收擾動并在擾動后恢復其功能的能力。美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從基礎設施、社區計劃、社會系統等方面制定的海岸恢復力指數(coastal resilience index),以及Serre 等[17]從抵御能力、吸收能力、恢復能力和目標準則等維度構建的韌性空間決策支持系統(spatial decision support system),為本研究提供了有益參考。我們認為,企業創新韌性是企業在外部沖擊、不確定性等復雜情境下的創新維持能力與恢復變革能力,包括吸收、維持、恢復、變革等維度,即企業的風險吸收能力、維持創新能力、形變恢復能力、柔性變革能力等,參考Serre 等[17]、單宇等[18]的研究形成創新韌性測度指標體系,如表1 所示。

表1 企業創新韌性測度指標
3.2 方法體系
(1)熵權TOPSIS 與泰爾指數。根據陳景華等[19]的研究,熵權TOPSIS 方法在原始指標標準化處理的基礎上,首先基于信息熵相關思想客觀賦予指標相應權重,獲取觀測指標信息熵的效用價值;其次,運用TOPSIS 檢測評價對象與最優解、最劣解的距離并進行排序得到創新韌性水平。為削減不同區域可能存在的韌性水平差異,參考蔡永龍等[20]的研究,本文運用泰爾指數法識別區域企業創新韌性差異來源。該方法將總體差異分解為區域間和區域內差異,可直觀地刻畫企業創新韌性結構性差異。
(2)探索性空間數據分析(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ESDA)。本文基于探索性空間數據分析思想,運用空間自相關、吉爾里指數(Geary'sC)、莫蘭指數(Moran'sI)等方法,考察區域企業創新韌性的空間聚類與分布特征。
3.3 數據來源
當前,有關企業創新韌性的統計資料并不多見,已有研究多以調研數據為主。國家統計局在2016—2021 年出版發行的《全國企業創新調查年鑒》,為創新韌性研究提供了優良借鑒。該年鑒調查范圍涉及制造業,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批發和零售業,交通運輸,建筑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等國民經濟行業,調查對象包括規模以上工業企業、限額以上批發和零售業企業,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企業等,調查內容涵蓋產品創新、工藝創新、組織創新、營銷創新等,是較為全面反映我國企業創新情況的高質量調查資料。極個別指標的缺失值采用當年全國均值代替。因我國西藏和港澳臺地區部分指標數據缺失,研究樣本暫不包括上述地區。
4 企業創新韌性測度結果分析
4.1 企業創新韌性水平分布動態
圖1 報告了大型企業、中型企業、小型企業創新韌性水平,其中小型企業為規模(限額)以上小型企業。整體上,不同規模企業韌性水平略有起伏,中型企業韌性水平波動相對明顯,大型企業韌性水平波動較為平穩;近5 年大型企業、小型企業創新韌性均值分別為0.52 和0.40,較中型企業高67.7%、28.8%,具有“兩頭高、中間低”特征。特別地,疫情暴發前大中小企業韌性水平分別為0.52、0.31、0.42,疫情暴發后不同規模企業創新韌性分別增長2.7%、4.5%、7.1%,表明在突發事件沖擊下企業仍有良好的維持創新能力。

圖1 不同規模企業創新韌性水平
從圖2 看,得益于我國特色創新生態、發展戰略及多重政策組合形成的激勵效應,地區企業創新韌性總體趨勢平穩,發展水平從2016 年的0.21 逐年增至0.24,其中2020年創新韌性較2019年增長3.5%,在總體上反映出規模以上企業創新受疫情沖擊后的形變恢復能力較強。分地區看,創新韌性水平5 年均值排名前10 位分別為廣東(0.572)、江蘇(0.566)、浙江(0.496)、山東(0.364)、上海(0.259)、安徽(0.258)、河南(0.246)、湖南(0.234)、湖北(0.219)、北京(0.214)。由圖4 可知,企業創新韌性峰值主要集中在江浙滬、廣東等地,韌性水平與地區經濟水平存在一定關聯。疫情暴發后,韌性水平增幅較明顯的地區分布在山東(20.6%)、江西(14.0%)、北京(13.5%)、河南(12.0%)、安徽(11.5%)等。

圖2 按地區分企業創新韌性分布
上述結果表明,我國地區企業創新韌性呈東高西低、南高北低分布,具有區域分異特征。表2 報告了四大經濟帶企業創新韌性水平。從京津冀、長三角、長江經濟帶、黃河流域視角看,雖然四大經濟帶企業創新韌性稍有起伏,但總體上具平穩增長特征,疫情后四大經濟帶企業創新韌性均有不同程度增長。
圖3 為采用熵權法計算得到的地區企業創新韌性二級指標分值。整體上看,除2014 年外,其余年度地區企業創新韌性波動較小,2016—2020 年5 年均值得分排在前列的指標分別為市場開拓能力(1.408)、本土研發能力(1.029)、創新活動開工率(0.827)、創新戰略前瞻性(0.689)、合作創新穩定性(0.595),這些方面亦構成了企業創新韌性的核心維度。具體來看,人才約束容忍度、創新鏈依賴性、資金約束容忍度等指標得分在部分超預期因素影響下逐年下降,而工藝流程創新、市場約束容忍度、創新活動開工率、市場開拓能力等指標得分在疫情暴發后分別增長23.0%、8.0%、7.8%、5.1%,反映出提高企業柔性和市場約束容忍度是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影響的重要方面。

圖3 地區企業創新韌性二級指標水平
4.2 企業創新韌性空間關聯與差異結構
表3 報告了采用z 統計量和單側檢驗法得到的創新韌性空間自相關判定系數及其顯著性水平。吉爾里指數(Geary'sC)和莫蘭指數(Moran'sI)取值均在[0,1]范圍,且全局空間自相關指標在5%或10%的顯著性水平下拒絕“無空間自相關”的原假設,可認為企業創新韌性存在正空間自相關特征,即韌性水平高值與高值相鄰、低值與低值聚集。參照郭蕓等[21]的思路,我國企業創新韌性水平可分為以下4 種空間關聯模式:(1)“高-高”集聚,本區域與周邊區域的企業創新韌性均較高,呈顯著正相關,空間關聯表現為溢出效應。(2)“低-高”集聚,本區域企業創新韌性較低,但周邊區域企業創新韌性相對較高,呈負空間自相關,空間關聯表現為過渡區域。(3)“低-低”集聚,本區域與周邊區域的企業創新韌性均相對較低,亦呈顯著正相關,空間關聯表現為低增長區域。(4)“高-低”集聚,本區域企業創新韌性較高,但周邊區域企業創新韌性相對較低,空間關聯表現為極化效應。

表3 企業創新韌性空間自相關檢驗
采用莫蘭指數(Moran'sI)檢驗方法對企業創新韌性空間集聚與躍遷趨勢進行空間相關性檢驗,結果表明:(1)我國企業創新韌性具有顯著空間相關性,即本區域企業創新韌性與鄰近區域存在空間關聯,本區域與鄰近區域企業創新韌性具有一定的變化相依特征。(2)企業創新韌性空間集聚趨勢表現為東部地區“高-高”集聚,創新發展具有顯著的空間溢出效應;大多數中西部地區呈“低-低”集聚,即本區域企業創新韌性低值與鄰近區域企業創新韌性低值聚集,具有顯著的正空間相關關系。(3)在研究期內,我國大多數地區及其企業創新韌性未出現顯著的躍遷變化,僅個別地區向鄰近象限躍遷,表明企業創新韌性空間集聚特征較為平穩。(4)相比2019 年,2020 年北京、福建、河南等地企業創新韌性空間分布向“高-高”集聚躍遷,表明上述地區企業創新韌性分布在疫情影響下發生躍遷的可能性較高。
4.3 創新韌性水平差異來源及結構分解
表4 報告了東部地區、中部地區、西部地區、東北地區四大區域1)企業創新韌性泰爾指數及結構分解,結果表明:(1)2016—2020 年區域企業創新韌性差異明顯,泰爾指數總體差異從0.091 升至0.135,4 年增長48.4%,表明地區企業創新韌性水平距離進一步擴大。(2)平均而言,2016—2020年區域內創新韌性差異、區域間差異占總體差異的比重分別為52.3%、47.7%;區域內差異主要由東部地區貢獻,其5 年貢獻率分別為91.4%、92.5%、91.6%、92.7%、89.6%,即區域內差異是創新韌性水平總體差異的主要來源,而東部地區韌性水平差異則是形成區域內差異的重要因素,亦與上文結論相近。(3)東北地區、西部地區創新韌性水平差異占區域內差異的比重處于低位,表明該地區企業創新韌性水平相對均衡。

表4 四大區域創新韌性泰爾指數
5 進一步研究:政策組態
為提高企業在超預期因素沖擊和多重風險挑戰下的創新發展韌性,本文以黨中央、國務院近年實施的大規模減稅降費政策為研究視角,探討怎樣的創新政策組合有助于強化企業韌性。根據杜運周等[22]的研究,政策組合具有鮮明的組態特征,而傳統的計量經濟學方法多認為不同因素之間存在線性和單向因果關系,在揭示多變量交互對結果變量的影響方面存在局限。參照王臘銀等[23]、趙會會等[24]的經驗做法,基于組態思維構建政策組合聯動匹配框架,選取企業研發費用加計扣除稅收優惠、企業研發活動專用儀器設備加速折舊、高新技術企業所得稅減免、科技創新進口稅收優惠以及技術轉讓、技術開發收入免征增值稅和技術轉讓減免所得稅優惠等5 項主要政策,以在開展創新活動企業中認為以上政策效果明顯的企業家占比衡量政策效力并將其作為條件變量,將上文測算的企業創新韌性視為結果變量,運用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法(fsQCA)考察創新政策組合并發協同效應。參照Greckhamer[25]的研究,將條件變量和結果變量校準為模糊集,以85%、50%、15%分位數作為完全隸屬閾值、交叉點、完全不隸屬閾值,變量校準如表5 所示;同時,為規避不具代表性的條件組合,將原始一致性閾值、PRI 值、案例頻數閾值分別設為0.8、0.7、1,并通過對比中間解與簡約解確定關鍵的政策組態路徑。

表5 變量校準
從單個條件必要性檢驗結果看,任一條件的存在或缺失均不可作為高企業創新韌性的必要條件。從表6 創新政策組態路徑看,產生高企業創新韌性的組態共有3條,總體解和單個解的一致性均高于0.8且總體解的覆蓋度約0.77,表明識別出的政策組態可解釋約77%的企業創新韌性案例。從組態1a 看,以研發費用加計扣除稅收優惠政策、高新技術企業所得稅減免政策為核心條件,互補非研發活動專用儀器設備折舊政策及非科技創新進口稅收優惠政策為邊緣條件,是提高企業創新韌性的有效政策組合。該組態一致性水平為0.88,原始覆蓋度、唯一覆蓋度分別為0.32、0.13,能夠解釋約32%的地區企業案例,且13%的地區企業案例僅可通過該組態路徑解釋,多見于北京、上海等地企業案例。據統計,在大規模減稅降費政策等激勵下,北京市2022 年1-11 月大中型重點企業研發費用同比增長10%,中關村示范區規上高新技術企業技術收入占總收入的比重達21.7%,同比提高2.1 個百分點,體現強勁的企業創新韌性。組態1b 指出,除技術轉讓、技術開發收入免征增值稅和技術轉讓減免所得稅優惠政策外,余下4 項政策作為核心條件有助于增強企業創新韌性,該組態原始覆蓋度高達63%,在高企業創新韌性政策組態中居首位。該組態強調了多元政策的并發協同效應,廣東、江蘇、浙江、湖北、河南、江西、遼寧等地均出現由該組態解釋的企業案例。
在組態1c 中,企業研發費用加計扣除稅收優惠疊加研發活動專用儀器設備折舊政策、科技創新進口稅收政策以及技術轉讓、技術開發收入免征增值稅和技術轉讓減免所得稅優惠可產生高企業創新韌性,原始覆蓋度為61%,多見于山東、安徽、湖南、重慶等地企業案例。此外,非高新技術企業所得稅減免政策、非技術開發收入免征增值稅優惠以及非科技創新進口稅收政策組合對非高企業創新韌性具有顯著影響,該組態原始覆蓋度和唯一覆蓋度分別為70%、3%,在非高企業創新韌性組態中居首位。以上結論表明,企業研發費用加計扣除稅收疊加高新技術企業所得稅減免政策、企業研發費用加計扣除稅收疊加專用儀器設備折舊與科技創新進口稅收政策,是產生高企業創新韌性的兩類核心政策體系,在后者主導的政策體系中,高新技術企業所得稅與技術開發收入免征增值稅和技術轉讓減免所得稅政策或將存在替代效應。
為進一步提高上述結論的可靠性,參考孫建鑫等[26]的經驗做法,對產生高企業創新韌性的前因組態開展穩健性檢驗。首先,將原始一致性從0.8 提高至0.85,產生的政策組態與上述結論基本一致。其次,考慮到校準錨點的選取可能影響組態結果,故將原15%、50%、85%分位數分別改為10%、50%、90%分位數,依次作為完全隸屬、交叉點、完全不隸屬的校準錨點,得到的政策組態路徑亦未發生顯著變化,佐證上述創新政策組態具有良好穩健性。限于篇幅,僅報告提高原始一致性閾值得到的穩健性檢驗結果,如表7 所示。

表7 創新政策組態穩健性檢驗
6 結論與啟示
本文首先回顧了中國式創新生態發展歷程,探討孕育企業創新韌性果實的土壤結構及其演化變遷,隨后以規模(限額)以上企業為主要研究對象,從風險吸收、維持創新、形變恢復、柔性變革四大維度構建企業韌性測度體系,運用探索性空間數據分析、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等技術方法,系統梳理不同規模企業、不同區域企業創新韌性時序演化、差異結構與政策組態,得出以下結論。
(1)中國式創新生態體系歷經艱難探索、萌芽初起、加速生成、全面建設等發展階段,其主體結構可概括“內核-外圍”式,即以企業、客戶、消費者、高校院所、金融部門等為主體的內核,以及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超大規模市場、新型基礎設施、政策體系、發展戰略等組成的“五位一體”式外圍結構。
(2)從韌性水平看,受益于我國特色創新生態體系的基礎性保障,企業創新韌性總體呈增長態勢,基本呈東高西低、南高北低分布,具有區域分異特征。同時,企業創新韌性空間自相關顯著,表現為東部地區“高-高”集聚,大多數中西部地區“低-低”集聚,空間集聚趨勢平穩。
(3)從發展差異看,地區企業創新韌性水平差異具上升趨勢,泰爾指數整體差異不斷擴大,區域內創新差異是企業創新韌性總體差異的主要來源,而東部地區企業創新韌性差異則是形成區域內差異的重要因素。相比之下,東北地區、西部地區創新韌性差異占區域內差異的比重較低,表明地區企業創新韌性水平相對均衡。
根據研究結論,為有效應對超預期因素頻發和多重風險挑戰沖擊影響,進一步推進企業研發費用加計扣除稅收優惠與高新技術企業所得稅減免政策聯動匹配,釋放研發費用加計扣除稅收、專用儀器設備折舊與科技創新進口稅收政策疊加效應。完善企業、客戶、科研機構、金融部門等創新鏈主體構成,以創新鏈強鏈推動完善外圍結構體系,促進內核主體與外圍結構緊密結合,優化區域創新生態,夯實韌性培育土壤。
注釋:
1)東部地區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和海南10 個省份;中部地區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6 個省份;西部地區包括:內蒙古、廣西、重慶、四川、貴州、云南、陜西、甘肅、青海、寧夏和新疆11 個省份。東北地區包括:遼寧、吉林、黑龍江;因部分指標數據缺失,西藏和港澳臺地區暫未列入研究樣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