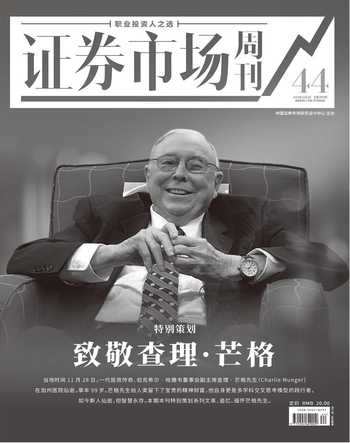北交所擴容投行集體跟進新老“王者”演繹精彩競爭
惠凱
在滬深IPO 上市節奏放緩的背景下,北交所近期股價的持續走牛營造了一二級共振的良好局面,一些符合北交所上市條件的企業攜保薦機構轉戰北交所。但不同于滬深市場,北交所的投行格局仍較為分散,很多頭部券商因受早年間新三板業務調整等因素的影響,錯過了布局北交所IPO 最佳時機。
在監管層進一步壓實中介機構的角色和責任下,近期北交所IPO 業務量排第二的券商和相關保代因IPO 業務被罰。面對交易所“壓實發行人、中介機構責任,堅持申報即擔責,嚴防‘帶病闖關’”的政策導向,在北交所這個新興市場上,投行機遇和壓力并存。
從新三板到北交所,從成交稀疏、投資價值受到質疑,到如今走出技術牛態勢、成交趨于旺盛,北交所正步入它的“高光時刻”。今年11 月以來,北證50 指數連續多日大漲,日成交額持續走高并穩定在百億元以上,成為近期引領A 股行情的“旗手”。
北交所熱度的持續走高,是有堅實的政策和基本面基礎的。不久前證監會發布的《關于高質量建設北京證券交易所的意見》,速度和力度就超出了市場預期,投資者適當性、上市標準、轉板機制、融資融券等多項制度利好的逐步落地讓很多資本興趣大增。此外,在當前小盤股、微盤股板塊走俏的大背景下,北交所還聚集了一大批專精特新概念的“小巨人”企業,匯聚了不少新能源、新材料行業的成長型公司。對比目前滬深市場中的良莠不一的小盤股,北交所主流企業的業績和硬實力顯然更為扎實。
更為重要的是,北交所二級市場的火熱也為一級市場提供了良好土壤,在近期滬深交易所IPO 有所降速下,發行節奏不受限制的北交所市場成為很多投行的“必爭之地”。據統計,在IPO 節奏優化后的首月(9 月份),全市場IPO 注冊數下降到17 家,其中,主板、科創板、創業板分別有3 家、2 家、1家,而北交所公司卻達到了11 家,月度注冊量創下年內新高。
據了解,在《關于高質量建設北京證券交易所的意見》出爐后,企業可直接掛牌、縮短新三板掛牌時間就可申報北交所的吸引力較大。利好政策助推下,進入11 月份后,北交所擴容加速,月內有9 家企業IPO 受理,其中有一些是此前滬深IPO 遇阻后轉戰北交所的發行人。
值得一提的是,在滬深IPO 發行節奏放緩,而北交所發行又不受限下,“三中一華一海”等大型券商很可能會將更多精力轉向北交所,將其視作中短期內投行業務的“主戰場”。
對券商來說,北交所市場機遇和挑戰并存。2019 年前后,A 股市場IPO快速擴容,一些后進券商為提升效率,采取了高薪聘請其他券商成熟保代團隊攜項目跳槽的方式來快速增厚自己的項目儲備。此外,一些老牌投行比如西南證券、廣發證券等,因保薦項目出現較嚴重的財務問題引發重罰,使得部分骨干保代跳槽到其他券商,而其所負責的IPO 公司也往往會選擇保代的“新東家”來接替保薦承銷工作。比如大鵬工業在2021 年創業板IPO 失敗后,近期沖擊北交所就更換了保薦機構,不再選擇申萬宏源承銷保薦為上市合作券商。
iFinD 顯示,從北交所開板到現在,已上市+未上市的保薦總業務量排名中,保薦業務量超過20 家的券商有5 家,其中前三家是中信建投有39 家,開源證券有36 家,申萬宏源承銷保薦有32 家,其后是東吳證券、安信證券。
中信建投之所以能在北交所項目上“力拔頭籌”,主要就在于其持續多年的跟進,而開源證券的成功,則凸顯了不少券商戰略調整的遺憾。
2015 年前后,多數券商涌入新三板市場,把新三板作為業務重點的券商不止開源證券,但2016 年新三板驟然進入“冰河時代”且持續低迷,不少券商又開始裁撤新三板業務團隊,尤其2017 年下半年開始,越來越多的投行開始裁撤新三板團隊。比如某龍頭券商在2017 年后調整了組織架構,只保留新三板業務部門作為公司一級部門,各地分支執行團隊或被裁或并入總部投行,而正是這一調整,讓其錯失布局北交所最佳時機,目前其在北交所中IPO 業務量僅排在10名左右。
類似的情況還有國信證券,盡管公司的新三板業務部門得以保留,但人員配備也是大幅減少,現如今,國信證券的北交所IPO 業務量僅排在全行業25 名左右。
一位受訪保代坦言,北交所單家公司上市募資額低于滬深IPO,此前一些大型券商權衡后決定不對北交所業務投入太多資源。公開信息顯示,北交所成立以來,單家企業的上市募資額大約在兩億元左右。而這可能也是北交所開板兩年多,部分大型投行投入資源不多、展業動力不足的原因之一。
截至目前,在傳統的頭部投行“三中一華一海”中,海通證券的北交所IPO 已上市+ 未上市公司數是10家,國泰君安是8 家,而招商證券、國信證券、光大證券等均為6~7 家左右,排在20 名左右或更低。華泰聯合的北交所保薦IPO 項目有4 家,排名約35名左右。
不同于滬深市場,北交所IPO 項目中,投行的格局分布較為分散、集中度偏低。比如在承銷保薦費用排名前十的IPO 項目中,業務量在全行業中排第二位的開源證券只有一單。考慮到當前北交所業務量居前的投行不乏中型券商,在研究水平、保薦資歷、承銷能力方面,往往弱于傳統頭部投行,在大行投入更多精力下,未來北交所保薦機構集中度是否會趨于集中,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
需要注意的是,北交所的撤否現象較頻繁。比如申萬宏源證券承銷保薦公司的北交所首發保薦業務總量僅次于中信建投、開源證券,迄今擔任了32 家北交所公司的上市保薦機構,iFinD 顯示,這些項目中有10 家被審核終止。
招商證券擔任了8 家公司的北交所IPO 保薦機構,其中,中鎂控股、集美新材IPO 終止。更嚴峻的是光大證券,其作為6 家北交所公司IPO 的保薦機構,有三個項目被終止,分別是振有電子、騰信軟創、秦森園林。11 月24 日,南京試劑終止北交所IPO,作為最新一個終止審核的案例,南京試劑的保薦機構選擇的是同為江蘇籍券商的華泰聯合。
一些企業和券商寄希望于把滬深市場的傳統模式照搬到北交所,以此來擴大自己的成單率,比如北交所IPO 業務量排在15 名左右的財通證券。今年10 月,眾合科技公告稱計劃分拆子公司浙江海納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交所上市,上市輔導機構是財通證券。
往年“A 拆A”情況在A 股頗為流流行,但今年受阻,多數還未上市的“A 拆A”動作被終止,那么“A 拆北”是否會成為分拆上市的另一個出口?一個多月過去了,浙江證監局還未公布財通證券和海納股份的輔導公告。直到11 月24 日,浙江證監局發布了對眾合科技和總經理潘麗春等高管的《采取責令改正措施的決定》顯示:眾合科技未對海納股份上市事項履行相應審議程序,且未按規定進行信息披露。海納股份和財通證券的北交所上市合作能否繼續,未來還需觀察。
同滬深交易所類似,全面注冊制下,中介機構是否履職盡責也是北交所監管導向的關注重點。在今年11 月的金融街論壇上,北交所董事長周貴華表示:“要推動股票發行注冊制在北交所走深走實,以信息披露為核心,在減少管制的同時加大發行監管力度,提升審核問責的精準性、有效性,壓實發行人、中介機構責任,堅持申報即擔責,嚴防‘帶病闖關’。”
嚴監管基調下,有越來越多的中介機構受到北交所的處罰。今年7 月,北交所發布監管決定,由于相關公司IPO 過程中存在違規行為,決定對天健會計師事務所的何降星、徐毅、曹小琳采取自律監管措施,這是北交所的首個中介機構被監管案例。
最新一個保薦機構被處罰的案例是開源證券保薦的箭鹿股份。今年11 月中旬,北交所發布公告指出,開源證券及保代在箭鹿股份IPO 項目中存在對發行人收入函證程序執行不到位、對發行人關鍵人員的異常資金流水核查不充分等嚴重問題,據此對開源證券、保代向明明、保代孫鵬出具警示函。
對于北交所的“錢景”,有業內人士在興奮之余也表示應理性看待。資深保薦代表人、IPO 上市號創始人何道生向本刊表示:北交所2022 年募資總額約167 億元,其中IPO 募資總額163 億元,今年1~11 月募資總額大約140 多億元(iFinD 統計口徑),體量較滬深市場還比較小。“綜合考慮新三板創新層掛牌滿一年、符合‘專精特新’、年凈利潤3000 萬元~5000 萬元等條件,北交所擬IPO 公司的數量并不是特別多。投行未來的競爭會比較激烈。”
(本文提及個股僅做分析,不做投資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