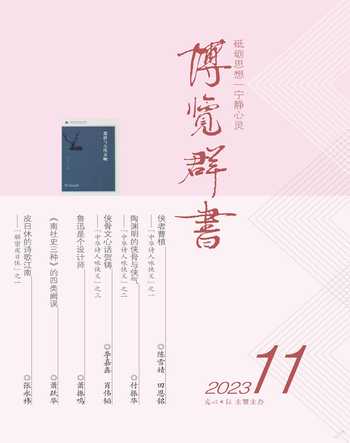皮日休詩的“載道”主張與實踐
孫笑娟
晚唐文人皮日休以儒家思想為精神內核,接過韓愈“文以載道”的理論旗幟,推舉儒家圣人之道,強調文學的美刺、教化之用,于一片頹靡之音中,爆發出時代的強音。他在《請韓文公配饗太學書》文中極贊韓文:“夫今之文,千百士之作,釋其卷,觀其詞,無不裨造化,補時政,系公之力也。”皮日休之所以如此推舉韓愈,正是因為韓愈之文擔負起了傳播儒家圣人治世之道的重任,其中,“裨造化,補時政”的儒家功用主義文學觀正是皮子文學思想的核心,故其在《皮子文藪》序中強調此十卷詩文“皆上剝遠非,下補近失,非空言也”。
關切社會民生
皮日休心系民瘼,詩興亦多因民生疾苦而發。他在《正樂府十篇》之序亦云:
樂府,蓋古圣王采天下之詩,欲以知國之利病,民之休戚者也……詩之美也,聞之足以觀乎功;詩之刺也,聞之足以戒乎政。
皮日休將所作十篇樂府詩稱之為“正樂府”,即是取撥亂反正之意,企圖以此恢復詩歌觀百姓民生與察政治得失的作用。
我們先來看皮日休的《卒妻怨》:
河湟戍卒去,一半多不回。
家有半菽食,身為一囊灰。
官吏按其籍,伍中斥其妻。
處處魯人髽,家家杞婦哀。
少者任所歸,老者無所攜。
況當札瘥年,米粒如瓊瑰。
累累作餓殍,見之心若摧。
其夫死鋒刃,其室委塵埃。
其命即用矣,其賞安在哉?
豈無黔敖恩,救此窮餓骸。
誰知白屋士,念此翻欸欸。
此詩將敘寫視角聚焦在“卒妻”這一特定的身份上。作為戍卒之妻,她既要承受丈夫因戍邊而不幸離世的痛苦,還要在家徒四壁的困境中艱難存活。然而,時疫肆虐,又逢荒年,百姓饑饉,餓殍遍地。作為戍卒遺孀,卒妻不僅沒有受到朝廷的半分恩賞與優待,反而落得身委塵埃的悲慘結局。皮日休通過“卒妻”這一小人物鋪開描寫的寬度與廣度,將戍卒之苦、卒妻之哀、荒年之難、人命之輕納入筆下,客觀而又真實地再現了晚唐時期民生凋敝的慘狀。
皮日休還選擇了“橡媼”“隴民”“農父”等具有特定身份的下層人物,全方位展示社會苦難。《橡媼嘆》中的黃發媼雖然“山前有熟稻,紫穗襲人香”,但因田稅苛重與狡吏勒索,只得在荒蕪山崗撿拾橡子以充饑腸。《哀隴民》中,蚩蚩隴民為滿足上層社會玩賞鸚鵡的愛好,被迫登上萬仞之高的隴山之巔,卻落得“百禽不得一,十人九死焉”的凄慘下場,可見隴民生活之艱苦、生存之艱難。《農父謠》則以農父這一底層人物為切入點,以其“農父”之口親述遭遇感慨,筆鋒越發直接、犀利。農父冤辛苦,向世人述其情:
難將一人農,可備十人征。
如何江淮粟,挽漕輸咸京?
黃河水如電,一半沉與傾。
均輸利其事,職司安敢評!
三川豈不農?三輔豈不耕?
奚不車其粟,用以供天兵?
此詩敘議結合,以農父之口陳述農事之艱難,其不述躬耕之苦,而是將矛頭對準了京師對農民的盤剝與掠奪。不合理的運輸方式,掌管物資運輸官員的以權謀私,以及舍近求遠的征糧政策,加重了江南地區農民的負擔。漕運傷民,惡性循環,農父苦不堪言。
皮日休對民生疾苦感受頗深,在詩歌中還毫不避諱地提及官吏兇狠、貪婪的丑態,如《貪官怨》:
國家省闥吏,賞之皆與位。
素來不知書,豈能精吏理。
大者或宰邑,小者皆尉史。
愚者若混沌,毒者如雄虺。
傷哉堯舜民!肉袒受鞭箠。
吾聞古圣王,天下無遺士。
朝廷及下邑,治者皆仁義。國家選賢良,定制兼拘忌。
所以用此徒,令之充祿位。何不廣取人?何不廣歷試?
下位既賢哉,上位何如矣?胥徒賞以財,俊造悉為吏。
天下若不平,吾當甘棄市!
因朝廷在選拔人才之時,未以“仁義”之士為先,又對所擇官吏不加束縛,以致所選“人才”不通詩書,不精吏治,愚蠢者對生民之苦視而不見,狠毒者殘害百姓不知收斂,無辜百姓因此受難。面對朝廷人才選拔機制的弊病以及由此帶來的一系列后患,皮日休提出“廣取人”“廣歷試”的建議,企圖沖破當權者以門蔭或裙帶關系壟斷科舉,致使賢良之士難以入仕的局面。這不僅是皮日休放眼大局提出的建設性意見,也是他立足自身處境發出的呼號。
清胡壽芝評皮詩云:
《正樂府》十章,雖不及樂天《新樂府》深透沉痛,而指抉利弊,何讓諷喻。時無忌諱,乃得此稗世之作。(《東目館詩見》)
皮日休對社會民生苦難的揭示,對官吏陰狠毒辣的披露,對不合理的制度的批判,皆筆鋒犀利,毫不留情, 真正踐行了“詩可以觀”的社會功能,其思想“實上承韓愈以文明道之旨,而益以闡發”(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
追慕經綸賢才
皮日休始終堅守儒家之道,強調入世,志存天下。科舉則為寒門子弟實現儒家理想提供了可靠途徑,然而,科舉制度發展至晚唐早已變了味道,世家貴族及官僚將科舉的決定權牢牢握在手中,中第者多“以門閥取之”,有真才實學的寒門子弟可及第者寥寥無幾。皮日休看到了仕進之難,故在科舉之前,編撰《皮子文藪》“送呈在社會上、政治上、文壇上有地位的人,請求他們向主司推薦,從而增加自己及第希望”(程千帆《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然,賢能之士屢屢落第的現狀擺在眼前,使皮日休心中始終縈繞著酸澀與苦楚,其不禁搦筆和墨,以詩歌的形式揭露這一黑暗的制度。《賤貢士》云:
南越貢珠璣,西蜀進羅綺。到京未晨旦,一一見天子。
如何賢與俊,為貢賤如此。所知不可求,敢望前席事?
吾聞古圣人,射宮親選士。不肖盡屏跡,賢能皆得位。
所以謂得人,所以稱多士。嘆息幾編書,時哉又何異!
《禮記·射義》云:“諸侯歲獻貢士于天子,天子試之于射宮。”古代明君圣主選才擇賢,總是親自考核,所選皆賢能之士。而今珠玉之士不僅難以面見天子,且為朝廷所賤待,如此境遇,又怎么能希求天子能夠如秦孝公接見衛鞅般“不自知膝之前于席”呢?
皮日休雖心存郁悶卻并未消沉,其追慕經綸賢才,常以古之圣賢為榜樣,借此抒泄心中塊壘。
首先,皮日休常借賢相能將之事跡,抒發心中之志。《七愛詩》之《房杜二相國(玄齡、如晦)》《李太尉(晟)》即是。《房杜二相國(玄齡、如晦)》云:
吾愛房與杜,貧賤共聯步。脫身拋亂世,策仗歸真主。
縱橫幄中筭,左右天下務。骯臟無敵才,磊落不世遇。
美矣名公卿,魁然真宰輔。黃閣三十年,清風一萬古。
巨業照國史,大勛鎮王府。遂使后世民,至今受陶鑄。
粵吾少有志,敢躡前賢路。茍得同其時,愿為執鞭豎。
房玄齡與杜如晦為唐太宗李世民的宰相,《舊唐書·房玄齡杜如晦傳》載:
世傳太宗嘗與文昭圖事,則曰“非如晦莫能籌之”。及如晦至焉,竟從玄齡之策也。蓋房知杜之能斷大事,杜知房之善建嘉謀。
房玄齡擅長出謀劃策,杜如晦則善于在諸多的謀劃中做出定奪,史書美稱二人為“房謀杜斷”。皮日休之所以愛慕房杜二相,既是欽佩二人才華蓋世,更是羨慕他們可得遇明主,施展抱負,創立萬世功業,名留千古。皮日休心中之志,便是渴望有朝一日能夠循著房杜二相的足跡,輔明君,創巨業。
其次,皮日休對清高正直的良吏亦贊賞有加。身懷“匡皇符”的安邦濟民之志的皮日休積極入世,企盼能夠得到賞識,入朝為官,實現理想抱負。如何能夠拯唐王朝于危難之時,匡扶皇室?政績斐然的清介能臣為皮日休的為官之路指明了方向,《七愛詩》之《白太傅(居易)》云:
吾愛白樂天,逸才生自然。
誰謂辭翰器,乃是經綸賢!
欻從浮艷詩,作得典誥篇。
立身百行足,為文六藝全。
清望逸內署,直聲驚諫垣。
所刺必有思,所臨必可傳。
忘形任詩酒,寄傲遍林泉。
所望握文柄,所希持化權。
何期遇訾毀,中道多左遷。
天下皆汲汲,樂天獨怡然。
天下皆悶悶,樂天獨舍旃。
高吟辭兩掖,清嘯罷三川。
處世似孤鶴,遺榮同脫蟬。
仕若不得志,可謂龜鑒焉。
皮日休之愛白居易,簡直是將其當成了自己的偶像。縱觀皮子一生,其雖未達到白居易的政治高度,但創作經歷與心態轉變與之十分相似。未第之前,皮日休所作之詩文皆以“上剝遠非,下補近失”為旨歸,儼然是對白居易前期創作“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路子的模仿與追尋。后其與陸龜蒙相識,往來唱和,多抒發超逸悠然的情感,此又與白居易后期詩歌表現“知足保和,吟玩性情”的淡薄閑適之情調不謀而合。
此詩與其說是對白居易的仰慕與贊美,莫若說是他政治理想的寄托。皮日休筆下的白居易儼然是一位藝德雙馨、清介正直、聲望遠播而又心系政治的賢才,詩之多角度、多方位地對白居易的文才、政才進行稱贊,乃是基于其內心深處對此類文人、政才的艷羨與渴望。自詡身負異才的皮日休渴望能夠如同白居易一樣,于朝堂之上施展理想抱負,獲得清明聲望,故其贊美之,追慕之。皮日休既以圣賢之人為榜樣,寄托政治理想,亦從賢良身上尋找調和理想與現實矛盾的方法。皮日休雖欲挽晚唐頹勢,振綱紀,拯黎民,以補時補教為志,然而,殘酷黑暗的現實卻使皮日休的政治生涯舉步維艱。如何彌合現實與理想的差距,皮日休將目光放在了前賢身上。白居易率性超脫、卓然獨立的處世哲學與適性逍遙,為皮日休指明了另一條人生道路,使其在仕途不如意之時,仍可為身心找到歸宿。
《七愛詩》之《盧征君(鴻)》中的盧鴻亦能夠在紛紛擾擾的塵世中,保持自我人格的高潔:
天下皆哺糟,征君獨潔己。天下皆樂聞,征君獨洗耳。
天下皆懷羞,征君獨多恥。銀黃不妨懸,赤紱不妨被。
而于心抱中,獨作羲皇地。
盧鴻不屈志從俗,不為名利所誘、物欲所惑的氣節,以及追求精神“自適”人格態度令皮日休追慕不已。“粵吾慕真隱,強以骨肉累”,皮日休何嘗不想達到盧鴻身心高度自由的境界,但是他身在藩籬中,心為形役,難以放下“立功揚名”的政治理想。他對自身的認知清晰且深刻,故云“如教不為名,敢有征君志”。皮日休內心十分清楚,若要得到精神上的曠達自適,首先要消解對功名的執著追求,但他無法放下,又無法打破現實的殘酷與黑暗,因此他反復地歌詠通脫率性的賢人,以此安慰躁動的靈魂,彌合理想與現實間的裂隙。
直承美刺風雅
皮日休繼承了《詩經》開創的風雅傳統的現實主義創作,以詩歌反映“國之利弊,民之休戚”,其“上剝遠非,下補近失”的創作原則,“非有所諷,輒抑而不發”的創作取向,以及頌美諷諫、補察時政的詩篇均是對風雅傳統與風雅精神的堅守與闡釋。
皮日休的《三羞詩》,或傷忠臣被謗,或哀征兵之苦,或憫荒年離亂,字字皆血,句句皆淚,于史有證,真實、典型地鋪開了晚唐末世充滿混亂與死亡氣息的社會畫卷。此三首作于唐懿宗咸通七年,詩前小序細致交代了創作的緣由。皮日休“射策不上”,退居肥陵,出都門時見“朝列中論犯當權者,得罪南竄”的現象,“愵然泣,衂然羞”,因作《三羞詩》其一。皮日休以鋒利的筆觸諷刺了懿宗年間奸臣當道、忠臣被謗的政治現實,“忠者若不退,佞者何由達,君臣一肴膳,家國共殘殺”,小人得道以致君子蒙難,君臣異位,乃使家國秩序顛覆。“倉惶出班行,家室不容別,玄鬢行為霜,清淚立成血”,被貶之臣無法與家人道別就要被倉惶驅逐,何等悲哀,何等可憐,無怪乎詩人見此情景要愁結心頭,泫然落淚了。
《三羞詩》其二云:軍庸滿天下,戰將多金玉。刮得齊民癕,分為猛士祿。
百姓不僅要為兵為卒,隨時付出生命的代價,更被搜刮殆盡。強征而來的許昌師旅意氣風發進擊南詔卻慘敗而回。“昨朝殘卒回,千門萬戶哭,哀聲動閭里,怨氣成山谷”,陣亡士兵的親屬悲痛欲絕,哀慟之音縈繞城郭,怨恨連天,百姓所遭浩劫與所受傷痛可見一斑。
《三羞詩》其三,作于皮日休退居肥陵別墅時,逢浙東淮泗叛亂,淮右潁川一代蝗旱嚴重,民生凋敝,他目睹了民生之苦難。詩歌真切地還原了懿宗年間淮右地區人民的悲慘境遇:荒年饑饉致使家破人亡,夫妻相離,親子相棄,兄弟陌路,人間種種悲劇一一上演。熱鬧的故土一夕之間變成“荒村墓鳥樹,空屋野花籬”的慘狀,“兒童嚙草根,倚桑空羸羸。斑白死路旁,枕土皆離離”,哀鴻遍野,生靈涂炭,唐末流民慘狀,如在目前。
《正樂府十篇》亦是皮日休秉持“有可悲可懼者,時宣于詠歌”的原則進行的創作,借鑒了白居易新樂府“一吟悲一事”的創作方式,細致而又集中地對苦難進行客觀描述,以犀利之筆,賦陳目之所及、耳之所聞的客觀現實,觀其文可知社會之弊、生民之病,頗為真切。
皮日休心懷救時濟世的儒家政治理想,繼承了韓愈“文以載道”的文學觀與白居易開創的新樂府傳統,多興發于民生疾苦等社會現實,其或有感于民眾備受盤剝之苦,或有諷于官吏之狡詐無情,皆于時有補,真實、細致地反映了晚唐的社會現實,有別于晚唐雕金琢玉、傷時懷舊的風氣,自拔于流俗,“在唐末混亂靡萎詩壇之中可說是極有價值的一派”(蘇雪林《唐詩概說》)。
(作者系文學博士,邯鄲學院文史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