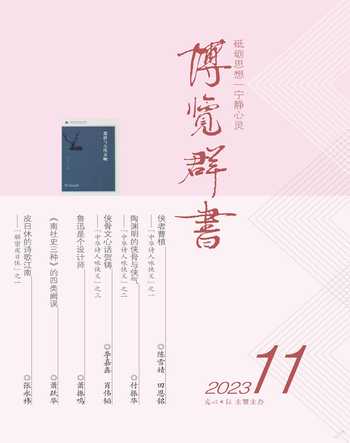“關鍵是研究要深入下去”
湯序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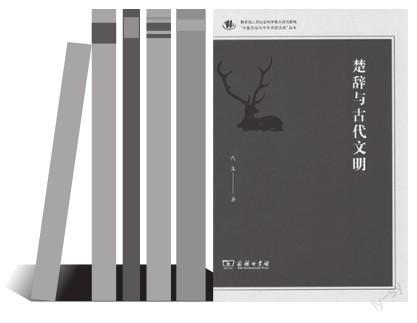
此標題乃借已故楚辭學大家陳子展先生語而來。日前,我有幸讀到山東師范大學代生副教授的新作《楚辭與古代文明》(商務印書館2022年版),是書乃作者真正“深入下去”之作,而在楚辭與古代文明兩個領域均有不俗成就,是近年來難得的佳構,令人讀后,不禁擊掌稱賞。
代著正文除緒論、結語外,共分四章;另有兩個附錄。緒論總結考古發現與楚辭研究的相關成果,指出其中的特點和尚待解決的問題,說明“本書的選題及理論方法”。第一章,以考古資料為基礎,探討《天問》所保存的上古史事,如早期夷夏關系等重大難題;第二章,結合出土文獻,研究和辨正楚辭所涉的古史人物如禹、啟、伍子胥等的事跡。第三章,依據考古資料,推進楚辭神話、神祇的研究。第四章,以《天問》為中心,結合上博簡考察屈原的歷史觀及其創作來源。結語,對全書進行簡要總結。附錄一各篇皆著重以考古資料研究楚辭的相關問題,每多創見;附錄二共《淺論孫作云先生的楚辭研究》《讀〈楚辭類稿〉札記》兩文,均甚具識力。
史學名家王曾瑜曾感慨道:
盡管大家都不會承認自己是不老實治史,但實際上,治史確是存在著老實治史和不老實治史之別。老實治史的規則其實相當簡單,如前輩王毓銓先生從秦漢史改行治明史,他的辦法也無非是通讀《明實錄》,并做了大量的史料卡片,就成為公認的明史大家。
代氏乃“老實治史”者,“一本書(《天問纂義》)抄寫下來,我有了豁然開朗的感覺”(《后記》)。代氏在讀碩、博期間,皆以《楚辭》作為自己主攻方向。該書是他在碩士論文《考古發現與〈天問〉的研究》(2008)、博士論文《考古發現與楚辭研究:以古史、神話及傳說為中心的考察》(2011)基礎上的修訂升級版。鉤沉搜佚、爬羅剔抉,可謂“十年磨一劍”。史學名家安作璋曾對自己這位弟子說:“做學問,只有持之以恒鉆研下去,才能取得成就,淺嘗輒止是永遠不能成功的。”他一直遵循老師的教導,以歷史學家的身份堅持不懈地研究楚辭,并以楚辭為突破口,繼而探討中華古文明。
眾所周知,《楚辭》一書具有卓越的文學價值;然這一中國古代文明的“寶藏”,兩千年來卻一直未被學界重視,而至王國維才“發其端”(P3)。王氏發表于1917年的《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最先采用“二重證據法”來破解楚辭中的“密碼”,指出《天問》“該秉季德,厥父是臧”之“該”,即卜辭所祭之殷先公王亥,王亥之父即卜辭中的王季。此二句說王亥能秉承王季之遺德?“這一研究可謂‘鑿破混沌,意義甚大”。(P38)在代氏看來,王氏的研究既“證明了楚辭的重大史料價值”,又“為楚辭研究指明了”另一“方向”,而其“本書的主旨,即通過考古發現(包含考古遺址、出土器物、出土文獻等)來解析楚辭,探究楚辭中的文明史內涵及其價值”(P4-5)。此真“識其大者”者也,而是書即作者往這另一“方向”努力的重要成果。
王國維曾說:“研究中國古代史,為最糾紛之問題。上古之事,傳說與史實混而不分。史實之中,固不免有所緣飾,與傳說無異;而傳說之中,亦往往有史實為之素地:二者不易區別,此世界各國之所同也。”(《古史新證·總論》)“上古之事”云云,《楚辭》之謂也。代氏認為,以“二重證據法”為指導,《楚辭》中的許多“上古之事”,經過考古資料的印證,不僅可以證明其真實可靠性,而且其中的傳說與附益成分,也得以分解、辨明。見于此,代著在前賢的基礎上,利用新出材料,后出轉精,取得了新的突破。
《楚辭》中所見的“上古之事”,主要集中在《天問》一篇。代著既以此為研究中心,《天問》自然是其研究的重點。屈原在詩中,針對夏、商、西周、春秋時的古史與傳說,一口氣提出170多個問題,步步追問,環環相逼,氣勢磅礴。是以,清代學者夏大霖譽之為“奇氣縱橫,獨步千古”。歷史學家兼楚辭學家的孫作云也說:“研究上古史的人絕對不能忽視這篇作品。”盡管《天問》的研究成果已極豐富,但代氏經過努力,仍能挖掘出不少尚未被學者注意的重要史事,并將之與古史建立聯系:一、《天問》保存了大量有關東夷習俗的史料,如后羿好射之“封豨”乃東夷族廣泛存在的葬豬、殺豬祭祀習俗的“遺存”;二、《天問》某種程度上道出了五帝時代中期至夏初東夷、華夏兩大集團的密切關系;三、《天問》保存有易氏的某些資料,除有易氏和商先公王亥、王恒婚姻與斗爭的關系外,還記錄了商湯借助有易氏勢力滅夏的史事;四、《天問》記錄了商末周初的一些史料,如紂王通過俎醢的方式強迫文王盟誓等等。總之,《天問》對于上古歷史文化研究而言,實在是一座巨大的寶庫。(參第一章)
同樣出彩的是,代氏結合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簡,從史源學的角度對屈原創作過程進行考察,辨析詩中的史實與附會成分。我們知道,這批楚簡中有五篇楚辭類作品皆不見于今存文獻。從體裁和句式看,其比屈原作品更具原始性。如屈原時代流行的《容成氏》一篇,“從上古帝王容成氏講起,一直到武王克商,是對上古史事的系統記載。其中內容多可與《天問》相印證,有些問題,正是借助該篇才能使《天問》得到正解。而且《天問》的古史傳說中,最為學者稱道的王亥、上甲微的史事也見于清華簡,故而可以說,目前出土資料所見的古史傳說,與《天問》相比,并不遜色。屈原的創作《天問》時,極有可能參考了這些資料”(P191)。比較詩篇的用詞、句式與思想各方面,上博簡《李頌》篇與今本楚辭《橘頌》篇,兩者有著極為相似之處。考慮到“屈原之后,形成了一股模擬屈原作品的風氣。根據與上博簡楚辭類作品的比較”,不難推測,“屈原極有可能也模擬他人作品,不僅用詞,在主題思想等方面也有參照”(P187注3)。最明顯的是《天問》中所載伊尹事跡。伊尹是夏末商初一位舉足輕重的人物,他的事跡在甲骨卜辭、青銅銘文、簡牘、帛書中廣泛記載,而在今存先秦文獻中,記載伊尹事跡最為全面的,要數《天問》。“據統計,《天問》僅有172句1550多字,但有關伊尹事跡的就是多達14句120字,其中包括了他的出生、身份、經歷、死后受祭等。可以說,《天問》為我們提供了一份完整的伊尹‘履歷表。”(P94)但比類整合以上述各種材料后,不難發現,屈原對伊尹的認識,顯然“受到了時代的影響,把伊尹看作出身低微的人”。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天問》的史詩性質,因為“其中包含了大量的歷史信息,多數資料可與出土甲骨,金文資料記載相合”。(P102)
代氏是姜亮夫、孫作云、李學勤諸先生的再傳弟子,學術功力深厚。書中對諸說作了有理有據的辨正,多有超軼前賢時彥者。是可謂一家之說也。另外,代著的部分內容一經發表,即引起學界注意,如被《新華文摘》等權威期刊轉載。
漢學名家楊聯陞在《書評經驗談》中曾說:“許多人認為書評不重要。我則以為一門學問之進展,常有賴于公平的評介。”的然。平素我喜歡讀書評,亦喜歡寫書評。葉公超曾說,“書評是作者和讀者的見解和趣味的較量”。我寫此書評亦是抱著這種心態的。
(作者系貴州大學兼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