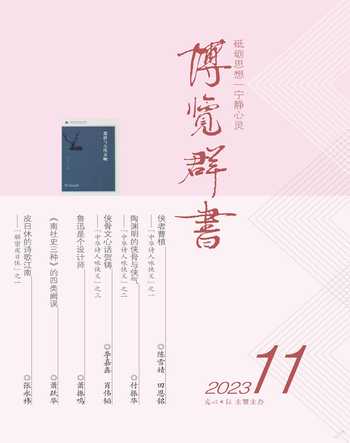理解“大藝術家”
劉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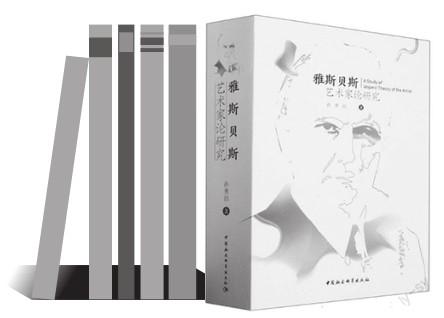
孫秀昌教授長期致力于雅斯貝斯(Karl Jaspers)學說的研究。2006年5月,他撰寫的《生存·密碼·超越——祈向超越之維的雅斯貝斯生存美學》通過中國人民大學博士學位論文答辯(人民出版社2010年5月版),這是漢語學界第一部系統研究雅斯貝斯美學思想的專著;2020年6月,他翻譯的《斯特林堡與凡·高》(雅氏早期藝術家專論的代表作)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這是該書在漢語學界的第一個中譯本;2023年2月,他撰寫的《生存·悲劇·超越:雅斯貝斯〈悲劇的超越〉導讀》由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出版,該書被列為潘知常教授主編的“西方生命美學經典名著導讀叢書”之一種。在與雅斯貝斯進行的近二十年的生命對話中,孫秀昌循著專題研究與原典翻譯相互成全的治學路徑,不斷地敞開著雅氏學說的多重面向。他最近出版的《雅斯貝斯藝術家論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3年7月版),系其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雅斯貝斯藝術家論研究”的結項成果,這部一百萬言的書稿是漢語學界首部深入探究雅氏藝術哲學思想的學術著作。
壹
正如作者在該書“緒論”部分指出的,雅斯貝斯并不是一位嚴格意義上的學院派哲學家:
他從未將喚醒生存意識的哲學活動當作一種專業化的職業來對待,也沒有興趣自創一套自圓其說的哲學思想體系。就其藝術哲學思想來看,他始終立足于“生存”這一根源來思考哲學與藝術的張力問題,他的諸多見解并沒有像康德的 《判斷力批判》、黑格爾的 《美學》、 叔本華的《作為意志與表象的世界》那樣以某種美學體系的形式公之于世,而是散見于其畢生精神求索的多種著述之中。(《雅斯貝斯藝術家論研究》,P10)
這意味著對雅斯貝斯“藝術家論”的研究需要面向他的宏富的哲學文本,從總體上把握其中心命意與致思理路,只有這樣,才有可能通過細致的爬梳和深度的闡釋,理解作為雅氏生存哲學有機組成部分的“藝術家論”;與之相應,把“藝術家論”安放在雅氏哲學大廈中“是其所是”的位置,又可從整體上推進對其生存哲學的理解。
該書正是在這種良性的“闡釋循環”中考察雅氏與其心儀的“大藝術家”所進行的對話,并介入其中與雅氏及其所論的藝術家展開對話。這讓該書在方法上頗為切近雅氏“做哲學”的旨趣,即用體驗性的思維(而非科學性的說明)來理解作為“大哲學家”的藝術家。就此而言,該書不僅展現了雅氏與藝術家們的對話,更是作者投身其中的體驗之旅、發現之旅。作者以內在于雅氏思想中的“生存”與“理性”之間的張力為運思樞紐,逐層深入地闡發了雅氏的思想淵源、藝術之思、藝術家論的韻致及其所論藝術家的生存樣態,在此基礎上對雅氏所區分的三種典型樣態的藝術家——客觀表現型的生存藝術家、主觀體驗型的生存藝術家、理性生存型的藝術家——分別進行了深度詮解。
就作者對雅斯貝斯藝術哲學思想所研究的規模和力度而言,該書堪稱紀念碑級的典范之作。無論是杜夫海納與利科合著的名作《雅斯貝爾斯與生存哲學》(1947),還是在中國引發存在主義美學熱潮的《存在主義美學》(今道友信等著),抑或其他當代相關著述,對雅氏藝術哲學思想的研究仍停留于片段式闡釋,尚未實現整體的綜合把握與微觀的細膩闡釋的充分融合。研究的現狀本身顯示出兩個疑難:其一,藝術(家)之思散見于雅氏的著述中,是否它本身就缺乏體系性故而沒有替雅氏將其整理出來的必要?其二,藝術(家)之思在雅氏哲學中是否沒有我們想象的那么重要?
貳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正如該書作者所指出的,在雅斯貝斯那里作為聯結“生存”與“超越存在”之中介的“密碼”乃是其全部運思的輻輳點,“而藝術恰恰以其直觀的特征成為以理性思辨為其特征的哲學無可替代的一種密碼語言,這樣一來,雅氏的藝術之思在其整個學說中的地位也就彰顯出來了”( 《雅斯貝斯藝術家論研究》,P103)。在漫長的精神求索歷程中,雅氏由精神病理學轉到純正哲學領域,從生存哲學階段發展到理性哲學階段,“生存”的種子也隨之從萌芽狀態逐漸發育成熟。帶著深入骨髓的人生體驗關注人的生存境遇,關注特異之人在臨界狀態下呈示出來的人的可能性及其邊界,正是雅氏選擇精神病理學與生存哲學雙重視域與藝術家對話的原因;我們甚至可以將他的藝術家論視為一種人類觀察活動,觀察那種既賦有“生存”之根又祈向超越之維的“真正的藝術”,這種真正的藝術作為“生存”直觀“超越存在”的一種介質,它所喻說的就是“超越存在”的“密碼”。此即《雅斯貝斯藝術家論研究》這本體大思精之作的要津,它本身已經說明對藝術(家)之思的研究之于理解雅斯貝斯的重要性。
實際上,雅氏的藝術(家)之思不僅不是一個“邊緣”話題,甚至在其哲學整體中相當關鍵。作為一種沉思人之整體存在的哲學,藝術及其創作主體勢必是一個繞不開的意義空間,而就生存及其超越的維度而言,藝術顯然是至關重要的。雅氏自露心跡:“讓自己著手于思忖人的整體存在的哲學探究。”(卡爾·雅斯貝斯:《斯特林堡與凡·高》,孫秀昌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年版,P108)這正是海德格爾評論《斯特林堡與凡·高》一書時看到的關鍵所在:
您把自己的哲學的學術態度更加清晰地表達了出來,特別是從您所嘗試的方面來看,將古老意義上的因果性、心理上的事情,置于積極意義上的精神、歷史的世界之中去理解。(瓦爾特·比默爾、漢斯·薩納爾編:《海德格爾與雅斯貝爾斯往復書簡》,李雪濤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P114)
雅氏已經將這些藝術家的作品視為人之生存的密碼,一種現代西方文化衰微時代的象征,特別是將荷爾德林、凡·高等藝術家的創作視為抵抗大眾秩序與技術統治的“真理”。
在雅氏的哲學中,藝術既有喚醒生存的力量,又有形而上學的深度,對哲學而言藝術顯然是一種珍貴的支援。藝術讓生存擺脫經驗世界的羈勒,它通過想象力的解放讓人自由地擁有生存的可能性。在《哲學》(第三卷)中,雅氏將原初的神話與語言相連接,神話作為人類語言的持存本身是一種藝術,藝術將原初的神話帶往生存密碼的道路,它無須模仿現實而將現實轉變為密碼,誠如杜夫海納、利科所詮解的:
真正的藝術時刻,是藝術家將深埋在物中的總體性以及形式從物中釋放出來的時刻,也就是將既普遍又獨一無二,總之就是不可模仿的無限理念從物中釋放出來的時刻。(米凱爾·杜夫海納、保羅·利科:《雅斯貝爾斯與生存哲學》,鄧冰艷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P326-327)
可以說,《雅斯貝斯藝術家論研究》牢牢把握住的正是藝術之維之于人之生存的真理性。
叁
該書濃墨重彩的一筆是對雅斯貝斯所論的藝術家的分類闡釋。雅氏在精神病理學-心理學時期所著的《斯特林堡與凡·高》(1922)一書中,根據所涉獵的精神分裂癥藝術家的生存樣態的不同,將他們區分為如下兩種范型:一種是“客觀表現型的生存藝術家”,如斯特林堡與斯威登堡;另一種是“主觀體驗型的生存藝術家”,如荷爾德林與凡·高。進入理性哲學-世界哲學時期后,雅氏又在大全論的視域下分別闡說了歌德、萊辛、達·芬奇等具有理性精神的生存藝術家,依雅氏一以貫之的分類原則,作者將其稱為“理性生存型的藝術家”。這種范型的藝術家誠然更多地為“生存”插上了“理性”的翅膀,不過當他們訴諸直觀思維對不可見的“超越存在”進行喻示時,便使自身的“生存”始終保持著某種開放的局度,由此把“未完成”的藝術品轉換為明證“超越存在”之消息的“密碼”。
該書發現的是一個關注藝術家獨一無二的生存樣態的雅斯貝斯,作者就此指出:
雅斯貝斯藝術家論的韻致在于闡明藝術家獨一無二的“生存”,其詮說路徑主要有兩條:其一,在“生存”與“超越存在”所構成的張力中,詮說生存藝術乃是解讀“超越存在”之消息的“密碼”,而藝術家正是雅氏用來詮說“生存”之旨趣的范例;其二,在“生存”與“理性”所構成的張力中,詮說“生存”的超越尚有賴于“理性”對“生存”的澄明,雅氏探究不同類型的藝術家及其生存性征的精神歷程恰恰透露了這一意趣。(《雅斯貝斯藝術家論研究》,P243-244)
雅氏所論的藝術家借助形式所呈現的正是他們無所保留的人格以及人在臨界狀態下明證的生存的真理,他們如同卡夫卡筆下的饑餓藝術家,即使因疾病而無法在現實生活中與人交流,卻以其作品吁求無限的可交流性。荷爾德林、凡·高、歌德、萊辛、達·芬奇等頗富個性的藝術家無疑是無可取代、獨一無二的,他們的存在本身就是我們理解“生存”之旨趣的范例。
創造全新的生存的可能性,重建人格和生活方式,這是只屬于藝術的交流性真理。雅氏所祈念的正是多維度的、可交流的真理。薩尼爾在《著眼于卡爾·雅斯貝斯論藝術與哲學》一文中將雅氏的藝術概念厘定為“藝術家感受存在物、設想非存在物,并將其傳達給他人的方式”(卡·雅斯貝爾斯等:《哲學與信仰:雅斯貝爾斯哲學研究》,魯路譯,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P246),可以說是深得雅氏藝術哲學的真意的。可能的生存,那些拘囿于日常秩序的人們無法觸及的真實的可能性,只有在對話中才能由潛在變為現實。
該書“附錄”部分收入孫秀昌教授翻譯的《哲學與藝術》《藝術是解讀密碼的語言》《悲劇的超越》《我們的未來與歌德》《歌德的人性》《作為哲學家的達·芬奇》《論萊辛》等七篇雅斯貝斯論藝術(含藝術家)的文字,讓該書在專題研究之外,兼具文獻功能。“余論”進而考察雅斯貝斯與詩人馮至的“相遇”,由此生發出雅氏藝術哲學與中國詩學的交往問題。綜上可知,該書已將漢語學界雅斯貝斯藝術哲學思想的研究帶入一個全新的階段。
(作者系文學博士,杭州師范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