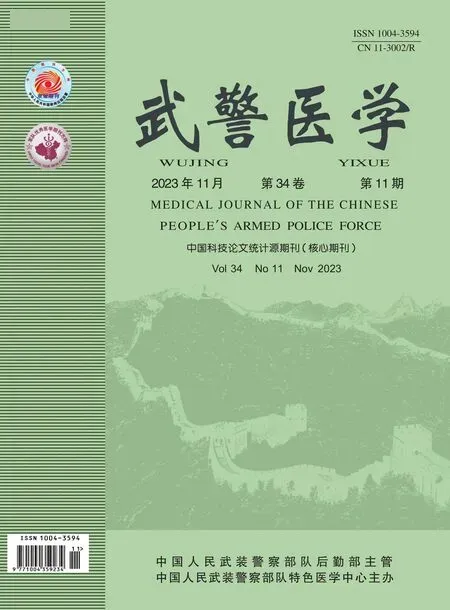一起家庭聚集性鸚鵡熱衣原體感染
田東華,肖 灑,蔣希萌,谷燦玲
鸚鵡熱衣原體感染(鳥疫)是人類、鳥類及一些哺乳動物均易感的自然疫源性衣原體病。人類感染主要是由排菌鳥及其污染物引起的,故是典型的動物源性傳染病。本文為一起家庭聚集性鸚鵡熱衣原體感染,患病者共5例,其中4例出現肺炎,1例為輕型患者,僅出現上呼吸道癥狀。經外院“靶向探針捕獲和高通量測序技術檢測(Gene+tP-Seq)”明確為鸚鵡熱衣原體感染,給予抗生素治療后病情好轉。
1 病例報告
病例1:患者,男,64歲,主因“間斷發熱4 d,突發暈厥0.5 d”入院。入院前4 d無明顯誘因出現發熱,最高體溫39.0 ℃,伴咳嗽、咳痰,痰量較少,不易咳出。入院前1 d突發暈厥,持續約1 min后意識恢復。行血常規檢查可見“白細胞10.3×109/L,中性粒細胞百分比80.9%,紅細胞4.97×1012/L,血小板155×109/L”。C-反應蛋白:144.2 mg/L。胸部CT檢查可示“左肺下葉炎癥”(圖1)。查體:聽診雙肺呼吸音粗,左肺吸氣末可聞及濕啰音。既往高血壓、糖尿病、腦梗死等病史多年。行肺炎支原體、衣原體檢查,結果提示“肺支原體IgM、肺衣原體IgM等均為陰性”,白介素-L6:92.5 pg/ml;診斷“肺炎”。入院后給予“頭孢曲松鈉”2.0 g,1次/d,3 d后體溫無明顯好轉。追問病史 ,發熱前1周有兩只鸚鵡幼鳥接觸史,后鸚鵡均于一周內不明原因死亡。根據病史及臨床表現,不排除“鸚鵡熱衣原體感染”,給予口服米諾環素100 mg, 2次/d,靜脈注射左氧氟沙星氯化鈉注射液0.5 g,1次/d。后患者留取痰液,于外院行“靶向探針捕獲和高通量測序技術檢測(Gene+tP-Seq)”,采用靶向探針捕獲和高通量測序(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NGS)技術,對病原體進行檢測,結果提示“鸚鵡熱衣原體”為陽性。

圖1 病例1胸部 CT 影像
病例2:患者男,66歲,主因“發熱1 d”入院。入院前1 d出現發熱,最高體溫37.6 ℃,伴鼻塞、流涕,咳嗽、咳痰較少,行血常規檢查可見“白細胞7.04×109/L,中性粒細胞百分比76.5%,紅細胞4.52×1012/L,血小板174×109/L”。C-反應蛋白:40 mg/L。胸部CT檢查可示“左下肺炎癥”(圖2)。查體:聽診雙肺呼吸音粗,未聞及明顯干濕啰音。既往高血壓病史多年。該患者與病例1為兄弟關系,共同居住,密切接觸。入院后行肺炎衣原體檢查,結果提示“肺衣原體IgM弱陽性”,考慮為“鸚鵡熱衣原體感染”,診斷“肺炎”。后患者留取痰液,于外院行“靶向探針捕獲和高通量測序技術檢測(Gene+tP-Seq)”,采用靶向探針捕獲和NGS技術,對病原體進行檢測,結果提示“鸚鵡熱衣原體”為陽性。
且入院后體溫37.9 ℃。給予口服米諾環素100 mg,2次/d,靜脈注射鹽酸莫西沙星氯化鈉注射液0.4 g,1次/d,抗感染藥物治療。

圖2 病例2胸部 CT影像
病例3:患者,男,92歲,主因“發熱1 d”入院。入院前1天出現發熱,最高體溫37.5℃,伴咳嗽、咳痰,咳痰困難,外院行血常規檢查“白細胞6.84×109/L,中性粒細胞百分比76.4%,紅細胞3.82×1012/L,血小板135×109/L”。C-反應蛋白:97 mg/L。胸部CT檢查可示“右肺中葉肺炎,右側胸腔積液”。查體:右下肺叩診呈濁音,聽診雙肺呼吸音粗,右下肺呼吸音低,未聞及明顯干濕啰音。既往高血壓、糖尿病、高脂血癥、冠心病、腦梗塞、心力衰竭等病史多年。該患者與病例1為父子關系,共同居住,密切接觸。入院后行肺炎支原體、衣原體檢查,結果提示“肺支原體IgM、肺衣原體IgM等均為陰性”,患者入院后體溫38.4 ℃,行血氣分析檢查:PH 7.443,PCO242.4 mmHg,PO265 mmHg,HCO329 mmol/L,堿剩余(BE)5 mmol/L,SO2 93%,B型腦利鈉肽(BNP):277 pg/ml,白介素-L6:110.6 pg/ml,白蛋白:26.9 g/L。根據病史及臨床表現,不排除“鸚鵡熱衣原體感染”,后患者留取痰液,于外院行“靶向探針捕獲和高通量測序技術檢測(Gene+tP-Seq)”,采用靶向探針捕獲和NGS技術,對病原體進行檢測,結果提示“鸚鵡熱衣原體”為陽性。給予口服米諾環素100 mg, 2次/d,及靜脈給予鹽酸阿莫西沙星注射液0.4 g, 1次/d,抗炎治療,3周后復查上述靶向檢測未查到鸚鵡熱衣原體。
病例4:患者女,62歲。主因“間斷發熱3 d”。患者入院前3 d出現發熱,最高體溫39.5 ℃,伴咳嗽、咳痰。行血常規檢查可見“白細胞8.23×109/L,中性粒細胞百分比79.1%,紅細胞4.39×1012/L,血小板237×109/L”。C-反應蛋白:64 mg/L。胸部CT檢查可示“左肺下葉炎癥”(圖3)。既往無明確慢性病史。發熱前有鸚鵡接觸史1周,鸚鵡于一周內不明原因死亡,該患者與病例1為夫妻關系,共同居住。根據病史及臨床表現,考慮為“鸚鵡熱衣原體感染”,診斷“肺炎”。因特殊情況未入院治療,門診靜脈注射莫西沙星氯化鈉注射液0.5 g,1次/d,一周,口服米諾環素100 mg,2次/d,抗感染治療3周,病情明顯好轉。

圖3 病例4胸部 CT影像
病例5:患者男,35歲。主因“間斷發熱3 d”。患者無明顯誘因出現發熱,體溫最高39.0 ℃,伴咳嗽、咳痰,痰量較少。未行血常規檢查,胸部CT檢查未見明顯炎癥。既往無明確慢性病史。該患者與病例1為父子關系,與病例4為母子關系,共同居住。根據病史及臨床表現,考慮為“鸚鵡熱衣原體感染”。給予口服米諾環素100 mg,2次/d,抗感染治療一周后體溫恢復正常。
2 討 論
鸚鵡熱是一種以鸚鵡熱衣原體感染為誘因引起的動物疫源性疾病,主要通過接觸感染的禽類的糞便及其他排泄物、羽毛粉塵或吸入其感染的氣溶膠致病[1]。經常以呼吸道感染為主,表現為高熱、寒顫、頭痛、肌肉酸痛、咳嗽及肺部影像學表現為浸潤性病變等特征,一般癥狀類似感冒,大部分患者出現肺炎。表現為社區性獲得性肺炎(community acquired pneumonia,CAP)。傳染源不僅只限于鸚鵡科鳥類,還包括禽類等,其次宿主為人以外的哺乳動物。流行病學調查發現野生禽類是本病的主要傳染源,多數病案報道也提示家禽同樣為重要傳染源。人接觸受感染的動物后會發病,其中隱性感染、亞臨床感染不常見, 人感染后不能得到持久免疫,易復發及再感染。潛伏期一般為5~21 d[2]。鸚鵡熱被視為單獨疾病以來,凡有調查的地區,幾乎都有發現,故本病呈世界性分布[3]。鸚鵡熱衣原體因缺乏常規檢測[4],感染患者由于臨床癥狀無特異性而不易識別,如有明確的鸚鵡熱衣原體暴露史,早期使用NGS檢測方法,及時進行病原學診斷以指導臨床合理用藥,對降低患者病死率、改善不良預后、減少住院時間及費用和減少因應用不恰當的經驗性抗感染治療方案而導致細菌耐藥增加,均具有重大意義[5]。鸚鵡熱衣原體肺炎的胸部影像學表現無特異性[6,7],從影像學來看,病變多為一側肺葉實變影像,可見肺門向外呈扇形,或可出現胸膜下楔形斑片影,內可見支氣管充氣征,也可出現部分實變結節或磨玻璃影;少部分患者累及雙側肺葉;當胸膜受累時,可見單側或雙側少量胸腔積液。SARS-CoV-2現在是CAP患者的主要病原體,CAP的不常見或罕見原因應被視為具有特定病原體危險因素的患者或特殊人群的可能病原體,鸚鵡熱衣原體則被歸為非典型細菌[8]。所以病原診斷是所有感染性疾病診斷的核心,根據《中國成人社區獲得性肺炎診斷和治療指南(2016版)》列出的不同年齡段和科室常見的病原譜,對CAP特定情況下的病原學檢查項目的開展給出了建議,對臨床的快速診斷及治療極具參考價值。根據指南中診斷標準及診治思路,結合臨床表現、實驗室檢查及影像學特點,推測CAP可能的病原體及耐藥風險,適時安排合理的病原學檢查,及時給予經驗性抗感染治療,后根據患者病情變化評估抗感染效果,若初始治療失敗,及時查找原因,并盡快調整治療方案,提高有效的治愈率[9]。
本文為家庭聚集性發病,其中病例1、病例4鸚鵡接觸史明確,接觸的鸚鵡均于一周內死亡,病例2、病例3、病例5與病例1、4均密切接觸,考慮通過呼吸道傳播致病。病例1、病例2、病例3、病例4病情較重,導致肺炎。其中病例3高齡,基礎病較多,后合并其他多重致病菌感染導致呼吸衰竭,經聯合抗生素治療一月后肺部感染控制較好,已出院。病例1、2、3例入院后因痰液收集困難,均先行采取定量宏基因二代測序(Q-mNGSTM3.0) 病原微生物檢測,結果均為陰性;后通過3%生理鹽水霧化吸入,反復留取痰標本,行靶向探針捕獲和高通量測序技術檢測(Gene+tP-Seq),結果為鸚鵡熱陽性,根據《中國成人社區獲得性肺炎診斷和治療指南(2016版)》治療原則,首選方案為多西環素或米諾環素抗感染治療,備選方案為阿奇霉素、克拉霉素、紅霉素抗感染治療。目前大多數臨床實驗室未常規開展鸚鵡熱衣原體培養檢查,因為鸚鵡熱衣原體培養靈敏度較低,程序過于復雜;并且血清學檢測和 PCR 方法中,靈敏度和特異性都具有局限性,而Q-mNGSTM3.0病原微生物檢測技術將潛在的病原體可快速而準確地識別,其中包括細菌、真菌、病毒和寄生蟲[10]。Q-mNGSTM3.0 病原微生物檢測技術比其他的傳統的微生物檢測方法有較明顯的優勢:(1)無偏向性檢測,能夠檢測出環境中所有微生物的基因;(2)不依賴培養,可檢測不可培養的物種,可檢測痕量微生物;(3)能夠檢所檢測基因組的所有序測;(4)能夠發現新的或罕見的病原體。Q-mNGSTM3.0病原微生物檢測通過對生物標本中提取的病原微生物核酸進行富集與高通量測序,利用生物信息學進行比對分析,獲取標本中包含的微生物種類和豐度信息,檢測全面覆蓋24000余種病原體,包括細菌、真菌、病毒和寄生蟲等多種病原微生物。覆蓋病原體較多。Gene+tP-Seq產品采用靶向探針捕獲和NGS技術,對樣本中的目標病原微生物進行檢測,含306種病原微生物(細菌187種、真菌43種、DNA病毒21種/型、RNA病毒56種/型)、76種耐藥基因、46 種毒力基因進行檢測,輔助臨床鑒別樣本中的病原微生物感染情況,同時提供耐藥和毒力基因檢測結果。相比Q-mNGSTM3.0 病原微生物檢測來說,Gene+tP-Seq檢測病原體較少,但靈敏度較高。本次病例最終通過檢測出Gene+tP-Seq鸚鵡熱衣原體感染明確診斷,選擇敏感抗生素治療后病情好轉。肺部感染后病原體的檢測是選擇針對性治療的抗生素的首要前提, 較為傳統的病原體培養檢測法陽性率較低, 特別是在未明確病原體及取樣前給予經驗性治療應用廣譜抗生素的患者。在2020年病原學診斷的專家共識中指出, 肯定了Q-mNGSTM3.0 病原微生物檢測在感染性疾病診 斷領域中的優勢[11]。應用宏基因組測序能夠有效、迅速、準確的明確病原體,為準確選擇針對性治療藥物及提高治療效果提供保障。但是目前mNGS技術發展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主要原因是檢查費用偏高。但對于疑難雜癥、危重癥、免疫缺陷等特殊人群中仍具有成為病原體診斷,仍是較為重要的手段[12]。疑似鸚鵡熱衣原體感染者在條件允許情況下,仍建議盡快通過Q-mNGSTM3.0 病原微生物檢測技術明確診斷,盡快開展針對性治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