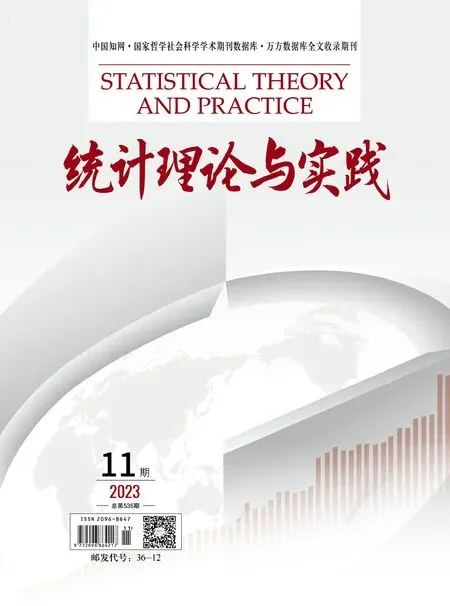中原城市群城鄉融合發展的時空分異特征分析
齊偉麗 朱云章 王清雅 高 毓
(河南科技大學商學院,河南 洛陽 471000)
一、引言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經濟發展的空間結構正在發生深刻變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為承載發展要素的主要空間形式。突破城市行政區劃謀求城市群范圍的城鄉融合發展,正在成為構建新發展格局背景下促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縮小地區發展差距、提升城市群競爭力的重要路徑。中原城市群作為城鄉融合發展的區域空間重要單元,其區域內部地區間的城鄉融合發展水平是落實鄉村振興戰略、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的重要體現。所以,測度中原城市群城鄉融合發展水平,分析中原城市群城鄉融合發展的時空特征意義重大。
關于城鄉融合發展,國內研究主要基于復合論與系統論視角進行分析。復合論思想從目標導向入手強調城鄉總體的多維融合,陳志鋼和茅銳等(2022)[1]認為城鄉融合發展是基于供給制度創新和空間結構優化的經濟、社會、環境全面融合的發展。楊志恒(2019)[2]認為城鄉融合發展是以城鎮與鄉村資源要素流動為主線,通過產業、設施、制度、生態維度的融合來實現。魏后凱(2020)[3]認為城鄉融合是一個多層次、多領域、全方位的概念,包括要素、產業、居民、社會和生態各方面的內容。系統論思想則強調城鄉融合發展是城市與鄉村兩種不同社會形態的系統,在保持各自發展特色的基礎上相互促進、相互補充、協調發展的結果。方創琳(2022)[4]、葉超和于潔(2020)[5]認為城鎮與鄉村作為城鄉融合發展的子系統,具有協同性、互補性和融合性的特點。與之相對應,目前國內城鄉融合發展評價指標體系也可歸納為兩類:一類是復合論評價體系,基于社會、經濟、人口[6]等評價城鄉融合發展的主要維度,隨著人們對城鄉關系認識的加深,空間[7]、生態[8]、生活[9]、產業[10]等維度不斷被引入城鄉融合發展指標體系,提高了城鄉融合評價的全面性和系統性。另外,部分學者[11-12]基于新發展理念,從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5 個維度構建城鄉融合發展指標體系。另一類是系統論評價體系,劉金鳳和吳文恒等(2023)[13]、馬逸嵐和胡光偉等(2023)[14]、阮美娟(2023)[15]、梅志宇和趙映慧等(2022)[16]把城市與鄉村視為城鄉融合發展的兩個子系統,考察兩者間的耦合協調度。
城市群研究成果豐碩,主要集中于城市職能及其關系的探討,重點放在國家或省域間經濟的作用和聯系,對城市群內部城鄉融合發展的探討相對薄弱,而關于中原城市群城鄉融合發展綜合水平的定量研究更是少之又少。鑒于此,本文堅持定性與定量相結合,采用熵值法、耦合協調度和空間格局分析法,就中原城市群城鄉融合發展的時空分異特征進行實證研究,考察十年來中原城市群城鄉融合發展水平的時空演進,探討中原城市群城鄉融合發展的空間相關性,提出促進城鄉融合發展的對策建議。
二、指標、數據與方法
(一)指標體系的構建與數據來源
借鑒孫群力和周鏢(2021)[17]的研究,構建包含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2 個子系統、8 個維度層的指標體系,如表1 所示。

表1 城鄉融合發展水平指標體系
(二)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2011—2021 年中原城市群30 個城市的年度數據,構建城鄉融合發展指標體系,數據來源于EPS 數據庫、《中國區域經濟統計年鑒》、《中國城市統計年鑒》、《河北經濟年鑒》及相關省份的統計年鑒,個別缺失數據利用趨勢函數補齊。
(三)研究方法
1.熵值法
熵值法是一種客觀賦權方法,它克服了主觀賦權法的主觀偏見,提高了權重的可信賴性,使整體結果更具說服力。為了能夠實現對不同年份進行比較,本文借鑒楊麗和孫之淳(2015)[18]的做法,加入時間變量,對熵值法進行改進,使分析結果更加合理。改進后,具體模型如下:
(1)指標選取
設有r 個年份,n 個城市,m 個指標,則xθij為第θ年城市i 的第j 個指標值。
(2)指標標準化處理
鑒于不同指標有不同的單位和量綱,需進行標準化處理:
正向指標標準化:
負向指標標準化:
(3)確定指標權重
(4)計算第j 項指標的熵值
其中,k>0,k=ln(rn)。
(5)計算第j 項指標的信息效用值
(6)計算各指標權重
(7)計算各城市新型城鎮化水平與鄉村振興水平綜合得分
2.耦合協調度模型
農村是國之根基,更是城市穩定發展的重要基礎,能為城市提供充足的勞動力、物資等基礎;城市又能反哺農村,推動農村現代化的進程,為農村發展提供技術、資本等支持。可以認為,城鄉融合發展是耦合協調發展程度的體現。城鎮化與鄉村振興作為城鄉融合發展的子系統相互影響、相互滲透,共同提高城鄉融合發展的廣度與深度。同時,二者耦合協調發展狀態也是城鄉融合發展水平的具體體現。因此,本文選用耦合協調度模型測度整個系統的融合發展水平。
式中,C 是兩個系統的耦合度,表示兩個子系統間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的程度,其值介于0—1,各子系統越離散,C 值越小,反之,C 值越大;U1和U2分別代表城鎮化子系統和鄉村振興子系統對城鄉融合發展水平的貢獻;n 為子系統的個數,本文n=2。
由于耦合度僅能表征系統間的相互作用和影響程度,無法反映彼此間的融合程度,當城市和鄉村子系統的發展水平較低時,二者較高的關聯度也會造成耦合度偽高的問題。因此,在耦合度模型的基礎上進一步借助耦合協調度模型測度城鄉融合發展水平,具體的運算公式如下:
式中,D 表示城鄉融合發展水平;T 表示新型城鎮化水平和鄉村振興水平的綜合評價指數,反映了兩個子系統整體發展水平對協調度的貢獻;α 、β 為待定系數,考慮到城鎮化與鄉村振興對我國經濟發展水平同等重要,因此待定系數設為0.5。
參照已有研究,本文將耦合度劃分為6 個類型:C=0 表示處于無關、無序發展狀態,0<C≤0.3 表示處于一定水平耦合階段,0.3<C≤0.5 是拮抗階段,0.5<C≤0.8 是磨合階段,0.8<C<1 表示處于高水平耦合階段,C=1 表示處于良性共振耦合并有序發展狀態。其中,耦合度值越小,表明所處耦合水平越低;反之,其所處耦合水平越高。
同時,參照蔣輝和張康潔等(2017)[19]的研究,把城市與鄉村的耦合協調度劃分為10 種類型,其耦合協調值越大,表明協調性越好。

表2 城鄉耦合協調度劃分類型
3.空間格局分析方法
本文利用全局Moran's I 指數和局部Moran's I 指數進行空間關聯性研究。其中,全局Moran's I 指數用來反映研究對象在整個研究領域內的關聯度情況,局部Moran's I 指數用來測算某城市與其周圍城市間是否存在關聯性。其中,全局Moran's I 指數取值范圍為[-1,1],負值說明該空間內城鄉融合發展水平值分布呈負相關,正值則代表具有正的相關性,0 代表不存在相關性;值越小,表示自相關性越弱。可以通過局部Moran's I 指數進行HH、HL、LH、LL 型四種空間自相關類型劃分。
式中,xi、xj分別表示不同城市單位i 與j 的城鄉融合發展水平;表示城鄉融合發展水平的均值;wij是空間權重矩陣,表示中原城市群的空間關系;s2是xj的離散方差;n 是各城市單元總數。
三、測度結果與分析
(一)城鄉發展的綜合水平分析
對中原城市群各城市城鄉、新型城鎮化、鄉村振興發展現狀進行比較分析,然后從時間序列上對城鄉綜合發展水平、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鄉村振興發展水平進行趨勢與比較分析,了解各市城鄉系統的總體水平及發展態勢。
由表3 排名看,邯鄲、鄭州、邢臺、洛陽的城鄉融合發展水平較高,遠超排名較后的運城、長治、平頂山。以2021 年為例,就城市城鎮化發展水平而言,處于前五位的是鄭州、洛陽、蚌埠、晉城、濟源,從時間序列看,各城市總體均呈現上升趨勢。就鄉村振興水平而言,邢臺發展水平最高,邯鄲、聊城、菏澤、開封次之,長治、運城、許昌、宿州、平頂山發展水平相對較低。

表3 2021 年各城市城鄉綜合發展水平排名
2011—2021 年,鄭州的新型城鎮化指數在數量、增長速度上均遠超其他城市,呈較快增長趨勢,鄉村振興指數雖總體呈上升趨勢,但增速較慢,且波動較大,數值遠低于新型城鎮化指數。從鄉村振興發展水平看,邢臺、邯鄲、聊城、菏澤與其他城市的區別度較大,在較高水平呈較快增長趨勢。相比而言,邯鄲與邢臺的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在較低水平上呈較慢的增長趨勢。其他城市在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與鄉村振興水平上沒有很大的區分度,均表現為較低的水平。由表4可知,中原城市群各市城鄉綜合發展水平整體呈上升趨勢,且除鄭州、安陽近幾年緩慢降低外,其余城市城鄉綜合發展水平均呈穩步上升趨勢。此外,近年來雖然長治、運城城鄉綜合發展水平總體呈上升趨勢,但仍低于中原城市群平均水平。從具體數值看,中原城市群各城市目前城鄉發展綜合指數均不高于0.5。綜合而言,中原城市群各城市新型城鎮化、鄉村振興、城鄉綜合發展水平有待進一步提升。

表4 2011—2021 年各城市城鄉發展水平綜合評價結果
(二)城鄉發展的耦合度與耦合協調度分析
對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與鄉村振興發展水平加權計算得到的城鄉綜合發展水平,是把城鎮與鄉村視為兩個相互獨立的系統,與城鄉融合的內涵尚有差距。耦合度主要用于測量各系統之間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協同程度,一定程度上能夠較好地解釋城鄉系統達到臨界狀態后會轉向何種結構。
由圖1 可知,目前中原城市群30 個城市城鄉融合發展的耦合度總體處于高水平耦合階段,部分處于磨合階段。2011—2021 年中原城市群30 個城市耦合度均值分別為0.879、0.893、0.924、0.929、0.920、0.940、0.953、0.950、0.946、0.959、0.958,其值一直在緩慢增加,耦合度等級較高。2011 年,有11 個城市城鄉融合發展水平的耦合度低于平均值,其中信陽、淮北、菏澤遠低于平均水平,信陽最低為0.447,漯河最高為0.999。到2021年,仍有7 個城市城鄉融合發展水平耦合度低于平均水平。總體看,城鄉融合發展水平的耦合度低于平均水平的城市在逐年減少。

圖1 2011—2021 年中原城市群各城市城鄉融合發展耦合度
由于耦合度只能評估系統之間相互作用的絕對強度,僅反映發展的相似性,不能很好反映要素發展的總體水平和協調度,因此有必要引入耦合協調度來描述這種作用的利弊。
2021 年,除鄭州、洛陽、邢臺、邯鄲為中級協調,長治、運城為瀕臨失調,中原城市群其余城市均為勉強協調或初級協調。其中,瀕臨失調或耦合協調度更差的城市從2011 年的28 個城市(邢臺、邯鄲除外)降至2018 年的7 個城市(鶴壁、三門峽、信陽、亳州、宿州、晉城、運城)。并且,伴隨著中原城市群城鄉各方面的協調發展,2021 年瀕臨失調及耦合協調程度更差的城市已基本消除。2011—2021 年瀕臨失調及耦合協調程度更差的城市的數量分別為28 個、26 個、25 個、22個、22 個、19 個、14 個、7 個、5 個、1 個、2 個;2021 年中原城市群中級協調型城市占比僅為13.33%,且涵蓋鄭州、洛陽兩個中原城市群中心城市。由此可見,中原城市群耦合協調程度總體向好發展,但仍處于較低水平。
(三)城鄉融合發展的時空關聯分析
根據全局Moran's I 指數與局部Moran's I 指數結果,從空間角度分析中原城市群總體城鄉融合發展水平的關聯度及各城市與周圍城市間的關聯程度。
鑒于數據的可得性,在做空間自相關分析時暫不考慮濟源示范區。利用STATA 計算出2011—2021 年中原城市群城鄉融合發展的全局Moran's I 值。從時間序列看,2011—2015 年中原城市群城鄉融合發展水平的全局Moran's I 值大于0 且在95%顯著水平下顯著,表明城鄉融合發展在空間上呈現集聚分布態勢,具有空間關聯性。但全局Moran's I 值呈下降態勢,表明程度有所減弱。由于Moran's I 指數不顯著并不能判定城鄉融合發展與其他城市無關,因為這種相關性可能只存在于部分地區,或者正負相互抵消,導致統計上不顯著,因此2016 年、2018—2021 年Moran's I 值雖然在95%水平下檢驗不顯著,但仍可以說明城鄉融合發展存在一定的空間自相關性,城鄉融合空間集聚現象已經客觀存在。

表5 2011—2021 年中原城市群城鄉融合發展全局自相關情況
Moran's I 指數統計量只能顯示中原城市群城鄉融合發展存在空間集聚,不能顯示相應的空間集聚特征,因此,使用局部Moran's I 指數彌補其不足。根據局部Moran's I 指數的統計結果,在95%顯著性水平下可以區別出局部空間格局類型。其中HH 型代表該城市與相鄰城鄉融合發展水平高的城市間相互推動;HL 型表示該城市城鄉融合發展水平高但阻礙了鄰近其他城市城鄉融合發展水平的提高;LH 型表示雖然該城市城鄉融合發展水平不高,卻對鄰近城市的城鄉融合發展水平具有促進作用;LL 型表示自身城鄉融合發展水平不高且與鄰近城市相互制約。表6 為由局部Moran's I 指數散點圖匯總得到的結果。
由表6 可知,2011—2015 年平均有18 個市處于第一、第三象限,占比61.49%,表明中原城市群城鄉融合發展主要呈現出高- 高(HH)、低- 低(LL)的空間集聚特征,進一步印證了全局Moran's I 指數所表明的城鄉融合發展呈現全局正的空間自相關性的初步判斷。自2018 年以來,城鄉融合發展呈現出負的空間自相關性,尤其是2021 年,高- 低(HL)型、低- 高(LH)型區域占比達到最大。開封、新鄉、焦作、邢臺、邯鄲多為HH 型,城鄉融合關聯性較強,空間溢出作用明顯;洛陽、蚌埠多為HL 型,自身城鄉融合發展集聚水平較高,但與之相鄰的亳州、宿州、南陽、平頂山等城鄉融合發展集聚水平不高,即高集聚地區被低集聚地區包圍,空間溢出效應不明顯;鶴壁、平頂山、濮陽、長治、運城多為LH 型,本身城鄉融合發展集聚水平不高,與周邊地區存在一定差距,若加強區域間城鄉合作,可以受到來自鄭州、洛陽、邯鄲等周邊地區的輻射帶動;駐馬店、信陽、周口、南陽、阜陽多為LL 型,城鄉融合發展集聚水平與空間溢出水平均不高。
四、結論與啟示
本文運用熵值法、系統耦合協調度模型、Moran's I指數等定量研究方法,探討了2011—2021 年中原城市群30 個城市城鄉融合發展水平的時空特征,得到結論如下:中原城市群內各城市城鄉融合發展水平緩慢上升,整體看,鄭州、洛陽、邢臺、邯鄲城鄉融合發展水平較高,中原城市群總體新型城鎮化水平、鄉村振興水平、城鄉融合水平向好發展,但目前仍處于初級階段。中原城市群內各城市早期城鄉融合發展具有正的空間依賴性,呈現出顯著空間集聚特征,相當部分區域為高- 高(HH)型和低- 低(LL)型,但集聚程度逐年減弱,2018 年以來呈現出負的空間依賴性,2021 年高- 低(HL)型和低- 高(LH)型區域占比達到最大。
根據以上結論,得到進一步提升中原城市群城鄉融合發展水平的啟示如下:中原城市群各城市提升城鄉融合發展的側重點差異明顯,以鄭州、洛陽為代表的新型城鎮化水平較高的城市,促進鄉村振興是其提升城鄉融合發展須重點加強的薄弱環節;以邯鄲、邢臺為代表的鄉村振興水平較高的城市,提高城鎮化水平是其提升城鄉融合發展須補上的主要短板;其他城市在兩方面都有較大提升空間,亟須強化中原城市群內部的會商協調機制,破除城市間城鄉融合發展的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