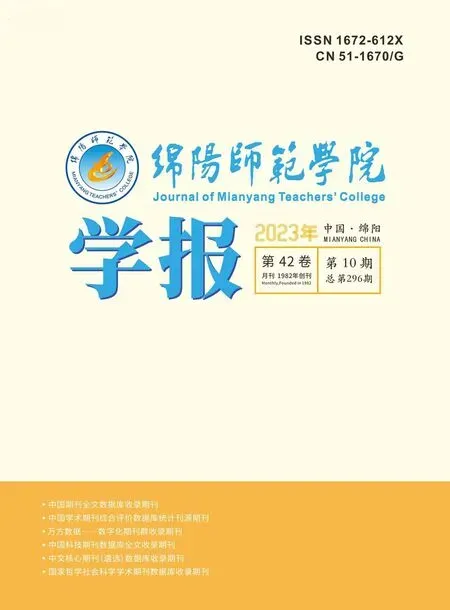中國網絡科幻小說的文體變奏與審美闡釋
——以五組典型性文本的分析論證為例
鮑遠福
(貴州民族大學傳媒學院,貴州貴陽 550025)
中國網絡科幻小說作為當代文學實踐中最有影響力的網絡文學亞文類之一已經歷了二十多年的發展歷程。在起步階段,網絡科幻小說創作就因其高起點、高完成度與高口碑而受到“網生代”接受群體的追捧。除了作為“三大奇書”之一的《小兵傳奇》之外,《夜色》(衛悲回著)、《尋找人類》(RAYSTORM著)、《文明》(智齒著)等早期代表作品都具有較高的藝術水準與廣泛的受眾基礎,使其以相當突出的藝術風格與傳統科幻文學創作相區別,并在網絡文學圈中獨立開來,成為一種富有生命力的新媒體文藝新類型。2010年以后,中國網絡科幻小說迎來了一波創作井噴期,大量優秀的網絡科幻小說作家與作品迅速出圈,并受到了國家層面和主流學術界的關注。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網絡科幻小說在主題和類型上都已多點開花、精彩紛呈,逐漸成長為當代中國網絡文學五大頭部文體類型之一,并在文學創作、傳播、接受、反饋、再生產以及學術研究領域產生廣泛的影響。此外,較為寬松的網絡創作環境讓網絡科幻作家能夠自由地在世界觀建構、主題內涵變奏與思想情感表達層面充分放飛想象力,從而開創出與傳統科幻小說有所不同的藝術路徑與文本風格,從最早的“近未來想象”“太空歌劇”與“人工智能”等傳統題材,逐步擴展為集合了“軟科幻”“硬科幻”“混合科幻”與“擬科幻”等多種主題類型,充分與都市、懸疑、推理、仙俠、修真、歷史、神話、現實、二次元與克蘇魯等亞文類形式并存,融合了“末世廢土流”“穿越架空流”“游戲升級流”“平行世界流”“古武機甲流”“穿越無限流”等多元化藝術風格流派的幻想型文本家族譜系。
題材類型的深度融合與審美話語的無限迭代讓網絡科幻小說與傳統科幻文學創作之間并不存在簡單的繼承和延續關系,而是作為一種奇異的“雙螺旋結構”,系統地參與中國當代新文學實踐的學術場域中。后人類狀況、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跨物種的生命政治學、游牧式的身體經驗與身份認同以及新烏托邦/異托邦實踐等新藝術追求與生命倫理話語的新形態,成為網絡科幻小說敘事話語范式轉型過程中必須直面的時代主題,這也讓其在敘事風格、文體特征與美學訴求層面表現出與傳統科幻文學實踐大相徑庭的理論重心與價值維度。同傳統的科幻文學相似,優秀的網絡科幻小說必須具備“科學元素”“邏輯自洽”和“人文思考”三要素。網絡科幻小說一方面繼承了傳統科幻文藝的創作模式和想象建構方法,另一方面它在新媒體(互聯網、移動媒體、賽博空間以及以“混合現實”為主要感知特征的“元宇宙”)、新技術(超鏈接技術、大數據和云計算技術、人工智能技術等)的共同加持下,也呈現出與傳統科幻文藝不同的特征,諸如網際性、跨媒介性、強交互性、技術生成性以及敘事表意的“影像化”“游戲化”與“泛文藝屬性”等,這些新趨勢與新動態都為我們界定網絡科幻小說帶來一定的難度。因此,在學術研究中,我們不能簡單地將網絡科幻小說與傳統科幻文學歸并到一個學術脈絡中,而是要緊密結合網絡科幻小說審美實踐的新技術生產環境與跨媒介傳播語境,揭示其對當代科幻文藝理論話語范式體系建構的價值和意義。
一、高起點的“近未來”想象與“太空歌劇”書寫
在中國網絡科幻小說的近三十年的簡短發展史上,《尋找人類》與《文明》既是具有“開拓者氣息”與中國特色的“太空歌劇”作品,也是被“網文界”長期忽略了審美價值的、具有“遺珠棄璧”特征的“硬科幻”網絡文學經典。《尋找人類》展現了人類生存以及“身份認同”的困境,進而借此揭示了宇宙生態中所有“碳水化合物”智慧生命體的生存悖論。人類文明因為核戰而遭到毀滅,殘存的人類大多基因變異,必須在人工智能的嚴密監管下茍活。超級外星文明薩爾摩爾人面臨文明的末路,因此不惜一切代價偷竊包括人類在內的碳水化合物生命的基因,妄圖茍延殘喘。“人類”探險者唐風、美拉妮和甲拉在宇宙漫游過程中發現,幾乎所有碳水化合物智慧生命的生存都是建立在對其他生物侵害和掠奪的基礎上的。優雅的“綠星人”被智能細菌操控,獲得解放后立馬調轉矛頭對“寄生者”進行屠殺;“本圖魯人”是薩爾摩爾人創生的人工智能,它們獲得獨立后念念不忘的則是對曾經主人的無情驅逐;進化成超級智能的“三智者”生存的唯一目的是對誤入其生存空間的智慧生命進行“意識剝離”和“思維同化”;就連號稱要守護人類的超級人工智能“父親”與替薩爾摩爾人保存基因庫的“原型”,它們智能程序的運行邏輯也都包含著自私、勢利、劫掠和排外的基因代碼。在作者RAYSTORM的筆下,宇宙是另一重意義上的“黑暗森林”,而驅動“黑暗森林法則”運行的動力則是智慧生命“自私基因”的“源力”。
智齒的《文明》則為讀者徐徐展開一幅氣勢磅礴的星際文明戰爭圖景與蕩氣回腸的生命探索史詩。小說用邏輯自洽的科技設定想象人類文明在構建“星辰大海夢想”時所遭遇的歷史與文明的“雙重終結”。二十二世紀的人類剛剛突破星際旅行技術瓶頸,就遭到來自宇宙深空的劫掠文明“風雷帝國”的戰爭脅迫,人類經過苦戰后丟失家園,被迫逃亡宇宙深處。在凄慘而漫長的星際征途中,人類終于在仙女星系的沙星找到落腳點。人類文明在仙女座星系中的類地行星“沙星”上獲得重生,并實現了科技的重大突破,他們相繼征服黑洞、白洞甚至精神空間(人類繼承“風星人”的“念能技術”并將其發揚光大)。超遠程通信技術的成熟和軍事技術的空前強大,讓這些星海游子萌生了“打回故鄉”的雄心,于是“沙星艦隊”與同樣被“風雷帝國”驅逐的外星文明結盟,他們在“死亡走廊之戰”大敗“風雷帝國”皇帝親自率領的超級艦隊,最終光復地球。不過,結果卻出人意料,地球已經被“風雷帝國”創造的強人工智能“降臨者”改造成為“智能核心”,沙星文明不得不再次同人工智能“降臨帝國”機器人大軍陷入經久不息的戰爭。秉持著戰天斗地精神的人類(沙星)文明在與“風雷帝國”、人工智能、“卡洛斯生命體”的戰斗中逐漸強大,最終征服宇宙很多角落,成就一段星海傳奇。不過,即便如此,人類文明殘暴好斗、自私傲慢、爭權逐利的本質依然沒有改變,文明進化歷程總是包含著許多灰暗甚至殘酷的真相。《文明》展現了網絡寫手“對中國的更廣義的文明,甚至……對宇宙的文明”所作出的理性“回應”,以此彰顯出“康德式的人和無限之間抗爭的雄渾壯麗”[1]。
《尋找人類》大約創作于新世紀初期,它先由現代出版社于2002年10月出版,后又陸續在起點中文網和17k小說網等網站連載。在網絡文學的萌芽期,《尋找人類》為讀者出色地構建了一種典型的“后人類世界”圖景,作者通過對智慧生命生存悖論的想象以及對人性(更廣泛意義上講也是所有智慧生命的本性)的深入反省呈現了網絡文學應有的審美反思維度。與此同時,這部作品還在新世紀以來科幻文藝的思想建構和藝術批判層面,對傳統科幻理論的話語范式體系的開拓創新做出了富有意味的嘗試。《文明》即使與2010年后出現的太空歌劇類型網絡小說相比也毫不遜色,它借助史詩一般的鴻篇巨制和宏觀敘事維度為讀者展示了其對“科技狂想”“人文精神”與“未來烏托邦”的內在悖論的開拓性思考。小說中對內憂外患的人類社會(沙星文明)及其在大宇航時代的命運的抒寫極為精彩,沙星文明的“雙執政官體制”(行政執政官與軍事執政官)的設想與現實社會各種社會體制的樣本之間構成了內在的邏輯張力,引人遐思。此外,小說還借助于文明個體的人性以及群體的種族特征的描摹,為我們展示了更加宏大磅礴的政治體制改革與星際文明生態思考的意識形態話語愿景。不過,由于網絡文學創作生態的變動生長性以及科幻題材的“小眾接受圈層”等特點,《尋找人類》《文明》這兩部網絡科幻小說的“開拓者”在網絡文學發展初期的傳受語境中并沒有產生太大的影響,頗有“遺珠棄璧”的遺憾,但在2010年之后,《間客》《地球紀元》《深空之下》《死在火星上》《天阿降臨》《千年回溯》《復活帝國》《我們生活在南京》《夜的命名術》《7號基地》等相對“硬核”的網絡小說陸續引發“網文界”、評論界的震動后,這兩部“元祖性質”的科幻作品所蘊藏的思想價值與審美內涵才得以重新獲得被發掘和闡釋的機會。
二、“后人類敘事”與命運共同體的詩學構建
在人文學術研究領域“后人類轉向”的宏觀理論視域下,網絡科幻小說也在這一領域中大展身手,《地球紀元》與《千年回溯》同傳統科幻文藝經典《三體》一樣展現了網絡科幻小說在“光年尺度”以上的宏大藝術建構。理工科出身的作者彩虹之門以《地球紀元》五卷本的龐大體量和宏大文本結構為讀者描述了地球文明在“近未來”可能會經歷的五種典型“后人類情境”。小說第一卷講述地球文明與其所創造的“等離子體生命體”之間的矛盾沖突(“太陽危機”);第二卷揭示地球即將陷入某種神秘未知空間的危機,人類在科學家領導下的自救(“星辰之災”);第三卷描述了地球文明陷入科技“死結”,人類世界為沖出太陽系探索星空而選派孤勇者衛風展開漫長星際探索(“時間旅者”);第四卷講述人類文明應對沒有道德倫理取向的機器人文明針對整個銀河系智慧生命星球的入侵危機(“惡魔之巢”);第五卷則描述了流浪太空的人類文明如何突破帶有致命輻射的星際塵埃重返地球的故事(“星塵信使”);除此之外,小說還以一部短小精悍的“副本故事”(“恒星人的進攻”)補充了第一卷的部分情節,使得整部小說呈現出史詩一般的磅礴結構。小說使用“星叢式文本”框架建構了一個波瀾壯闊的“未來世界”,其敘事所構筑的道德觀和價值觀是道德至上主義與人類中心論,因此,它也是一種典型“人類命運共同體”模式的藝術想象。小說的主題宏大,敘述冷靜克制,卷與卷之間的故事情節環環相扣,主線人物(如與“等離子體生命”生死博弈的趙華生、同機器惡魔斗智斗勇的肖云等)的刻畫栩栩如生,作品對“近未來”可能出現的人類危機的預見也客觀真實,既蘊含著平實客觀的科學思維,也充盈著邏輯思辨色彩的理性主義輝光。小說在敘述過程中圍繞著人類生存與自身利益的優化來展現價值視角,對處于危局和困頓中的“人類救世英雄”的心理描摹細膩而深刻,具有極大的藝術感染力,例如小說第三卷對“孤膽英雄”衛風的命運書寫,極易引發讀者情感共鳴。
《千年回溯》原名《我沒有想當救世主啊》,從事環保工作的作者火中物通過這部結構宏大奇特的幻想文本為讀者展現了“后人類”的生存奇景與命運奇遇。小說以都市文的套路模式著手,不溫不火地展示了小人物陳鋒的瑣碎日常,但在進入到十萬字以后,故事情節突然迎來爆發式噴涌,在揭開波瀾壯闊的世界觀的同時,一個孤獨的“救世英雄”形象躍然紙上。小說通過十個具有內在邏輯關聯卻又形態各異的“穿越副本”來展示“最強兵王”主人公的救世壯舉,以陳鋒與身處平行時空(2019年與3019年)中兩位女性鐘蕾和唐天心等為代表的人類文明一次次悲壯而決絕的反抗,演繹出了古典英雄的壯麗和未來戰爭的熱血。小說完美地結合了科幻的硬核設定(超級科技)、網絡類型文的節奏感(詼諧幽默)與電子游戲的汪洋恣肆(副本敘事),展現了面對生存危機和文明困境的“后人類”如何實現“逆天改命”夢想的故事。《千年回溯》把網絡類型文的各種“套路”“修辭”“文風”“技巧”與“策略”熔于一爐,讀者既可以從中看到精彩的劇情推理,也能從閱讀過程中獲得游戲闖關的“具身體驗”,還能從主人公對抗未知命運拯救人類的故事中體驗到肆意馳騁想象力的快意與舒適。最重要的是,小說通過“時空穿越”與“星際戰爭”的噱頭將現實與未來合理地串聯起來,構建了一種奇觀化的敘事文本。在主題層面,它不僅為讀者書寫了一種肉眼可見的“未來史”,還在這種“新歷史演繹”的敘述實踐中寄寓了作者對歷史進程的詩學思考[2],特別是小說中作者借助其對“創世紀”“亞特蘭蒂斯文明”“羅斯威爾事件”以及“人魚傳說”的歷史—神話復述來隱喻人類社會的現實,揭示人類文明歷史演變的復雜樣貌,也為“多文明共生”的未來敘事場景提供了想象的可能性。
我們看到,在呼應國家“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發展戰略方面,優秀的網絡科幻小說始終保持著高度的敏感性與先鋒性。《地球紀元》以“人類中心主義”的立場來實現“命運共同體”的“后人類敘事”與想象,它把人類文明的存亡、延續、發展與超越的終極目標當作推動文本敘述和想象力建構的原動力。小說在構建這一宏大宇宙冒險故事即“太空歌劇”的過程中始終透露出年輕作者(彩虹之門是典型的“90后”)對現實問題的熱切關注,表達了深刻的人文價值關懷取向。作為致敬傳統科幻文學的手段,《地球紀元》在美學意蘊層面也顯現出不輸于《三體》宏大格局的史詩質感和悲壯意味。《千年回溯》在故事框架設計層面顯得更加恣肆奔放,都市生活的幽默日常與游戲筆墨的文體架構融為一體,小人物群像的塑造與主角光環的呈現相得益彰,某些精彩副本(如陳鋒第八次穿越遭遇的人類與人工智能“鐳”的戰爭,類似于“故事中的故事”)還在經典科幻題材的基礎上繼續反思人類與其他生命之間復雜的生命政治關系,借以強化網絡科幻小說文體變革與文本探險的反思力度。從商業化寫作的角度看,網絡科幻小說不僅是邊緣文類,而且還是極難為創作者帶來實際收益的文類。即便如此,《地球紀元》《千年回溯》的作者卻很難得地在資本誘惑之下將才華和情懷保持到了最后,用“人類命運共同體”想象的優秀答卷及時地呼應了社會熱點,也提升了網絡科幻創作的審美品味與人文價值。
三、“軟科幻”寫作如何彰顯人文情懷
科幻作家或寫手在“觸網”之后,需要在數字復制(與個人收益掛鉤)與文學理想(涉及人文情懷)之間作出慎重選擇,他們通常要對作品既能夠實現“以‘爽文’寫‘情懷’”[3]的目標又能夠達成“人氣”與“品質”雙贏的局面而費盡周折。貓膩的《間客》和會說話的肘子的《第一序列》是真正意義上實現這種創作理想的“軟科幻”爆款文,放到當代中國科幻文學的整體生態中,這兩部作品都可以被當作“精品”。從敘述主題的角度看,它們都是借助“人類未來史”的細致想象來刻畫人性的多重面向、揭示人文精神的可能性及其價值何以實現的網絡文學新文類;也就是說,它們真正地實現了“以爽文抒寫情懷”創作意圖,是在“資本”與“審美”間找到平衡點,并將網絡科幻寫作的整體格調提升到較高水準并受到了官方和主流學術界深度關切的“軟科幻”類型文。
《間客》是人文寫手貓膩“后人類世界”三部曲的第二部作品,它在內容上構成了《慶余年》和《大道朝天》故事情節的“過渡”。小說的開頭就引用了哲學家康德的名言“世界上有兩件東西能夠深深地震撼人們的心靈,一件是我們心中崇高的道德準則,另一件是我們頭頂上燦爛的星空”,并以此作為敘事的引子,進而呈現出作者在氣勢恢宏的世界觀構架層面以及精微深邃的人文價值反思方面的宏大創作野心。主人公許樂是星際時代人類聯邦東林大區公民,他從一顆荒涼的半廢棄星球離開,腦海里留存著稀奇古怪的知識,身體里則隱藏著神秘的力量,在這個波詭云譎的星際大時代里,他露著白牙,瞇眼傻笑,身上籠罩著莫名的光芒,懷著堅定的人生信條,一步步地邁向堅實而未知的遠方。廣闊無邊的星海疆域、密不透風的陰謀詭計、深不見底的人性淵藪,在不疾不徐的故事節奏中被作者娓娓道來。現實與虛無、奮斗與迷茫、復仇與背叛、殺戮與柔情、追求與彷徨、信念與希望,種種自由意志、情感寄托與道義思想都在跌宕起伏且極具感染力的故事情節中流淌出來,令萬千讀者身臨其境、如癡如醉。穿插于全文的名言警句,像“大人物報仇,隱忍十年也不算晚,小人物的復仇,卻是從早到晚”“人死并不如燈滅,燈有光明,照不見的地方是黑暗。做錯了事情,就必須付出代價”“公正不但必須做到,為了令人信服,它還必須被人看到”如此等等,閃爍著人生的明悟與哲學的思辨色彩。由此,小說的敘述所產生的“爽文機制”在連綿不絕的情緒鋪墊與環環相扣的故事情節中徐徐展開,小人物的命運沉浮與悲歡離合也通過作者意味深長的筆觸被揭示出來,理性而不失親和、客觀而隱藏情懷的敘事風格極易拉近敘述者與接受者的情感距離,這讓小說能夠適應絕大多數讀者的閱讀口味,彰顯了它在審美經驗營造上的大眾化與普適性。
同樣具有“軟科幻”色彩的《第一序列》所展現的則是另一種意義上的人文情懷,這種情懷熱烈奔放而又催人淚下。更巧妙的是,《第一序列》也是“肘子”“后人類未來史”三部曲的第二部(過渡)作品(首是《大王饒命》,尾是《夜的命名術》)。《第一序列》將“系統文”的表面結構與“末世文”的內在肌理有機融合,為讀者呈現了“廢土求生”的嶄新幻想敘事范式。小說講述了因覺醒異能而自帶“升級系統”(主角意念中的宮殿,類似于游戲中的儲物櫥窗,它可以根據主角“感謝幣”多少而向他提供各種魔法、武器和秘籍等)的任小粟帶領流民在壁壘林立的廢土世界艱難求生的故事。作為具有情懷的“軟科幻”作品,《第一序列》也有很多警句,例如“不要讓時代的悲哀,成為你的悲哀”“唯有信仰與日月亙古不變”“人生應該如同蠟燭一樣,從頭燃到尾,始終光明”“如果你感覺自己在不停的被黑暗吞噬,那不正說明你自己就是那束光嗎?”“當災難來臨時,希望才是人類面對危險時的第一序列武器”,等等。小說最出彩的地方是“人物群像”的成功塑造,作者簡單幾筆就將每個出場人物寫活。例如幻想自己是齊天大圣的精神病人陳無敵,他是本書中至善的象征。他不是頑劣的齊天大圣,而是守護人間的斗戰勝佛,他的戰斗、犧牲、隱忍、重生與救贖都始終跟他對人間正義極善的堅守信奉相關。他就像灑向廢土大地的一束人性輝光,它不停被滿世界的黑暗吞噬、將要熄滅卻仍然釋放出最后的但卻堅韌的光和熱,幫助殘存的人類幸存者抵御絕望,走向新生。通過陳無敵、“西北王”張景林、“惡魔耳語者”李神壇、慶氏私生子羅嵐、火種指揮官P5092(改造人)、弱女子姜無老師甚至克隆替身慶慎這些有血有肉、有棱有角、有情有義的生命個體,小說構建了性格各異的人物群像“譜系”,也傳達出作者悲天憫人又善惡分明的人道主義情懷。
作為“人文傾向”濃烈的網絡科幻佳作,《間客》的最大亮點是大到宇宙的廣闊無邊與小到人性的精深幽微都在作者游刃有余的筆下被生動地展現出來。小說借此表達的人性之思與人文關懷一方面凸顯出內在的理性主義光芒;另一方面則表現出它直面現實社會與蕓蕓眾生的“落地精神”,整部作品有品位、接地氣,既能啟迪智慧,也能引人深思。《第一序列》的現實指向與人文關懷則以更加激烈奔放且又自帶“無厘頭”屬性的風格在字里行間被釋放出來,任小粟對“壁壘世界”及其生活方式的“無情調侃”,陳無敵對黑暗與罪惡近乎“零容忍”的抗爭與戰斗,克隆人慶慎對胖子羅嵐義無反顧的“死亡獻祭”,慶縝(慶慎的本體)為了打碎壁壘腐朽勢力的陰謀以身犯險的決絕,這些情節讀來都令人熱血沸騰、情難自已。小說以極具感染力的人物刻畫和氣氛營造將人文主義情懷的釋放以及對人性的深刻洞見展現得淋漓盡致。這兩部“軟科幻”佳作在新世紀網絡科幻小說的發展歷程中如同“雙璧”一樣光彩奪目,它們不僅將網絡科幻類型文創作的水準拉高到足以同傳統科幻文學比肩的程度,而且為科幻文藝創作題材類型的拓展以及科幻理論話語范式的更新提供了潛力與可能。
四、“廢土世界”生命政治與哲學反思
在“后人類情境”的敘事框架中,“廢土末日流”模式是網絡科幻小說常用的一種審美敘事策略。黑天魔神的《廢土》開啟了中國網絡科幻小說的“廢土末日流”敘事范式,煙雨江南的《狩魔手記》則進一步拓展了這一模式的語義邏輯與隱喻功能。《廢土》文如其名,少有地在早期網絡科幻創作語境中為讀者塑造了某種高度“黑化”的“人類未來史”。主人公林翔被未知細菌寄生并在核輻射的干擾下進化為強大的基因戰士(“寄生士”/“寄生將”),他“重生”后在廢土世界的多個勢力間盤亙游歷,依靠自身強橫的實力終于聚攏了大量的被侮辱者與被損害者,一邊努力查找世界大戰的真相,揭示邪惡資本家族的罪惡,另一邊消滅各種人間苦難與人性的墮落,隨后,他主導建立世界新秩序并成為新人類文明的守護者。《廢土》中充斥著大量的人性“異變”和“魔化”的描寫,也包含作者的某些“惡趣味”。就像歐美科幻電影《未來水世界》《末日侵襲》的設定一樣,《廢土》通過出色的“末日生存法則”描摹向讀者宣示了一種經典、黑暗而又殘酷的“批判性編碼范式”。這種“廢土法則”包含了極強的現實世界隱喻和反思意圖——這個強者恒強、弱者恒弱的世界,沒有法律、規則、道德和秩序可言,比如某些霸權國家,經常繞開二戰后所建立的世界秩序另立一套規則,以“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恐怖主義”“邪教勢力”等借口肆意侵略、掠奪和欺負弱小國家。在現代文明發展的背后,也有很多“廢土(叢林)法則”,只有以良善、和平、公正、共贏、合作發展的新秩序予以治理、糾偏,全人類在未來才能共享和諧穩定、永續發展的新世界秩序,而不是小說中某超級家族所主張的帶有“納粹化傾向”的“地球聯邦”。正因為如此,我國號召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才有劃時代的價值和意義。
《狩魔手記》是煙雨江南憑借《褻瀆》“封神”之后的又一力作,與《廢土》的世界觀相似,它也展現了核戰廢土上小人物的艱難生存。不同的是,它還加入了外星文明、“克蘇魯神話”“伴生物種”等因素,形成一個文本構架更加宏大、世界觀體系更加廣闊的“廢土世界”。小說通過對人類族群內部以及人類與其他智慧物種關系的深入考察,建立了一種形而上的生命政治話語闡釋范式[4]。雖然自帶“金手指”與“超能力”,但是主角蘇、麗、帕瑟芬妮等人仍然以平民身份來審視和約束自己,并對更加卑微、貧苦和凄慘的流民施以悲憫之心和人文關照。在消滅了文明內外的惡敵后,基因覺醒的蘇選擇自毀,麗也自殺殉情,帕瑟芬妮則帶著蘇的“異種”后代穿越空間門進入外星神族“貝因都薩”世界,為幸存的人類消除威脅,留下一片生存的凈土。小說以網絡文學少有的瑰麗辭藻和氣勢雄渾的敘述風格展現了宏大的世界觀與抽象的哲理情思,有力地拓展了“末日廢土流”敘事張力與詩學品格,提升了“末世類型文”的審美藝術價值。
從“后人類敘事”的邏輯框架看,《廢土》《狩魔手記》這類“廢土末日”題材網絡類型文的審美價值和現實意義在于,它們為讀者描述了最殘酷、血腥、絕望的“后人類惡托邦”,并通過敘事“自反性建構”的方式為現實社會與人類文明提供“警世寓言”。它們也揭示了在如同“黑暗森林”一樣令人絕望的“廢土世界”里,一個(群)人恒久地保持人性的不可能和掙扎求生的不易性,從而以另類的敘事維度來昭示“人性光環”與人文精神的偉大可貴。這是因為,如果我們深陷于充滿罪惡的非人類、后人類語境或反倫理的“機器監獄”時,人類個體要么變成了“逆來順受的平庸之輩”或待宰的羔羊,要么變成徹底喪失人性的恐怖“異類”[5]492,即自我異化為“非人/反人”的他者,就像《異形》《阿凡達》《超能泰坦》等歐美科幻電影中被“異種化”的人類一般。它們不再像人類一樣思考,也沒有了人的靈魂,或異變為行尸走肉,或徹底崩塌為迥異于人類的危險“他者”或“敵對物”。顯然,這種“他者化的未來”是值得我們警惕和反思的。
五、“擬科幻”的文類突破及其“醒世恒言”
神話與科幻是當代網絡文學類型文體變革的重要藝術手段。臥牛真人的《修真四萬年》(后更名為《星域四萬年》)即為讀者呈現了神話與現實、玄學與科技、仙魔與世俗、大世界與小世界等不同環境相互交織的復雜世界建構模式。小說描述了地球人李耀“魂穿”進入科技與修真并重、集古代武技與現代都市生活于一體的“天元界”,他機緣巧合得到古代煉器大師歐冶子真傳,結合現代科技與修真系統修煉成長,并成為一方霸主和“新聯邦的英雄”,然后縱橫馳騁“三千小世界”的勵志故事。在修真世界的主構架之下,小說細膩地再現了萬千世界中蕓蕓眾生的世俗生活,同時借助意識形態層面的對抗與博弈(所謂“大道之爭”)來抒寫敘述者的文學情懷,表達社會政治文化思考,直擊現實與人性的多重價值維度。從題材和類型來看,小說建構了一種“科幻+X”或“擬科幻”的敘事模式,即科幻題材僅僅是被揉進小說題材聚合系統中的“一味輔藥”,在整個文本的復雜文體關系中自覺地承載著某種想象力建構的職能。各種現代科技及其造物(如探測妖獸靈力的“妖獸探測器”、具有無人機功能的靈寵等)的描寫和想象僅僅為主角修仙、煉器、成長和戰斗提供輔助,真正推動故事情節發展的要素依然是(玄幻小說)修真話語體系及其所構建的世界觀。從主題和內容來看,《修真四萬年》與其說在寫修真故事,倒不如說是在寫人類社會制度的變遷,寫人類族群(無論是修仙者還是普通人)在世俗生命政治實踐中的處境,更深的層次上則探討了文明之間交流、對話和博弈的復雜模式。修仙門派的世俗化,修煉體系的社會化,人物關系的日常化以及神話故事的“祛魅化”,再加上百科全書式的文本系統,共同成就了這部網絡科幻小說“科技修仙流”網絡類型文的典范形態。
相比而言,一十四洲《小蘑菇》的科技設定更加簡單淺顯,科學機理的幻想(如跨物種生物間的共生問題)在小說中更像是一種滿足文學言說豐富性的敘事策略和修辭技巧。正如肖映萱所指出的那樣,以非天夜翔《二零一三》、priest《殘次品》、扶華《末世第十年》以及《小蘑菇》等為代表的“女頻科幻文”(網絡文學意義上的“她科幻”)僅僅將“科幻”或其他題材類型當作純粹“設定”,其作用只是一種實現某種審美意圖的敘述手段。“比起強調科學技術對世界的改變,甚至帶有某種技術預言性質的傳統科幻小說,女頻的‘末世文’更應該被理解為一種異世界的未來幻想,它所涉及的‘科學’是一種純粹的設定,重要的不是技術的可操作性,而是設定發生之后的社會寓言。”[6]因此,《小蘑菇》就是在這種“擬科幻”類型設定基礎上的“后人類寓言”,它以核輻射的末日背景展開敘事,描述了一個丟失孢子的小蘑菇“安折”通過“寄生變異”方式獲得人形并潛入人類社會觀察、親歷人類命運變遷的故事。同《二零一三》等“女頻科幻”一樣,《小蘑菇》通過“科幻要素”與“科學精神”介入文學敘事方式來傳達“女性向”科幻寫手們對于“后人類未來史”的“警世通言”“喻世明言”與“醒世恒言”。
隱喻與象征、寓言式書寫和“批判性編碼”共同建構了《修真四萬年》《小蘑菇》《從紅月開始》《大王饒命》《深海余燼》《末世第十年》等“軟文科幻”特征明顯且蘊含多重想象主題的網絡小說豐富多彩的文本世界。它們通常以烏托邦、異托邦甚至惡托邦“未來史”的詩學建構以及對人性化書寫與正向道德倫理力量的強調來表達網絡寫手對“后人類情境”的審美關照,在陰郁殘酷且又隱含希望的末世敘事模式中彰顯出蘊藉深厚的人文精神。借助于這種外化于現實生活的文學想象,“軟科幻”“擬科幻”“科幻+X”等兼具“科學精神”與“人文思考”的網絡類型文在創作傳播過程中建立了它們同現實世界及其生存方式的闡釋邏輯,表達了“科幻現實主義”①的創作宗旨與美學主張。因此,網絡科幻小說雖然是“幻想的科學體系”[7]、虛構的“異世界”、奇觀化的“未來史”以及寓言性“烏托邦/異托邦”雜糅共生的“敘述時空體”[8]39,但其本質卻又是最為接近現實社會生活的參照性結構,它們借助各種審美手段對現實世界發出警示之語,提出反思需求,體現出諷喻價值。
總的來說,新世紀以來網絡科幻小說的爆發式增長重塑了當代中國科幻文學的敘述方式,拓展了科幻小說文體、題材與類型的疆域,某種程度上也改寫了當代科幻文藝的審美版圖,把一百多年來中國科幻文學的三次轉型推向了新的一次也即“第四次轉型”的道路②。在由《遠古的星辰》(蘇學軍)、《伊俄卡斯達》(趙海虹)、《偃師傳說》(潘海天)、《三體》(劉慈欣)、《地鐵》(韓松)、《宇宙晶卵》(王晉康)、《天意》(錢莉芳)、《彼方的地平線》(拉拉)、《荒潮》(陳楸帆)、《北京折疊》(郝景芳)、《公雞王子》(雙翅目)等傳統科幻經典所構建的文本譜系之外(這個譜系只有兩種題材類型:未來科技世界的想象與冒險以及遠古神話世界的重塑與重述),網絡科幻小說開辟了新世紀中國科幻文學創作的另一譜系,即超越“硬科幻”之外的文體改革(超長篇、混合式、“擬科幻”與“軟硬科幻”相結合的復合型文類系統)與題材拓展(科幻與玄幻、奇幻、魔幻、穿越、架空、軍事、機甲、游戲、修真、黑科技雜糅與混融的主題模式),以此奠定了新時代中國科幻文學發展轉型的重要理論基礎。這也是網絡科幻小說在文體學、敘事學、主題學以及文藝美學層面所凸顯的意義和價值所在。
注釋:
① “科幻現實主義”的創作主張由老一輩科幻作家鄭文光在1981年提出。為了擺脫當時科幻文學“少兒化”“科普化”“邊緣化”的標簽,鄭文光希望通過“現實生活關懷”和“社會理性批判”的方式來發揮科幻文學的社會功能,借以強化科幻文學“未來想象的現實價值立場”,同時凸顯出科幻文學借助科學技術想象來研究和探討社會現實問題的創作宗旨。當代知名科幻作家吳巖、韓松、陳楸帆、劉洋等人都是“科幻現實主義”理念的支持者。詳見詹玲《中國當代科幻小說轉型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2年版,第235-236頁。最近,著名科幻學者和作家吳巖又提出“科幻未來主義”的理論主張,并對其基本內涵和表現形式作出界定。參見吳巖《中國科幻未來主義:時代表現、類型與特征》,《中國文學批評》,2022年第3期。
② 具體內容可參看詹玲《當代中國科幻小說轉型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2年版以及鮑遠福《“中國式現代化”語境下的網絡科幻小說》,《中國藝術報》,2023年4月5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