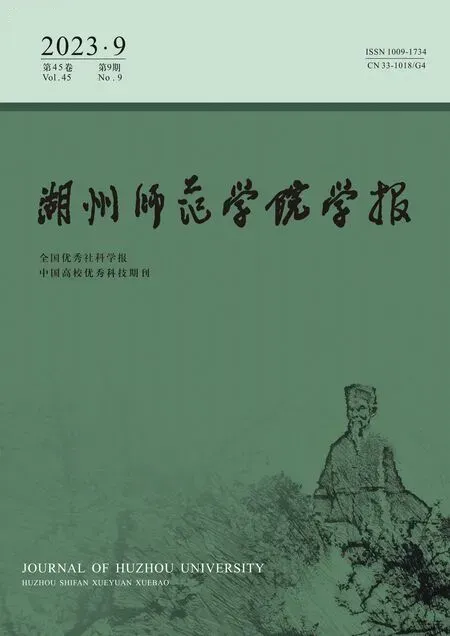呂祖謙《宋文鑒》的選賦特色及賦史意義*
華若男,楊許波
(蘭州大學 文學院,甘肅 蘭州 730000)
呂祖謙《宋文鑒》作為現存最早最全備的北宋詩文總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北宋各體文學發展的真實樣貌。相對于詩文,《宋文鑒》的選賦尚未受到學界關注。事實上,《宋文鑒》收錄了52位賦家90篇賦作,是現存最早且篇幅最大的北宋賦選集,對于北宋賦史的建構有著重要作用。劉培在《兩宋辭賦史》開篇指出,“在宋代文學研究中,宋文研究是薄弱環節,宋代辭賦又是宋文研究的薄弱環節”[1]1,《宋文鑒》的選賦無疑值得我們進行深入探討。《宋文鑒》的選賦在宋代獨樹一幟地呈現出某種程度的“異化”傾向:在宋代持續不斷的詩賦與經義之爭風潮下,依舊對賦體傾注了特別的情感,選賦數量多且有代表性,較為明晰地呈現了北宋賦的發展流變脈絡;在宋代科考重律賦的大環境下,古、律賦兼收,且選錄古賦數量遠超律賦;在宋人辨體、破體意識強化的影響下,打破了《文選》開創的以類選賦的傳統,首開以選本辨賦體的先河。可以說《宋文鑒》的選賦既是北宋賦壇生態的縮影,同時又表現出與北宋賦壇主流風氣的疏離。基于此,本文試圖以《宋文鑒》的選賦作為研究切入點,分析其選賦特色、背景及后世影響。
一、《宋文鑒》的選賦特色
宋之前專門的賦集很少,入宋以來賦集的編纂才蔚然成風(1)許結:《歷代賦集與賦學批評》,《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6期,第28頁:“唐人專門賦集甚少,像王棨《麟角集》收律賦數十篇,乃是鳳毛麟角。考《新唐書·藝文志》,見錄有李德裕雜賦2卷、陸龜蒙賦6卷、李商隱賦1卷、薛逢賦集14卷、盧獻卿《愍征賦》1卷、謝觀賦8卷、盧肇《海潮賦》《通屈賦》各1卷、林絢《大統賦》2卷、高邁賦1卷、皇甫松《大隱賦》1卷、崔葆數賦10卷、宋言賦1卷、陳汀賦1卷、樂朋賦1卷、蔣凝賦3卷、公乘億賦集12卷、林嵩賦1卷、王翃賦1卷、賈嵩賦3卷、李山甫賦2卷等。宋人輯選辭賦之風較唐人盛。”。《宋史·藝文志》記載的北宋賦集即有:徐鍇《賦苑》200卷、《廣類賦》25卷、《靈仙賦集》2卷、《甲賦》5卷、《賦選》5卷、《桂香賦集》30卷,楊翱《典麗賦》64卷、《類文賦集》1卷[2]5394,王咸《典麗賦》93卷[2]5402,李祺《天圣賦苑》18卷[2]5403等。此外,范仲淹亦主編有指導士子作律賦的《賦林衡鑒》,但僅序文得以流傳至今。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五“總集類”亦載:“《后典麗賦》四十卷”,下行小字注“金華唐仲友編。……此集自唐宋末以及本朝盛時,名公所作皆在焉,止于紹興間”[3]457;“《指南賦箋》五十五卷、《指南賦經》八卷”下行小字注“皆書坊編集時文,止于紹熙以前”[3]458。這些書大多都已散佚,我們僅能通過目錄書的存目確定其曾存在,但無法進一步獲知北宋賦收錄的具體情況,頗為可惜。與此同時,宋人編選的文章總集所收北宋賦數量卻并不多,《宋文海》雖收錄賦,但根據祝尚書《宋人總集敘錄》的爬梳(2)祝尚書:《宋人總集敘錄》,中華書局,2004年,第97頁:“《新雕圣宋文海》一百二十卷,宋江鈿輯,存卷四至九,計六卷。……卷四古賦,卷五賦,卷六賦,卷七記,卷八銘,卷九詔。”,可知其留存下來的賦僅三卷(卷四至卷六):卷四為“古賦”,選錄8篇,卷五、卷六為“賦”[4]97,分別選錄7篇、1篇[5]107,共計16篇。佚名《宋文選》、魏齊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均未列賦體且未收賦作;王霆震《古文集成》、樓昉《崇古文訣》未列賦體但收錄了極少量的漢賦,然而并未收錄北宋賦;謝枋得《文章軌范》僅收錄北宋蘇軾賦2篇,林之奇《觀瀾文集》收錄北宋賦6篇,數量均極少。而《宋文鑒》共選錄了52位賦家的90篇賦作,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研究樣本,通過總結其選賦特點可以大致勾勒出北宋賦的發展流變歷程。
《宋文鑒》選賦橫跨了整個北宋時期,歷時一百六十余年,且選錄賦的數量高達90篇,較同時代的大多數選集更為可觀;其選錄的賦作中,騷體賦、逞辭大賦、律賦、散體文賦各種體式兼備,同時,其所涉及的題材亦十分豐富,幾可涵蓋此前賦家的各類題材,并呈現出一些新特點;后世公認的北宋重要賦家如梅堯臣、歐陽修、王安石、蘇軾、黃庭堅、張耒等人的代表作,也盡數被囊括其中,因而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
首先,《宋文鑒》選賦時期跨度大,選取了自趙宋王朝建國(960)到北宋滅亡(1127)這167年間52位賦家的90篇賦作,其中包括古賦71篇,律賦19篇。呂祖謙全面考量了不同時期賦作的選錄標準及數量,簡要勾勒了北宋賦發展流變的線索。郭維森、許結合著的《中國辭賦發展史》將北宋賦的發展劃分為三大階段:宋初太祖、太宗、真宗三朝(960-1022)是北宋賦在繼承前代中求新變的時期,《宋文鑒》選錄賦家11人,占比21.2%、賦作12篇,占比約13.3%。這一時期沿襲唐人科舉考賦制度,故賦在體制上多沿襲前代,但在寫作手法及賦作風格方面均表現出新氣象,名家、名篇均較少。慶歷(1041-1048)到元豐(1078-1085)年間是北宋賦由變革而繁榮的重要階段,選錄賦家20人,占比38.5%,賦作40篇,約占44.5%。這一時期抒情小賦、騷體賦創作頗為興盛,文賦創作興起,出現了文賦大家歐陽修和長于騷體賦的王安石,選錄名家、名作數量較多。元豐以后為北宋辭賦發展的又一個高峰期,選錄賦家21人,占比40.3%,賦作38篇,占比42.2%。此期散體文賦大興,出現了以蘇軾及“蘇門四學士”為代表的辭賦名家,名家、名篇數量亦多。概括言之,《宋文鑒》的選賦大體上涵蓋了整個北宋,且各個時期的選賦數量也大致合于賦壇發展的實際情況。
其次,《宋文鑒》開啟了文章總集辨賦體的先河,透露出宋人對賦體認識的深化及強烈的文體自覺意識。與此同時,其選錄賦的題材極為豐富,鮮明地呈現了北宋士人審美旨趣的多樣性。許結《歷代賦集與賦學批評》一文指出:“緣于唐人賦‘大抵律多而古少’(祝堯《古賦辯體》卷七《唐體》),賦學批評亦因創作變化而確立‘古賦’‘律賦’之名,盡管唐以后科舉試賦與否,然此后賦論史的古、律賦之辨與賦體之爭,實為其批評主潮。”[6]31此系針對賦學批評而言,賦體之辨在唐代并未體現于文體分類的實踐層面。至宋代,文學總集才開始有意識地區分古賦與律賦,《唐文粹》專選古賦,以古為尊,而《文苑英華》惟取律體,以時文為尊。呂祖謙則采取了一種更為折中的態度:古賦與律賦兼收,且將其分別置于不同的編次,古賦在前,律賦在后,不偏廢一方的同時亦更凸顯二者間的差異,已然呈現出較為鮮明的“辨體”傾向[7]34。呂祖謙選賦還兼顧了題材的豐富性。根據清人陳元龍《歷代賦匯》的分類,《宋文鑒》所收錄賦的題材多達28個大類,涵蓋宮殿、典禮、曠達、蒐狩、地理、草木、音樂、天象、性道、都邑、室宇、歲時、花果、仙釋、情感、禎祥、懷思、覽古、言志、人事、飲食、玉帛、鳥獸、鱗蟲、行旅、武功、諷喻、治道等題材,其中典禮、地理、天象、性道、治道類賦選錄較多。從這些豐富的題材中,我們既可以看出宋代社會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高度發達,還可在一定程度上看出宋代文化的某種轉向:一是追求文學的經世致用,二是士人的政治參與熱情空前高漲,三是士人的關注重心內轉,注重個人修養的提升。
最后,《宋文鑒》選錄的賦家、賦作均極具代表性,宋室南渡之前的重要賦家大多被選入其中,其所選賦作也多為后世贊譽的名篇,當代最重要的辭賦史北宋部分重點介紹的賦家皆出于《宋文鑒》。馬積高《賦史》[8]北宋賦部分重點介紹的賦家有梁周翰、張詠、楊侃、王禹偁、范仲淹、葉清臣、宋祁、劉敞、司馬光、王回、梅堯臣、歐陽修、王安石、沈括、蔡確、狄遵度、崔伯易、蘇轍、蘇過、黃庭堅、秦觀、張耒、晁補之、米芾、刑居實,多達25人,約占《宋文鑒》所選賦家總數的50%;郭維森、許結合著《中國辭賦發展史》[9]北宋賦部分設置專節或進行專門介紹的賦家即有:梁周翰、張詠、夏侯嘉正、楊侃、種放、楊億、王禹偁、范仲淹、歐陽修、邵雍、周敦頤、司馬光、劉敞、劉攽、王安石、沈括、蔡確、蘇軾、蘇轍、黃庭堅、秦觀、張耒、晁補之、周邦彥、米芾、刑居實,共計26位,恰好占《宋文鑒》所選賦家的50%;劉培《兩宋辭賦史》[1]北宋賦部分則重點介紹了王禹偁、晏殊、宋祁、宋庠、范仲淹、王安石、王回、梅堯臣、歐陽修、劉攽、劉敞、蘇軾、蘇轍、黃庭堅、張耒、晁補之16家,約占《宋文鑒》選錄賦家的31%。由此可見,《宋文鑒》所選賦家大多都可獨立名家,在北宋賦學史的地位得到學界公認。
與此同時,呂祖謙還能十分準確地挑選出最能代表宋賦特色且又最富于賦家個性特色的佳作,在入選的賦家中,蘇軾賦選錄最多,共8篇,其次是張耒(6篇)。唐子西評價蘇軾最負盛名的文賦代表作《后赤壁賦》:“余作《南征賦》,或者稱之,然僅與曹大家爭衡耳。東坡之《赤壁》二賦,一洗萬古,欲仿佛其一語,畢世不可得也。”[10]261浦銑稱贊張耒的抒情小賦《鳴蛙賦》:“張文潛《鳴蛙賦》,熟讀之使人矜平躁釋,此宋文之勝唐人處也。”[10]399此外,后世所公認的宋賦名篇如錢惟演《春雪賦》、歐陽修《鳴蟬賦》《秋聲賦》、王安石《思歸賦》、蘇軾《滟滪堆賦》《昆陽城賦》《秋陽賦》、崔伯易《感山賦》、黃庭堅《煎茶賦》、周邦彥《汴都賦》、秦觀《黃樓賦》、刑居實《南征賦》、蔡確《送將歸賦》、范鎮《長嘯卻胡騎賦》(按入選《宋文鑒》所屬卷數排列)等也大多為呂祖謙所選錄,在當前通行的各類賦學專著中都均占有一席之地。
概括言之,《宋文鑒》的選賦在宋人總集中呈現了獨特的風貌:時期跨度廣,體量大;注重辨體,體式全備,題材豐富;所選賦家、賦作具備典型意義。
二、《宋文鑒》選賦的特定背景
《宋文鑒》的選賦在宋代無疑別具一格,在當時已然興起的古律賦之爭中采取了相對折中的處理方式,但其中還是明顯透露出“重古輕律”的觀念,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對宋代賦壇主流風氣的背離。
首先,唐代開創的以詩賦取士傳統為宋人所繼承,不同之處在于:唐人取士重于詩,宋人取士重于賦。歐陽修《六一詩話》已有記載,其中提到宋初“自科場用賦取人,進士不復留意于詩,故絕無可稱者”[11]16。劉克莊《后村題跋·李耘子詩卷》對唐宋詩賦取士還作過一番比較:
唐世以賦詩設科,然去取予奪,一決于詩,故唐人詩工而賦拙。……本朝亦以詩賦設科,然去取予奪,一決于賦,故本朝賦工而詩拙。[12]1484
雖然北宋科舉曾因詩賦與經義之爭幾度罷賦:熙寧四年(1071)罷賦,元祐元年(1086)恢復考賦,紹圣元年(1094)再罷,建炎二年(1128)再復,但賦在宋人仕進過程中依舊占據了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有人因具備優秀的作賦能力而名動一時,聲名甚至遠播異域,如《宋史·范鎮傳》記載:“(范鎮)少時賦《長嘯》(即《長嘯卻胡騎賦》),卻胡騎,晚使遼,人相目曰:此‘長嘯公’也。兄子百祿亦使遼,遼人首問鎮安否。”[2]10790還有人因為杰出的作賦才能順利躋身仕途,《宋史·崔公度傳》記載:“歐陽修得其(崔伯易)所作《感山賦》,以示韓琦,琦上之英宗,即付史館,授和州防御推官,為國子直講,以母老辭。”[2]11152還有不少如今為我們所熟知的詩詞名家也以賦聞名于當時,比如晏殊即是一例,《宋史·晏殊傳》記載:
景德初,張知白安撫江南,以神童薦之。帝召殊與進士千余人并試廷中,殊神氣不懾,援筆立成。帝嘉賞,賜同進士出身。宰相寇準曰:“殊江外人。”帝顧曰:“張九齡非江外人耶?”后二日,復試詩、賦、論,殊奏:“臣嘗私習此賦,請試他題。”帝愛其不欺,既成,數稱善。[2]10195
甚至秦觀在北宋文壇嶄露頭角也是因為賦,浦銑《歷代賦話》記載:“見蘇軾于徐,為賦《黃樓》,軾以為有屈、宋之才。”[10]106其因杰出的賦才見賞于蘇軾,最后成為蘇軾最得意的門生。上述例子無一不說明賦在北宋文壇的重要地位。
其次,《宋文鑒》的選賦特點還與宋人辨體、破體意識的強化有關。元人祝堯《古賦辯體》卷八“宋體”序即云:
王荊公評文章嘗先體制, 觀蘇子瞻《醉白堂記》曰:韓白優劣論爾。后山云:退之作記, 記其事爾。今之記乃論也。少游謂《醉翁亭記》亦用賦體。范文正公《岳陽樓記》用對句說景,尹師魯曰“傳奇體”爾。宋時名公于文章必辨體, 此誠古今的論。然宋之古賦往往以文為體, 則未見其有辨其失者[12]卷八。
由此可見,北宋各類文體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破體傾向,宋人就已注意到了這一問題并開始有意識地辨體。祝堯更為明確地指出,學界鮮有針對宋人“以文為賦”這一破體現象的得失探討。北宋總集的選賦已然呈現出較鮮明的辨體意識,比如《唐文粹》全選古賦,《文苑英華》則全選律賦,而《宋文海》已有意識地在區分“古賦”(卷四)與“賦”(卷五、卷六),《宋文鑒》則顯然受到了《宋文海》的影響,將賦體分為“賦”與“律賦”。以上是總集的情況,別集亦然,因為宋代沿襲了唐代科舉考律賦的傳統,故宋人別集中大量收錄律賦,如劉攽《彭城集》、王禹偁《小畜集》、文彥博《潞公集》等,甚至還有人在自己的別集中專門區分“古律賦”與“律賦”,比如楊杰《無為集》。根據目前所能了解到的情況,我們可以推知,宋人已有較為自覺的辨別賦體意識,且會在選賦過程中有意識地區分“古賦”與“律賦”,可以說《宋文鑒》選賦注重分體是賦體發展到宋代的必然趨勢。
此外,《宋文鑒》選賦更為特殊之處在于,其選錄古賦(還可再細分為騷體賦、仿漢大賦、駢賦和文賦)數量明顯多于律賦,但宋代科舉考律賦而非古賦,范仲淹《賦林衡鑒序》即有語云:
律體之興,盛于唐室。貽于代者,雅有存焉。可歌可謠,以條以貫。或祖述王道,或褒贊國風,或研究物情,或規戒人事,煥然可警,鏘乎在聞。國家取士之科,緣于此道。[14]508
他編選《賦林衡鑒》的初衷是為了襄助士子科考,雖然這一賦集已散佚,但律賦在宋代科考的地位我們于此序言亦可見一斑。呂祖謙選錄古賦遠多于律賦是出于何種考量,這又是一個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或許這與古人的文體正變觀念有關,明代吳訥《文章辨體·凡例》有語云:“四六為古文之變,律賦為古賦之變,律詩雜體為古詩之變,詞曲為古樂府之變。”[15]10由此可以推知,呂祖謙應該也受到了文體源流正變觀念的影響,視古賦為正體,律賦為變體。
最后,《宋文鑒》的選賦可能還與呂祖謙的教書先生身份息息相關。《呂東萊先生本傳》記載:“乾道二年丙戌,丁母夫人曾氏艱。護喪歸婺,廬于武義明招山墓側,四方之士爭趨之。”[16]319由此可知,呂祖謙于乾道二年(1166)回故鄉浙江武義丁母憂期間開啟了其教學生涯。呂祖謙《東萊呂太史別集卷第九·與劉衡州》記載孝宗乾道三年(1167):“近日士子相過,聚學者近三百人。”[17]453從這則材料可以看出,呂祖謙在當時的士子中有著非同一般的影響力,吸引了大批求學士子慕名而來。此外,呂祖謙還創辦了專門的書院——麗澤書院聚眾講學,其年譜記載他于乾道六年(1170)閏五月:“八日,會諸生于麗澤,有《規矩七事》”[16]306。甚至連朱熹都將其長子朱塾送至呂祖謙門下受教,可見呂祖謙作為教書先生得到了時人的高度認可。
持續不斷的廢賦與復賦之爭導致眾多士子喪失了作賦能力,乃至到了哲宗元祐年間突然恢復考賦的時候,一度出現找不到考官、改卷老師的荒唐局面。《續資治通鑒長編》記載丁騭所上奏章:
竊睹明詔,欲于后次科舉以詩賦取士,天下學者之幸也。然近時太學博士及州郡教授,多緣經義而進,不曉章句對偶之學,恐難以教習生員。臣愚欲乞下兩省、館職、寺監長貳、外路監司各舉二人曾由詩賦出身及特奏名入仕者,以充內外教官。蓋經義之法行,而老師宿儒久習詩賦,不能為時學者,皆不就科舉,直候舉數應格,方得恩命。今或舉以為教官,當能稱職。[18]9963
這僅是北宋年間的情形。“賦荒”對南宋年間產生的影響,我們僅看宋人吳處厚所編《三元元祐衡鑒賦》及元祐賦在南宋科場受到的推崇便可見一斑,陳讜謂“舉子詞賦,固不敢望如《三都》,得如《三元元祐賦》足矣”[19]。正是因為幾度罷賦造就的賦荒,才使得元祐賦在南宋大放異彩,最具代表性的即為“蘇文熟,吃羊肉;蘇文生,吃菜羹”這一佳話的廣為流傳,雖然不是專門針對賦而言,但從中亦足以看出以蘇軾為代表的元祐文人文學創作(其中自然包含賦體)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呂祖謙在《宋文鑒》選錄大量北宋賦固有存一代文獻的考量,但也不排除有為科場士子樹立賦作典范的特殊用意,畢竟在此之前,呂祖謙已有憑借自身科考成功經歷為士子編選《古文關鍵》的經驗。呂祖謙選錄的賦家在當時幾乎都可獨立名家,并因作賦才能或在當時順利躋身仕途,如王曾、崔伯易;或為名家所激賞并由此在宋代賦壇占據一席之地,如張耒、刑居實;其所選賦作也大多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或在藝術或在思想方面有可資借鑒之處,足資作為士子學習的典范。根據呂祖謙為士子編選《古文關鍵》的經歷,不難發現他在文章鑒賞方面的卓越才能。該文集所選6篇北宋賦(蘇軾《赤壁賦》《后赤壁賦》、蘇轍《黃樓賦》、秦觀《黃樓賦》、歐陽修《秋聲賦》《憎蒼蠅賦》)全為北宋大家手筆,且均為有較明顯破體傾向的古賦或文賦,其選賦成因就更有跡可循了。
簡而言之,《宋文鑒》選賦特點的形成,首先離不開當時科舉重賦才的特定歷史背景以及持續不斷的罷賦與廢賦的特定政治環境;其次還與它順應了宋代文學發展的總體趨勢,即“破體為文”的風尚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最后,還與呂祖謙個人獨特的教書先生的身份密不可分,他自己就曾兩度高中(3)杜海軍:《呂祖謙年譜》,中華書局,2007年第304頁。據記載,呂祖謙于孝宗隆興元年癸未(1163)“春,試禮部(奏名第六人)。四月十二日,賜進士及第,改左迪功郎。又中博學鴻詞科”。,積累了豐富的科考經驗,而賦體作為重要的科場文體之一,其地位不言自明,呂祖謙重視賦體亦屬于情理之中。
三、《宋文鑒》選賦的后世影響
呂祖謙憑借獨特的選賦眼光,呈現出對古賦審美旨趣的回歸,表現出對當時科場積弊已久賦風的糾偏;而《宋文鑒》的選賦在體裁與題材方面的齊備性,不僅為北宋賦選提供了范例,還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宋賦的經典化;同時由于《宋文鑒》選賦在數量和質量方面的獨特優勢,相對較為全面地展示了北宋賦的整體概貌,促進了北宋賦史的初步建構。
首先,《宋文鑒》首次以選本的形式開辨賦體的先河,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后世古律賦之爭中的“復古”傾向,表現出對科場賦風的有力反撥。
《文選》開啟了總集選賦的先河,在它之后賦集的編纂都不約而同地以《文選》作為藍本。同時,許結還指出:“由于賦‘類’的意識得以擴展,且受類書的影響,古人編賦尤其是編賦總集時,多以類相分,賦集的類編成為一種常態。”[20]256《文選》代表了以類選賦的濫觴,所以賦集的類編傳統也一直得以延續,乃至到清代陳元龍編《歷代賦匯》,依舊采用類編方式。而到呂祖謙編《宋文鑒》,采用的卻是以體裁而非題材的分類方式,將所選賦劃分為古賦和律賦兩大類,雖不及詩體分類那般細致,但較類編無疑更為進步,反映出更為明晰的辨體意識。《宋文鑒》之后的賦集多數仍舊采取類編的方式,但其體類意識無疑較之前更為凸顯,這在賦學批評著作如元人祝堯《古賦辯體》、清人陸葇《歷朝賦格》等書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四庫總目提要》(集部)云:
其書(《古賦辯體》)自楚詞以下,凡兩漢、三國、六朝、唐、宋諸賦,每朝錄取數篇,以辨其體格,凡八卷。[21]卷一百八十八
由此可見,祝堯已開始自覺地對賦體的源流正變進行專門探討,并在此基礎上提出鮮明的“祖騷宗漢”的賦體復古主張。陸葇《歷代賦格》亦將賦格分為三大類,即騷體、散體、駢體(包含律體),呈現出較為自覺的辨體意識。
其次,《宋文鑒》選錄了大量北宋賦名篇,涵蓋逞辭大賦、騷體賦、散體文賦、律賦等各種體式,在囊括傳統賦題的基礎上又有新的開拓,對扭轉前代賦風起到了重要作用,并為后世北宋賦選提供了具有較高借鑒價值的范本,是宋賦經典化過程中的重要一環。翻閱當前通行的幾部辭賦史,無論是馬積高《賦史》,許結、郭維森合著《中國辭賦發展史》,還是劉培《兩宋辭賦史》的北宋賦部分,都不難發現其重點介紹的賦家乃至賦作,均與《宋文鑒》選錄情況存在高度重合。
最能體現宋賦特色的無疑是文賦,《宋文鑒》選錄的歐陽修《秋聲賦》、蘇軾《后赤壁賦》無疑是北宋文賦最負盛名的代表作,即使后人對文賦這一文體頗有微詞,也不得不承認歐、蘇這兩篇賦的出彩之處。元人祝堯《古賦辯體》即有語云:
今觀《秋聲》《赤壁》等賦, 以文視之, 誠非古今所及;若以賦論之, 恐坊雷大使舞劍, 終非本色。學者當以荊公、尹公、少游等語為法, 其曰“論體”“賦體”“傳奇體”, 既皆非記之體, 則文體又果可為賦體乎?[13]卷八
祝堯雖是立足于賦體源流正變的角度,批評歐、蘇文賦不合于正體,但另一方面他也承認歐、蘇的文賦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若放置在更廣義的“文”的范疇來看待,無疑是可獨立名世的佳作。受歐陽修倡導的古文運動的影響,宋人的騷體賦創作亦別具特色。王安石、劉攽、劉敞、黃庭堅、晁補之等人都深于騷體賦的創作,且多有佳作流傳,比如王安石《思歸賦》《歷山賦》,風格沖淡寧靜,呈現出較為濃厚的詩化傾向,劉敞《離憂賦》《栟櫚賦》、劉攽《不寐賦》則以騷體來說理,劉培認為劉氏兄弟的該類創作“反映了宋代騷體賦以理入情、以理節情的發展方向”[1]227。在北宋理學影響下興起的哲理賦同樣不可忽視,以王回《事君賦》《責難賦》《愛人賦》、周敦頤《拙賦》等為代表,其出現標志著北宋賦重說理、議論傾向發展到新的高度。而在傳統的逞辭大賦領域,亦可看出宋人創作熱情并不減退,反而有所增加,從側面反映出宋代士人高度的文化自信,甚至出現了楊侃《皇畿賦》、周邦彥《汴都賦》、王仲旉《南都賦》等京都賦佳作。而作為科場文體的律賦創作雖然較唐代更趨于程式化,內容亦更趨于枯燥,但依舊出現了像范鎮《長嘯卻胡騎賦》、蘇軾《濁醪有妙理賦》、秦觀《郭子儀單騎見虜賦》這樣廣受贊譽的名篇。以上論述所涉及的篇目,在各類辭賦史的北宋賦部分均成典范之作被屢屢提及。
最后,同時代的文章總集中,《宋文鑒》所選北宋賦無論是在數量還是質量方面無不占據壓倒性的優勢,對北宋賦整體面貌的呈現堪稱最為全備,可以說在一定意義上建構了最早的北宋賦史。
當前通行的辭賦史都傾向于將北宋賦史劃分為三個階段:北宋初期為宋賦的發軔期。這一時期賦家有從五代入宋的徐鉉、梁周翰、夏侯嘉正等人,創作主要承襲晚唐五代駢儷賦風,其中,梁周翰《五鳳樓賦》、夏侯嘉正《洞庭賦》為此期賦作代表;此期還有西昆體作家如張詠、楊億、楊侃、錢惟演諸人,在賦作形式上依舊沿襲前代,但已呈現出不同于五代賦體的卑弱風格,別具雍容華貴的盛世氣象,以張詠《聲賦》、楊侃《皇畿賦》、錢惟演《春雪賦》為典型代表;還有開辟宋初辭賦新境界的王禹偁,開始在賦作中大量抒情、論政,《籍田賦》為其代表。北宋中期為辭賦新變期。這一時期賦家輩出,文人、學者、政治家、理學家等群體均有數量或質量較為可觀的賦作流傳,且無論是在體式還是風格方面,均呈現出多樣化特征,宋賦面貌得以初步確立。這一時期賦的議論色彩更趨于強化,以范仲淹的《明堂賦》《金在熔賦》為代表;此外,此期宋賦的散文化、說理化傾向亦更為凸顯,以歐陽修《秋聲賦》、邵雍《洛陽懷古賦》為代表;梅堯臣、劉敞、劉攽、王安石、崔伯易、狄遵度等人也有佳作流傳。北宋后期是宋賦成熟定型期。這一時期的賦家以蘇軾及其周圍的蘇門文人群為代表,他們對賦境、賦藝多有開拓。這一時期賦的題材、風格更趨于多樣,手法亦更臻于圓熟,比如,蘇軾的《后赤壁賦》標志著文賦的成熟;蘇軾《濁醪有妙理賦》、黃庭堅《煎茶賦》將士人日常生活引入賦域;蘇轍《黃樓賦》、秦觀《黃樓賦》、蘇過《思子臺賦》則反映出此期亭臺樓閣賦的興盛,進而體現出北宋士人喜“登高作賦”的高雅情趣;張耒《鳴雞賦》《鳴蛙賦》、蘇過《颶風賦》等均為此期涌現的佳作。而以上所列舉的篇什均被選入《宋文鑒》,足以看出呂祖謙在選賦方面的杰出才能。
綜上所述,我們不難發現,《宋文鑒》的選賦大體上與北宋賦的發展歷程相契合,其選所賦家在北宋具有相當的代表性,選錄的賦也大多被視為北宋賦的經典在當前的各類辭賦史中屢屢出現。
《宋文鑒》的選賦一方面繼承了《文選》重視賦體的傳統,將賦列于首位,另一方面,它又打破了《文選》開創的賦的類編傳統,嘗試以體編次。呂祖謙在選賦時不僅能關注到不同時期、不同風格的賦家,在注重題材的多樣性,兼顧體式完備的同時,還能敏銳地選出最能代表宋賦特色的典范之作,并且能有意識地調和時下興起的古律賦之爭。《宋文鑒》選賦呈現的這些特點與當時科舉考試大環境密切相關,宋代科考重賦故而呂祖謙給予了賦這一文體特別地關注;幾度反復的經義與詩賦之爭使得元祐賦的價值得以凸顯,故而他大量選錄元祐時期的優秀賦作;賦體發展到宋代各種體式均已趨于成熟,開始注重辨體與破體,為此《宋文鑒》首先區分了古賦和律賦,并且選錄的賦作也多呈現出鮮明的破體傾向。《宋文鑒》古賦與律賦兼收且將古賦列于前,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元、明古律賦之爭的傾向,帶動了從重律賦到重古賦的轉向;而選錄大量北宋時期重要賦家的代表賦作又于無意間助推了北宋賦在后世的經典化進程;最后呂祖謙通過在選賦數量、體裁、題材、風格等方面的綜合考量,建構了較為粗疏但與此同時亦是最早的北宋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