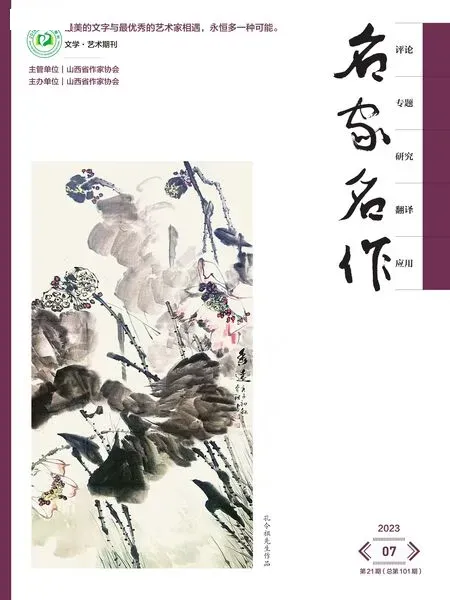當代戲曲電影的意象塑造
——以《白蛇傳·情》為例
夏浩哲
中國電影自誕生之初就與戲曲結下不解之緣。戲曲成為中國電影藝術的開端,而戲曲電影作為中國所獨有的電影類型,伴隨著中國電影的發展,在戲曲本體與電影本體的碰撞中探索著中國電影的發展路徑。中國戲曲講求“立象盡意”,即通過塑造客體形象,詮釋主體思想,以致意象表達之效。戲曲電影基本可劃分為“舞臺紀錄片”與“戲曲藝術片”,前者忠實于戲曲本體的特點,電影僅作為紀錄工具,發展至當代,即使在舞臺影像中加入簡單的鏡頭運動與景別的切換,但就戲曲中意象塑造的方式上仍然是完全依托于舞臺戲曲表演。而后者則在探索戲曲藝術與電影藝術融合的平衡點,緊跟電影技術的發展,革故鼎新地嘗試以電影化的方式塑造戲曲意象。粵劇電影《白蛇傳·情》改編自同名現代粵劇,在敘事文本上二者完全一致,皆是以經典粵劇曲目《白蛇傳》為藍本的改編作品,現代粵劇《白蛇傳·情》很好地保持了傳統粵劇的風格,其舞臺影像亦具有“舞臺紀錄片”的特點,而粵劇電影《白蛇傳·情》則作為一部優秀的當代“戲曲藝術片”,在戲曲電影的意象塑造方面拓展了探索空間。
一、電影特效構建奇觀意象
“虛擬”作為中國戲曲的美學基礎,在賦予了戲曲程式化表演無限想象空間的同時提高了戲曲藝術的欣賞門檻,若無足夠的戲曲欣賞經驗,便難以在欣賞戲曲表演的同時進行合情聯想,戲曲動作所指涉的意象也會被這個門檻所阻隔。當代以來,隨著電影技術的逐漸發展,運用電影特效技術塑造戲曲意象已然成為戲曲電影的主要探索方向。與舞臺表演相比較,電影特效在戲曲意象的塑造上呈現出兩個特點,一是對經典意象的奇觀映現,二是對傳統意象的創新移置。
(一)經典意象的奇觀映現
在《白蛇傳·情》當中,集中體現經典意象奇觀映現的段落無疑是“水漫金山,闖陣救夫”一段。在戲曲舞臺上,此段落本身就以武戲著稱,“劍舞”“水袖舞”“踢槍”等大量的動作戲令此段落極具舞臺觀賞性。十二位佩戴水袖的戲曲演員飾演滾滾浪潮,六位飾演僧人的戲曲演員手撐袈裟化身金山寺壁,滔天的巨浪與堅固的寺壁分別象征白蛇的真情與法海的責任,在水袖群舞與僧眾的復雜調度中塑造出“水”與“壁”這一對意象,表達出“情”與“理”的矛盾沖突。在表現白素貞孤身一人闖寺救夫的情節中,以一敵多的“踢槍”動作更是戲曲舞臺上的動作奇觀,一次次被拋起、踢開、再拋起、再踢開的短槍已然成為指涉“理”之重壓與“情”之抗爭的重要意象,在短槍的上下翻飛間,似乎流轉著“情”的不屈與“理”的決絕。但在電影中刪去了“踢槍”的表演,一定程度上簡化了“救夫”情節中的戲曲動作表現,而將重點放到了白素貞與許仙情感表達層面。而在“水漫金山”的情節中致力于視覺奇觀的塑造,運用數字特效完美地塑造出澎湃恢宏的滔天巨浪,配合CG 錨定技術,使洶涌的巨浪靈動地環繞在白素貞身旁,與她程式化的水袖舞相輔相成,電影特效在填補戲曲程式化表演動作所預留的想象空間的同時起到了聚焦作用,借助環繞在白素貞周身的洪流形成中心構圖,放大了戲曲動作——水袖舞本身的動作奇觀。
(二)傳統意象的創新移置
多樣化的特點體現在對傳統意象的創新與移置中。《白蛇傳》故事作為家喻戶曉的民間傳說,自明末馮夢龍所著《白娘子永鎮雷峰塔》后,故事基本定型,后被搬上戲曲舞臺,在一代代戲曲工作者的演出修改中,逐漸固定了一套諸如“雨傘”“佛缽”“斷橋”等經典意象。在粵劇《白蛇傳·情》中,基本依照著經典的意象系統,表現出純正的戲曲格調。而在電影中,借助電影特效,創造性地將白素貞與許仙在斷橋的對唱“我愿修煉千年”,轉移到了純由電影特效制作的紫荊樹下表演,紫荊樹,漫天紫荊花成為二人“不離不棄,矢志不渝”的意象。二人新婚燕爾,柔情蜜意時構建了滿池紅荷與一樹桃花,創新地引入魚戲荷間的意象,指涉白、許二人的感情,移置自《詩經·桃夭》的桃花意象也令二人的愛情愈加濃烈直觀。但多樣化的意象在豐富影像表達與增強情感抒發的同時也難免產生雜糅混亂之感,諸如“紫荊”“桃花”“荷花”等多種含義有所重疊的意象輪番出現,略有刻意煽情之嫌。
得益于電影特效技術的日臻成熟,在銀幕中塑造曾經只能在戲臺下想象的奇幻恢宏場面也愈加得心應手,《白蛇傳·情》的實踐為電影特效呈現奇觀意象與構建全新意象增強情感表達兩方面做出探索,其核心在于平衡電影特效與戲曲表演之間的關系,不可讓迅猛發展的電影特效掩蓋吞噬了戲曲表演本身的神韻,正如京劇表演藝術家梅蘭芳先生所言:“移步不換形。”也就是說: 在戲曲舞臺上創新必須謹慎, 推陳出新不能離開傳統,電影特效為步,必將日益精進,戲曲表演為形,神韻不可被遮蔽。
二、鏡頭語言豐富古今意象
戲曲電影(戲曲藝術片)跨越了戲曲與電影兩種藝術形式,戲曲中講求“四功五法”與“唱念做打”,如王國維于《戲曲考原》中所言:“戲曲者,謂以歌舞演故事也。”其中的意象也依托于相對完整、固定的歌舞塑造。而電影中的最小單位是鏡頭,依靠蒙太奇為畫面元素賦予意義,從而塑造意象,即通過鏡頭語言為事物賦予含義,使其成為意象。主要體現為兩種方式,一是對傳統戲曲意象的再詮釋,二是對電影中當代意象的新創造。
(一)傳統意象的再詮釋
在《白蛇傳》故事中,“傘”一直是代表白、許二人愛情的經典意象。在舞臺版《白蛇傳·情》中,首尾呼應式的、高懸在舞臺中央的油紙傘以極富劇場感的造型方式謳歌著二人忠貞不渝的愛情,這是結合了戲曲傳統與現代舞臺美術的塑造方式。而在電影中,則通過鏡頭語言,以電影化的方式對“傘”這一經典意象進行了再詮釋。在白、許二人在斷橋雨中首次共撐一傘的情節中,許仙手中的油紙傘只在戲曲動作中有三次運動中的完整出現。在遠景說明二人油紙傘下一見鐘情之后,油紙傘相對穩定地出現在畫面中心位置,隨后接中景二人湖中倒影,此時,油紙傘框住二人,湖面上雨落漣漪,頗有幾分風雨同舟的意味,令油紙傘不僅成為戲曲傳統中“恩情”與“愛情”的意象,同時還象征了影片所表達的“愛情是同舟共濟的守候”這一主題,在影片結尾部分,許仙斷橋邊對白素貞的表白、懺悔中得以佐證。對“傘”這一戲曲傳統意象的再詮釋,豐富了原意象的含義,為經典意象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二)當代意象的新創造
更具電影特點、為中國戲曲電影中的意象塑造進行有力探索的則是通過鏡頭組接,將電影中美術道具賦予意義,使其成為區別于戲曲傳統的新意象。得益于《白蛇傳·情》電影中盡善盡美的電影化美術設計,較于《白蛇傳·情》的舞臺紀錄片,將更加豐富的道具與設計的場景明顯或隱秘地賦予含義。其中明顯地通過鏡頭組接為道具賦予含義的效果在“白素貞飲雄黃現原形”的情節中得以體現,許仙端著酸梅湯來到白素貞的帷簾邊,在許仙的主觀鏡頭中掀開帷簾,看到白蛇,隨后接近景,展示許仙的驚恐表情,后接特寫鏡頭,盛著酸梅湯的瓷碗落地,應聲碎裂。盛著酸梅湯的瓷碗是許仙對白素貞之愛的意象,在經過法海游說,自己目睹白蛇真身后,他對白素貞的愛因驚恐而產生了動搖,碗碎湯灑,即是他心境的外化。這一情節段落在舞臺紀錄片版本中則以全景展示許仙進入帷簾,以甩袖動作配合閃電雷鳴的舞臺光效,表現許仙的內心狀態。顯然,通過前后鏡頭組接所產生含義更具有沖擊力,產生了“兩個鏡頭之積”的效果。而隱秘地將場景賦予含義則更具中國電影“寓情于景”的傳統,在白、許二人新婚后家中飲茶的段落中,采用固定鏡頭,位于中景的夫妻二人相敬如賓、互訴愛意,白素貞盡顯傳統中式妻子的溫婉,正如前景中的一方小香爐,端莊秀雅。而在白素貞現原形,嚇死許仙后,又接香爐特寫,此時的香爐焚香裊裊。香爐成為白素貞身上人性與妖性的共同意象,香爐的靜置與焚香影射了白素貞人性與妖性的兩種狀態。在“法海入院勸誡青蛇、白蛇”的情節中,多次將法海與院門進行關聯,強調法海“理之守門人”的身份責任,同時始終敞開的院門也暗示了此時法海留有人情的一面,直到“水漫金山”,法海法力所化的寺門,與白蛇和青蛇的洪水對抗,代表著雙方的徹底對立,也是對法海勸誡二人后所說的“下次見面,法不容情”的體現。
鏡頭語言的使用使電影中的意象塑造更加多元化與靈活化,和戲曲表演中意象塑造的經典化、固定化有著明顯的區別,顯然更適合當代觀眾的觀影習慣,但正因電影語言的使用極大地拓展了意象的選取空間,設計與戲曲風格相吻合的意象,精準地為影片中的道具、場景賦予含義就更為重要。
三、戲影相融共筑意象神韻
戲曲通過歌舞的虛擬呈現引發聯想,電影通過鏡頭的前后組接創造意象。兩種藝術形式的異曲同工使它們的結合——戲曲電影(戲曲藝術片)獨具魅力。但二者終究存在著本體上的差異,“以影就戲”抑或是“以戲就影”一度成為戲曲電影創作的探討焦點。電影《白蛇傳·情》,沒有糾結于“就戲”與“就影”的傾向選擇,在戲曲方面與電影方面各自都做了修改與妥協,企圖通過以戲適影與以影承戲,從而實現“戲影相融”之效。
(一)以戲適影
戲曲為電影作出的修改體現在對傳統戲曲“唱念做打”的改編上。在“唱念”方面,影片沒有采用古代粵劇使用假嗓演唱官話的方式,而是選擇采用平嗓的白話演唱,細膩婉約,通俗易懂,配合電影媒介所營造的真實感,進一步降低了粵劇的欣賞門檻,使唱詞中的“碧漆紅艃”“更隔蓬山一萬重”等意象變得愈加清晰明了,在電影呈現的視覺畫面外又增添了一層戲曲的想象畫面,令影片的觀影體驗更具虛實相生的層次感。在“做打”方面,出于對鏡頭剪接節奏與景別變化的考慮,影片刪去了較為夸張的走位調度,刪去了舞臺色彩濃厚的“踢槍”表演,保留了傳統粵劇身段,如白素貞的甩袖、法海的站相、小青的云步、鹿靈童子與鶴靈童子的亮相等,傳統戲曲通過動作塑造意象的方式幾乎完全保存,并且在電影中的小景別鏡頭下更易被強調,使意象表達更為清晰。
(二)以影承戲
電影為戲曲作出的妥協表現在對小景別鏡頭的克制使用。《白蛇傳·情》中鏡頭景別變化豐富,尊重戲曲本體,常使用多機位、大景別、固定鏡頭來輔助戲曲動作塑造意象,諸如近景、特寫的小景別鏡頭所用較少,旨在通過鏡頭組接,完善戲曲動作。小景別常在強調傳統意象特點或強調演員情緒之時短暫地介入。這一點在“白素貞孤身闖寺救夫”的情節中有代表性體現,白素貞孤身闖入封禁許仙的寺舍,在羅漢陣中舞動水袖,水袖在傳統戲曲中是象征白素貞“妖性”與“法力”的意象,在此段落中,大量地使用全景鏡頭,從各個角度展示水袖舞,在白素貞水袖卷燭臺的時刻,加入了水袖纏上燭臺的特寫鏡頭,將水袖這一傳統戲曲意象所象征的白素貞柔中帶剛的特質表現得淋漓盡致。
戲曲與電影的結合亦是傳統藝術與現代藝術在意象表達方式上的結合。《白蛇傳·情》做出了一次較為成功的嘗試,充分認識兩種藝術形式各自的優勢與局限性,在具體創作時取長補短,才能繼續探索戲曲電影甚至中國電影的發展創新之路。
四、結語
戲曲電影是中國電影的創作起點,如今伴隨著中國電影工業的日漸進步,以及國人文化自信的提高,戲曲電影的發展前景更為明朗。在傳統中創新,首先借助電影特效,構建傳統戲曲的恢宏意象。其次運用電影語言,豐富傳統戲曲的經典意象。最后平衡戲曲與電影,探索中國電影意象塑造的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