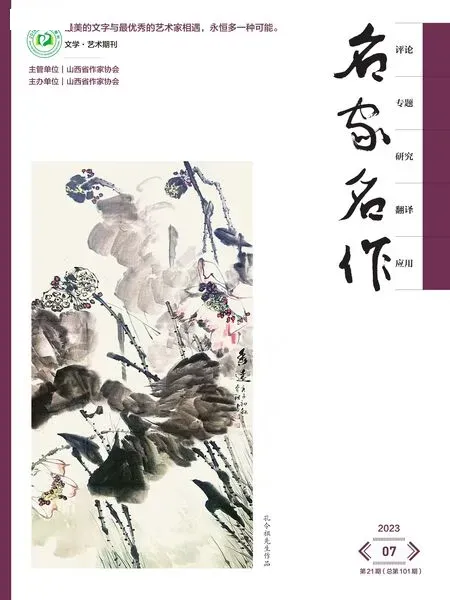愛的指引:淺析《野草莓》中對自我意義的追尋
趙 雪
《野草莓》(1957 年)講述了年近 80 歲的伊薩克在兒媳的陪同下回到母校接受榮譽學位。途中,伊薩克順便故地重游,回憶往事。本文將重點探討主人公伊薩克如何追尋自己生命的意義。在影片中,伯格曼用一個簡單的故事框架作為公路電影的載體,讓主人公完成了對意義的追尋。伊薩克的追尋可以概括為三個階段:死亡引發的動機、自我的審判和自我的重建。在經歷了這些階段之后,這位困惑的老人達到了某種程度的人生圓滿。文章的第一部分,主要分析夢境與動機之間的關系。第二部分,討論伯格曼如何通過回憶和幻覺的電影手法來表現審判階段。第三部分,分析伊薩克在路途中與不同的人產生的幾段對話,以及這幾段對話是如何完成他的自我建構的。在這三個主要階段的背后隱藏著一條線索:伊薩克對死亡態度的轉變。在這三個部分中,分別討論他對死亡的態度是怎樣的,并與他對死亡態度的轉變過程聯系起來。
一、尋找的動機
伊薩克尋找生命意義的動機源于他對死亡的恐懼。這種恐懼以夢的形式表現出來。伊薩克·博格在夢中描述了他做過的一個可怕的夢。我們看到他在一個不知名的地方走過荒蕪的街道;他看到一個沒有指針的鐘,鐘下有一雙受傷的大眼睛;然后他看到一個黑衣人倒在地上,臉上的特征模糊不清,瞬間就死了; 一個小馬車夫突然出現,當它與路燈相撞時,一個輪子掉了下來;一個打開的棺材滑到博格附近的街道上;在棺材里,他看到一具帶著他的臉的尸體;當他靠近尸體時,尸體的手抓住了他的手,可能是想把他拉進去,也可能是想讓他把尸體拉出來,然后他就醒了。在這個夢中,大多數抽象元素都與死亡有關。“然而,可以說的是,這部電影的每一個場景都是圍繞著生與死的關系構建的,我們無法將它們完全分開,也無法在任何一個時刻決定哪一個是主導。”[1]面容模糊的男子表明了生命的脆弱、死亡的突然和麻木,扭曲的面容代表了伊薩克自我認識的模糊性。受傷的眼睛將時間形象化,當伊薩克注視時間時,時間也回望著他,這種注視和回望在伊薩克、時間和死亡之間形成了一種虛擬的對峙。此外,棺材中的另一個伊薩克,“這種精神死亡的形象直擊影片的主題核心。伊薩克的夢告訴他,他的一生都是‘雖生猶死’。”[2]伯格曼將光明與黑暗、生命與死亡的二元對立置于伊薩克與死去的他之間。
一方面,伯格曼使用了強烈的燈光,黑白分明,令人眼花繚亂,毫無生氣。背景音樂的省略進一步強化了強烈的黑白光影對比,只有伊薩克的心跳聲和后來靈車發出的一連串聲音,進一步烘托出陰森、恐怖的氣氛。另一方面,這些聲音都是用傳統的畫外音引入并發出信號的。例如,在第一個夢境情節中,從伊薩克亮著的臉切換到他黑暗的軀體,而他的軀體則出現在燈火通明的街道的前景中。在荒蕪的街道和破舊的房屋之間,他的畫外音描述了他在“小鎮的一個奇怪地方”的“晨間散步”。
夢境作為影片的敘事動機,表現了伊薩克壓抑的內心、對死亡的焦慮以及對生命價值的不確定。之所以用夢境來表現死亡,是因為夢是無意識最真實的內在表達。“弗洛伊德認為,夢的意義是愿望的實現(舊譯為欲望的達成)。”[3]夢是被壓抑的欲望的修正實現,是清醒狀態下精神活動的延續。這個夢集中反映了伊薩克混亂的思想,也是他當前生活狀態的縮影。這種對死亡恐懼的壓抑一直延續到第二部分,因此我將在下一部分中具體分析對死亡的恐懼是如何進一步促成人物對自我的判斷的。
二、自我的審判
在通往隆德的路上,伊薩克對意義的追尋進入了第二部分:面對自己是如何變成一個冷酷的人。“通過夢境重溫過去是對過去的再創造,電影利用特殊的技巧對其進行了進一步的美化,博格在敘事中經歷的夢境成為他的一個個插曲,讓他對自己是什么和變成了什么有了更深的理解。”[1]在這條有目的的道路上,伊薩克在現實與虛幻之間徘徊,以一種批判的態度讓他擺脫一切偽裝,回歸真實的自我。
自我判斷通過回憶和夢境表達出來。 他的回憶與幻想相結合,年長者以旁觀者的身份審視自己的童年。“在影片中,我們看到博格處于所見所聞的邊緣。他是一個看不見的觀眾,就像我們在影院中看到的正在發生的一樣。”[1]例如,昔日戀人薩拉在樹林里采摘野草莓時,年邁的伊薩克近距離凝視著年輕、美麗的臉龐,眼神中流露出喜愛的神情。薩拉被伊薩克的表哥親吻,倒在草地上痛哭,她對背叛伊薩克充滿了愧疚和掙扎,但她無法抗拒。生日派對上,熟悉的面孔出現,歡樂的氣氛似乎又感染了伊薩克,那些溫馨的場景至今歷歷在目。“因此,這個夢提醒了老伊薩克他在生活中錯過了什么,提醒了他早年的孤獨,這種孤獨一直伴隨他多年。在慶祝活動中,他聽到薩拉形容年輕時的自己‘極其知性和冷漠’。這一指控與瑪麗安在去隆德的旅途中對他岳父的控訴不謀而合,她認為岳父是一個完全不顧他人的利己主義者。”[2]這種幻想與回憶的結合開啟了伊薩克自我批判的開端,那些隱藏的、被忽視的傷痕是他之前孤獨的原因,是他在初戀被背叛后對人際交往的回避。幻想讓伊薩克從死亡焦慮中短暫地解脫出來。 幻想與做夢的區別在于,一個是主動的行為,一個是無意識的、被動的行為。伊薩克在幻想中逃避了對死亡的恐懼,而在現實中,卻無法逃避對死亡的恐懼,對生命無意義的焦慮。這一點在下一個夢中得到了無情的揭示。
伯格曼喜歡在私密的環境氛圍中延伸和擴展故事,擴展人物的心理和情感。莎拉二世透過車窗為伊薩克送花后,他的笑臉和車周圍的燈光同時黯淡下來,直到畫面中只能看到他的臉,空間的其他部分與黑色的畫框融為一體(充分利用燈光營造窗外的背景是通過背投實現的),畫框的物理特性和人物的情緒都被戲劇化了:伊薩克被無限寬廣的陰影所包圍在這個狹窄的空間里,觀眾的注意力被接下來的恐怖噩夢所吞噬。
通過夢境,審判揭示了他余生孤獨的原因。在夢中,伊薩克對死亡的焦慮由三部分組成:薩拉的啟示、對他職業的審查和他妻子的指責。此時,薩拉直接與現在的他聯系。她拿著一面鏡子對著他的臉,敦促他審視自己,他是一個瀕臨死亡的焦慮的老人,他甚至無法面對現實,他什么都不明白,尤其是他為什么會陷入痛苦之中。在下一個場景中,伊薩克站在門外,看著莎拉和她的丈夫西格弗里德幸福的婚姻生活。“在這種親密關系中,伊薩克被形象地隔離在墻外,他感到自己被拋棄了”。[2]莎拉幸福的家庭生活場景就像一面鏡子,讓伊薩克看到了自己在婚姻中的缺失,也無情地揭示了伊薩克自己孤獨、冷漠的生活。
夢中對自己職業生涯的否定象征著他對自己價值的全盤否定。“就在他進入檢查室之前,博格不小心弄傷了自己,一根突出的釘子劃破了他的手掌。這是在為博格像基督一樣必須接受的痛苦做準備”。[1]只有經歷了這次考驗的痛苦,伊薩克才能獲得精神上的重生。他在兩個方面失敗了,被宣布為不稱職。首先,他無法識別黑板上聲稱代表醫生第一原則的語言。阿爾曼提醒他,這表示醫生現在必須請求寬恕。總的來說,阿爾曼宣稱博格缺乏醫生必須對受苦受難的病人給予的同情和個人接觸。接著,博格接到一個任務:一個女人閉著眼睛坐在椅子上一動不動。博格報告說她已經死了。然而,她突然睜開眼睛,狂笑不止。伊薩克的考試失敗了,他懷疑自己的專業能力,否定了自己的全部個人價值。
然后,博格被阿爾曼帶到一個小樹林里,在那里他可以看到自己作為丈夫的失敗。伊薩克的妻子將自己出軌的罪過歸咎于伊薩克和他的冷漠。她對伊薩克的絕對蔑視加重了表妹薩拉的不滿,阿爾曼也認為博格缺乏感情,無法成為一名成功或誠實的醫生。在一系列對他人的指控之后,伊薩克感到孤獨。阿爾曼——作為考官的自己——對老人的一生做出了評判。阿爾曼:她走了。每個人都走了。你沒聽見這里有多安靜嗎?一切都被解剖了,博格教授。外科手術的杰作,沒有痛苦,沒有流血,沒有顫抖,但這同類中最完美的成就的代價是孤獨。
在表現形式上,伯格曼使用了大量特寫鏡頭來穿透人物的內心活動。德勒茲曾評價,伯格曼將臉的虛無主義推向了極致,那就是它與虛無或不存在的恐懼關系,臉面對虛無的恐懼。在夢境中,伊薩克的臉被多次特寫,放大了他內心對死亡的恐懼和對人生無意義感的迷茫與痛苦。同時,他用重疊的畫面來展示虛幻與現實的邊界,這種手法自然地將兩個時區聯系在一起。內心的變化先通過特寫鏡頭放大,再通過重疊的繪畫可視化。
在這一部分中,他對死亡的態度是焦慮,這種焦慮變成了對與人建立新聯系的可能性的否定。自我判斷的結果是,他意識到生命的價值在于有機會與人建立聯系。然而,死亡的逼近讓他否定了自己尋找生命價值的可能性。然而,在徹底否定自我之后,他的心靈進入了下一個階段,為最終打開重建之門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三、自我重建
第三階段是伊薩克的自我重建。通過審判部分,他在“雖生猶死”的狀態下明白了生命的意義在于愛和與他人建立聯系。然而,對自我的全盤否定使他也否定了與他人建立關系的可能性。但是,在第三階段,通過在路上遇到的陌生人、與兒媳的對話以及加油站的那對夫婦,他對建立人際關系的可能性找到了信心。到達隆德后,他的行為也反映了他內在精神的重生。在心理上,他不再害怕死亡,而是張開雙臂接受死亡,平靜地走進他的野草莓之鄉。
伊薩克和瑪麗安在通往隆德的路上遇到的人,都是對他尋找意義的重要人物。首先,伊薩克在一次撞車后撿到的阿爾曼先生和阿爾曼太太,對他來說具有重要的個人意義,這也是伊薩克用客觀的眼光審視自己的契機。夫妻二人互相嘲諷,在車內爭吵、打鬧,車內氣氛尷尬、詭異,夫妻二人沒有絲毫恩愛,冷漠無情,更像是仇人,互相諷刺。瑪麗安要求阿爾曼夫婦離開這輛車,因為他們的相互憎恨給車里的年輕人樹立了一個壞榜樣。伊薩克說,他們讓他想起了自己的婚姻。此外,在下一個也是最令人不安的夢中,我們發現了他心中的想法。
然后,在旅途中,博格在一家修車廠加油時得到了一張強有力的信任投票。這家修車廠是他多年前住在那個農村社區時的一位前病人開的。這位服務員和他懷孕的妻子看起來婚姻幸福,他們真誠地贊揚這位老人在當地當醫生時對他們、他們的家庭和鄰居的仁慈和慷慨。然而,伊薩克把這對加油站夫婦的積極反饋理解為一種職業成就,而不是對他個人的尊敬。小莎拉和她朋友們的陪伴讓伊薩克重獲新生。一方面,一路上兩個男孩關于上帝和理性的爭論幫助伊薩克發現了生命的真諦。他們征求伊薩克的意見,但年長的伊薩克對他們稚嫩的認真只報以寬容的微笑。然后,伊薩克開始朗誦一首贊美詩,突然間,歡愉變成了一種令人不安的莊嚴:這首贊美詩是瑞典贊美詩中最熟悉的選段之一,選自 《最后的審判》部分,標題是“基督徒死前的希望”[2],這首詩歌頌了愛情,伊薩克似乎找到了他一直在尋找的問題的答案。另一方面,薩拉的陪伴和對他的尊重也為他樹立了自信。年輕人的熱情,就像火熱的太陽,照亮了伊薩克艱苦的生活,這是年輕人才有的溫度。在與莎拉二世的相處中,我們可以看到伊薩克會開玩笑、會讀詩、會追求情感上的東西。儀式結束后,伊薩克躺在床上,聽到三個年輕人在樓下唱歌。當他們向他行最后一個禮時,伊薩克輕聲說:“給我寫信吧。”這是與人交流的行動,象征著他開始主動與人建立聯系。
伯格曼在訪談中說過:“我們不是被上帝拯救,而是被愛……人生最重要的是與他人建立聯系。否則,你就死了,就像今天許多人死了一樣。然而,假設你能邁出第一步,走向溝通,走向理解,走向愛……那么你就得救了。”[4]最后,伊薩克明白,人應該與他人溝通,只有愛才能拯救死去的靈魂。他將這種理解體現在行動中。自我肯定的增強,加上他與兒子艾瓦爾德重新建立聯系,以及瑪麗安承認她確實喜歡他,這一切都讓他如釋重負。有了與他們輕松溝通的能力,伊薩克將話題轉移到了他給兒子的一筆貸款上,并與管家阿格達小姐建立了更加人性化的聯系,這讓他恢復了對生活的信心。影片最后一幕,他臉上露出了平和的微笑。在夢中,初戀莎拉指引他來到一個小海灣,他的父親正在那里釣魚,而他的母親則在陽傘下讀著他年輕時在夏日地區讀過的一本書。他們給予伊薩克一種被接納的感覺,而這正是他和伯格曼以及其他人一樣,一生都在尋求的。
四、結語
本文分析了伊薩克尋找人生意義的三個階段,包括動機、自我審判和自我重建,并探討了死亡與尋找人生意義之間的聯系。《野草莓》采用公路電影的敘事形式幫助主人公尋找生命的意義。“縱觀伯格曼的電影,他通過意識流表現手法傳遞出一種特殊的救贖思想:神在人群之中,是你也是我,且彼此之間的關系依托‘愛’來聯結。”[5]當伊薩克到達目的地隆德時,他尋找意義的內心旅程也在愛和與他人的聯系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