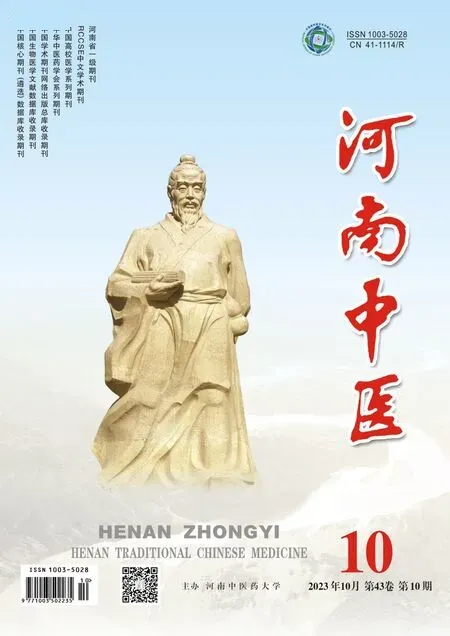從兵法角度探析《傷寒雜病論》“重攻”治疾思想*
林靖欣,溫易雯,廖華君,文小敏
南方醫科大學中醫藥學院,廣東 廣州 510515
南齊褚澄《褚氏遺書》曰:“用藥如用兵,用醫如用將。”兵法與中醫學皆植根于中國傳統文化,二者之間關系緊密,醫道中處處可見兵道之理法。前人已對兵法與中醫學之間的聯系探討得較為深入,總體而言,古人對人體生理、病理規律的認識晚于對戰爭規律的認識,因此治則的確立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兵法的總結[1],尤其是論治和遣方用藥,以兵法之精妙指導中醫之應用,《傷寒雜病論》便是其中代表。前人已對《傷寒雜病論》與兵法的廣泛聯系進行了闡述,在此基礎上,文章擇其中之一——“重攻”的思想著重進行探討,以期拋磚引玉。
1 兵法攻守與中醫攻補之醫史文化背景
戰爭離不開進攻與防守,兵法萬變不離其宗,皆以攻擊與打敗敵人為目標、守護己方安全為前提,達到擴張領土、保衛家園等目的;而治病救人也與之相似,遣方用藥意在祛除病邪,同時也要顧護正氣,從而使病人恢復健康。所以,歷來醫家都認為臨床治療如同用兵作戰,兵法對臨床治療有重要指導意義[2],兵法中的攻守與中醫的攻法、補法有相通之處。《傷寒雜病論》是集理、法、方、藥為一體的經典著作,其思想亦受到兵法的影響,這與其所處的歷史背景及醫學文化有關。
1.1 醫學分科之疾醫我國在周代已將醫學分為食、疾、瘍、獸四科。《周禮·天官冢宰》云:“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春時痟首疾,夏時有癢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對于此處之“癘”,《玉篇·廣部》解釋為“疫氣”,《說文解字》認為“癘”是“惡疾”,皆為環境中的邪氣。可見,疾醫專治“癘疾”,治病的主要方法就是祛除外來之邪,與之相對的,食醫則通過調整飲食營養來使人恢復健康。從兵法的思維分析,疾醫所采取的策略便是“攻”,攻邪外出以復正氣;食醫青睞的策略是“守”,扶正以防邪。這種根據治療思路和方法進行分類的思維對后世影響頗深。
1.2 建安之疫仲景在序文中提到:“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可見當時疫病之兇險,傳染性強,致死率高,而這次疫病也是張仲景立志鉆研醫學的緣由之一。曹植《說疫氣》認為,疫病的發生是由于“陰陽失位,寒暑錯時”,正如《素問·六微旨大論》中對“至而不至,未至而至”的論述,認為“應則順,否則逆,逆則變生,變則病。”氣候異常不利于自然界萬物的正常生長,故能致病,此即外邪,可參照疾醫的治病思路,使用祛邪外出之法治療。故可推斷,張仲景受時代影響,較為注重“攻”法,即以祛邪為主。
1.3 從《黃帝內經》看兵法與醫學的淵源張仲景在《傷寒論》原序中提到,本書是其博取《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藥錄》等眾家之所長后而成,故可以《黃帝內經》為例,追溯其與兵法的淵源。《黃帝內經》與《孫子兵法》成書年代相近,且同根同源,皆植根于中國古代哲學思想[3],故《黃帝內經》中多處可見以兵法證醫理。如《靈樞·逆順》化用《孫子兵法·軍事》中的“勿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陣”一句與刺法的禁忌進行類比說理:“兵法曰:無迎逢逢之氣,無擊堂堂之陣。刺法曰:無刺熇熇之熱,無刺漉漉之汗,無刺渾渾之脈,無刺病與脈相逆者。”故而在《素問·陰陽應象大論》引出治療之法:“善用針者,從陰引陽,從陽引陰,以右治左,以左治右。”正如《孫子兵法·虛實篇》云:“進而不可御者,沖其虛也。”皆為避實就虛之法[4]。《傷寒雜病論》對《黃帝內經》進行了傳承與發展,在將兵法運用于中醫理論與臨床治療方面更是頗有特色,如重視“攻”與“守”之法,尤其重視“攻”法。
2 張仲景“重攻”思想與“攻守”策略
《傷寒雜病論》中多次直接或間接出現“攻”法。直接出現“攻”字的有33處[5],如論述病在臟則“當隨其所得而攻之”,治療水氣病中的浮咳喘逆“當先攻擊沖氣令止”,桂枝湯可“攻表”等。也有間接體現“攻”法的治療方法,如汗、吐、下、清等[6]。張仲景應用“攻”法時靈活多變,相較而言,“守”法較為固定,主要體現為顧護胃氣,多為人參、甘草、大棗、生姜配合使用[7]。
2.1 有邪必攻《孫子兵法·虛實篇》中提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認為善于作戰者是主動的,能調動敵人而不被敵人所調動,如此才能取得主動權,掌握局勢,使作戰游刃有余,以求取得勝利。在論治時,則應積極地祛除病邪,有邪必攻,而非被動防守,須知敵不卻則戰不勝,邪不祛則病不瘥。此法尤適于邪實者,如陽明腑實證、痞證、結胸、水氣等。
以陽明腑實證為例,《傷寒論》第180條陽明病的提綱條文為“陽明之為病,胃家實是也”,“實”之一字道出了陽明病的核心。陽明,兩陽合明也,陽氣極盛。在《傷寒論》中,陽明病涵義豐富,可言其病位為手、足陽明經,主要累及胃與大腸二腑;也可指病性為燥熱,因熱而燥,因燥而結。六腑以通為用,若胃熱腸燥,津液耗傷,燥結成屎,無法外排,則腑氣不暢,可見便秘、腹滿疼痛、熱結旁流等燥熱之象。故陽明病的辨證論治要從實證切入,若燥實已成,則須攻其實,因勢利導,應選用攻下之法,用承氣湯類方,正如尤在涇言:“蓋陽明以胃實為病之正,以攻下為法之的。”若一味防守,只行滋陰潤燥之法,不攻其積,則病邪無出路,閉門留寇,病情愈加嚴重。
再如痞證,《傷寒論》第149條云:“但滿而不痛者,此為痞,柴胡不中與之,宜半夏瀉心湯。”痞證病機為脾氣虛寒而胃有郁熱,脾胃無以升清降濁而氣塞,故溫補脾氣和清熱缺一不可,此雖虛實并見,也需攻邪。原文第164條云:“傷寒大下后,復發汗,心下痞,惡寒者,表未解也。不可攻痞,當先解表,表解乃可攻痞。解表宜桂枝湯,攻痞宜大黃黃連瀉心湯。”此條雖為熱痞,卻因下、汗后而陽氣虛弱,虛實兼見,故大黃黃連瀉心湯之煎服法為“以麻沸湯二升漬之,須臾絞去滓”,既可清中焦之熱,又可避免過于苦寒以傷及脾胃之陽[8],以達攻痞之效。吳昆在《醫方考》中注解半夏瀉心湯:“姜、夏之辛,所以散痞氣;芩、連之苦,所以瀉痞熱;已下之后,脾氣必虛,人參、甘草、大棗所以補脾之虛。”故在治療痞證的方劑中,如半夏瀉心湯、生姜瀉心湯、甘草瀉心湯、附子瀉心湯和大黃黃連瀉心湯,都有黃芩、黃連二藥,以瀉熱除痞,正中“瀉心湯”之“瀉”。
同樣,結胸與水氣病的治療也以攻法為主。結胸為邪氣結于胸中,故治以祛除邪氣。水氣病則為本虛標實之證,多由臟腑功能障礙導致水液滯留于體內所致,故常水與寒并見。張仲景提出治療水氣有三法,“腰以下腫,當利小便;腰以上腫,當發汗乃愈”和瀉下逐水,以祛除病理產物為要。
2.2 速攻速決《孫子兵法·作戰篇》強調速攻:“故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說明作戰要速戰速決,再巧妙的計謀也經不起久戰的消耗。此句放于治療亦準,病邪初襲則容易祛除,久病則必虛,治病需趁早。《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早已指出早期治療的重要性:“邪風之至,疾如風雨,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膚,其次治筋脈,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臟。治五臟者半死半生也。”感受外邪,必須盡早治療,否則病邪會由淺而入深,由輕而轉重,最終不可醫治。
該思想在《傷寒論》中也有體現,如治療外感的方劑隨著病邪由太陽到陽明的深入而變換,由表及里依次為麻黃湯、大青龍湯、麻杏石甘湯、白虎湯。寒邪襲表,太陽首當其沖,衛陽被遏,營陰凝滯,太陽經氣不利,但正氣足,邪氣盛,正邪相爭,故為表實證[9],證見“頭痛發熱,身疼腰痛,骨節疼痛,惡風,無汗而喘”,故以麻黃湯發汗解表則可愈。若遲遲未治療,當汗不汗,則錯失良機,病情進一步演化,表邪不解,陽氣郁而化熱,便從表寒證轉化為表寒里熱證,證見“脈浮緊,發熱,惡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煩躁”,此時已不適合用麻黃湯,須解表與清里同用方可奏效,故用大青龍湯,在麻黃湯的基礎上倍用麻黃,再加石膏、生姜、大棗,故與麻黃湯相比,發汗之力更強,且能清熱除煩,即增強了攻勢,氣隨液脫,此時則會對正氣產生更大的損耗,故用生姜、大棗顧護胃氣,以資汗源,可見治療并非一味攻邪,以攻勢猛為佳,也須隨機應變。若寒邪由表入里,“肺主皮毛”,故襲肺,此時表邪將盡,而里熱未盛,發為肺熱喘咳證[10],可見“汗出而喘,無大熱”,治宜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方中石膏倍于麻黃,故重清宣肺熱而輕發汗解表,再加杏仁助平喘而降肺氣,甘草顧護胃氣,共奏清熱宣肺、降氣平喘之功。若仍未能在此階段祛除病邪,邪氣進一步入里,則熱入陽明,見“身熱,汗自出,不惡寒反惡熱”,此時里熱熾盛而腑實未結,用白虎湯。白虎湯以清陽明里熱為目的,而非清脾胃之熱,故用粳米、甘草,防止脾陽因寒涼之劑衰敗。可見,及時治療、早期治療之重要,“用藥如用兵”,戰機不可耽誤,病情亦不能延誤,故攻邪宜速攻速決,治病宜早。
此外,進攻重速,收兵也需及時,用于治療,則講究中病即止。在論述服藥方法時,張仲景多次提到“停后服”“止后服”,亦體現了速攻速決的思想。
2.3 伺機攻邪速攻速決,非沖動而為,應乘機以攻。《孫臏兵法·見威王》言:“事備而后動。”說明作戰應做好充分準備之后才可行動。《孫子兵法·火攻篇》言:“非利不動,非地不用,非危不戰。”指沒有利益不要行動,沒有取勝的把握不要用兵,不到危急關頭不要開戰。二者都強調了作戰要講求時機,而臨證用藥亦然[11]。作戰時機有先后之分,前者先發制人,后者先按兵不動,試探而后攻,二者各有所長,皆在《傷寒論》中有所體現。
2.3.1 先發制人《傷寒論》第54條言:“病人臟無他病,時發熱,自汗出而不愈者,此衛氣不和也,先其時發汗則愈,宜桂枝湯”。此時臟腑無病,卻時發熱而自汗,以其衛氣不和,“衛氣不共榮氣諧和”,衛氣不能固外,營氣不能內守,故發熱自汗。可見,病邪在表不在里,仍需攻邪。其發熱汗出時發時止,若在發熱汗出之時服藥,正值正邪交爭激烈,藥力難以發揮作用。《孫子兵法·軍爭篇》云:“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故應避開正邪相爭之時,趁虛而入,在發熱汗出之前服藥,此時榮衛不和,病邪也處于將發作而尚未發作之際,可使藥力直達病所,從而能驅邪外出[12],此謂“先其時發汗則愈”。
2.3.2 角而后攻《孫子兵法·虛實篇》云:“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處。”通過與敵人試探性接觸以知敵人兵力部署,找出薄弱之處,便可避實就虛,取得勝利,體現了試探法之妙。《傷寒雜病論》中多處運用了試探之法,通過給予少量藥物或飲食后觀察病情變化[13-14],以鑒別并確定病因病機,避免誤診誤治。《傷寒論》第209條曰:“若不大便六七日,恐有燥屎,欲知之法,少與小承氣湯,湯入腹中,轉矢氣者,此有燥屎也,乃可攻之;若不轉矢氣者,此但初頭硬,后必溏,不可攻之,攻之必脹滿不能食也。”大承氣湯的適用條件為陽明腑實證,“胃中有燥屎”,但僅憑不大便無法判斷。因此,仲景用少量的小承氣湯進行試探,若服后僅矢氣而無大便,可見燥屎已成,而小承氣湯之力雖能下卻尚不足以通便,此時便可用大承氣湯攻下。若服后無矢氣而大便下,大便先硬后溏,下后腹部脹滿而不欲食,此非陽明腑實證之燥屎,而是脾虛證[15],故不能用承氣湯攻下。此外,也可用飲食來試探,如用水“少少與飲之”來辨別津傷胃燥抑或是蓄水證,前者可不藥而愈,或用白虎湯類方,后者則用五苓散化氣利水。
伺機攻邪,或先或后,關鍵在時機的把握,即準確判斷病情,抓住時機,及時用藥,如此才能藥到病除,不作無謂的戰斗。
2.4 攻守權衡而以攻為主《孫子兵法·軍形篇》對攻與守有深刻的認識:“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若要不被敵人打敗,必須先作好防守工作;要戰勝敵人,就要進攻,若要取勝,必先保證己方絕對安全然后再交戰,而防守是為了更好地進攻。在《傷寒雜病論》中,因病的特性、當時的認知等原因,多注重攻邪,正如兵法中認為防守是基礎,但要戰勝敵人,進攻依然必不可少。《傷寒雜病論》中的攻守權衡可大致分為以攻為主、守為輔和先進攻、后防守。
2.4.1 攻為主、守為輔《孫臏兵法·勢備》曰:“故有鋒有后,相信不動,敵人必走。”論述了陣型若前鋒與后衛具備且穩定協調則實力大增。《孫臏兵法·客主人分》云:“客倍主人半,然可敵也。”“客人”為進攻之意,“主人”為防守之意,即進攻比防御兵力多則可以交戰。在治療虛實夾雜證時,張仲景多以攻為主而輔之以守,即以祛除病邪為主,扶正補虛為輔,其目的并非是補其不足,而是為了使機體能承受藥物的攻伐之力,補虛多是在病邪祛除后進行,如十棗湯服后需“糜粥自養”。
《傷寒論》全書113首方,生姜、大棗、甘草合用共有31首方,三者配伍有調和營衛氣血、補脾扶正祛邪之功。在治療頑疾,或復雜病證時,有時需要使用峻猛之藥,然而此時病人往往正氣不足,恐難以承受藥力,配伍生姜、大棗、甘草,則可顧護胃氣不受峻烈藥性所傷,邪祛而正存。如《傷寒論》第161條的旋覆代赭湯:“傷寒發汗,若吐若下,解后,心下痞硬,噫氣不除者,旋復代赭湯主之。”外邪雖發汗而解,但經誤下誤吐,中氣已傷,脾胃失司而痰涎內生,肝胃氣逆,可見虛實夾雜。然而張仲景并未峻補脾胃,蓋因未見極虛之象,故仍以攻邪為主,以旋覆花、代赭石、半夏降逆化痰、理氣消痞,但此三藥易進一步耗傷中氣,故用人參、大棗、生姜、甘草益氣健脾[16],顧護胃氣。《醫宗金鑒》注:“方中以人參、甘草養正補虛,生姜、大棗和脾養胃,所以安定中州者至矣。”全方重在化痰降逆,兼以補虛,以攻為主,守為輔,故邪祛正安。
2.4.2 先進攻、后防守《孫子兵法·虛實篇》云:“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于進攻能使敵人無法防守。故張仲景祛除病邪重用攻法,尤其是當正氣猶存,可耐受藥力時,更是純攻無守,如抵當湯。《傷寒論》第125條言:“太陽病,身黃,脈沉結,少腹硬,小便不利者,為無血也,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血證諦也,抵當湯主之。”此為瘀熱深結、痼結太甚。尤在涇認為:“瘀熱在里者,其血難動,故須峻藥以破固結之勢也。”故方中用水蛭、虻蟲直入血絡、攻堅破瘀,桃仁、酒浸大黃活血化瘀瀉熱,皆峻猛之藥,共為攻下瘀血之峻劑,以治療瘀血重證[17]。病邪深結,痼疾日久,若非猛攻定攻之不下,病邪未祛,而又反復服藥,更是損傷正氣,病邪入里傳變,后患無窮。故宜速攻、重攻,集中兵力,祛其病邪為當務之急,即便稍有虛象,也宜瘀熱已盡后再復其正氣,即后以防守。
純攻非長久之計,擊敗敵人后回守以防過度消耗和后續攻擊才是正道。《司馬法·仁本第一篇》言:“故國雖大,好戰必亡。”早已總結出窮兵黷武必亡國的道理,祛邪亦非唯用猛藥或用藥以大劑量。《孫子兵法·行軍篇》言:“兵非貴益多也,惟無武進,足以并力、料敵、取人而已。”說明取勝的關鍵不在于兵力多,而在于不冒進,集中兵力,精準打擊。用于治療,則以辨證論治為原則,對證下藥,中病即止,速戰速決,否則易損耗正氣,導致體弱,甚至矯枉過正,引發他病。正如兵法中講究“兵在精而不在多”,《傷寒論》第16條指明要“觀其脈證,知犯何逆,隨證治之”,故治療貴在辨證。
3 結語
兵法思想與中醫學都建立在中國傳統哲學思想基礎之上,哲學中的陰陽五行等學說對軍事與醫學領域均有較大影響,二者有互通之處,故可借兵法理解歷代中醫學說的理、法、方、藥,啟發臨床診療新思路。從兵法的角度探析《傷寒雜病論》,發現其遣方用藥之規律與用兵作戰之道相似,論治思路亦與兵法謀略有異曲同工之妙。其治疾思想以攻為重,力求盡早驅邪外出,輔以必要的防守,即顧護胃氣,以能承受藥物攻伐之力為度,與兵法中防守為前提、進攻為關鍵的作戰思路相一致。
雖然兵法與中醫學有諸多相似之處,但二者也存在差異,如兵法還善于利用敵我雙方的心理,也需要考慮國家、將士的實力與人民的支持等,對于中醫學的研究并無大用,故不可走進形而上學的困境,牽強附會,而應尊重中醫學的學科特點,有所取舍地學習與借鑒,才能使中醫學在多學科的背景下兼收并蓄,取長補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