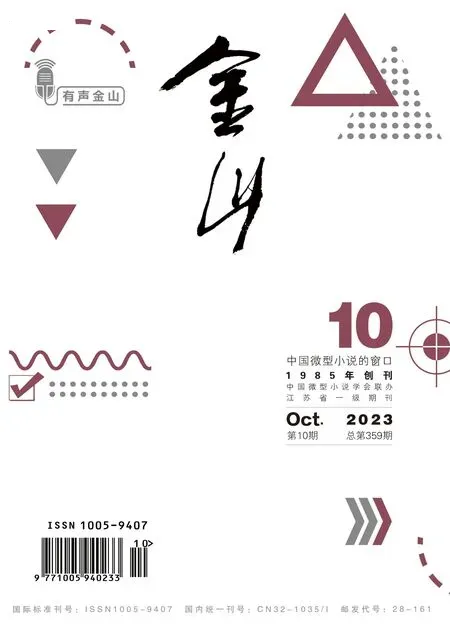拴住靈魂的兵團連隊
新疆/王東江
連隊人來自四面八方,之前互不相識,休說血緣,地緣也少有,隔省隔州隔縣,八竿子打不著;連隊人姓氏繁多,你張我李他趙,步步“高”、虎頭“王”、順水“劉”,不同宗不同族,鮮有關聯;連隊人民族眾多,交談起來南腔北調,但卻熱絡和諧。大家聚集在連隊的旗幟下,竟有磐石之堅、利刃之鋒。是怎樣的魅力使他們五指一拳、筋骨相連?又是怎樣的“誘惑”使他們內修同心軟功、外練團結硬功呢?他們為是兵團人而驕傲,他們把“兵團”二字吐得清清脆脆,像砸釘子,恨不能釘進人家的骨子里。連隊,這個兵團最末級的建制單位,一定有一種震懾靈魂的力量,若不,何以有如此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將連隊人打造成一支分開是一根根鋼釘,聚集是一塊鋼板的硬核隊伍呢!
從弱冠之年起,我便加入了連隊。那時正值我人生低谷,連隊張開雙臂熱情地接納了我這個遠方游子,替我揩干眼淚,植入骨氣,扶我挺直腰桿做了兵團一員。自此,我生命的根就扎在了連隊,與樹根、草根、莊稼根一起,拼命吸吮這片熱土的營養。
屈指算來,我扎根連隊已逾三十年,我的足跡在連隊的街巷阡陌一次次鮮明,又一次次風干。滴灌加壓站是我的摯友,林帶樹木是我的良朋,每塊戈壁都與我相識。沙棗樹上的松鼠能聽出我的聲音,荊棘叢中的野兔能分辨出我摩托車的馬達聲,就連路邊草垛里的田鼠,在我每一次咳嗽時,都躍上路基,瞪著友善的圓眼望著我。這里有我的小家,有相濡以沫的妻子、乖巧伶俐的兒女,可我更愿把連隊認作大家,連隊的每一個人,都是我的至親。我自幼孤苦,希望得到眾多兄弟姐妹的眷顧,在連隊,我感受到了家的溫馨。
我最好的哥們兒,河南人小鄭,14 年前千里迢迢從老家來到連隊。起初他是抱著試試看的態度,一個人來的。春三月來的連隊,冬十月他就心急火燎跑回老家,把老婆孩子連戶籍加學籍一起遷了過來。為斷心血來潮時想回家的后路,他干脆把老家的房產變賣得一干二凈。一次把酒言歡,我問他當年為何如此決絕。他狡黠一笑,一杯酒入口,一箸菜入肚,方道:“一個連隊抵老家一個鄉鎮,農民,根就扎在地上,有地種是農民的幸運、福氣。豫劇《朝陽溝》里栓寶媽有句話:縱有天大的本事、地大的能耐,誰也不能把脖子扎起來。民以糧為天。糧食哪來?地里來!抓住地,就抓住了藏寶洞的金鑰匙,這是最誘惑人的。再者,連隊人講團結、夠義氣,誰遇上個山高水遠、馬高蹬短的,那是真出手、幫真忙。這點,我最佩服,有點你們梁山好漢的風格(我老家山東)。最抓人心的,是連隊處處充滿生機、朝氣、活力,那種蓬勃向上的氣息,讓人熱血沸騰,教人不愛她都難。她吧,有那種感覺,怎么說呢?能將人的靈魂拴住!”
“能將人的靈魂拴住。”我反復咀嚼著這句頗有深意的話。我們這個邊境小連隊,靠什么拴住了幾百號人的靈魂?答案只有一個,就是“兵團精神”,它觸及靈魂、震撼靈魂、蕩滌靈魂、升華靈魂。
被連隊拴住靈魂的,還有大學生志愿者小李。他是外省一所農業學院的本科生,響應“西部計劃”報名應聘而來的。他說:“在眾多西部地區中,我一眼就挑中了兵團。”他把“挑”字說得很著重。一來到連隊,他就有游龍入海、林鳥飛天的快感。萬畝條田是他的用武之地,各種實驗田最大限度地滿足著他的求知欲和成就感。短短兩年,他就有了聊以自慰和足以傲人的成果。他參與培育的玉米新品種,同樣水肥條件下,畝產增一百公斤以上。單我們一個連隊,每年種植玉米都在萬畝,那就能增產一百萬公斤。向科技要效益,已成為了現實。現在,小李不再是我們的志愿者了,他把工作關系轉到了連隊,成了一名地地道道的連隊人。
在與連隊相鄰的某口岸經商發了大財的河北人老魏,最近撇下樓房搬到連隊,成為“編外”連隊人。問其緣由,答曰“宜居”。老魏看好連隊清幽的環境,連隊四周被密密麻麻的莊稼地包圍著,名副其實的天然氧吧,他說他這個“連隊人”當定了,當“鐵”了。看來,老魏的靈魂也被拴住了。
連隊拴住了一群人的靈魂,連隊的凝聚力令人向往、迷戀,不離不棄、矢志不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