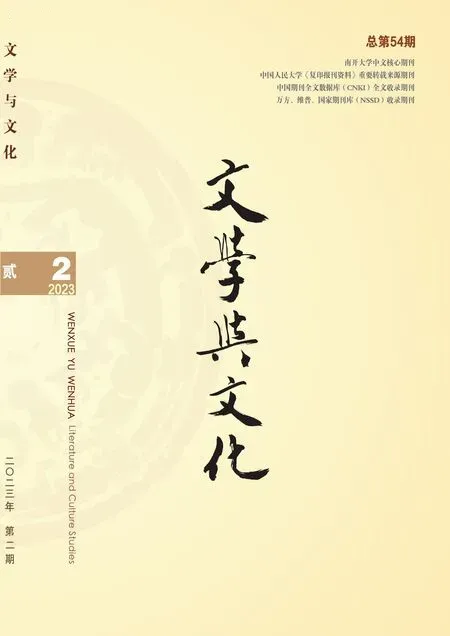朝向自我的詩歌寫作
——評梁平近年來的詩歌創作
程繼龍
內容提要:梁平詩歌的精神維度是多向的,近年來他的寫作的一個顯著變化是對“自我”的關注,這在他新出的詩集《時間筆記》中有集中的表現。復雜的現實刺痛了梁平的內心,致使他從超我的、宏大的事物中后退,轉向了對自我的尋找和重建。因此,不論是晏居、讀書,還是出游,他都在追求心境的恬適和對萬物的親近,接近了莊子和一些他所欽敬的西方詩人的風儀。梁平苦心找到的、在詩歌中建構起來的自我是多樣的,活潑潑的。這也使他產生了對詩歌及其與世界關系的新認識。
梁平說自己“寫詩四十年”,他的詩歌寫作和個人精神成長、歷史進程一樣,呈現出持續的階段性的變化。他一步步按照自己對現實、歷史、文化的理解、體悟、投入寫作,逐漸地長成了他想成為的詩人的模樣。梁平回顧他20世紀80年代的寫作,認為是憑借才華和靈感的一時的青春寫作。后來的詩集《巴與蜀:兩個二重奏》和《家譜》,則是攜個人的生命記憶溯游在更為宏大、久遠的文化地理長河中,充滿了家國情懷。長詩《三十年河東》是對“改革開放”過程的全景式的記錄,“一個偉大的時代,一個我們參與、親歷和踐行的時代,如果不用詩歌記錄下來使其成為文學的記憶,這是中國詩歌的悲哀,也是中國詩人的悲哀”①舒晉瑜:《梁平:宏大敘事的境界和主旋律詩歌的技巧》,《中華讀書報》2018年8月8日第19版。。最近幾年,隨著人生閱歷的積淀和對詩歌持續思考的深入,他的詩歌寫作集中地指向了“自我”。他堅定地說:“我的詩一定是我在……在我的詩歌里看得見我的喜怒哀樂。”②舒晉瑜:《梁平:宏大敘事的境界和主旋律詩歌的技巧》,《中華讀書報》2018年8月8日第19版。新出詩集《時間筆記》進入又超離時間,外在于物又不離于物,自我對話又沉默冥想,展示了一個詩化了的自我的繁復狀態。批評家耿占春說,“《時間筆記》就是詩人的心路歷程”,是詩人自己的“私人檔案”。③耿占春:《從“私人檔案”勘探的密碼編輯——梁平〈時間筆記〉的一個導讀》,收入梁平《時間筆記》,花城出版社,2020年,第1頁。“自我”既是一個立足點,又是一個理想,梁平借以繼續打開他的寫作,我們也借以進入他詩歌的世界。
一 現實的隱痛
梁平一度很看重“現實”。他說:“現實對于一個作家、一個詩人的寫作而言,絕不是可有可無的符號,而應該是作家、詩人的高度自覺,應該把抒寫現實作為這個時代的留下文學記憶的己任。”①梁平:《閱讀的姿勢——當代詩歌批評札記》,四川文藝出版社,2014年,第22頁。現實既指正在展開中的某種整體性的客觀實在,也指個人參與其中的充滿質感和細節性的生活現場。在梁平這里,現實并不是康德意義上的“物自體”,完全與個人的感受絕緣;相反,個人在它面前有一定的靈活度,在一定范圍內可以參與、感知到。整體性的現實分衍出了“時代”,梁平曾經對這“時代”充滿了投入和擁抱的熱情,比如《三十年河東》的寫作。但之后更多地是感受到了“現實”不可抗拒的,乃至冷硬、非人性的一面。《時間筆記》第二輯就保留了一些和現實“硬碰硬”的典型文本。比如《鄰居娟娟》,這首詩克制地敘述了“鄰居娟娟”的事跡。娟娟是一個坐臺女,她笑稱自己是“臺商”,她的笑“比哭難看”。“白天是娟娟的夜,/夜是娟娟不為人知的繁華。”她在夜里賺取她的生涯,也揮霍她的青春,“搖晃的燈光,搖晃的酒瓶……搖晃的床”。“背后有人指指點點”,娟娟也哭過,她的哭“穿透冷硬的墻”,后來她被警察帶走,被人遺忘了。這是一個“巷子”女孩的淪落史。而娟娟這位女子最初只不過是一個中學就輟學了的普通孩子。姊妹篇《刑警姜紅》中的人物“姜紅”,最初是一個頗有英雄氣息的“正面人物”,只不過后來終于認識到“出來混都是要還的”,“勛章與手銬都閃閃發光……姜紅的紅,與黑只有一步”。“我”去監獄探視他,只能和這位少年同窗“相擁而泣”。梁平將詩的觸角探入了底層、邊緣人群生活的一角,黑暗中突起的刺,刺痛了他的神經,提醒著我們現實的另一個模樣。
更大的“隱痛”,在于現實的宰制性力量對人的控制。這種力量是灰色而無邊的,淡漠無聲地網羅住活生生的人,使人就范,磨損、扼殺人的生命激情。“一只鋼針扎進身體,/隱隱作痛。”(《斷片》)“藍天的藍不藏刀斧,藍得透徹。”(《舍與得》)反讀此詩,可知與“藍天”相對的事物是“藏了刀斧”的。“看見一堆笑,/看不見笑里藏的刀。”(《城市的深睡眠》)這樣隱藏了實際所指,借助象征不斷向真相閃回的詩句,在《時間筆記》中比比皆是。這和他敏銳、柔軟的詩人的心靈有關,也和他在實際生活中所從事的職業、擔任的角色有關。現實的危險造成了詩人內心的掙扎和撕裂。《如果要當兇手》:
餐桌即舞臺,形形色色,
從海里打撈的大牌不分主次。
鮑魚、生蠔、刀魚、海膽,悉數登場,
蝦蟹不在演員表上。
我正襟危坐,心生驚悸,
只好躲在杯盞的后面,
灌醉自己。我的表演比專業更專業,
始終舉不起一雙竹筷。
好想把筷子扔進海里長出海藻。
這首詩寫置身飯局時的左支右絀、欲罷不能的心態。我們都知道,飯局不單是為了吃,生理性的吃變成了次要的,重要的是吃喝這一儀式背后隱藏的利益、人情、權力關系,因此構成飯局的諸多要素,進入飯局的各個角色,都具有了矛盾的二重性。“海里打撈的大牌”鮑魚、生蠔之類既是名貴的菜肴,眾目聚焦、眾口所向的對象,同時又是可悲的犧牲品。“我”與其他參與其中的“客”在“主人”面前,既是所款待、敬重的對象,又是被套入,難得自在的“失去了主體性”的人。“主”和“客”均戴上了“面具”,同時成為演員和觀眾。在這種情況下,“我”的緊張、不適可想而知,“我正襟危坐,心生驚悸,/只好躲在杯盞的后面,/灌醉自己。”“我”驀然“記起釋道海師傅對我說,/忘其耳目。”想超脫而不得,無奈中一再幻想,“海洋里的生命自由、鮮活,/海上風平浪靜,蔚藍,一直蔚藍”。吃火鍋的情景和在海上“撈藻”的想象交疊了起來,造成亦真亦幻的效果。而“我”作為“兇手”對“生猛海鮮”的殺戮,也可以說是對鮮活的人的象征性殺戮,對人的自由的殺戮。會議、喝酒、飯局是日常工作、生活的不可避免的內容,“現實”借此施展著它的控制力,也一再伸出它的尖刺。
事實上,出于詩學轉化的需要,梁平對現實荒誕、非人性的一面較少做直接的記錄和表現,更多地是間接、迂回的透露。所以“記夢”“寫夢”就成為一個常規的修辭手段。中國人常說,“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弗洛伊德的釋夢學說也是眾人皆知。白天、現實中遭到壓抑,無法實現的欲望、念想就會以畫面、情節等形式改頭換面地表現出來。因此“夢”即“現實”的一個棱鏡。“夢”及幻覺、走神這些“夢的近似物”散布于梁平的寫作,一起折射著他對現實的“創傷性經驗”。“這個夢是一次殺戮,/涉及掩蓋、追蹤、反追蹤,/和亡命天涯。”(《我經常做重復的夢》)在另一個夢中,“我”置身一個酒局,“我看不見他們的五官……此刻有一束光打在桌上,/像一把利刃劃過,/幾只被切割的手有點慘白”(《在某個夜里突然失蹤》),光線變成了刀子,切割人的肢體,白天生活的印記在夢中帶來多么悲慘、恐怖的后果。“我夢里都是神出鬼沒,/那天神對我說,/賜你萬能的權力,詛咒你敵人。”(《夜有所夢》)現實中的“貪嗔癡”要求在夢中予以實現。為了應對生活,詩人曾陷入了怎樣的“恐怖”和“顛倒夢想”。
弗洛伊德認為現實是一種壓抑機制,遵從的是實利原則。為了維持大局,趨利避害,壓抑了人的本能的快樂,甚至整個文明都建立在對本能壓抑的基礎上。詩人受到的現實壓抑并不一定多于常人,但詩人因其感受力的敏銳和對心靈世界的執著,感覺到的現實的痛苦就比常人多一些。梁平正好是這一類詩人,而且他的感受具有普遍性。《有病》一詩所說的“有病”,不但是詩人自己的“病”,而且是能統攝整個現實的時代病。“我”坐在車里,所有的車都“沖我而來”,“后視鏡看見有車燈在快閃,/有呼吸急促的鳴笛”,人們都匆匆忙忙,怒氣沖沖,“我”“被逼起步,被裹挾著奔向前方,/一座城市向我砸來,/找不到出口……”,以至于“我心生恐懼”,身不由己,成為一個擺設。詩人明白,“問題在于這絕不是某個偶然,/而是我的常態”。現代都市生活節奏就像紅綠燈路口的人流、車流一樣,匆促到“靈魂趕不上肉體”。超現實場景成為生活的真實狀態,“病態”成為“常態”。
在詩人的感覺中,“無邊的現實”猶似一個巨大的牢籠,詩人在其中孤獨,掙扎,噩夢連連。詩人直言“厭倦”,“厭倦時刻分明的一日三餐,/厭倦早出晚歸兩點一線……厭倦口蜜腹劍勾心斗角。/厭倦虛情假意心照不宣”(《喜歡厭倦》)。他甚至宣稱“喜歡厭倦”,這厭倦超出了現實,有了形而上的色彩。
二 重新面對自我
“自我”往往是危機的產物。若無外在壓力,詩人那個童蒙、混沌的“我”會一直保持下去。拉康認為嬰兒受突然闖進腦海的自己的鏡中形象的刺激,開始了艱難的“自我”建構過程。這一情形和詩人的是相通的。在現實的歧路紛披中,現實帶來的痛苦掙扎中,梁平將內視的目光對準了自己。這無疑是一種更深刻的覺醒。那個“我”出場了。“我被我自己掩蓋,/草堂的荒草爬滿額頭,/碑林之間,只看見天空的背面。”(《我被我自己掩蓋》)“我懷疑夢里的另一個我,/才是真實的我。”(《經常做重復的夢》)“我是我自己的錯覺。”(《我是我自己的反方向》)“我是一個病句,/不再給自己搭配主謂賓。”《我是一個病句》“我”在主體的心境中來回撞擊,反復詰問。主體內部的這種混亂,既提供了新的“自我”創生的機遇,也為這種創生注入了巨大的能量。“新我”在“舊我”的軀體上破繭而出。在此,“自我”既是主體,又是對象,成為一個巨大的問題,一個任務,等待著詩人去艱難地完成。拉康認為,“主體最終只得承認,他的存在絕非別的什么,而只是他自己在想象中的構造(oeuvre)”①轉引自王先霈、王又平主編:《文學理論批評術語匯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543頁。。在痛苦的沖蕩和抉擇中,梁平側轉身去,旁逸斜出,艱難地找到了一個符合自己心愿的、有更高真實的自我。正如膽小的孩子走夜路,越害怕越高聲唱歌給自己,梁平說:“真正優秀的詩人不是把玩文字的高手,而是把自己的思想和情感真正注入自己詩歌的人。”②梁平:《閱讀的姿勢——當代詩歌批評札記》,第249頁。批評家魏天無也注意到這一點,他說《時間筆記》是“一個赤裸裸的‘有我的世界’”③魏天無:《“我是我自己的反方向”:再論詩和梁平的詩》,收入梁平《時間筆記》,第224頁。,詩人艱難地聚攏起“自我”的光芒,竭力打開生命新的可能。
在現實面前,梁平選擇抽身而退,也同時退出了那些超我的、宏大的山岳般的事物。他松動了與現實的緊張關系,放慢了身心,開始半是嚴肅、半是游戲的新的自我的生活和抒寫。新的自我,帶來了新的生命境界、新的詩意境界。這種境界之新,一方面體現在內在心態的變化上。《耳順》中:“耳順,就是眼順、心順,/逢場不再作戲,馬放南山,/刀槍入庫,生旦凈末丑卸了妝,/過眼云煙心生憐憫。”“年齡”的變化帶來心態的變化,從原有的角色退出,與現實拉開距離,“耳順”也就是心空起來,外面的各種聲音“皆可入心入耳。/以后任何角落冒出的雜音,/都可以婉轉,動聽”。“卸下面具,/卸下身上的裝扮。”(《卸下》)做出了如此選擇以后,“是非、曲直與黑白面前,/我行我素,不裁判”。有意地消泯了是非曲直,回避了價值判斷。原來的現實是有對錯、好壞之分的,置身其中的人為了應對事務、趨利避害必須做出選擇。而從現實后退以后,就可以俯仰裕如了。“詩”作為藝術,是一種突入,也是一種回避,可以在這一空間中逃開二元對立、非此即彼。置身黑白之外,領略到別樣的色彩、風景。這種對價值判斷的擱置帶來一種“和光同塵”的氣息。在《盲點》一詩中,詩人說自己“面對萬紫千紅,/找不到那款顏色”。這種“色盲”使他“只能讀一個臉譜”,饒有意味的是,“我對自己的盲點不以為恥”,而且精心呵護,直到“把盲點繡成一朵花”。“盲”反倒轉化成一種優勢,詩人對此頗為自得。另一首詩《盲》,繼續論說這一話題,河里的白鷺,有“純潔的白,過目不忘的白”,“集百寵于一身”,但是這種“白”“我羞于正視”,這種非凡的美“太耀眼”,使我“感到不適”,“從此落下病根”。梁平不但對反向的價值展開反思,而且在正向的價值中,諸如善和美中,發現了非人、荒謬的東西。《惡作劇》寫得意味深長,可以說是《時間筆記》中最典型的一首:
我在大前門設過局,
小心思地助紂。
北京的士拉我兜圈子,
三百米路程,花了四十幾塊錢,
卸下我,在建國飯店。
司機滿心歡喜地走了,
我也滿心歡喜,成功地助長了一次宰客,
他會一整天都沉浸在歡樂之中。
這首詩的幽默令人捧腹。詩人以諧謔的口吻說自己設過局,助紂為虐幫的士司機宰客,非常成功,人我都滿心歡喜——但被宰的是自己。在整個過程中,“我”對司機的意圖心知肚明,但是“我”非但不說,而且小心翼翼地成全司機,司機不知道我的心思。善惡顛倒、主客換位產生了喜劇的強烈效果。后半部分寫“我”坐在飯店大廳的沙發上,等待原來等“我”的人,那人還沒到。“我”便開始了“歡樂的”想象,“那人又上了剛才的的士,/司機重蹈我的覆轍,/出現在我的面前”。“我”再一次上前“義無反顧慷慨解囊,/再給他一個滿心歡喜”,買他半生的羞愧。末尾奇上加奇,借助想象性情節將戲劇效果推演到了高潮,消解了“買你半生羞愧”這一勸諷行為的用意,實現了反諷。
另一方面是對自己生活和世間萬物的欣賞、把玩。中國人早已熟悉“無用之為用”和“空納萬境”的好處,“花甲”“耳順”以后的梁平深諳自處、晏居和優游之法。梁平說他在日常生活中喜歡“宅”,也喜歡“游”,總之都要輕松上陣,不要擔負太多的東西,不要太多的條條框框。《晚上七點》,夜晚將至,“南苑河爬上五樓的樹枝,/在書房的玻璃窗外,向我致意。/這是由來已久的儀式,/我打開窗,伸手與它的葉片相握……知道它的心事”。“我的書房就是我的江山”,寧靜的自我真切地進入它置身其中的空間和時間中,細細地打量、觸摸事物的色彩、陰影,體驗每一個真實或虛幻的局部、細節可能會有的滋味。自處的靜寂變成了淵默雷動,自處的孤獨也變成了一個人的享樂。“比如左鄰右舍,/誰也叫不出誰的名字,/過道上側身,一個微笑,/就有了春風拂面。”(《蟄居哲學》)蟄居生活充滿了善意和和諧,這自然源于和善的心境。即使行走、出游,也是持一種率性觀覽的態度。“我在致民路上改寫了身份,/行走多了彈跳節奏,/談笑少了歲月的皺紋。”欣賞“紅衣女摩拜單車擦肩而過”,“重金屬打擊樂連綿不絕”(《在致民路》),路上的風景像陽光一樣灌進自我的心田。即使是出訪域外,呈現在視野中的風景也是輕逸的,幾乎要隨風而去。在歐洲小城,發現“修女不見了”“修道院空置多年”,“煙火人間里,市民捉放‘跳蚤’”,自由交易舊物件,“卸裝的云騰出了天空”,“我”多少感到一絲失落,但一陣清風很快就“吹走了我的失落”(《梅斯的“跳蚤”》)。
在此情況下,自我進入了萬物,萬物也進入了自我。這種詩意的精神狀態仿佛使詩人獲得了“逆生長”①魏天無:《“我是我自己的反方向”:再論詩和梁平的詩》,收入梁平《時間筆記》,第217頁。的態勢,以赤子的眼光好奇、歡樂地凝視、觸摸萬物,結束了自我的分裂狀態,實現了和世界的無間合和。《南岳邂逅一只蝴蝶》:
那只蝴蝶應該是皇后級別,
在南岳半坡的木欄上,望著我。
過山的風驟然停息,
它的兩翅收斂成屏風,
驚艷四射。我不忍心驚擾它,
感覺我們之間已成對視,
時間在流走。
這是流連光景中的一個動人的瞬間,只有恢復了自我,擁有了赤子之心的人,才能注意到這樣細微的情景。山道上一只美麗的蝴蝶斂翅靜息,和“我”形成對視。不知道在蝴蝶奇異的眼中,“我”呈現怎樣的形象。蝴蝶仿佛洞開了一個無形的中心,“我”沉溺其中,而來往的人對此視而不見,“一個道姑從我身邊走過,/一個和尚從我身邊走過”。這頗有“莊生曉夢迷蝴蝶”的意趣,莊子夢醒后不知是自己在夢中變成了蝴蝶,還是蝴蝶在夢中變成了自己。人生難得一“迷”,時刻醒著,與他人、外物分得太清會太累、太孤獨。詩有時候就是要以化蝶般的“迷”阻斷過分的清醒。
此類書寫,在《時間筆記》中很多,梁平也隨之變成了有莊子意趣的詩人。這其實是千百年來中國詩人的常態,晚明王思任說:“蓋廊廟必莊嚴,田野多散逸。與廊廟近者,文也;與田野近者,詩也。”①王思任:《王思任小品全集詳注》,李鳴注評,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8年,第315頁。逃出“廊廟”,就會解除戒心,解除外物對自我虛空、自由狀態的入侵和宰制,像落花、麋鹿一樣放浪山水,親近草木。明末清初文人屈大均說:“莊生之學,貴乎自得。”②轉引自錢穆:《莊子纂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第11頁。“自得”一詞,真是確評。體認了“道”的清虛、廣漠的存在本體和運行規律以后,觸摸到了“真我”的本相,像大鵬鳥那樣扶搖直上,像蝴蝶那樣翩然翻飛,都是擺脫了“物累”的自然、自由的生命行為。“自我”也在若有若無、亦真亦幻之中獲得了存適的自在狀態。
梁平接通了道家“生活藝術化”的方法,為“自我”找到了生存、展開的新空間。這種做法及其風度,也能在一些頗具東方神韻的西方詩人那里領略到。梁平就很喜歡辛波斯卡和米沃什,在《時間筆記》中以獻詩的形式真誠地表達了對他們的欽敬和喜愛,比如詩作《時間上的米沃什》和《一只簡單的母鹿——致辛波斯卡》。米沃什《禮物》“在我身上沒有痛苦。/直起腰來,我望見藍色的大海和帆影”。這種經過了歷史風暴,最終在時間中化煉成的物我兩忘、寧靜莊嚴的心靈境界,也是莊子的境界。辛波斯卡那種“一只簡單的母鹿”般的超越了機巧,獲得了普遍智慧的赤誠的詩性生命品質,也都是梁平在生活和詩歌中所真誠追求的。
三 詩歌:重建與世界的關系
梁平新收獲的、在詩中面世的這個“自我”,恬靜如處子,活潑如孫悟空。《取舍》:“身心放松的輕,像一片羽毛,/越是自由飛翔,越懂得愛惜。”《石頭記》:“裸露是很美好的詞,/不能褻瀆。只有心不藏污,/才能至死不渝地坦蕩。/我喜歡石頭,包括它的裂縫。”《我的肉身里住著孫悟空》:
我和悟空相見恨晚,
一個眼神可以托付終生。
從胸腔到腹腔相伴而行,
膽囊的結石在火眼金睛的照耀下,
正在生成舍利子。
孫悟空進駐“我”的身體,成為“我”的一個“相知”,最后分不清誰是悟空,誰是“我”。“腸道里巡游十萬八千里”,“額頭上的時間,年月日不詳”,很有善惡偕忘、恢恢乎游刃有余的意思。“孫悟空”的機敏、慈悲也是“我”所喜歡的,這也是詩人新的自我的豐富面相之一。
到此,我們可以跳出來,從另外的角度進一步思考詩歌與世界、人的關系了。不平則鳴,現實帶來的危機、自我分裂的矛盾滋養了詩人的寫作,反過來,詩歌也滋養了詩人的人生、世界。對新的自我的渴求、滋育和培護,也是對自我與世界的新關系的找尋和重建。自我從來都不是完全封閉、孤立的存在,就像精神分析學家所說的,它是一個有待于借助他者、外物去積極實現的對象。這種重建,改變了原來對世界的那種非此即彼的態度,不是批判、對抗,就是毫無保留地歌頌,他們之間的關系改善了,變得多樣而久遠。詩人對鄰人報以微笑,欣賞路人的風采,和一片綠葉握手,與一只蝴蝶對視,毋寧說降低了自己的姿態,克服了“人”在世界之上特立獨出的處境,恢復了和他人、動物、草木乃至天地萬物的平等關系。他就在萬物之中,是他們中的一員,謙和、誠樸,這也就是道家所說的“齊萬物”。在此基礎上,他不但重新獲得了“日常生活”世界,而且獲得了自然界。這正是身處都市現代化的當代人所失去的和最渴望的。詩歌這門藝術,作為精神內部的一種凈化、治療機制,擴展、豐富了詩人生活的世界,發現了更為細微,也更為深切動人的生命相關物,也改善詩人的生存質量。我們這個時代的另一位詩人張執浩說:“在如此悲涼的人生處境之下,生命的存在感其實只是一種有意味的形式,而詩歌寫作卻能將這種形式變成一種儀式——通過某種獨特的音調,讓我們內心世界里的喜怒哀樂得以附體,并在傳遞的過程中讓卑微的生命獲得存在的尊嚴感。”①張執浩:《不是日常生活,而是日常生活態度》,《草堂》2019年第1期。
而且,在這種情況下,詩歌本身的存在及其性質也得到了改善。詩歌被用來急功近利地記錄、批判、宣揚的一面(百年新詩長期如此),終于退到了后面,它本身和人相依相存,雍容不迫的一面發揮了出來,恢復了“天容海色本澄清”的本相,獲得了它獨立不懼的地位。附加太多就會扭曲本來面目,人需要自由自在,詩歌也一樣。記得韓東曾說,過了一定年齡,他不再折磨詩歌,詩歌也不再折磨他,相信詩人梁平也認同這一精妙的體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