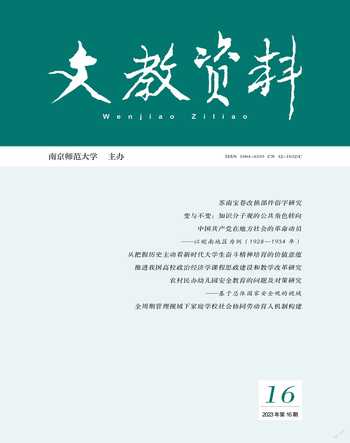傳統童蒙教育經驗在海外華文識字教育中的應用
邵夢溪

摘 要:本研究以蒙學《千字文》為研究對象,利用傳統語文教育吟誦、書寫、講解的寶貴經驗,對《千字文》經典原文進行有針對性的解構,以期通過吟誦語音幫助兒童感知記憶漢字字音;利用漢字三平面理論對重點字進行字形、字構、字用三個維度的分析,將漢字字理的分析與漢字字用中的意義有效對應,以此幫助學生建立漢字系統思維、字理思維、字用思維,達到識字學詞的目的;有效利用蒙學文化性、知識性、故事性的特點編寫現代漢語閱讀語料,將語言教學和文化教育有機融合,為華裔兒童中文教育探索新的方向。
關鍵詞:識字教育 傳統童蒙教育 海外華文教育 《千字文》
一、研究緣起
近年來,隨著漢語走向世界步伐的加快,海外華文教育取得了不錯的成就,但也面臨著新的問題。其中,以華語課堂教學為主要渠道的華文教學,是海外華文教育的主要實現形式。華文教學主要面向海外華裔兒童開展母語教學,是國際漢語教學的重要組成部分,需要充分結合國內語文教學與國際中文教育的優秀經驗,探索出適合的發展路徑。
漢字及其漢語書面語的教學日益受到學界重視。在過去,文字界囿于西方語言學的影響,側重漢字形體學的研究,把漢字作為單純的工具與符號,強調書寫、筆順、認讀的教學,忽略漢字構形規律、漢字職能、漢字文化等,這讓“漢字難學”成為漢語教學界一直以來的難題。近三十年來,隨著漢字本體與教學研究的發展,學界越發注重漢字自身特點和規律,尊重漢字造字理據,將漢字教學作為漢語教學的關鍵環節。尤其是在面對海外華裔兒童、以漢語為傳承語的海外華文教育中,漢字在中文書面語教育、漢語字詞教學、漢語文化傳承教育中的作用更加重要。
同時,海外華文教育不應只重視語言的交際工具功能,更要承擔起助力中華文化的縱向傳承與橫向傳播的重任。但是,漢語教學的核心任務仍然是漢語言文字教學,文化教學是伴隨式的、潛移默化的,不能成為教學的主要內容。為此,漢語教學應該依照語文教學的發展路徑,探究適合的教學內容以及方法,在華文教學中不斷加強漢字的文化闡釋,在漢語書面語教學中融入中華文化的優秀內容。
當下華文教育資源相對不足,教材編寫仍須進一步改進。陸儉明認為,漢語教學所伴隨的文化教育,其內容必須浸潤在漢語教學之中,尤其是要浸潤在漢語教材之中。[1]同時,當今教學強調本土化、國別化,還需要一本普適性漢語教材作為開展教學的前提。李宇明等指出,漢語教學在“當地化”的同時,教學內容仍應該以“中國故事”為主,分享中華文明智慧與中國發展的優勢。[2]編好能夠實現科學語言教學、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適合海外各地華裔兒童學習、展示當代中國形象的教材,是海外華文教育當下最迫切的需求。
二、研究基礎
國際中文教育中,漢字及漢語書面語的教學日益受到學界重視。以漢語作為傳承語的國際中文教育中,漢字在中文書面語教育,漢語字詞教學,漢語文化傳承教育中作用更加重要。如何有效解決華裔兒童漢語教育中的漢字教學瓶頸,利用漢字結構中的理據性加強漢字用字組詞的教學,借鑒傳統韻文識字、集中識字經驗來處理克服蒙童早期快速識字的困難,這些問題都能從傳統蒙學教育中找到可以學習借鑒之處。
中國古代傳統的語文教學方式為海外華文教育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張志公將傳統語文教育劃分為四個階段,其中第一階段以初期識字寫字為主,第二階段識字教育與思想教育、知識教育相結合,第三、四階段以讀寫訓練為主。[3]傳統語文教育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識字寫字教學體系、閱讀教學體系、寫作教學體系,三個教育體系是環環相扣、相互促進、彼此激發的。從古代教育的分期階段看,傳統語文教育主要分為家學、蒙學、學館、官學、交游五大階段。古代的村族十分重視蒙學時期的教育,這些族學、村塾、家教、女館就構成了中國古代社會的基層教育單位。因為學習大多數是免費的,或者只收取較低的費用,所以蒙學教育的對象不只有精英階層,也包括許多普通民眾,具有實踐證明了的普適性。
識字教育是童蒙教育的開端。童蒙教育的對象為3—8歲的兒童,在三四年的學習中,兒童需要掌握三四千個漢字,識字數量要能達到自由閱讀線。蒙學教育孕育了豐富的課本,豐富的蒙學教材是傳統語文教育經驗的集中展示,為當下的教材編寫、課程設置提供了靈感。漢字的語音是有意義的,傳統吟誦是利用語音吟誦刺激漢字記憶、培養學生語感的有效手段。陸儉明認為,掌握書面語的具體做法是要“大量閱讀、大聲朗讀甚至需要背誦,而這也正是我國傳統私塾教學的特點之一”[4]。古代兒童自入學便開始吟誦,吟誦伴隨學生語文教育的全程。識字教育階段積累了豐富的識字經驗,如集中識字、韻語偏旁聯系識字、讀寫分流識字與語文教育生活教育結合、字理講解等方面提供了寶貴的經驗。李運富的漢字“三維屬性”理論認為應該從形體、結構、職能三個角度,以漢字為核心展開漢語教學。[5]結合這一最新的漢字理論與古代童蒙識字的教育經驗,可以探索出適合當下漢語教學現狀的教學方式。
南北朝時期周興嗣編寫的《千字文》是經典蒙學讀本與識字教材。在編成之后,《千字文》很快成為了流行各地的通俗識字課本,自唐宋以下,一直是全國流行的啟蒙教材,也是國外學習者學習漢文使用的讀本。從句式和字數上看,《千字文》效仿《詩經》四四句式,共250句,將1000個基本不重復的漢字組織成通順且能表達一定意義的句子;從內容上看,文本編排并非枯燥的文字堆砌,它囊括了日常社會生活中常見的自然、歷史、名物、倫理等知識,在識字中結合思想與生活教育,前后連貫,具有條理性;從語言上看,韻文編排與對仗對偶句式通順可讀,具有抑揚頓挫的韻律,既可以吸引學生的學習興趣,又能在高低錯落的旋律中加深對文本的理解與記憶,便于兒童朗讀背誦,讓海外漢語學子產生語言感情,身臨其境地感知傳統文化之美。
三、傳統童蒙識字經驗在華文教學中的應用:以《千字文》為例
《千字文》是最經典、最有代表性的蒙學識字教材之一。作為海外華文教育中漢字教學的一次有益探索,本部分內容旨在將兒童蒙學教育的經驗與漢字教學結合,利用傳統語文教育的寶貴經驗,對《千字文》經典原文進行有針對性的解構,從而為母語識字教學帶來啟發,為海外華裔兒童漢語學習、國際中文教學帶來新的思考。
(一)吟誦與書寫價值的再利用
兒童在學習漢字時大多是靠整齊押韻的語音刺激來記憶的。據統計,《千字文》共出現294個不重復的音節(包括多音字在內,不區分聲調),占漢語音節總數的72.06%。掌握《千字文》漢字的讀音教學,能為漢語的語音語言教學做好鋪墊。
吟誦是古人讀書的常用方式:依字行腔、依義定調,吟誦時字正腔圓,融感性與藝術性于一體。利用傳統吟誦韻文識字的寶貴經驗,通過吟誦語音刺激可幫助兒童感知記憶漢字字音,累積語感,將漢字內化為自己的心理詞匯。吟誦鼓勵學生依據內容自己創造,這可以激發學習的主動性。
《千字文》是周興嗣在王羲之書法作品中選取的1000個不重復漢字。歷代書法家的臨摹讓《千字文》具有書寫臨摹范本的功能,使其具有其他蒙學教材所不具備的書法價值。雖然學界強調識字與書寫分流,但作為童蒙的養成教育,傳統軟筆書法書寫也非常重要,觀賞《千字文》碑帖可以使學生在潛移默化中感受古代書法家書寫的線條美,體會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魅力。
(二)語言教學價值的再開發
1. 講解漢字
王寧先生認為,講解漢字字理是小學識字教育中不可或缺的內容。[6]國際中文教育與海外華文教育同樣適用于此經驗,但目前諸如“新說文解字派”的講解脫離了漢字構件的系統性,雖然短期內有所收效,長遠看不利于提升學生的閱讀能力。因此,教師應該根據漢字構造的規律,科學地闡釋漢字,授課方式還要符合兒童的接受能力,講解不宜艱澀。《千字文》所選字都是古書中常見的漢字,沒有生僻艱澀的漢字。教師在選擇要為海外華裔兒童講解的漢字時,既要考慮到漢字的六書構造,又要盡量選擇教學大綱中的常用字。
運用“漢字學三平面理論”對重點字進行字形、字理、字用三個維度的分析,將漢字字理的分析與漢字字用中的意義有效對應,以此幫助學生建立漢字系統思維,字理思維,字用思維,達到識字學詞的目的。《千字文》只有1000個字,事實上是不夠的,由于《千文字》幾乎沒有重復的漢字,學生也得不到復習鞏固。字形部分的講解重點不在筆順、書寫、形近字,而要以該漢字或該漢字部件為核心,利用字族識字。字理是漢字闡釋環節的重要組成部分,以“三百千”為代表的蒙學教材以集中識字、韻文識字為主,缺少對漢字構造規律的介紹。漢字闡釋需要遵循漢字構形規律,在訓詁解字的基礎上突出識字目的,省略現代漢語中不存在的含義以及艱澀難懂的義項。字用部分圍繞漢字的義項挑選詞語或成語,判斷的標準不是頻率的多少,而是語素義的覆蓋面及代表性,兼顧漢字的常用性、文化性、語義完整性(見表1)。
2. 編寫故事
張志公認為,“韻語讀物”是古人設計的一座跨越口語和書面語之間那條鴻溝的橋梁。[7]傳統語文教育中,學生需要在完成集中識字后進行隨文識字,將識字教育與思想文化和知識積累結合,以實現識字向書面語的讀寫的過渡。
從內容看,以《千字文》為代表的蒙學教材內容包含著豐富的自然、歷史、典故、名物故事。需要注意的是,這些課本內容大多與兒童生活日常相隔太遠,學生難以理解,也無法學以致用;部分內容宣揚的封建禮教觀念,已不再適用于當代中國社會。加之其高度凝練的文本,很多故事以三言兩語簡單概括,如果沒有豐厚的古文素養,教師難以理解與傳授文本背后的故事與價值指向,因此要選擇、整理、改編蒙學教材讀本的故事,使其符合兒童學習和生活的實際情況,傳承并弘揚優秀中華傳統文化。從語體看,傳統語文教材大多是為文言文、書面語學習服務的,對海外華裔兒童來說,語言教學還需要與現代漢語接軌,處理文言文與白話文的關系,同時不應忽視口語訓練。
因此當代華文教育要以《千字文》為藍本,篩選改編相關的神話、歷史、傳說故事,有效利用《千字文》的文化性、知識性、故事性特點編寫現代漢語閱讀語料,將語言教學和文化教育有機融合,內容上與當代中國生活相貼合,為華裔兒童中文教育探索新的方向。同時可以借助網絡平臺,將文字故事與視聽素材相結合,打造融合專業性與趣味性的電子讀本。
四、結語
明代學者呂坤的《社學要略》中提出:“初入社學,八歲以下者,先讀《三字經》以習見聞,《百家姓》以便日用,《千字文》亦有義理。”[8]在以蒙學教材為藍本的語言教學中,文化教育始終貫穿全程。
取哪些文本作為蒙學教育課本內容,在文本中選取哪些漢字,如何編好課文、傳播中華好故事,如何將字理用于漢字闡釋,如何發揮漢字的核心作用,如何創新練習形式……這些都是今后要考慮的問題。在系列推文應用于教學實踐的同時,我們需要及時跟進學生與教師反映的問題并加以改進,讓傳統語文教育的經驗真正作用于漢語教學的實踐。
當代華文教育要進一步挖掘傳統蒙學教育資源,梳理古代童蒙教育的經驗與語文教育的發展史,在經典材料中選取有代表性的中國文化內容,為應用傳統語文經驗打下堅實的基礎。除《千字文》外,中國其他的童蒙教育也值得研究,如何使傳統蒙學教材與當代中國相適應,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也是海外華文識字教育要重點關注的研究方向。
參考文獻:
[1] 陸儉明.對漢語教學要有這樣的認識[J].語言戰略研究,2016(2):77-82.
[2] 李宇明,施春宏.漢語國際教育“當地化”的若干思考[J].中國語文,2017(2):245-252,256.
[3] [7] 張志公.傳統語文教育教材論[M].北京:中華書局,2013:10,70-71.
[4] 陸儉明.關涉國家安全的語言戰略實施中語言文字基礎性建設問題[J].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8(3):57-64.
[5] 李運富.漢字學新論[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13-17.
[6] 王寧.漢字構形學導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254-263.
[8] 陳宏謀.五種遺規[M].上海:新文化書社,1935:48-50.
(責任編輯:向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