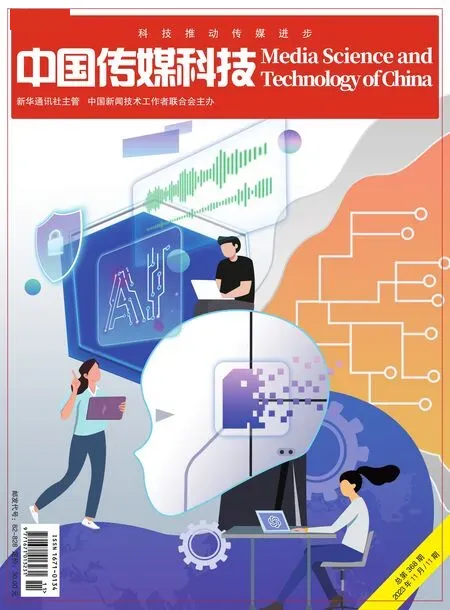司肖視域下的教育報刊集群化發展實踐與思考
孫曉燕
(江蘇教育報刊總社,江蘇 南京 210036)
“司肖”是英文“Corporate Identity System”的中文音譯,縮寫為CIS(或CI),即企業識別系統,司肖戰略指導下的企業( 團 體法人、團體、組織)對自身經營理念、行為方式、視覺形象三位一體系統設計、傳播,以塑造富有具備特有性、價值性、長期性、認知性的公眾形象。[1]
美國國際商用機器公司于1956 年聘請專業設計者將公司全稱“INTERNATIONAI BUSINESS MACHINES”濃縮為藍色標準色的IBM 造型,被視為CIS 創立的典型標志。此后,歐美各國的大型企業紛紛導入司肖系統,使市場競爭力得到增加。[2]我國香港、臺灣地區在20 世紀70 年代末導入司肖。改革開放后我國更多企業紛紛重視并導入CIS 系統,并形成了“中國型CI”,如太陽神集團、健力寶、李寧運動用品等,并因此取得顯著業績。其中太陽神集團是典型代表,在實踐與理論方面都對中國企業產生了示范推動作用。[3]
司肖(CIS)系統由三部分構成 :理念識別系統——Mind Identity(MI),可理解為企業的“腦”;行為識別系統——Behavior Identity(BI),可理解為企業的“手”;視覺識別系統——Visual Identity(VI),可理解為企業的“臉”。[4]主要結構及關系如圖1。

圖1 司肖系統結構及關系圖
CIS(司肖)戰略一般被用在企業性質的團體、組織、單位的市場化經營活動及其對應的語境中,這似乎與傳統事業單位的媒體運作毫無關系。但是從強化主流報刊媒體品牌競爭力,以順應行政托底逐漸弱化、導入市場勢在必行,現代媒體傳播格局根本性變革、傳者中心向用戶(讀者)為王轉變的趨勢來看,在報刊宣傳出版工作中轉換視角,借鑒司肖理念,系統謀劃傳統報刊新時期發展戰略理念與文化定位,并通過一系列的(對內對外)行為準則制定、形象品牌展示,實現報刊事業“堅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的發展目標,有著一定的實踐探索意義。
江蘇教育報刊總社(以下簡稱“總社”)是江蘇省教育廳直屬宣傳出版單位,其歷史可以追溯至1950 年的蘇南教育社。1953 年與江蘇建省同時建社、同時創辦《江蘇教育雜志》,歷經江蘇教育社、江蘇教育雜志社、江蘇教育報刊社。[5]目前總社擁有“兩報”(《江蘇教育報》《小學生數學報》)、“七刊”(《江蘇教育》《早期教育》《現代特殊教育》《江蘇高教》《初中生世界》《閱讀》《江蘇教育參考》)紙媒及江蘇教育新聞網及微博、微信、抖音等新媒體,構建起較為典型的教育報刊集群化運作模式。總社的辦報辦刊(新媒體)歷程,特別是近年來立足于宣傳出版新的時代、新的使命任務、新的事業,發展自身需求所做的實踐探索的歷程,即司肖理念引領下的實踐歷程。
1.理念——傳承八字社風傳統文化精神,引領新時期報刊永續發展
司肖系統的理念識別系統(MI)是企業(組織、團隊)在長期生產經營過程中所形成的企業共同認可和遵守的價值準則和文化觀念,以及由企業價值準則和文化觀念決定的企業經營方向、經營思想和經營戰略目標。
理念上的認同才能形成團體組織精神上的認同、戰略目標上的共識,對內取得向心力和凝聚力,對外構成品牌力影響力。理念具有抽象性,但是對團體組織運行的外顯的行動、操作具有意識、精神引領意義。
總社有著悠久的辦報辦刊歷史,優良報刊人精神基礎深厚。歷經新中國建設、特殊年代、改革開放等重要歷史節點,事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與時俱進、做大做強,是因為傳承了陶白、周承澎、繆詠禾、錢聞等老一輩革命家、教育家堅守媒體出版人艱苦奮斗、開拓進取的職業擔當、尊重教育規律、勇于探索創新的精神基因。也正因為如此,通過辦報辦刊,江蘇教育報刊總社傳播的教育經驗理念,如“楊思之路”“蘇派教育”、推出的杰出教育人物,如斯霞、李吉林、打造的教師專業發展服務品牌,如“教海探航”系列教師征文活動等,更是在全省乃至全國教育領域產生了重要影響,為江蘇省乃至全國教育改革發展貢獻了“蘇派教育”實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教學理論的創新作出了貢獻”。[6]
這一過程中總社自身事業歷經的成長史和發展史,凝練、形成了“團結勤奮高效創新”的八字社風。[9]盡管歷經不同發展時期,辦報辦刊人不斷更迭,傳播出版格局因時而變,但八字社風蘊含的精神力量一直是總社“集體精氣神”的寫照,它“概括了全社上下艱苦奮斗、開拓進取的精神”,是“立社之基、興社之魂”“引領全社解放思想、求新創新,奔向新高”“融于血脈,持續提升全社員工的編輯情懷”。[7]
總社伴隨不同發展階段要求,近年來分別提出“媒體+智庫”“幸福總社”“報刊育人、融媒服務、學術高地、活力文化”十六字辦社方略等,均是在“八字社風”精神傳承基礎上的、適應不同發展時期的辦社內涵的拓展與豐富化詮釋,發揮著教育、凝聚、約束、協調的重要作用。
2.行為——以制度規范辦報辦刊行為,推動事業良性發展
司肖系統的行為識別系統(BI)是企業(團隊、組織)實際經營理念與企業(團隊、組織)文化的統一準則化的行為系統。
總社屬于“二類公益”事業單位性質,近年來,隨著行政管理力度強化、江蘇省事業單位所辦企業集中統一監管等政策要求的實施,總社從自辦發行、自負盈虧,公司化運營的探索中吸取經驗教訓,進一步強化了教育報刊的教育宣傳出版服務屬性,強化社會效益屬性、公益性屬性,以制度體系建設為抓手,更加注重指向對內組織架構上的集中、辦刊資源上的整合及對外經營行為上的統一。
為使制度建設更加專業系統科學,總社于2021年起用近一年半時間委托第三方專業機構進行內控體系研制,從控制環節、控制方法、組織架構和責任體系等均進行了立體閉環式設計,涵蓋了總社單位層面及業務層面的全部行為規范要求及風險控制的措施途徑等,使所有人均在規則內、事均在程序內行動運轉,突出了規范辦社、高效有序的報刊集群運行模式。
2.1 優化“編輯場域”,推進報刊編輯出版集群式聯動
總社所屬各報刊功能、內容、受眾各有不同,但辦刊方向相對集中,辦刊方向、讀者受眾基本實現全省教育領域全覆蓋,是典型的報刊集群發展模式,在物理空間、辦刊人力、內容來源、信息流通等方面有著聯動發展的基礎。總社制定出臺《江蘇教育報刊總社報刊聯動發展協作機制》,使教育學術、教育新聞宣傳報刊(江蘇教育、江蘇教育報)與少兒報刊(小學生數學報、閱讀、初中生世界)之間形成有機整體;通過搭建線上線下結合的工作環境,“網刊聯動”的出版手段,建立特約編輯制度、組稿會制度、活動策劃制度等開展版面協作、活動協作、發行協作,實現人力、渠道資源優勢互補,實現選題、運營、傳播等方面創意的碰撞和內容資源、運作手段的共享。
報刊新媒體編輯出版質量是報刊社事業的核心競爭力,為保障集群產品編輯出版質量,總社強化報刊出版質量管理全流程過程化管理,制定出臺了《江蘇教育報刊總社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實施方案》《江蘇教育報刊總社編輯規程》《江蘇教育報刊總社關于規范新媒體賬號運營管理的意見》等制度,并提供各種保障措施條件確保執行到位。如:為各編輯部采購正版化辦公、繪圖、新媒體排版軟件、工具,并開展相關的法律知識培訓,強化美術編輯、采編人員版權意識。
報刊聯動機制對拓展傳統媒體辦報辦刊手段、破除編輯部內部的“信息回音室”效應、促進報刊質量集群化推進,提升“江蘇教育報刊總社”品牌形象顯示度等都起到了積極作用。
2.2 宣傳通聯協作,宣傳服務活動集群管理
總社的宣傳服務活動一類為公益性的宣傳服務項目,另一類是經營性的媒體運營項目。較早時期,總社各報刊編輯部是各類活動的發起和扎口實施主體部門,活動比較多,且對外名稱不同,但參與人群有重疊、內容也有重復交叉,較大人力物力財力成本投入,但活動效果參差不齊,且品牌之間有內卷性競爭。聯動機制建立后,總社對報刊集群內活動進行科學整合,統一冠名、聯合創意、同步實施。
2.2.1 活動冠名統一
將面向教師的原《早期教育》編輯部的“新視野幼兒教師論文大賽”《初中生世界》的“五四杯中學青年教師教育教學論文競賽”《江蘇教育報》“新世紀園丁論文大賽”,《江蘇教育》“教海探航教師征文大賽”,統合并命名為活動品牌影響力最大的“教海探航”系列征文活動。
2.2.2 活動組織流程統一
出臺《江蘇教育報刊總社宣傳服務與媒體運營項目管理辦法》等制度,將活動審批規范、組織規范、行文規范、經費使用規范、品牌宣推規范。如所有活動通知均須以總社名義發布,總社名稱、報刊名稱、活動名稱不得泛化使用等。各類活動的開展對強化報刊出版的互動聯動、發揮廳屬教育報刊的宣傳服務功能、助推區域教育發展和服務師生成長、拓展報刊經營渠道、推進媒體內涵發展、提升總社品牌認知度和社會影響力產生了積極作用。
2.3 利用現代數字化技術助力集群管理提質增效
總社先后自主開發OA 辦公信息化系統、通聯發行信息系統、活動管理系統、質量管理系統等對應人事管理、采編出版、通聯發行、活動開展等工作的協同數字化管理平臺,使總社圍繞核心報刊的出版生產工作主責,實現管理制度化、制度流程化、流程信息化。以制度管人管事,減少了個人意志、個人行為對總社教育宣傳出版核心工作的“熵增”影響。
3.視覺——讓總社被看見。
視覺識別系統(VI)是將企業(團隊、組織)抽象屬性的具體、系統、標準的視覺化表達與傳播。
總社歷來重視報刊品牌可視化建設,2005 年前就由專業設計人員對總社相關品牌視覺系統開始標準化建設,對色彩構成、尺寸比例等進行了規范,可視為對品牌VI 系統的第一次行政化管理,并在2005 年啟動商標注冊工作。今年,總社將開展新一輪報刊標識集中商標注冊工作,申請類別涵蓋了印刷出版物、書籍、報紙、雜志(期刊)、新聞刊物、連環漫畫書、海報、家具除外的辦公必需品、培訓、演出制作、提供不可下載的在線電子出版物等在內的實際使用和預計使用場景范圍。這是出于知識產權保護,更是為適應主流媒體市場化激烈競爭及媒體傳播形態可視化趨勢下對品牌形象顯示度的迫切的需求。
4.傳統報刊集群化發展中司肖建設的反思
結合總社的品牌建設實踐,筆者認為,在司肖理念視域中,傳統報刊需引發以下反思。
4.1 傳統報刊人文精神如何與“數字原住民”青年采編隊伍的價值觀對接傳承
總社在報刊出版質量審讀中發現,年輕編輯編校差錯常集中在基礎常識性問題,如:結構助詞“的地得”用法混淆不清、標點符號使用混亂等,且在總社嚴格的獎懲制度下仍在同一人身上反復出現,難以杜絕,這反映的不是簡單的編校能力問題,而是與其集體榮譽感、專業進取意識較弱有關。總社青年采編人員(21 歲至40 歲)占比68.5%,是總社報刊生產主力軍,其中30 歲至40 歲的占比達到46.81%,他們也正是“數字原住民”(Digital Natives),數字技術和互聯網是其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他們的認知、態度及行為習慣等許多方面不同于“網絡移民”,且“正在重塑學校、工作以及民主的形式和功能”[8]對比70 后、60 后員工,總社青年員工“單位人”意識弱,“社會人”特征明顯,表現為人際關系扁平化,權威、層級概念弱,工作追求“佛系”,對于“團結”“勤奮”“團隊榮譽”等基于傳統集體意識傳承的職業精神的理解接收需要較長周期。如何促使優良辦刊傳統順利與年輕一代員工的價值觀體系對接,產生心理認同與行動自覺、統一制度化管理的剛性如何與個性化員工的發展訴求相平衡、程序化的工作在保障工作順利的同時,如何能調動員工個體的主觀創新積極性,等等,都需要立足總社人才培養管理新時期特點,構建促進青年員工賡續傳承優良社風精神,并與現代總社休戚與共、共同發展,同時實現個人人生價值的總社管理文化新形態。
4.2 主流傳統報刊品牌視覺系統如何服務傳播形態變化及市場化競爭環境需求
在總社注冊商標工作中有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一些被駁回的案例,如報刊名,有的是因為標識中含有行政區劃名稱,根據商標法有關規定不得作為商標使用;有的則因為刊名泛化,“缺乏顯著特征”被駁回。主流行政報刊因其職能定位要求,使得其在報刊名稱、單位名稱等稱謂上求嚴肅、求端莊、求兼容,也因此喪失了識別上的顯示性。而從認知心理來看,較之于被錨定了意向的名稱文字,視覺化的標識圖形、代言形象等則可以有更為舒朗的創新創意空間。
今天,媒體傳播形態發生變革,傳統紙媒單一形態已被移動傳播為標志的視聽新媒體樣態助推而置于融合轉型發展態勢中。同時,現代認知心理學中對于感知與思維、藝術與科學、感性與理性關系的對立統一關系的研究也為視覺化傳播重要性提供了理論依據。如美國藝術心理學家魯道夫·阿恩海姆運用了大量“視覺思維”的事實,揭示了視知覺通過產生代表某一類性質、某一類物體和某一類事件的意象來為概念的形成奠定基礎,這一長期以來被人們所忽視的思維心理學問題。[9]能被感知的,才能被關注;能被看到的,才能被記住。傳統報刊媒體是否可以通過創意打造獨特的社名、報刊(新媒體)名的視覺符號來對沖既有品牌名號的抽象、泛化?
新媒體,特別是視頻、直播等沉浸式新媒體環境下,品牌的標識應該是更加具有不可替代的基于直接的情感印射所形成的個性魅力屬性,即打造“人設”開展形象管理、構建公共關系,產生良性循環的經濟價值和社會價值。[10]正是由于用戶對“具體人格”的認可,較之于概念化、宏觀化的媒體及背后的機構,用戶更能與機構(媒體)關聯的具體形象產生“化學反應”。
今年上半年,各地文旅局長組團式在社交平臺亮相,以一己之力推介帶動一方產業,不少景點知名度大增,帶動起人們高漲的旅游熱情。一個個出圈視頻,成為網友們了解各地的一扇窗口,對促進文旅發展大有裨益。據統計,賀嬌龍“火出圈”一年后,當地助農直播銷售額達1.4 億元,帶動2830 人直接就業;“網紅局長”劉洪所在的甘孜,實現旅游綜合收入50224萬元,較去年同期分別增長106.33%和107.42%。“出圈”的文旅宣傳猶如催化劑,把吸引游客的關注力變成了產業發展的推動力。[11]
4.3 視覺系統風格定位呈現樣態主導權歸位
在當今現代傳播場域中,傳播者與受眾的關系已從傳播主體和傳播客體的關系,被更多地認同是同一傳播活動中共生的兩個主體;新的傳播價值理念告訴我們,向青少年傳播的信息無論從傳播方式還是傳播的信息本身上都必須發揮其在認識、理解、接受、運用信息上的主觀能動性、創造性。過去總社一本面向小學生讀書指導的期刊曾啟用“小書蟲”虛擬形象代言,但由于各種原因,如維持連續性設計的投入成本較高等而被棄用,但其中對造型觀念分歧也是一個主要原因。這既是由于辦報辦刊者對于讀者閱讀心理的科學認知不夠,也是因為作為傳媒人自身,基于培養藝術感知能力的“視覺思維”專業素養的薄弱而造成的。無論是審美、象征意蘊,要基于兒童(讀者)表征,還需要一段路要走。
結語
教育報刊要堅決守護主流意識形態的傳播渠道和傳播陣地,從而在新時代中更好地完成“舉旗幟、聚民心、育新人、興文化、展形象”的歷史使命,必須始終不斷深化鞏固以人民為中心辦報、辦刊的政治本色,以實際行動深度探索“高質量發展”的教育之為。司肖視域下的自我審視將傳統媒體品牌建設導入司肖系統審視,有助于樹立危機意識,以市場化視角關照現狀并科學前瞻布局報刊集群高質量發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