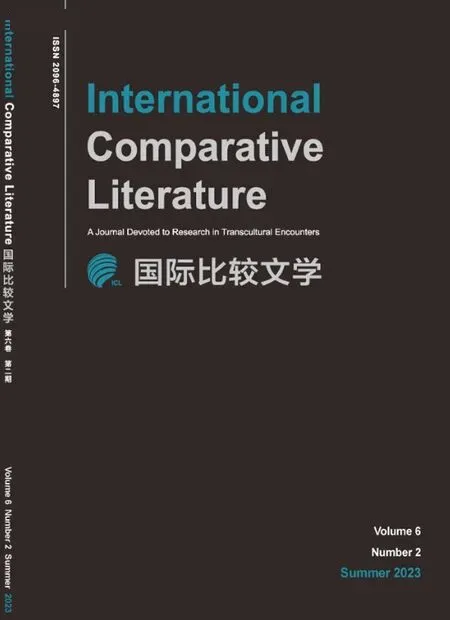揮之不去的卡夫卡味兒
童明 西安翻譯學院;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
一
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的文學作品中,那種介乎于荒誕、夢魘和黑色幽默之間的特質,被稱作the Kafkaesque。Kafka 加后綴 -esque,形容詞,也作名詞,中規中矩的譯法是 “卡夫卡式”,倒不如“卡夫卡味兒”直白生動,正像是“煙火味兒”“鄉村味兒”“凡爾賽味兒”,各自不同。
自從有了卡夫卡,現代文學和現代世界多了一個“卡夫卡味兒”的稱謂和概念,被頻繁引用,反復討論,作為概念一兩句也就說完了,惟其詭異纏綿,縈繞不去,細細思忖,時有心驚肉跳的發現;字句之間,嗅到現實生活的煙火味,不免疑惑: 難道現實世界先找到了卡夫卡做代言,而作者去世后這世界還在繼續創作?這卡夫卡味兒,像驚醒之后噩夢居然還在,又像抑郁的情傷四散開來,讓人避之不及。然而,偶爾得到一個溫暖的擁抱,也是卡夫卡味兒。
卡夫卡味兒是襲面而來的負面情緒?不盡然,此事要緩緩道來。
“[卡夫卡] 的作品將現實和夢幻的要素融為一體,其典型的描寫,是主人公面臨荒誕或超現實的困境,面臨無法理解的社會官僚權力,孤獨無助;對如此的描寫,通常解釋是對異化、存在境況的焦慮、負罪感、荒謬等主題的探索。…… Kafkaesque 一詞進入英語,用以描述那些與卡夫卡所寫相似的情景。” (His work fuses elements of realism and the fantastic. It typically features isolated protagonists facing bizarre or surrealistic predicaments and incomprehensible socio-bureaucratic powers. It has been interpreted as exploring themes of alienation, existential anxiety, guilt, and absurdity.... The term Kafkaesque has entered English to describe situations like those found in his writing.)1See “Franz Kafka” on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ranz_Kafka.
這是字斟句酌的標準辭典定義,但“異化、存在境況的焦慮、負罪感、荒謬”這些詞語,若不置于特定的卡夫卡環境中理解,依然語焉不詳。
卡夫卡的故事奇幻荒謬,卻具有強烈的現實感,按嚴格分類不是現實主義,而屬于諷喻(allegories)或寓言(parables),若造一詞,或可稱之為:諷喻現實主義。
在卡夫卡的諷喻世界里,將“人”逼于窘困的荒謬環境分為兩類。一類為威權體系,身陷其中,如同進入自行循環的迷宮;其法規極為冷酷,不是服務于人,反而無視人理常情,莫名其妙地加罪、騷擾、懲罰無辜,直至將其逼入絕境。
另一類,表面上是溫和的家庭環境,卻充滿激烈的矛盾。沖突集中在父與子的互動;父的背后是父權;據此體系,父為尊子為卑,子在父面前天然有罪。雖然有溫馨的偽裝,親情實際上已淪為父權施虐的借口和手段。讀讀《變形記》(“The Metamorphosis”)或《判決》(“The Judgment”),不難體會到那種令人窒息的惡。2See Franz Kafka, “The Metamorphosis,” in The Penal Colony: Stories and Short Pieces, trans. Willa and Edwin Muir(New York: Schocken, 1961), 67-132; see Kafka’s “The Judgment,” in the same book, 49-63. Hereafter the source is referred to as Muir’s translation.
在諷喻的意義上,上述兩類環境的本質一樣:威權即父權,父權亦威權,相互詮釋。
卡夫卡將荒誕而兇殘的夢魘,凝聚為一個個具足諷喻意味的場景,讀者身臨其境,恍然覺得那個孤獨無助、心靈深受煎熬的人,似曾相識。莫非我們都在卡夫卡世界里,體驗著卡夫卡味兒?
處在卡夫卡式的困境中,仿佛抬頭可見但丁留在地獄門上的那一行銘文:Abandon all hope ye who enter here (爾入此門,放棄所有冀盼)。 那么,內心的折磨、焦慮、負罪感、絕望,這般地獄門前的感受,就是卡夫卡味兒嗎?還是那句話:不盡然。
在但丁的神學想象里,《神曲》里的地獄是邁向天堂的第一步。卡夫卡的世界里沒有天堂的影子。卡夫卡融機智和幽默于文學的游戲,為讀者在痛苦的歷練中拓開思考和遐想的空間。幸運的讀者,從中獲取穿透黑暗的視力和抵抗絕望的內力,突然間發現手里攥一把鑰匙,或一把鐵鉗,也未可知。
二
如前引所述,卡夫卡的人物面臨“難以理解的社會官僚權力”而孤獨無助。英語加“order”(秩序)即為“社會官僚權力的秩序”(the order of socio-bureaucratic powers),而現代漢語里,則更習慣用“體系”或“體制”。
就卡夫卡研究而言,“官僚”一詞應做更細致的辨義。現代世界存在兩種不同的體系。一種,基于個人權利高于體制權力的理念,以社會契約形成法治(the rule of law);另一種,以體制權力高于個人權利為準則,形成權力至上的法律。兩種體系都產生官僚,但各自的涵義、表現形式和程度都有所不同。重點是,卡夫卡所諷喻的顯然是第二種。
卡夫卡諷喻的父權/威權體系,就其生成的邏輯而言,屬于當代西方思辨理論所說的“邏格斯中心主義”(logocentrism)的結構,大意是:此類結構或體系都有一個依照二元對立(即尊卑對立)的邏輯構成的“中心”。3“邏格斯中心”的詳細解釋,可參見童明:《解構廣角觀:當代西方文論精要》,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第一章,3~26.卡夫卡沒有采用過這個術語,但他作品中明指或暗諷的體系及其法律、法理,卻正是按邏格斯中心建構。
換用后殖民研究的術語,卡夫卡筆下的權力體系可稱為“內部殖民主義”(internal colonialism),即:以殖民主義邏輯形成的某個社會內部的秩序。內部殖民主義也是邏格斯中心(二元對立邏輯)的結構。在其社會象征秩序(socio-symbolic order)中,殖民者的權力和利益位居“中心”,被殖民者處于“邊緣”(periphery)。4For a more detailed explanation of “internal colonialism” (內部殖民主義),see John McLeod, Beginning Postcolonialism(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0).
在卡夫卡的作品里,中心和邊緣、尊和卑的(二元對立)兩端以不同的喻說呈現。在《城堡》(The Castle)當中,城堡代表體系的中心,必須遵從城堡的命令卻始終不解命令意義的村民們處于邊緣。城堡之謎即權力體系之謎。在《變形記》(“The Metamorphosis”)里,與公司聯手榨取兒子生命的父親是權力的一端,被逼成大甲蟲的兒子是另一端。
處在權力兩極之間的人物,對體系的態度和立場各異。直接服務于體系的,有些人,如《在流放地》(“In the Penal Colony”)中的“軍官”,屬于死忠,為了證明殺人機器仍然有效,甚至不惜赴死;有些則相對曖昧,如《在流放地》中的“新統帥”(New Commandant),雖做出改革流放地的姿態,卻并無行動。
被邊緣人群則呈現出不同程度的服從。強權之下,少有公開反對者,即便有,也不是有效反抗。長期的強壓之下,無可奈何演變為逆來順受。出于恐懼或無知,他們中許多人重復或模仿“中心”的言語和行為。
“中心”首先是觀念性的,代表權力認定的絕對真理。形成的體系,要求絕對服從,不容違逆。與之相應的法律制度和運作方式,遵照嚴格的等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居其位。其最高首領(卡夫卡筆下的老統帥、皇帝、嚴酷的父,等等)是“中心”的人格化身。權力體系慣于將其意志轉換為簡單易行的祈使句,以貫徹嚴酷的懲治措施。那些簡明扼要的口號,聽起來頗有正義感。《在流放地》中的殺人機器,其“頭部”組成部分發出的指令是:堅持公正(Be Just),而指令之下的懲罰毫無公正可言。
卡夫卡多以反諷或悖論呈現父權的特征。父權之絕對,為所欲為,驕橫跋扈,看似無比強大;另一方面,權力和死亡勢力連在一起,又非常脆弱。走向死亡的勢力日漸衰竭,卻依舊發威;幾近崩壞,卻愈見殘忍。
《在流放地》是一個完整體系的諷喻:老統帥、新統帥、軍官、士兵,各司其職;受刑人、貧苦民眾等處在被機器碾壓的底層。
那個用來處罰“罪犯”的殺人機器(Apparatus,又可作“工具”解)象征的意義很明顯;隨著故事的展開,機器開始失靈,卻仍然崩而不潰。流放地的靈魂是“老統帥”(Old Commandant),雖然早就死了,依然在墳墓里釋放著對全局的掌控力,腐臭彌漫在整個流放地。5See Franz Kafka, “In the Penal Colony,” in Muir’s translation, 191-227.
短篇《判決》(“The Judgment”) ,情節不同,寓意相同。故事里垂垂老矣的父親,并非和藹可親的老者。兒子實屬“孝子”, 年輕有為,經營家庭企業有方,而且馬上要迎娶新娘。父親對兒子蒸蒸日上的力量卻心懷恐懼(從父權的角度思考不難理解),他像魔法師一樣喚來父之權,一番邪惡的言語操作,玩弄兒子于股掌。最后,父命子去死,兒子直奔橋頭投江。這個將近死亡的父親,外強尚未中干,憑殘喘之氣,奪取年輕的生命,而且是自己兒子活生生的命。6See Franz Kafka, “The Judgment,” in Muir’s translation, 49-63.
卡夫卡筆下,空間或小或大,都有一種封閉中的恐怖感。《城堡》(The Castle)里的迷宮總也走不出去;《審判》(The Trial)里的法律像一張無處不在的蜘蛛網;還有只有一段話的寓言(parable)《皇帝的諭旨》(“An Imperial Message”),夸張地比喻著帝國的中心與其邊界之間巨大的距離。7See Franz Kafka’s “An Imperial Message,” in Kafka’s Parables and Paradoxes (in German and English) (New York:Schocken, 1961), 12-15. 注:本文中所有外語的漢譯皆出自童明。
皇帝快死了,躺在病榻上,大臣和王子們站立兩旁,靜等他駕崩。這時,四周的擋墻開始塌陷,死亡開始發力。皇帝令信差跪在床前,耳語向他下了一道諭旨,然后讓信差當場復述一遍。信差領旨之后立刻出發。他不知疲倦,日夜兼程,卻怎么也走不出帝國的京城。如此艱辛的歷程,即便“延續幾千年[原文如此],假設他最終穿過了最外面的大門(而這是永遠、永遠不會發生的),帝國的首都還是橫亙在他面前。這世界的中心,垃圾一般堆在那里。沒有人可以從這里闖出去。帶著死人諭旨的人更不可能” 。8同上,第15頁. [Ibid., 15]此處極夸張的手法強調了一個寓意:“幾千年”比喻帝國的時間和空間;一望無際的垃圾廢墟比喻“這世界[帝國]的中心” ;信差帶著一封死信,“死人的諭旨”,無望抵達外部世界。
帝國的封閉無法突破,噩夢揮之不去。故事的開頭有一個奇怪而且可怖的提示:從將死的皇帝那里接領諭旨的信差,不是別人,就是讀者“你”(you):“你在夜幕降臨的一刻坐在窗前,你可以夢到這一切”。9同上. [Ibid.]
皇帝的信息為什么不能傳遞?一種可能:皇帝當著眾人耳傳諭旨只是一個儀式。他知道諭旨無法傳出,也壓根兒沒有那樣的打算。絕對權力需要不透明的神秘自我保護,讓子民看不透其意圖。
這是邏格斯中心結構、內部殖民主義體系的文學實例。如此體系產生的官僚習氣,其荒謬遠不止于繁文縟節。
針對卡夫卡作品提出的“官僚”問題,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曾經講過一個故事。18 世紀的俄羅斯,曾有個總理大臣叫波將金(Potemkin)侯爵。波將金患有嚴重的憂郁癥,整日躲在宮廷深處。波將金是葉卡捷琳娜二世的寵臣,權傾一時。女皇需要速辦的公文,必須先由他簽字。而波將金幾乎不工作,大量公文積壓在文件柜里。沒有人敢接近波將金,也沒有人敢提波將金有病這件事。這一天,總理府的前廳聚滿了樞密官,他們急需波將金的簽字,卻不知所措。這時來了一個天真的小辦事員叫舒瓦爾金(Shuvalkin)。舒瓦爾金覺得,這還不是小事一樁?他把大家急需辦的文件收集起來,放進公文包夾在腋下,腳步不停,走向波將金的臥室,見門沒有鎖,擰動把手徑直走進去,但見昏暗的房間里,萎靡不振的波將金穿一件舊睡衣,坐在床上啃指甲。舒瓦爾金什么也沒說,走近寫字臺,把羽毛筆蘸飽了墨水,遞到波將金手里,把文件擺在他膝蓋上。波將金冷冷瞥了舒瓦爾金一眼,一言不發,開始在膝蓋上簽字,一件又一件,直到簽完所有文件。舒瓦爾金立刻離開房間。樞密官們興奮地涌過來,從他手里接過公文包,但看到文件的一刻他們都驚呆了。舒瓦爾金走上前來,也看到了,每份文件上的簽名都是:舒瓦爾金、舒瓦爾金、舒瓦爾金……。10See Walter Benjamin, “Franz Kafka: On the Tenth Anniversary of His Death,” in Benjamin’s Illuminations, ed. Hannah Arendt and trans. Harry Zohn (New York: Schocken, 1969), 111-13.
本雅明講的是卡夫卡之前兩百年的故事。表面上看,這個故事與卡夫卡的一個故事情節幾乎相反。在卡夫卡的極短篇《法律的門前》(也是《城堡》的一部分)中,一個農夫走進法律大樓,想看看里面究竟有什么,卻被守門人嚇住,不敢往前一步,就呆在門前等,一等就是許多年(這是寓言),最后老死在那扇門前。11See Franz Kafka, “Before the Law,” trans. Ian Johnston, kafka-online.info.
不過,本雅明的故事,卻問了卡夫卡要問而沒問的:假設我們比農夫幸運,走進了官僚權力的深處,會發現權力黑箱的什么秘密?
善良的平凡人會想:權力的核心必有不凡的智慧,而真相卻是:那里沒有什么不凡的智慧,甚至沒有常理,只有一個患有嚴重憂郁癥、萎靡不振的波將金。
位高權重的官僚在文件上簽低層辦事員的名字,意味著所簽文件無效。這不是簡單的懶政低能,而是出自權力病態的懶惰和任性。不妨設想,如波將金需要簽發的文件里有一份涉及帝國權力的利益,他會立馬簽下自己的大名,不會誤事。
深諳卡夫卡世界邏輯的本雅明,特意添了一條注釋:波將金是卡夫卡筆下“父”的又一化身,而天真的舒瓦爾金是“子”,他是《城堡》和《審判》里的K、《變形記》里的格里高爾·薩姆沙(Gregor Samsa)、《判決》里的喬治·本德曼 (Georg Bendemann)。12See Benjamin, “Franz Kafka,” 113.
卡夫卡所諷喻的威權體系尊卑分明,遵循僵硬的二元對立(邏格斯中心)邏輯;其服務對象不是邊緣的人,而是中心;其意識形態及其法律,強制要求順從。其基本原理是王在法之上,中心說一不二,不服從即是罪。
諷喻的寓意不受時間地點所限,上述體系可指中世紀的威權,也可指現代的威權,本質一樣。
本雅明曾言,波將金是“當權者的祖先”。波將金是“作為[卡夫卡作品里]閣樓上那些法官、城堡里那些書記官出現的。無論他們身居何種高職,永遠都是墮落或正在墮落的人。可是,在最卑微的人(如守門人和老朽的官員們)眼里,[這些人] 儼然就是威風凜凜的權力”。13Ibid., 112.
莎翁的一行詩句,一語概括這種體系:“良順的囚徒聽命于有病的首領” (“And captive good attending captain ill” )(Sonnet 66)。
三
在現代主義文學的評論中,“異化”“荒謬”這樣的詞語屢見不鮮。但同一個詞在不同語境里,意思又有所不同。譬如,“荒謬”。存在主義哲學家加繆(Camus)認為,存在先于本質,每個人都是有獨特經歷的獨特個體。人與人天然有隔膜,“荒謬”(absurdity)存在于普遍的人際冷漠里。卡夫卡眼中的“荒謬”,雖與加繆有重疊,卻主要指向他諷喻的權力體系。
不以正常法理為依據的法律,本身就是荒謬。首先,何為罪?《在流放地》里那個愚忠的軍官,向探險家鄭重宣告流放地的信條之一:“我的指導原則是:guilt 是不容懷疑的”(“My guiding principle is this: Guilt is never to be doubted”)。14Kafka, “In the Penal Colony,” in Muir’s translation, 198.在卡夫卡作品里頻繁出現的“guilt”(負罪感)一字,一方面,指體系強加的任何罪名;另一方面,指體系為了自身的合法,將“原罪”輸入被殖民者,使之內化,成為順民的無意識。
法治之下,先做無罪推定,經公正法律程序的審判方能確定有罪或無罪,以及有何罪。在卡夫卡筆下的流放地這樣的地方,有罪與無罪,取決于忠誠度,亦即你和權力中心的心理距離。懷疑、不服、反抗,是不同程度的不忠誠,對應不同程度的罪。《在流放地》里,那個被判死刑的“罪犯”,只是在規定向長官敬禮的那一刻打了個盹。
卡夫卡的語境里,“原罪”的潛臺詞是:處于權力邊緣的人,天然有罪。在《審判》里,K躺在床上,無緣無故被傳喚,其法律程序莫名其妙,卻自有其邏輯:我們認為你是威脅,但是我們不會告訴你為什么你是個威脅。這種極為荒謬的邏輯,就是卡夫卡味兒!
清白無辜的格里高爾·薩姆沙、喬治·本德曼,何罪之有?因為他們身為人子,在“父”面前天然有罪。“躺著中槍”,如果成為社會生活的常態,是讓人笑不出來的黑色幽默。
“苦難”的涵義,也各有不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的主人公,如《罪與罰》中的拉斯柯尼科夫,又如地下室人,是為自己的錯或罪承受苦難。卡夫卡的主人公受苦,卻是因為不知自己犯了什么罪,或做了什么錯事。苦難成了荒謬的一部分。卡夫卡味兒里,有蒙冤的苦澀,也有“陽痿式的憤怒”(impotent rage)。
細品卡夫卡味兒,荒謬也可分出層次。從由外向內的視角觀察,比如從《在流放地》的外來探險家(讀者的替身)的視角觀察,流放地的體系本身荒謬,而困在里面的人對荒謬習以為常,視為當然,又是荒謬中的荒謬,是雙重的荒謬。15Ibid., 191-227.
格里高爾·薩姆沙為什么變成大甲蟲?不言而喻,卡夫卡的文學虛構延續了奧維德(Ovid)《變形記》的傳統,但是其現代意義特別突出。故事讀到一半我們就明白了格里高爾變成蟲的原因:變蟲喻說著他的人性被嚴重異化。格里高爾以為父親喪失了勞動力不能工作,無力償還家里的債務;善良的他為了還債,為了養活父母、妹妹和自己,做起旅行推銷員。他從清早工作到深夜,付出了自己所有的時間和精力,犧牲了自己所有的私生活。諷刺的是,父親的身體沒有問題,他為了私利和一家公司簽約,私自把兒子的勞動力賣了。格里高爾的辛勤勞作,不僅還了債,還使得懶惰的父親有了可觀的私房錢。
卡夫卡式的荒謬是,我們被格里高爾變成了大甲蟲驚得目瞪口呆的時候,格里高爾自己似乎不特別在意。他第一個反應,是覺得蟲的身體特征太不方便,害得他上班要遲到了;他父母擔心的也不是兒子變成了蟲,而是兒子要遲到這件事;當辦公室經理追到家里興師問罪,格里高爾隔門向他乞求,試圖爭辯:我可以上班,我和家人要活下去,我不能丟了這份工作。
格里高爾想拿鑰匙打開房門,意識到自己沒有手,也沒有牙,只能用甲蟲的腮幫噙住鑰匙;他完全忘記了這樣做可能傷害自己,結果“褐色液體從嘴里涌出,在鑰匙上淌過,滴在地板上”。16See Kafka, “The Metamorphosis,” in Muir’s translation, 80-81.格里高爾此時已是蟲,那“褐色液體”是他的血液。小小一個細節,驚悚無比。
這個故事也揭示著權力體系二元對立的邏輯:父親+公司是“中心”;母親唯夫命是從,是脅從。格里高爾只是令家人感到不方便的“蟲”。妹妹的態度,隨著她對哥哥是人還是蟲的判斷在變化。哥哥死后,她替代哥哥,成為家庭收入的資源。
格里高爾這個甲蟲,是蟲和人的怪異組合,喻說著人性和蟲性(異化后的奴性)之間的搏斗。隨著他人性的消弱,格里高爾每況愈下,直至變成一只干癟的蟲死去。
格里高爾的情緒起伏變化,標示著各種自相矛盾中的荒謬:他焦慮,時而出自人性,時而出自蟲性;他善良,卻不能明辨是非;他順從,逼急了也會奮起反抗。
格里高爾深愛妹妹,拼命工作,一部分原因是為賺夠錢送她上音樂學院。妹妹一直不愿把他當作蟲,直到故事的終曲:妹妹在為房客演奏提琴,格里高爾不由自主向音樂聲爬去,最后爬進了房間,嚇壞了所有人;妹妹終于下了決心,宣布:她面前的不是她的哥哥,而是一條蟲。這等于宣告了格里高爾的死刑。
荒誕劇抵達高潮,人性中的荒謬反而更逼真。我們隨著格里高爾復雜情感的起伏而起伏,各種情感伴隨各種感悟,融入與故事邏輯相應的“感情結構”(structural emotions)。卡夫卡味兒,五味雜陳。
四
文學的本質在于其美學判斷。那么,卡夫卡作品的“美”在哪里?卡夫卡味兒又是怎樣的美學判斷?
美學判斷是大題目,此處只宜淺論。美學實為藝術學;“美感”只是諸多藝術命題之一。究其希臘詞源,aesthetics(漢語譯為美學)是“感知”(sense perception)和“靈敏度”(susceptibility)的意思。所以,aesthetics的基本內涵是:藝術以感知為基礎,是直觀的。
藝術的直觀,不等于沒有觀念。美學經驗(the aesthetic experience)是由感知進入感悟(即判斷)的過程,故而是美學判斷。美學的判斷并非不涉及道德和政治,只是不以既定的觀念先入為主。現代意義上的美學判斷,不以說教為目的,而是抗拒慣例思維或使之復雜化,由此形成是非善惡的判斷。另外,文學藝術調動的不是人性的某一種功能(比如邏輯理性),而是所有功能,如修辭、想像、角度、直覺、欲望、意志、邏輯,既各司其職,又融為一體。如此的感知感悟積少成多,潛移默化,就是藝術修養。
從文學獲得的感知感悟,除了用“美感”描述,還有“愉悅”(pleasure或delight)一詞。翻閱西方文學理論史,以“愉悅”指謂審美,使用更頻繁。“愉悅”指震撼心靈的感受,包括美感。
美感或愉悅由何而來?桑塔亞納(George Santayana)討論美學判斷時指出:古希臘有個詞,kalokagathia, 意思是:美和善是不可分割的一體。我們感受到美(the beautiful)時,已經直覺到善念(the good);善念是美的內在。17See George Santayana, The Sense of Beauty (1896) (New York: Barnes and Noble, 2005), 13.對美與丑的感知,已是對善與惡的判斷。
在眾多的美學判斷方式中,卡夫卡式是非常特殊的一種。直觀之下,卡夫卡作品中的負面情緒似乎不美,但那種渴望自由的強烈潛流,正是善念的潛流,由此產生的震撼即是卡夫卡式的愉悅,卡夫卡式的“美”。
卡夫卡的作品不是悲劇,而是荒誕劇。在希臘和莎士比亞的經典悲劇中,悲劇人物或悲劇英雄承受的苦難,是揭示生命之力、生命之謎的載體。卡夫卡塑造的小人物,面對父權或威權的威懾,往往手足無措,懦弱無力;內化的原罪,讓他們驚恐不安,敢怒而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這種苦,是苦悶和恐懼化為荒誕的苦汁。至于為苦情而苦情、為濫情而苦情、為其他目的而裝苦的作品,如今比比皆是,與卡夫卡味兒其實毫不相干。
卡夫卡喚起的美感,不是賞心悅目或似水柔情的美,不是人生不如意的長吁短嘆,也不是天人合一的自然達觀。
卡夫卡作品中,負面情緒為藝術所用,見證著文學的“負面能力”(Negative Capability)。英國浪漫詩人濟慈(John Keats)提出一條非常重要的美學原則。他認為,偉大文學有別于平庸文學之處,是其“強烈感”(intensity)可使“所有不快”(all disagreeables)隨風而逝。“強烈感”即強烈的感染力,產生于“負面能力”,即:“人能沉浸于不確定、神秘、懷疑,而完全不必急不可耐地引證理性和事實” (I mean Negative Capability, that is when man is capable of being in uncertainties, mysteries, doubts, without any irritable reaching after fact and reason)。18John Keats, “From a Letter to George and Thomas Keats,” in The Critical Tradition: Classic Texts and Contemporary Trends, 3rd ed., ed. David H. Richter (Boston and New York: Bedford/St. Martin’s, 2007), 333.
負面能力,即容納并轉化負面情緒、形成強烈感染力的美學能力;這種轉化有賴于藝術形式(form),包括:敘述視角的巧用、細節的設計、情節的安排、修辭格的選用、場景氛圍的烘托、表達情緒的語氣,乃至所有的藝術手段。卡夫卡的負面能力是卡夫卡轉化負面情緒的方式。事實上,負面情緒只要是真實的,發乎人性,就不能簡單斥為負能量而否定。
如何發揮藝術的負面能力?俄國形式主義美學理論家什克洛夫斯基(Shklovsky)論及藝術應該“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時這樣闡釋:現代生活中的習慣性思維,使人們的感受力麻木,導致異化,而藝術有意將熟悉的變得陌生,將習以為常的變得復雜,“因為感知的過程本身是美學的目的,必須延長” (because the process of perception is an aesthetic end in itself and must be prolonged)。 卡夫卡以藝術家的敏銳,善于在“習以為常”中捕捉荒謬,輔以修辭的夸張,形成強烈的沖擊力,意在驚醒于“習以為常”中沉睡的人,以辛辣的刺痛恢復人性中應有的敏感。卡夫卡還刻意揭示人內心沖突中的荒誕不經,雖然其效果常會令讀者感到不適。
我們通常的減壓是為了有喘息的空間,而卡夫卡的作品卻從不減壓,不留喘息的空間。一系列夢魘般的情節排列開來,如同沉沉黑夜中延伸出的一條道;讀者想停止噩夢,卻因好奇心順這條道走下去,直達夢魘深處,直至獲得某種啟示。我們閱讀《城堡》《審判》《在流放地》等等,就是這樣的體驗。
如果只有震驚而無啟示,那么,卡夫卡不過是營造哥特式恐怖的流行作家。顯然他不是。
卡夫卡的夢魘實際上是一個個雕琢的片刻(moment)。本雅明稱之為“形姿”(gesture),德語gestus。19See Benjamin, “Franz Kafka,” 121.本雅明說他使用這個詞的靈感來自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的戲劇表演方式。他同時提到中國演員的表演,或許與布萊希特接觸到京劇的形體表演有關。
這些“形姿”產生的綜合效果,為美學判斷開辟了充裕的空間。
有三個不易區分的修辭格(figures of speech):反諷、模糊、悖論。唯有成熟的作家才能運用自如,延長感知,啟動負面能力,引導判斷走向復雜和豐富。
反諷(irony):指想象、期待、猜測、相信的事,與真相相反,其中的反差提示某個道理。
模糊(ambiguity):指某句話、某個詞、某個情景,在上下文里產生了兩個相反卻似乎都合理的解釋,因而提出一個頗費思量的謎。作為修辭格的模糊使判斷復雜化。有時候,我們需要在兩個相反的解釋中做一個合理的選擇;有時候,我們覺得兩個解釋都有可取之處,于是兩者都保留。
而paradox,被譯為:悖論、吊詭,也被譯為:二律背反,指的是:兩個意思相反的命題必須并存,構成一個完整而且有道理的現象或邏輯。悖論的自相矛盾看似錯了,其實是對的。比如,美國現代文學中的“怪異人”(the grotesque)這個人物原型,其定義是:既可愛又扭曲,既正常又反常。根據這個規律,通常譯為悖論的paradox 也可以譯作:相反命題并存(正是二律背反)。
模糊有時要求我們做選擇,有時則讓人難以選擇。模糊有別于悖論,因其尚未形成一個完整的邏輯。
模糊、悖論、反諷,要從藝術效果來識別。在卡夫卡的作品里,這些效果往往是混合的:某個場景既有反諷又有悖論,或兼有模糊。究竟是何種效果,取決于讀者某時某刻的感受和解讀。無論那種效果,感知在沖突展現的過程中得以延長;判斷變得復雜而厚重,見證著卡夫卡“陌生化”和“負面能力”的功力。我們暫時采用“相反命題并存”(而不是二律背反)的說法來概括模糊、悖論、反諷的共性。請看卡夫卡作品中的幾個“形姿”或片刻。
喬治·本德曼(短篇小說《判決》中的人物)平日里是個快樂的年輕人。春季一個美好的周日,他望著窗外的河流,滿心喜悅和希望,在桌前給遠在圣彼得堡的朋友寫信,告知他要結婚的喜訊。想到有一段時間沒有見到父親,他把寫好的信放進口袋,向父親的房間走去。母親去世后,父親日漸衰老,滿頭臟亂白發的他坐在窗前,桌上擺著剩飯。喬治像抱孩子那樣,把瘦骨嶙峋的父親抱到床上。
這個爹明明是瀕臨死亡的樣子,見喬治來了,他穿著睡衣像孩子一樣在床上蹦跳。一個快死的人怎么有孩童的活力?不僅如此,這個瀕死的爹非常強悍:他以亡妻的名義無端指責兒子,編造關于他朋友的謊言,侮辱他的未婚妻,最后,命令兒子去死。喬治居然領命,跑出去投河自盡!
這前后鮮明而強烈的反差,是令人震驚、發人深省的反諷。
喬治還注意到:這個爹手里拿的是很久以前的舊報紙,無異于舊日的化石。但這爹手里又牽著一塊懷表的鏈子,意味著他想把時間留在他這一邊。報紙和懷表兩個象征意義的并置,是反諷,是悖論,又似乎是有待破解的模糊。我們姑且稱之為:相反命題并存。20For details, see Kafka, “The Judgment,” in Muir’s translation, 49-63.
《變形記》也有許多特意設計的“形姿”。格里高爾那份推銷員的工作,剝奪了他所有的時間和精力。唯一可以稱為他閑暇之作的是一幅裝框的畫。這是格里高爾從流行雜志上剪下的一位女士的圖像:女士身穿皮草,戴皮草帽,披皮草圍脖,手臂套著皮草手籠,整個人淹沒在動物皮草里。學界對這幅裝框畫至少有兩種合理的解讀:這是格里高爾的手工藝品,是他作為人的創造性的證據;畫中的女性也意味著格里高爾的性欲,確切說是他沒有時間顧及的正常欲望。就這兩點而言,裝框畫代表格里高爾的人性。但是,畫中的女性淹沒在皮草里,又暗示著動物性,是格里高爾自己變形為動物的鏡像。這幅畫既象征格里高爾的人性,又象征他的動物性。這是反諷、模糊,還是悖論?相反命題并存。
變成大甲蟲的格里高爾,內心的人性尚存,但行為一點一點變得更像蟲;他很快失去了人的聲音;他逐漸拒絕人類的食物;家人從他的房間移走所有家具,給他更多蟲的空間;他逐漸可以迅速在墻壁爬行,而且可以在天花板縱橫爬行。當母親和妹妹來房間搬移家具時,格里高爾想留住他的書桌。因為他已經不能用人的語言表達,他喜歡那張桌子是因為他作為人的過去記憶,還是他的蟲軀體有需要,我們不能確定。21For details, see Kafka, “The Metamorphosis,” in Muir’s translation, 67-132.
母親和妹妹要搬動那幅裝框的皮草女肖像圖時,格里高爾被激怒。他用蟲的身體和她們爭奪。他“迅速爬到畫跟前,緊貼在玻璃上。抱著玻璃面真好,他滾熱的肚子也舒適了”。22Ibid., 105.
對于此時的格里高爾而言,驅使他的究竟是人性還是蟲性?如果人和蟲的兩種解讀都合理,這似乎是模糊。但如果將這個“形姿”理解為人性和動物性并存的定格,那又是悖論。反諷的意味也不言而喻。到底是模糊、反諷、悖論,還是三者皆有,則需要讀者根據自己感受去判斷。
感受到相反命題并存形成的復雜效果,才算品到了卡夫卡味兒。
與哲學觀念相比,藝術中的觀念趨于模糊,留有更多回味的余地。濟慈為“負面能力”下定義時用的三個詞,“不確定、神秘、懷疑”,都指向藝術中有意而為之的模糊空間。在非美學語境里,模糊可能會視為缺點,而在文學佳作里模糊這個修辭格的使用意味著:感知得以延長,思辨在回味中進入未知,接近新知。
五
卡夫卡出生在布拉格一個猶太人的中產家庭,衣食無憂,在高中和大學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獲得法學博士學位,做過律師所和保險公司的工作。其生活看似無風無浪,內心卻波瀾起伏。
童年時,父母忙于各自的工作,卡夫卡多數時間跟著家庭教師和仆人生活。父親是家里說一不二的主人。在他眼里,這個身體強壯、食欲旺盛、嗓音洪亮、能說會道的父親,雖有識人之明,卻自視過高。這個形象和《變形記》中的父親有些相符,但不太像卡夫卡其他故事中的父。卡夫卡選擇法律專業,并非自愿,而是為了讓父親滿意。傳記作家都會談到卡夫卡如何酷愛文學哲學,列舉他閱讀的廣泛和品味。在大學里,他的演講和朗誦十分出眾。他也勝任律師所和保險公司的工作;上司對他的各種報告歷來滿意,但卡夫卡心生厭煩,覺得繁瑣的工作妨礙他喜歡的寫作。
卡夫卡與好幾位女性有過親密關系,卻一生未婚。他的健康狀況一直欠佳。1917年,他被診斷患有喉頭結核。1924年3月,他從柏林回到布拉格家里,病情惡化,由妹妹奧塔爾細心照料他。4月,他在女友迪亞曼特的陪伴下去了克洛斯特新堡,在霍夫曼醫生的療養院治療,兩個月后在那里去世。患喉頭結核進食非常痛苦。當時胃腸外營養療法還不成熟,卡夫卡其實是餓死的。臨終前,卡夫卡在創作短篇《一個饑餓的藝術家》(“A Hunger Artist”)。
卡夫卡的一生只有短短41 年,留下77 個短篇,3 部小說(其中兩部并非完整),還有一些結集和未結集的箴言式片段。他去世后,好友布羅德違背他的遺愿,把他本要銷毀的作品都出版了。布羅德將一部分手稿遺留給了秘書,現歸以色列國家圖書館所有。
奧匈帝國時期的布拉格,分為說捷克語、說德語兩大群體,猶太人夾在中間,還受到排猶偏見的歧視。卡夫卡的家人說的是變異的德語;卡夫卡在學校學的則是標準德語。因為他也說捷克語,他的德語夾雜了捷克語。卡夫卡時常覺得自己猶太人的身份帶給他諸多不便和煩擾,但是他逐漸喜歡上猶太經典《塔木德》,進而深入其中,汲取神秘的智慧。卡夫卡是用德語寫作的猶太人,這件事也值得深思。
我們可從卡夫卡的生平窺見他文學特點之一二,但只有細讀他的作品才可感知他的靈魂。
卡夫卡和我們同處這個實體世界,但他不完全屬于這里。他奮筆書寫生存的苦悶,指出種種荒謬,皆源自他對丑惡的痛恨;他描寫不自由的狀態,為的是詮釋自由的意義,突顯自由的可貴價值。這是一種堅強的善念,是卡夫卡美學的本質。
割下耳朵的梵高和畫向日葵的梵高,是同一人還是兩人?答案雖然兩者皆可,但判斷梵高是天才的依據,是他的向日葵,而不是割下的耳朵。梵高的向日葵有一種扭曲、亢奮的攻擊力,看似在病態和健康之間,卻通向宇宙間的永恒。卡夫卡的創作可與梵高畫的向日葵相類比。不過,或許換一個比喻更恰當:卡夫卡描寫的黑夜和夢魘,類似于據說可以接通另一個世界的“暗物質”。
這樣的卡夫卡,依然是猶太人敬重的先知(prophet)。先知將神諭內化,激情道出,即成詩句,因此有詩人-先知(poet-prophet)的美稱。
而先知的話,在菲利斯人聽來,是瘋言瘋語。在他們指指點點的圍觀下,先知被當作瘋子。
在卡夫卡的文字碎片中,有這樣一句瘋話:“一只鳥籠在尋找一只鳥”。
我們為鳥兒逃出籠子而歡欣鼓舞,又看到窮追不舍的鳥籠而心有余悸。這種相反心情并存的卡夫卡味兒,是濃縮的、清醒的,揮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