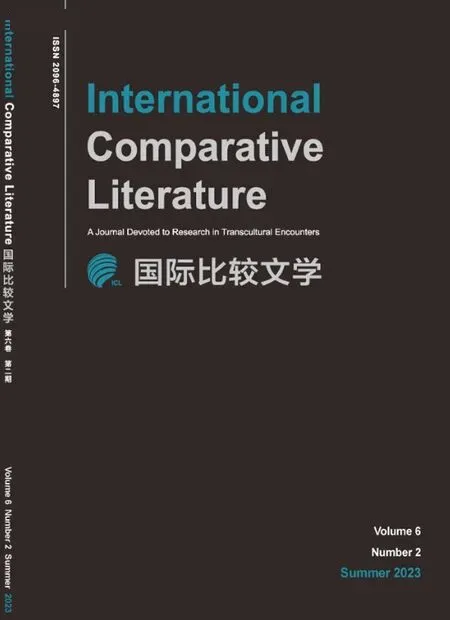威廉·福克納與中國新時期小說的發生*#
李萌羽 中國海洋大學 張悅 中國海洋大學
20世紀70年代末以降,隨著各種外來哲學、文藝思潮的涌入和外國作品譯介的傳播,中國新時期文學在與世界文化、文學的相互碰撞、滲透和交融下,整體風貌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形成了具有中國氣派,蘊含現代性主題意蘊和審美特質的文學,在此過程中,中國新時期文壇涌現出一大批在國內外具有影響力的作家,特別是莫言于2012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這一突破標志著中國新時期作家在世界文學場域中所得到的認可。“中國新時期作家的創作無論在主題意蘊的表達和文體形式的創新上都有一個質的飛躍,其文學觀念的轉變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外國文學的影響。”1李萌羽:《中國新時期作家與福克納》,見《東方論壇》2021 年第1 期,第58 頁。[LI Mengyu, “Zhongguo xinshiqi zuojia yu fukena” (Contemporary Chinese Writers and Faulkner), Dongfang luntan (Eastern Forum) 1 (2021): 58.]中國新時期作家所受外國文學和外國作家的影響是多方面、多層次的,其中美國作家威廉·福克納是被提及最多的外國作家之一,據馬原回憶,福克納“曾經在80年代前期的中國引起爆炸性的轟動。”2馬原:《小說密碼——一位作家的文學課》,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 年,第325 頁。[MA Yuan, Xiao shuo mi ma: yi wei zuo jia de wen xue ke (The Novel Cipher: The Literary Class of a Writer) (Beijing: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 2009), 325.]作為西方現代派文學重要代表性作家之一,福克納的作品晦澀艱深,如美國福克納研究專家罕布林教授所言,福克納的讀者是“精英讀者”而非“普通讀者。”3李萌羽:《福克納研究在美國”——羅伯特·罕布林教授訪談》,見《跨文化溝通與中西文學對話》,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 年,第192 頁。[LI Mengyu, “Fukena yanjiu zai meiguo: luobote hanbulin jiaoshou fangtan” (On William Faulkner: An Interview with Robert W. Hamblin), in Kuawenhua goutong yu zhongxi wenxue duihua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ry Dialogue)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17), 192.]福克納為何在中國新時期文學中受到作家們的“追捧”?這一現象發人深思。事實上,在新時期文學的早中期,福克納不但對莫言、余華、蘇童、賈平凹、格非、趙玫、馬原、遲子建、鄭萬隆、呂新、李銳、葉兆言、陳村、劉震云、阿來等作家在文壇創建各自的文學天地產生了直接或間接的影響,而且對其后的青年作家如徐則臣、雙雪濤等人的創作均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從中可以看出,福克納對中國新時期作家的影響并不是曇花一現,而是滲透在新時期文學的各個時期,這一影響和接受關系值得深入探究。
一、中國新時期作家比較視野中的福克納
中國“新時期文學” 這一概念、命名以及文學史意義在學界得到了普遍認可,它主要指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至今的中國當代文學,“新時期”之“新”主要體現在小說意識、主題意蘊和藝術性等方面,它張揚了“文學是人學”這一根本性主題的書寫,繼承了“五四”文學的啟蒙現代性敘述,并在立足本土文化,借鑒各種外來思潮、文學的過程中獲得了審美現代性的合法敘述,在這一過程中涌現出了劉心武、王蒙、宗璞、張承志、馮驥才、莫言、余華、蘇童、賈平凹、韓少功、王安憶、格非、趙玫、遲子建、馬原、劉震云、阿來、鄭萬隆、呂新、李銳、葉兆言、陳村、畢飛宇、李洱、徐則臣等一大批在國內外產生廣泛影響的作家,構成了中國新時期文學的蔚然景觀,本論文關于福克納與新時期小說的研討也正是在此范疇下展開。
一些學者和作家認為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對新時期文學的影響最大,其實,馬爾克斯的創作受到了福克納很大的影響,從此意義上說,新時期文學通過馬爾克斯間接受到了福克納的影響。盡管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對新時期文學影響甚大,但是追根溯源,馬爾克斯的寫作又受到福克納較大的影響,對于這一點,兼有作家和學者雙重身份的格非比較了解,“馬爾克斯所師承的歐美現代主義敘事大師,既不是詹姆斯·喬伊斯,也不是馬塞爾·普魯斯特,而是弗蘭茨·卡夫卡、弗吉尼亞·沃爾芙、威廉·福克納、海明威、胡安·魯爾弗。卡夫卡教會了他如何通過寓言的形式把握現代生活的精髓,并幫助他重新理解了《一千零一夜》的神話模式,打開了一直禁錮他想象力和寫作自由的所羅門瓶子。威廉·福克納則給他提供了寫作長篇小說的大部分技巧,福克納那些描寫美國南方生活的小說充滿陰郁、神秘的哥特情調,堅定了馬爾克斯重返根源的信心;而且福克納那龐大的“約克納帕塔法世系”也在刺激著他的野心。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他都在追隨福克納,甚至還按照他的教導,嘗試在妓院中的寫作。”4格非:《博爾赫斯的面孔》,南京:譯林出版社,2014 年,第155 頁。[GE Fei, Boerhesi de miankong (The Face of Borges) (Nanjing: Yilin Publishing House, 2014), 155.]余華也曾提及福克納戲謔寫作應該在妓院進行的典故,說他“曾經在一篇文章里讀到威廉·福克納經常在傍晚的時候,從奧克斯福開車到孟菲斯,在孟菲斯的酒吧里縱情喝酒到天亮。他有過一句名言,他說作家的家最好安在妓院里,白天寂靜無聲可以寫作,晚上歡聲笑語可以生活。”5余華:《奧克斯福的威廉·福克納》,《上海文學》2005 年第3 期,第84 頁。[YU Hua, “Aokesifu de weilian fukena”(William Faulkner of Oxford), Shanghai wenxue (Shanghai Literature) 3 (2005): 84.]這些評論當然帶有夸張的成分,但可以看出馬爾克斯和余華等新時期作家對福克納的熟悉程度。
實際上,馬爾克斯本人在《番石榴飄香》中坦率承認福克納對他創作的影響:“可能在我的早期作品中看出我是受了他的影響……因為在我創作的初期,由于需要而借鑒了他的東西。”6轉引自李德恩:《拉美文學流派的嬗變與趨勢》,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6年,第39頁。[LI Deen, Lamei wenxue liupai de shanbian yu qushi (The Evolution and Trend of Latin American Literary Schools)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96), 39.]馬爾克斯第一部小說《枯枝敗葉》模仿福克納《我彌留之際》的創作技巧,通過棺材里的一具尸體發出的曲折獨白追述了一家三代人命運,與《我彌留之際》的主題和情節設置有異曲同工之妙。
受福克納“約克納帕塔法”世系小說的影響,馬爾克斯也虛構了一個家鄉小鎮馬孔多,以魔幻現實主義的表現手法,展現了20 世紀上半葉哥倫比亞乃至整個拉丁美洲所處的封閉、落后、衰敗的圖景,其代表作《百年孤獨》以馬孔多鎮為背景書寫了布恩地亞家族七代人的命運,從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剖析了拉美社會的現實和精神痼疾。孤獨成為這個家族每個人共同的精神特質,該小說所表現的孤獨,不僅是馬孔多小鎮人的孤獨,更是人類心靈深處普遍存在的孤獨。因為有這種師承關系,馬爾克斯的創作中有很多對福克納的模仿和借鑒,“加西亞·馬爾克斯的小說在主題、題材和深層意識上與福克納的作品極為神似”,“如果加西亞·馬爾克斯沒有從福克納的作品中得到啟示,很難想象他能到達輝煌的今天。”7同上。[Ibid.]
莫言在《兩座灼熱的高爐——加西亞·馬爾克斯和福克納》一文中,詳細談到了他早期創作所受到的馬爾克斯和福克納的影響,指出他在1985年中,寫了五部中篇和十幾個短篇小說,“它們在思想上和藝術手法上無疑都受到了外國文學的極大的影響。”8莫言:《兩座灼熱的高爐——加西亞·馬爾克斯和福克納》,《世界文學》1986 年第3 期,第298 頁。[MO Yan,“Liangzuo zhuore de gaolu: jiaxiya maerkesi he fukena” (Two Searing Furnaces: Garcia Marquez and Faulkner), Shijie wenxue(World Literature) 3 (1986): 298.]其中對他影響最大的兩部小說是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和福克納的《喧嘩與騷動》。他指出,“《百年孤獨》這部標志著拉美文學高峰的巨著,具有駭世驚俗的藝術力量和思想力量。它最初使我震驚的是那些顛倒時空秩序、交叉生命世界、極度渲染夸張的藝術手法。”9同上。[Ibid.]這些藝術創作技巧,如打亂時空次序,運用多重人物敘述視角也是福克納小說的一些顯著特點。莫言認為藝術技巧終歸是屬于表層面的,《百年孤獨》給他更大的啟示在于馬爾克斯獨特的認識世界和人類的方式,“他之所以能如此瀟灑地敘述,與他哲學上的深思密不可分。我認為他在用一顆悲愴的心靈,去尋找拉美迷失的溫暖的精神的家園。他認為世界是一個輪回,在廣闊無垠的宇宙中,人的位置十分渺小。他無疑受了相對論的影響,他站在一個非常的高峰,充滿同情地鳥瞰著紛紛攘攘的人類世界。”10同上。[Ibid.]而莫言亦盛贊福克納的《喧嘩與騷動》是一部“同樣偉大的著作”,最初讓他注意這部作品的也是其藝術上的特色,但他又覺得這些藝術技巧,“委實是雕蟲小技”,他更為欣賞《喧嘩與騷動》回響的雙重基調 ,“應該通過作品去理解福克納這顆病態的心靈,在這顆落寞而又騷動的靈魂里,始終回響著一個憂愁的無可奈何而又充滿希望的主調。”11莫言:《兩座灼熱的高爐——加西亞·馬爾克斯和福克納》,《世界文學》1986 年第3 期,第299 頁。[MO Yan,“Liangzuo zhuore de gaolu: jiaxiya maerkesi he fukena” (Two Searing Furnaces: Garcia Marquez and Faulkner), 299.]在此,莫言對福克納《喧嘩與騷動》的深層意蘊的理解是比較準確的,他洞察了福克納對南方的復雜情感以及超越苦難的樂觀主義精神。在論及莫言所受到的福克納和馬爾克斯兩座火爐影響的深遠意義時,一位評論者指出,“對莫言來說,馬爾克斯和福克納與其說代表了種種具體而微的技巧,不如說是更寬泛意義上的文學的自由和解放的象征。他們就像是化學反應中的觸媒,能夠催化反應的發生,但本身并不直接變成反應的結果。莫言猶如蓄勢待發的反應體系,兩座‘高爐’激活了他多年的生活經驗,引爆了綿綿不絕的連鎖反應。”12嚴鋒:《感覺的世界譜系:重新發現莫言的現代性》,《中國比較文學》,2013 年第1 期,第3 頁。[YAN Feng,“Ganjue de shijie puxi: chongxin faxian moyan de Xiandaixing” (Sensory World: Rediscovering Mo Yan’s Modernity),Zhongguo bijiao wenxu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hina) 1 (2013): 3.]
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很多新時期作家喜歡把福克納和海明威做比較, 海明威廣為中國讀者和作家所熟知,然而一些新時期作家似乎更為推崇福克納,認為他在美國乃至世界的影響要勝過海明威。馬原在《小說密碼——一位作家的文學課》中對美國作家做了較為細致的比較分析,他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后,整個歐洲都在從一次災難到另一次災難的過程的時候,美國的文學走了自己一個新的蟄伏期。美國的主要作家成了世界上最著名的小說家,像海明威、辛克萊·劉易斯、考德威爾等等。這時在美國南方悄悄地出了一個讓全世界都瞠目結舌的大作家福克納。”13馬原:《小說密碼——一位作家的文學課》,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 年,第325 頁。[MA Yuan, Xiao shuo mi ma: yi wei zuo jia de wen xue ke (The Novel Cipher: The Literary Class of a Writer), 325.]他認為福克納不在傳統的美國主流文學之內,在美國本土的影響并不很大,反而在大洋彼岸的歐洲,贏得了很多歐洲作家和讀者的關注,故馬原特別看重福克納在國際上的文學地位,認為“福克納是現代主義運動在美國以至在全球最著名的小說家。”海明威在美國成名更早,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時間卻比福克納要晚幾年,馬原覺得福克納取得的成功甚至讓海明威嫉妒,因為福克納更早得到了國際文壇的認可。馬原還進一步比較了兩位作家不同的創作風格,“福克納的小說和海明威的小說可以說是兩極,是完全不同的兩種寫作。福克納的小說里面枝枝蔓蔓纏繞在一起非常繁復非常豐滿,而海明威的小說可以用一個‘瘦’字來形容,他幾乎就沒有一點多余的東西,就像骨架,像一棵不長樹葉的樹”14同上,第326頁。[Ibid., 326.]。馬原形象地對兩位作家寫作的繁復與簡約的不同文體風格的進行了分析,顯然他更為欣賞福克納的創作風格。
李銳也似乎偏愛福克納而對海明威頗有微詞,他同樣談到福克納在國際上受到重視,而在本國被忽視的情況,“我想,當初海明威在美國的大紅大紫,和福克納當初在美國本土的被忽視,最典型不過地說明了美國人的民族性格。(據說,福克納還活著的時候,他的書竟然在美國絕了版。福克納是在歐洲轟動了之后,美國人才恍然大悟:原來自己家里放著個大國寶。而這個國寶后來果然比海明威先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海明威是個硬漢,而且是個很善于推銷自己的硬漢,他在把自己同莫泊桑、司湯達、塞萬提斯相提并論的時候,用的都是拳擊術語......而福克納正好相反,總是說自己是個種莊稼的農民,總是遠遠地躲著批評家和新聞界,連總統請客吃飯也遭了他的閉門羹。”15李銳:《終于過了青春期的美國》,《天涯》1986 年第2 期,第4 頁。[LI Rui, “Zhongyu guole qingchunqi de meiguo”(America Has Finally Passed Adolescence), Tianya (Frontiers) 2 (1986): 4.]他認為海明威如果沒有《老人與海》,連和福克納比的資格也沒有。他還指出:“對于福克納的忽視是致命的,它再清楚不過地暴露出美國的短視和淺薄。在歐洲中心主義的文化鄙視中煎熬的美國人,本來是可以因為有了福克納而站起來自豪一次的。可惜,福克納的產生和存在,只為美國做了反證,而且是無可辯駁的反證。這真是一個民族的悲哀。”16同上。[Ibid.]總之,李銳為美國曾經一度忽視福克納而感到惋惜。
趙玫也認為福克納在國際上的影響力要遠高于海明威, “而此時34 歲的福克納依舊老老實實地待在他的奧克斯佛,但卻已經寫出了諸如《喧嘩與騷動》《我彌留之際》那樣的偉大作品,并名揚歐洲。以至于連薩特都不得不承認,‘在法國年輕人的心目中,福克納就是神’,可見他在法國乃至歐洲的名氣,是在長年生活在歐洲的海明威之上的。”17趙玫:《趙玫文化隨筆:Key West 的燈塔(上)》,《世界文化》2015 年第11 期,第45 頁。[ZHAO Mei, “Zhao Mei wenhua suibi: Key West de dengta shang” (Zhao Mei Cultural Essays: Lighthouse of Key West), Shijie wenhua (World Culture) 11 (2015): 45.]福克納在三十多歲的時候就寫出了《喧嘩與騷動》《我彌留之際》等傳世之作,這確實彰顯了一位大作家的才華,從而引發了新時期諸多中國作家對福克納的追捧和認同。趙玫對福克納與海明威的創作也進行了比較,認為“福克納是那種用他的頭腦和文字創造藝術的藝術家;而海明威,則是用生命本身創造藝術的藝術家。”18同上。[Ibid.]福克納“用頭腦和文字創造藝術”凸顯了福克納藝術創作的想象力和創造力,海明威“用生命本身創造藝術”則強調了海明威創作與人生經歷和生命體驗之間的關系。
格非對福克納和海明威的評價相對客觀,似乎并沒有帶更多個人的偏愛。他也談到了福克納和海明威的較量,“威廉·福克納曾經公開批評海明威‘重復’、‘缺乏創新的勇氣’。海明威曾在不同的場合對福克納反唇相譏,但對這種批評本身始終未作正面的答復。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海明威完全知道自己的宿命。”19格非:《小說敘事研究》,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 年,第56 頁。[GE Fei, Xiaoshuo xushi yanjiu (A Study of Novel Narration)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Publishing House, 2002), 56.]他對比分析了海明威的早期作品《在印第安人營地》以及后期的小說《老人與海》,發現海明威所有的小說都包含著同一個故事內核,“在海明威的作品中,始終存在著兩種基因的根本對立:拳擊手的僵持,戰爭中的敵對雙方,人與自然的搏斗等等。正是通過兩個人物對這種對立的不同態度,作者成功地向讀者闡述了他對世界圖景的看法與立場”20同上,第58頁。[Ibid., 58.]。
在格非看來,盡管福克納批評海明威寫作中的重復,而在他本人的一系列作品中,這種“重復描述”的故事內核同樣存在,只不過福克納的作品與海明威的小說相比,“故事線索更為復雜,技巧更加多變”21同上,第59頁。[Ibid., 59.]。格非把福克納的短篇小說《獻給愛米麗的一朵玫瑰花》和長篇小說《喧嘩與騷動》做了對比,認為前者 “出現的對一個時代的消失所唱的挽歌是由艾米莉小姐乖戾的行為和晦陰的心理說出的,而在《喧嘩與騷動》中,這一旋律又一次以‘家族衰敗’的形式奏出”22同上。[Ibid.]。他認為不同的是福克納在《喧嘩與騷動》中對“衰敗”的敘述分內外兩條主線,“這種衰敗是以客觀世界的變化和家族內部個人的精神頹喪、崩潰、分裂雙重線索來展現的,而家族內部的分崩離析又帶有某種‘亂倫’的特征”23同上。[Ibid.]。格非在此只提到了福克納的兩部小說,其實他的諸多作品如《押沙龍,押沙龍!》《我彌留之際》《圣殿》《八月之光》都存在這樣一個衰敗的主題。因而,格非通過對海明威與福克納小說的比較與歸納,發現了“在作家一生的創作中必然存在著某種聯系,在各個不同的故事中,也存在著一個基本的‘內核’”24同上,第59頁。[Ibid., 59.]這一文學創作規律。他的這一闡釋對幫助讀者和研究者從整體上把握作家筆下一以貫之的“作品的內核”有很大的啟發性。他還進而強調,“作家從事于寫作的基本理由之一,就是力圖通過寫作將某種隱藏在心中的意圖呈現出來。也許他最終并不能徹底完成這一任務,但這種努力構成了作品與作品之間似斷若連的鏈索,作家經由這條鏈索傳達出他對生活著的這個世界(包括歷史)所表明的態度,以及其他豐富的信息。”25同上,第60頁。[Ibid., 60.]
應該指出的是,無論是福克納、馬爾克斯還是海明威,他們的創作各有其優長和特色,作為研究者應擯棄上述一些作家喜愛福克納和輕視海明威的偏見。筆者認為,新時期作家偏愛福克納的一個原因可能在于其作品主題意蘊的豐富性以及藝術形式的創新性。而海明威的小說,與福克納的作品相比,因缺乏一定的歷史縱深感,以及語言風格的電報體等,不能很好地滿足新時期作家對文學創作深層變革的要求,故出現了福克納更被新時期作家所青睞的情況。
二、新時期作家對福克納作品的不同接受
從新時期作家對福克納作品的接受來看,其長篇小說《喧嘩與騷動》與《我彌留之際》閱讀面和接受度最高,其次是短篇小說《獻給愛米麗的一朵攻瑰》,此外 《八月之光》《熊》《公道》等小說也被偶爾提及,但即便是對福克納的同一部作品,作家們的欣賞趣味也存在著一定的差異性。
《喧嘩和騷動 》是福克納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也是新時期作家“津津樂道”的一部作品。莫言覺得閱讀此小說沒有什么障礙,“許多人都認為他的書晦澀難懂,但我卻讀得十分輕松。我覺得他的書就像我的故鄉那些脾氣古怪的老農的絮絮叨叨一樣親切,我不在乎他對我講了什么故事,因為我編造故事的才能決不在他之下,我欣賞的是他那種講述故事的語氣和態度。他旁若無人,只顧講自已的,就像當年我在故鄉的草地上放牛時一個人對著牛和天上的鳥自言自語一樣”26莫言:《用耳朵閱讀》,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年,第25-26 頁。[MO Yan, Yong erduo yuedu (Reading with Ears)(Beijing: The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 2012), 25-26.]。對莫言來說,初讀《喧嘩和騷動》給他帶來了一種文學觀念的解放,這部作品使他醍醐灌頂,他回望故土,找到了寫作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庫。后來他坦率承認自始至終沒有讀完《喧嘩與騷動》,但《喧嘩與騷動》對他文學經驗的喚醒產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上面所提及的《兩座灼熱的高爐——加西亞·馬爾克斯和福克納》一文中,莫言評析《喧嘩與騷動》時指出,“ 過去的歷史與現在的世界密切相連,歷史的血在當代人的血脈中重復流淌,時間象汽車尾燈柔和的燈光,不斷消逝著,又不斷新生著。”27莫言:《兩座灼熱的高爐——加西亞·馬爾克斯和福克納》,《世界文學》1986 年第3 期,第299 頁。[MO Yan,“Liangzuo zhuore de gaolu: jiaxiya maerkesi he fukena” (Two Searing Furnaces: Garcia Marquez and Faulkner), 299.]莫言參悟了福克納在該小說中所表現的時光流逝,過去和現在之間相互影響等主題,因此,他對《喧嘩與騷動》的理解非常精辟。他的《紅高粱家族》《豐乳肥臀》《生死疲勞》等小說中也同樣表達了對過去和現在相互關聯的思考。在該文中,莫言總結道,“去年一年,在基于上述認識的基礎上,我認為我的作品中對外國文學的借簽,既有比較高極的化境,又有屬于外部摹寫的不化境。”28同上。[Ibid.]“化境”是莫言在文學借鑒中最高層次的寫作追求,他希望自己能夠擺脫單純模仿的局限,達至入乎其內、出乎其外的境界。
趙玫對福克納的喜愛是從閱讀《喧嘩與騷動》開始的,“我是一字一句地讀完這本書的,之后隨手即可翻到我想要找到的任何章節。閱讀中總有血液在燃燒的那種陌生而又令人悸動的感覺。我對這本書偏愛到一種固執,甚至心懷某種宗教感”29趙玫:《趙玫文化隨筆 美利堅夜空中最輝煌的星座》見《世界文化》2015 年第3 期,第3 頁。[“Zhao Mei wenhua suibi Meilijian yekong zhong zui huihuang de xingzuo”(Zhao Mei Cultural Essays:The Most Brilliant Constellation in the Night Sky of America.), Shijie wenhua (World Culture) 3 (2015): 37.]。她感到幸運的是一開始寫作時就讀到了福克納的《喧嘩與騷動》,她對藝術的探索因之受到了福克納較大的影響,她認為,福克納“在藝術的表現方面,他無疑是一個更具探索精神的大膽的嘗試者。《喧嘩與騷動》堪稱福克納意識流小說的登峰造極之作”30趙玫:《靈魂之光》,鄭州:河南文藝出版社,2002年,第7頁。[ZHAO Mei. Linghun zhi guang (The Light of the Soul)(Zhengzhou: He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2), 7.]。后來在其隨筆《一本打開的書》中,她重申了此書對于她的意義,“我再度傾述這本書之于我的生命的重要性。這里沒有一絲夸張。我確實一直視這本書為生命的一部分。那很重要的部分。我最早讀這本書的時候,已經是1986年。不那么早了。但我卻在那個時刻震顫起來,我感覺得到那種身體的抖動。幾乎周身的血液都在沸騰”31趙玫:《一本打開的書》,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94 年,第111 頁。[ZHAO Mei, Yiben dakai de shu (An Open Book) (Shenyang: Chunfeng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994), 111.]。她還用詩意的語言具體描述了對這部小說的印象和體悟,“《暄嘩與騷動》是一首憂傷而殘酷的長詩。關乎靈魂的。有點像黑人的靈歌。那種藍調。其中最著名的描寫,是昆丁在自殺之前,面對河水所聽到的那清晰的催促著生命的表的嘀嗒聲,以及白癡班吉的囈語。在隨時轉換的時態中,他深懷悲哀。昆丁自殺前的那段意識流的描寫堪稱經典。表針走動的聲響。河水。望著河水。日期的行進。河水的光反照上來。意識中愛情的始于凱蒂。無以解脫的亂倫的折磨。最終解脫。跳下去。亦是唯一的結局。從此世間不再有昆丁。福克納就是以這種流水的意緒,解釋了一個愛情和精神追求者崩潰的全部過程”32趙玫:《趙玫文化隨筆 美利堅夜空中最輝煌的星座》,第37 頁。[“Zhao Mei wenhua suibi Meilijian yekong zhong zui huihuang de xingzuo”(Zhao Mei Cultural Essays:The Most Brilliant Constellation in the Night Sky of America.), 37.]。在此,趙玫解讀了小說中的一個經典片段,即昆丁自殺前在河水旁意識的流動,分析了鐘表和流水兩個意象所指向的時間和死亡,把昆丁對凱蒂的那種含混、復雜的情感以及由此走向的毀滅做了深度剖析,盡管其中對昆丁情感的解讀有某種程度的誤讀,事實上,昆丁所要守護的是凱蒂的貞潔,即南方傳統文化的象征,他對她的情感不是一種愛情。
閻連科在與文學博士梁鴻的對話錄中,特別談到了他對福克納不同作品閱讀和接受的情況,“我至今沒有看完《喧嘩與騷動》,而他的《八月之光》、《熊》、《我彌留之際》,我卻看得津津有味。為什么沒有看完《喧嘩與騷動》,我卻說不清,不知道為什么。”33閻連科 梁鴻:《巫婆的紅筷子:作家與文學博士對話錄》,沈陽:春風文藝出版,2002年,第95-96頁。[YAN Lianke and LIANG Hong, Wupo de hongkuai: zuojia yu wenxue boshi duihualu (The Witch’s Red Chopsticks: Dialogue between an Author and Doctor of Literature) (Shenyang: Chunfeng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2), 95-96.]閻連科認為其中存在著契機,“有時候,一部好的作品與作家產生碰撞是需要契機的,尤其那種靈魂的碰撞,是需要靈魂溝通的契機。如果有了這種契機,可能你讀幾頁、甚至幾行就使你領會了他作品的全部。之所以你還要把他的作品繼續讀下去,僅僅是為了證明那種契機、溝通的正確”34同上,第96頁。[Ibid., 96.]。從中可以看出,一部作品和作家的相遇既是一種緣分,更是一種心靈的碰撞和溝通。
余華則對《我彌留之際》的結尾印象深刻,在《永存的威廉·福克納》的一文中,他稱道:
就像《我彌留之際》里那一段精彩的結尾——
“這是卡什、朱厄爾、瓦達曼,還有杜威·德爾,”爹說,一副小人得志、趾高氣揚的樣子,假牙什么一應俱全,雖說他還不敢正眼看我們。“來見過本德侖太太吧,”他說。
余華在文中直接引用了上述《我彌留之際》結尾的段落,認為福克納寫的精彩篇章讓“我們著迷”,并指出“它們之所以精彩是因為它們其實就是生活。”35余華:《永存的威廉·福克納》,見《環球時報》編輯部編:《二十世紀外國文學回顧——〈環球時報〉國際文化備忘錄》,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第53頁。[YU Hua, “Yongcun de weilian fukena” (William Faulkner Forever), in Ershi shiji waiguo wenxue huigu: huanqiushibao guojiwenhua beiwanglu (Review of Foreign Literature in the 20th Century: Global Times International Cultural Memorandum), ed. Global Times Editorial Office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2001), 53.]由此可見,余華對《我彌留之際》這部作品了熟于心。
在《八位作家和二十四本書》一文里,呂新將《喧嘩與騷動》《我彌留之際》《百年孤獨》《魔山》《乞力馬扎羅的雪》等世界文學名作稱為“不朽的峰巒”,并且重點評析了福克納的上述兩部作品,他認為福克納在《喧嘩與騷動》把“廉恥與懷疑像南方潮濕的龍舌蘭一樣時刻交織、攀援在他的意識里。有時,即使面對迪爾西這樣的女人時,他也不免會感到拘謹。為什么?因為他成功地將人格與偉大的尊嚴賦予了她。”而在分析《我彌留之際》時,呂新又指出,“從本德侖到他的女兒杜威德爾,甚至小兒子朱厄爾,又無一不在用各自的生命印證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個痛苦: 被侮辱與被損害的。”36呂新:《八位作家和二十四本書》,《花城》1998 年第3 期,第51 頁。[LV Xin, “Bawei zuojia he ershisiben shu” (Eight Writers and Twenty-Four Books), Huacheng (Flower City) 3 (1998): 51.]因此,呂新對福克納的上述兩部重要代表作的理解非常透徹,他洞察了福克納小說所書寫的南方特質以及不同人物的精神內核。
阿來似乎也很偏愛《我彌留之際》,他說:“其實我寫小說最早受的是《魚王》的作者阿斯塔菲耶夫的影響。當然,在不久之后,我就改變了我的‘精神之父’,但每一個作者的影響,換言之,對每個作家的喜歡都是階段性的。我不認為海明威的長篇小說寫得多么出色,我喜他《亞當·尼克斯故事集》以及《屹力馬扎羅之雪》這樣的短篇。再后來,喜歡福克納,他的《喧嘩與騷動》固然有特點,但更震撼我的卻是《我彌留之際》。”37冉云飛、阿來:《通往可能之路——與藏族作家阿來談話錄》,《西南民族學院學報(人文社科版)》1999年第5期,第10頁。[RAN Yunfei and A Lai, “Tongwang keneng zhilu: yu zangzu zuojia alai tanhualu” (The Road to Possibility: A Conversation with Tibetan writer A Lai), Xinan minzu xueyuan xuebao (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5 (1999): 10.]《我彌留之際》看似荒誕不經卻直抵真實人性的寓言性書寫,在新時期作家心中喚起了強烈的情感共鳴,所以得到了諸多作家的關注。
《獻給愛米麗的一朵玫瑰花》是福克納最具代表性的一部短篇小說,自1930 年4 月發表在《論壇》雜志上以來,引發了持續關注。小說從愛米麗的死亡寫起,借兩代人的回憶表現了愛米麗身處社會轉型時期的精神異化狀況,成為福克納探討新與舊,傳統與現代關系的經典之作。
蘇童非常欣賞福克納的這部短篇名作,因為《獻給愛米麗的一朵攻瑰花》與他喜愛的《傷心咖啡館之歌》“讀來有息息相關之氣”,并且他認為后者可能借鑒了前者,“從寫作時間上推斷,《傷心咖啡館之歌》有可能是受了這一朵‘玫瑰’的影響,但這不是我要探討的問題,我一直想努力和讀者一起弄清楚的是:一部好小說的外部動力可不可以是二流的甚至不入流的小說?眾多熱愛福克納的人會下意識地反問,為什么把低級的哥特式小說與偉大的福克納相比呢?我打賭這不會是福克納先生本人的反應。最優秀的作家在寫作上可能是最民主的最無成見的,不恥下問不僅是人生態度也是一種藝術態度。”38蘇童選編:《影響了我的二十篇小說·外國卷》,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5 年。[SU Tong, ed., Yingxiang le wode ershipian xiaoshuo· waiguojuan (The Twenty Novels That Have Influenced Me: Foreign Volume) (Tianjin: Baihua Literary and Art Press, 2005).]在此,蘇童似乎認為哥特小說屬于“低級”藝術形式,其實,哥特小說是美國文學的一個傳統,哥特小說也并不必然就是“低級”的。相反,哥特元素的巧妙運用會凸顯小說的特色。蘇童還把《獻給愛米麗的一朵攻瑰花》這部短篇經典之作和福克納的長篇小說做了進一步比較,“《玫瑰》區別于福克納其他波瀾壯闊深刻沉重的長篇巨制,顯得那么精致易讀,在我看來,與其說他借助了哥特式小說陰沉怪誕的敘述氣氛,不如說是這類小說中人物推開沉重大門的動作給了他非凡的靈感,于是他在短短的篇幅中完成了兩個推門動作,一扇門是愛米麗小姐居住的破敗宅屋的塵封之門,還有一扇門是愛米麗小姐的內心之門,這么直接,這么精妙絕倫,我們最后看見的是比《傷心》的結尾更加驚人的場景,看見愛米麗小姐塵封四十年的房間,死去多年的情人依然躺在她的床上,看見‘一綹長長的鐵灰色頭發’,愛米麗小姐其實也是躺在那兒的,她的內心一直孤獨地躺在那兒,是一顆世界上最孤獨的女人之心。讀哥特式小說是要讓你害怕的,《獻給愛米麗的一朵玫瑰花》當然也讓人害怕,不過由于圣手點化,恐懼不是因為恐懼引起,是為了一種尖銳的孤獨和悲傷”39同上。[Ibid.]。蘇童通過對愛米麗兩個推門動作的細致解讀,揭示了愛米麗對愛情的堅守和決絕以及深藏于內心的孤獨和悲傷,他對此細節的精辟闡釋講透了此小說的巧妙、深邃之處。
趙玫則直接把《獻給愛米麗的一朵玫瑰花》寫到了她的小說里,“女人在說著這些的時候并不知道還有一位叫福克納的美國作家,更不知道還有一篇叫做《獻給愛米麗的玫瑰》的小說。那是女人后來才知道的故事。在曼菲斯。一個富家的老姑娘為了永遠占有一個男人而殺了他。讓他被風干的了尸體永遠在床上陪伴著她。直到她自己也已經死去。女人不知道福克納筆下的這個因愛而殺人的殘酷的故事。如果男人不再屬于她,她就會殺了他的想法是女人自己的。是她真實的愿望。她于是才會把他們之間的關系總是攪得像風暴一樣。席卷而來連天和地的位置都顛倒了,連世界都瘋狂地翻轉了。”40趙玫:《愛一次,或者,很多次》,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2006 年,第16 頁。[ZHAO Mei, Ai yici, huozhe, henduoci(Love Once, Or Many Times) (Chengdu: Sichu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6), 16.]因對福克納的小說非常熟悉,趙玫把愛米麗的故事水乳交融地搬進了自己的小說里,她試圖以此來分析愛在女人情感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女人為了愛不顧一切去占有所釀成的悲劇。
除了《喧嘩與騷動》之外,莫言還很欣賞福克納的短篇小說《公道》的結構藝術,在1985年前后,莫言讀到了福克納這篇小說。此后,他把它列為對自己影響最大的10部短篇小說之一,并選入《鎖孔里的房間 影響我的10 部短篇小說》一書里。在此書的前言,他專門寫了一篇評析性文章,對10部短篇小說一一做了介紹,“福克納是許多作家的老師,當然也是我的老師。他肯定不喜歡招收一個我這樣的學生,但作家拜師不須磕頭,也不須老師同意。福克納的這篇《公道》在他的短篇小說里并不是最有名的,我之所以喜歡它并要向讀者推薦,是因為這篇小說的結構。福克納的長篇和中篇大都有一個精巧的結構,但他的短篇不太講究結構,《公道》是個例外,《獻給愛米麗的玫瑰花》當然也不錯,但我認為不如《公道》巧妙。他用一個孩子的口氣講述了孩子聽爸爸莊院的傭人山姆·法澤斯孩童時代從他的父親的朋友赫爾曼·巴斯克特那里聽來的關于他的父親和他的母親等人的故事,所謂的小說結構的‘套盒術’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個結構就是福克納歷史觀的產物。小說中關于爸爸與黑人斗雞、與黑人比賽跳高的情節富有喜劇性而又深刻無比,就像刻畫人物性格的雕刀”41莫言:《鎖孔里的房間——影響我的10部短篇小說》,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99年,第6-7頁。[MO Yan, Suokongli de fangjian: yingxiang wode shibu duanpian xiaoshuo (The Room in the Keyhole: The 10 Short Stories That Have Influenced Me) (Beijing: New World Press, 1999), 6-7.]。莫言從中領悟到了此短篇小說在藝術結構上的別具一格,并且歸納了“套盒術”形式特點所折射的福克納的歷史觀以及獨特的喜劇性情節,莫言對此小說的“發現”和評析具有一定的開創性。
由上觀之,福克納對中國新時期文學的影響從20 世紀七十年代末開始一直持續到新世紀的當下,他的影響是持久而深遠的。中國新時期作家基于自己的經歷和閱讀視野,對福克納的接受既有一些共性的感悟和理解,又存在著不同的闡釋視點和偏好。其中一個焦點問題為:福克納是如何促進新時期小說發生的?下文將具體展開分析。
三、福克納與中國新時期小說的發生
新時期文學面臨的兩個核心議題為“寫什么”和“如何寫”的問題,而福克納對新時期作家的重要影響集中體現在以下的兩個方面: 其一,福克納“約克納帕塔法”世系小說對新時期“尋根文學”的發生起了催化劑的作用,對其立足一方水土,在地域和民族文化的尋根和省思等層面上均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其二,福克納作品中的象征隱喻、多角度敘述 、意識流以及時空倒置等現代派藝術表現形式對新時期“先鋒文學 ”的發生同樣起了催生的作用,特別是他的小說在語言表達、感覺訴諸、意識流敘事、多角度敘述等方面對渴望突破和創新的中國新時期作家解決如何寫的問題提供了借鑒的摹本,從而對新時期小說的文體革新產生了重要影響。
(一)福克納與新時期“尋根小說”的發生
福克納多次提及他虛構的“約克納帕塔法天地”,他也因描寫這塊“像郵票那樣大小的故土”而蜚聲世界文壇。福克納的“約克納帕塔法天地”為諸多中國作家所熟知,它喚醒了中國新時期作家的創作主體意識,不但促生了新時期“尋根文學”思潮,而且對韓少功、莫言、蘇童、賈平凹、阿來、鄭萬隆等中國新時期作家聚焦鄉土中國一方水土的書寫起了引領作用。
1985 年韓少功率先在一篇綱領性的文章《文學的“根”》中指出:“文學有根,文學之根應深植于民族傳統的文化土壤中。”他在2013 年發表的《文學尋根與文化蘇醒》一文中,進一步闡釋了文學尋根所包孕的“本土文化”與“現代文化”之間的辯證關系,“事實上,‘尋根’不僅是一個文學的話題,也是影響遍及一切文化藝術領域的話題,其要點是我們如何認識和利用本土文化資源,并且在這一過程中有效學習包括西方在內的全人類一切文明成果,投入現代人的文化創造。”42韓少功:《文學尋根與文化蘇醒——在華中師范大學的演講》,《新文學評論》,2013 年第1 期,第7 頁。[HAN Shaogong, “Wenhua xungen yu wenhua suxing zai huazhong shifan daxue de yanjiang” (Literary Roots and Cultural Awakening: Lecture at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Xin wenxue pinglun (New Literature Review) 1 (2013): 7.]有鑒于此,筆者認為,“尋根不僅涉及到‘新’與‘舊’的問題,在全球文化語境下,還關乎到‘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以及如何面對多種文明之關系等命題”43李萌羽、溫奉橋:《威廉·福克納與中國新時期小說的文化尋根》,《山東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1 期,第45 頁。[LI Mengyu and WEN Fengqiao, “Weilian fukena yu zhongguo xinshiqi xiaoshuo de wenhua xungen”(William Faulkner and the Seeking of the Cultural Roots of Chinese Novels in the New Period), Shandong shifan daxue xuebao(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1 (2019): 45.]。韓少功給出的答案是“在我的理解中,中西文化從來都不是一個非此即彼的關系,恰恰相反,是一個相得益彰的關系,互相激發和互相成就的關系。”44韓少功:《文學尋根與文化蘇醒——在華中師范大學的演講》,《新文學評論》,2013 年第1 期,第7 頁。[HAN Shaogong, “Wenhua xungen yu wenhua suxing zai huazhong shifan daxue de yanjiang” (Literary Roots and Cultural Awakening: Lecture at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7]
韓少功的《爸爸爸》被視為新時期尋根文學的代表作,盡管韓少功沒有直接提及他所受到的福克納的影響,但在這部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它與《喧嘩與騷動》以及《我彌留之際》的“相得益彰的關系”。丙崽智力低下,如《喧嘩與騷動》中的智障兒班吉一樣,是一個弱智者,其身體上和精神上處于停滯生長的反常規的狀態。韓少功通過對湘西雞頭寨落后、畸形、僵化文化的書寫,隱喻了他對民族文化劣根性的反思。丙崽和班吉都被塑造成智障兒的形象,但又都被賦予了異于常人的稟賦 ,筆者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從一定意義上說,班吉是一個失去了語言和行動能力的‘耶穌’的象征,對充滿喧嘩與騷動的世界無力干預,只能發出沒有意義的嚎叫。丙崽也和班吉一樣沒有與外界溝通、對話的能力,但他又是唯一能‘看見’雞頭寨‘鳥’的圖騰的人,而且具有頑強的生命力,被賦予某種超自然的能力。癡呆和神諭、詼諧和神圣等對立因素在《喧嘩與騷動》與《爸爸爸》這兩部作品中也是奇妙并置,形成一種強烈的反諷效果。”45李萌羽、溫奉橋:《威廉·福克納與中國新時期小說的文化尋根》,第43 頁。[LI Mengyu and WEN Fengqiao,“Weilian fukena yu zhongguo xinshiqi xiaoshuo de wenhua xungen” (William Faulkner and the Seeking of the Cultural Roots of Chinese Novels in the New Period), 43.]而且筆者認為《爸爸爸》與《我彌留之際》亦可作為互文性文本來閱讀,兩部小說都寫了身處特定地域的人們所遭遇的種種磨難和失敗,不合常規的信仰和行為,在盲目無知的狀態下所犯的錯誤,所付出的沉重代價,以及他們面對挫折的勇氣和尊嚴,從此意義來說,他們的故事是人類的縮影。“盡管韓少功的《爸爸爸》與福克納的《我彌留之際》在題材和人物塑造上因中美文化的不同存在著很大的差異性,但在通過鄉土寓言性故事表現人類的失敗、墮落與莊嚴、責任之雜糅關系上又有著一定程度的相似性。”46同上。[Ibid.]
在中國新時期作家中,莫言常被歸為尋根派文學的代表性作家,特別是他創作的《透明的紅蘿卜》《紅高粱家族》《酒國》《豐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勞》《蛙》等以“高密東北鄉”為背景的作品,帶有鮮明的地域文化特色,而莫言“高密東北鄉”王國的建立,則直接受到了福克納“約克納帕塔法天地”的觸發。
在上文提及的《兩座灼熱的高爐——加西亞·馬爾克斯和福克納》一文中,莫言認為在創建 “高密東北鄉”的過程中,福克納和馬爾克斯給了他重要啟發,受兩位作家的影響,莫言立下了文學創作的整體性目標:“一,樹立一個屬于自己的對人生的看法;二,開辟一個屬于自己領域的陣地;三,建立一個屬于自己的人物體系;四,形成一套屬于自己的敘述風格。”47莫言:《兩座灼熱的高爐——加西亞·馬爾克斯和福克納》,見《世界文學》1986 年第3 期,第299 頁。[MO Yan,“Liangzuo zhuore de gaolu: jiaxiya maerkesi he fukena” (Two Searing Furnaces: Garcia Marquez and Faulkner), 299.]莫言的《紅高粱》可謂是一部踐行其創作理念,為其贏得了世界聲譽的作品,該小說發表于1986 年的《人民文學》雜志上,在日后談及《紅高粱》的創作時他特別強調了文學尋根的重要意義,“我贊成尋‘根’……每個人都有自己對根的理解。我是在尋根過程中扎根。我的‘紅高粱’是扎根文學。我的根只能扎在高密東北鄉的黑土里,我愛這塊黑土就是愛祖國,我愛這塊土地就是愛人民。”48莫言:《十年一覺高粱夢》,《中篇小說選刊》1986年第3期,第102頁。[MO Yan, “Shinian yijiao gaoliangmeng” (Ten Years is a Sorghum Dream), Zhongpian xiaoshuo xuankan (Journal of Selected Novelettes) 3(1986): 102.]莫言從此和福克納一樣,開啟了文學的尋根之旅。
1997 年,為紀念福克納誕辰一百周年,莫言受邀撰寫了《說說福克納老頭》一文,他談到十幾年前,買了一本福克納的《喧嘩和騷動》,他回憶道,首先讀了該書譯者李文俊先生長達兩萬字的前言,“李先生在前言里說,福克納不斷地寫他家鄉那塊郵票般大小的地方,終于創造出一塊自己的天地。我立刻感到受了巨大的鼓舞,跳起來,在房子里轉圈,躍躍欲試,恨不得立即也去創造一方屬于我自己的新天地”49莫言:《會唱歌的墻》,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年,第102 頁。[MO Yan, Hui changge de qiang (The Wall That Can Sing ) (Beijing: The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 2005), 102.]。莫言的上述一番話道出了《 喧嘩和騷動 》對他創造文學新天地的喚醒 ,正是受此激勵,他才把“高密東北鄉”作為自己文學寫作的原點,“我立即明白了我應該高舉起‘高密東北鄉’這面大旗,把那里的土地、河流、樹木、莊稼、花鳥蟲魚、癡男浪女、地痞流氓、刁民潑婦、英雄好漢……統統寫進我的小說,創建一個文學的共和國”50同上,第102-103頁。[Ibid., 102-103.]。對莫言來說,福克納的《喧嘩和騷動》給他帶來的最大啟發是從其“約克納帕塔法”天地中獲得了對“高密東北鄉”書寫價值的確認。
2000年3月莫言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萊校區發表的“福克納大叔,你好嗎?”的演講中,再次談到了1984年12月一個大雪紛飛的下午,他閱讀福克納的《喧嘩與騷動》的欣喜,“我一邊讀一邊歡喜”,“尤其是他創造的那個‘約克納帕塔法縣’更讓我心馳神往”51莫言:《用耳朵閱讀》,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第25頁。[MO Yan, Yong erduo yuedu (Reading with Ears), 25.]。“他的約克納帕塔法縣尤其讓我明白了,一個作家,不但可以虛構人物、虛構故事,而且可以虛構地理......受他的約克納帕塔法縣的啟示,我大著膽子把我的‘高密東北鄉’寫到了稿紙上......決心要寫我的故鄉那塊像郵票那樣大的地方。”52同上,第26頁。[Ibid., 26.]在以上三篇文章中,莫言多次強調福克納立足“約克納帕塔法”的書寫而蜚聲世界文壇對他創立“文學王國”的影響,他因此在尋根文學的浪潮中創造了一個獨特的“高密東北鄉”文學世界。
難能可貴的是,在莫言于80 年代中期創作了諸多優秀作品后,開始反思自己和外國文學的關系,創作主體意識不斷覺醒。一方面他樂于承認自己在文學創作探索的過程中所受到的福克納、馬爾克斯等國外作家的影響;另一方面,他又擔心一味借鑒模仿,靠這“兩座灼熱的高爐”過近,會被其融化,而喪失自我創作的個性,所以他試圖“逃離這兩個高爐,去開辟自己的世界!”53莫言:《兩座灼熱的高爐——加西亞·馬爾克斯和福克納》,《世界文學》1986 年第3 期,第299 頁。[MO Yan,“Liangzuo zhuore de gaolu: jiaxiya maerkesi he fukena” (Two Searing Furnaces: Garcia Marquez and Faulkner), 299.]他為此提出了“用想象擴展故鄉”的觀點,認為自己有超過福克納的地方,福克納的“約克納帕塔法”只是一個縣,他所創造的“高密東北鄉是一個開放而不是一個封閉的概念”,是他構建的一個“文學的幻境”,他甚至立下志向,“我努力要使它成為中國的縮影,我努力想使那里的痛苦和歡樂,與全人類的痛苦和歡樂保持一致,我努力地想使我的高密東北鄉故事能夠打動各個國家的讀者,這將是我終生的奮斗目標”54莫言:《用耳朵閱讀》,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第27頁。[MO Yan, Yong erduo yuedu (Reading with Ears), 27.]。
蘇童的創作也受到了福克納較大影響,他多次提到福克納的小說對其文化尋根的啟發,他坦言“細心的讀者可以發現其中大部分故事都以楓楊樹作為背景地名,似乎刻意對福克納的‘約克納帕塌法’縣東施效顰。”55蘇童:《〈世界兩側〉自序》,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3 年,第1 頁。[SU Tong, Shijie liangce zixu (Preface to Two Sides of the World) (Nanjing: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1993), 1.]他試圖通過對故鄉歷史的書寫,觸摸“祖先和故鄉的脈搏”,“看見自己的來處”,以及“自己的歸宿”,并認為創作這些小說,是他的一次精神的“還鄉””。56同上。[Ibid.]他還借用福克納的“郵票說”,認為一個作家一生能畫好一張郵票就足夠,但因為擔心自己畫不好,就畫了兩張郵票,他在立足“楓楊樹鄉”鄉土故鄉書寫的基礎上,又創造了一個 “香椿樹街”的城市地標,“香椿樹街和楓楊樹鄉是我作品中兩個地理標簽,一個是為了回頭看自己的影子,向自己索取故事,一個是為了仰望,為了前瞻,是向別人索取,向虛構和想象索取”57蘇童:《關于創作,或無關創作》,見《新華文摘》2009 年第22 期,第91 頁。[SU Tong, “Guanyu chuangzuo, huo wuguan chuangzuo (About Creation, Or Not), Xinhua wenzhai (Xinhua Digest) 22 (2009): 91.]。蘇童旨在拓展文學空間,用城鄉兩個空間進行對照性書寫,這亦是他對福克納的超越之處。
蘇童和福克納各自寫了中美文學里的南方,他們對各自的南方故土懷有既愛又恨的情感,蘇童與福克納一樣,在審視故鄉之根時也是帶著雙重的批判視角,既肯定了其中包孕的“善”,又批判了其蘊含的反人性的“惡”。在《飛越我的楓楊樹故鄉》中蘇童借助“幺叔”這一故鄉的“精靈”,頌揚了他所代表的自由、無羈、灑脫的精神,又在《1934 年的逃亡》《罌粟之家》等小說中通過陳寶年、陳文治、劉寶俠等人物剖析了楓楊樹故鄉所隱藏的封建、腐朽的必然走向潰敗的文化之“惡”根,這與福克納對舊南方善惡交織的文化因子的洞察具有很大的同構性。
阿來在訪談錄《阿來:文學即宗教》中明確表示對自己影響最大的是美國文學,他覺得“美國南方文學的代表當然是福克納”,阿來尤為強調他長期生活的世界獨特的地理特點與文化特性,這使他特別關注福克納等作家,“在這個方面,福克納與美國南方文學中波特、韋爾蒂和奧康納這樣一些作家,就給了我很多啟示。換句話說,我從他們那里,學到很多描繪獨特地理中人文特性的方法”58阿來:《阿壩阿來》,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04 年,第159 頁。[A Lai. Abei alai (A Bei A Lai) (Beijing: China Workers Press, 2004), 159.]。其作品《塵埃落定》受福克納的《喧嘩與騷動》與《我彌留之際》影響較大,在地域寫作、傻子視角敘事,特別是族群身份認同方面與福克納的作品有諸多相似之處。
阿來筆下的“嘉絨地區”同福克納作品中的“約克納帕塔法世系”一樣,都試圖借助家鄉的一隅呈現獨特的文學世界。盡管兩位作家處于不同的文化時空,但身份認同困境作為人類普遍面臨的生存境遇 ,成為了兩位作家創作的重要主題。福克納與阿來的作品均書寫了族群對抗中民族交往的隱痛記憶,福克納小說中的黑人與白人和阿來筆下的漢人與藏人之間都面臨著身份認同的困境,揭示了族群對抗的矛盾,認為文化的“圍城”和“疏離”會阻礙文化的認同,呼吁建立一種平等、互惠的族群關系。
鄭萬隆在《我的根》中特別談到從福克納、馬爾克斯等作家通過文學尋根而獲得的文學超越性啟示,“從本世紀二十年代起,或者說是從福克納他們那樣一批作家開始,他們想追求事物背后某種‘超感覺’的東西,也就是那些理想的內容與本質上的意義”59鄭萬隆:《我的根》,《上海文學》1985 年第5 期,第46 頁。[ZHENG Wanlong, “Wo de gen” (My Roots), Shanghai wenxue (Shanghai Literature) 5 (1985): 46.]。他希望自己也能同他們一樣,“企圖以神話、傳說、夢幻以及風俗為小說的架構”,在他的小說中“體現出一種普遍的關于人的本質的觀念”60同上,第45頁。[Ibid., 45.]。他創作了“異鄉異聞”系列小說,既表現了神秘的東北邊陲生活, 同時也展現了當地鄂倫春人的狩獵文化的原始、愚昧和殘酷,以探究鄉土之根的豐富性。樊星認為鄭萬隆的小說“努力去超越傳統的鄉土小說,去追求鄉土小說的現代感——人性內涵、神秘意味、象征底蘊”61樊星:《中國當代文學與美國文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年,第104 頁。[FAN Xing, Zhongguo dangdai wenxue yu meiguo wenxue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09), 104.],像鄭萬隆一樣,諸多新時期作家從福克納的鄉土性和現代性兩維書寫獲得了啟迪。
綜上,福克納的“約克納帕塔法”天地對新時期“尋根小說”在本土經驗的表達、地域文化的挖掘和反思以及文化根性的揭示等層面上產生了深刻影響,它以“世界文學”的視鏡激發了新時期作家的現代民族意識和尋根情結,使其認識到文學之根只有深植于民族文化傳統的土壤,并對其優劣進行現代性的審視和反思才能走向世界。
(二)福克納與新時期“先鋒小說”的發生
福克納作為20 世紀西方現代派文學重要的代表作家之一,其影響尤其體現在他在小說文體敘事上的革新帶給新時期作家的震撼,從而在深層次上激發了他們在文學觀念和藝術表現手法上的突破,這在新時期先鋒小說創作中表現得尤為顯著。
“先鋒”與現代性這一概念密切相關,甚至很多學者認為“先鋒派”即是現代主義,“先鋒”一詞不僅意味著一種前衛的藝術形式的變革, 而且標示著對社會文化變遷做出的超前敏銳反應,形式的革新服務于主題表達的需要。在新時期文學中,“先鋒小說”這一概念“是指那些與西方現代哲學思潮、美學思潮以及現代主義文學創作密切相關,并且在其直接影響之下的一批文學創作,其作品從哲學思潮到藝術形式都有明顯的超前性......”62李兆忠:《旋轉的文壇——現實主義與先鋒派文學研討會紀要》,《文學評論》,1989 年第1 期,第28 頁。[LI Zhaozhong, “Xuanzhuan de wentan: xianshizhuyi yu xianfengpai wenxue yantaohui jiyao” (The Revolving Literary World:Minutes of the Seminar on Realism and Avant-Garde Literature), Wenxue pinglun (Literary Review) 1 (1989): 28.]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中,先鋒派主要是指在20 世紀80 年代中后期崛起于中國當代文壇,以前衛的姿態進行文體形式探索的一種文學流派,代表性的作家有馬原、格非、莫言、余華、蘇童、葉兆言、北村、孫甘露等。
20 世紀20 年代以來,現代主義思潮在西方人類精神活動的各個領域延展,在歐洲文學界出現了喬伊斯、卡夫卡、艾略特、龐德、普魯斯特、薩特、加謬、尤奈斯庫等現代派作家。美國現代派文學則在二三十年代的“南方文藝復興”中達到高峰,福克納是美國現代派文學思潮中涌現出來的一位代表性作家。作為現代派小說文體實驗的探索者,福克納作品大量運用了象征隱喻、意識流、多角度敘述以及時空倒置等富有創新性的文學手法,豐富了傳統小說的表現形式,打破了傳統小說敘事結構的局限性,給讀者的審美想象帶來了全新的沖擊。特別是他的作品在語言表達、心理描寫、多角度敘述等方面對中國先鋒小說家解決如何寫的問題提供了有益的借鑒。正如馬原所坦言,“毫無疑問,喬伊斯們帶來了新的也有益的東西,他們影響了整個二十世紀,影響了包括我本人在內的許多中國作家。同時我們還應看到他們以后的一些大作家,他們一面承襲喬伊斯們的主張一面又盡力掙脫開來,福克納是最典型的例證,他身后還可以開出長長的一串名字。大作家們的優勢就在于他們審時度勢,不為時尚所障眼,對整個小說歷史沿革做到了然于心,自然也就有了明晰確切的價值準則。”63馬原:《小說密碼——一位作家的文學課》,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年,第9頁。[MA Yuan. Xiao shuo mi ma: yi wei zuo jia de wen xue ke (The Novel Cipher: The Literary Class of a Writer), 9]
福克納是一位在小說形式和寫作技巧上銳意創新的作家,瑞典科學院院士葛斯達夫·赫爾斯多來姆在授予福克納諾貝爾獎時所致頒獎詞中,對福克納在小說形式所做的探索給予了高度評價,他指出:“福克納是二十世紀的小說家中,一位偉大的小說技巧實驗家。他的小說,很少有兩部是相互類似的。他仿佛要藉著他那持續不斷的創新,來達成小說廣袤的境地。”64胡樹琨,譚舉誼等編:《諾貝爾文學獎全集縮寫本》,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1988 年,第380 頁。[HU Shukun and TAN Juyi, eds., Nuobeier wenxue jiang quanji suoxie ben (The Complete Works of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Nanning:Guangxi Nationalities Publishing House, 1988), 380.]其中,福克納作品中的意識流表現手法以及多角度敘事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福克納文體風格,對渴望突破和創新的新時期作家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新時期文學由外向內的轉向始于意識流敘事,“就敘事文學而言,新時期的敘事藝術革命是以‘意識流’這個舶來品為突破口的。站在文學發展意義的角度上,它則扮演了中國當代文學敘事藝術由外部社會歷史的描摹到對內部意識結構和復雜人性的抒寫的歷史性轉遞的角色。”65吳錫民:《意識流:轉遞中的中國當代文學敘事藝術之反省》,《江蘇社會科學》2003 年第2 期,第68 頁。[WU Ximin, “Yishiliu: chuandizhong de zhongguo dangdai wenxue xushi yishu zhi fanxing”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Reflections on the Narrative Art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in Transmission), Jiangsu shehui kexue (Jiangsu Social Sciences) 2(2003): 68.]從此意義來看,福克納等西方現代派作家對新時期小說文體敘事革命的影響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馬原認為小說其實就是一種由“作家本身的現實和幻覺交織”而成的想象,在本質意義上是一種虛構,主要體現在小說中的兩個關鍵性要素——時間和語言中。首先小說的時間是虛構的,特別是心理時間對物理世界的消解,這在福克納的作品中表現尤為明顯,對新時期小說時間敘事的變革影響甚大。其次是語言。語言可分為虛構的敘事語言和人物語言,特別前者,是小說的重要虛構因素。就語言的敘述而言,新時期作家敘述策略也發生了很大的轉向,由對外部客觀、寫實的第三人稱全知全能的敘事范式轉向了第一人稱內在、自我的主觀性傾訴。馬原以莫言的語言風格為例,特別分析了莫言的諸多小說與福克納的《喧嘩與騷動》語言風格的吻合性,他指出:“作家莫言的語言不是一種節制的語言方式,他是那種汪洋恣肆的。那么他在李文俊翻譯的《喧嘩與騷動》這個文本里面正好找到對應了,一瀉千里,奔騰浩瀚,正是他的風格,更重要的對他個人在那種方式里面找到一點呼應,使內心的情感找到一個出口。”66馬原:《小說密碼——一位作家的文學課》,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 年,第176 頁。[Ma Yuan. Xiao shuo mi ma: yi wei zuo jia de wen xue ke (The Novel Cipher: The Literary Class of a Writer), 176.]
福克納的重要作品 《喧嘩與騷動》《我彌留之際》《八月之光》《押沙龍,押沙龍》等均采用了復調意識流的創作手法,對同一個故事或事件,通過不同人物的意識流動和站在各自主觀立場的評判,達至一種多聲部意識流的交織、匯合與對話。《喧嘩與騷動》集中展現了凱蒂失貞給康普生家族的后代昆丁等所帶來的精神創傷。小說以康普生家族三兄弟的意識流構成主要內容延展的主線,三兄弟性格、智力和興趣各不相同,通過他們在不同的時間段內的心靈獨白講述了同一個故事,即凱蒂失貞帶給他們的情感反應以及心靈的影響,從而造成了一種不同的意識流疊加的效果。《我彌留之際》借講述美國南方農民本德倫為遵守對妻子的承諾,率全家將妻子的遺體運回家鄉安葬的“苦難歷程”,隱喻現代社會人性的墮落。此小說又進一步拓展了《喧嘩與騷動》三個人物意識流動的敘述主線,小說由本德倫家、鄰居及相關人員59 節內心獨白構成,用本德倫一家受難和墮落的故事映射人類共同面臨的苦難和人性的弱點。《八月之光》在三條平行的線索中展現了裘·克里斯默斯苦苦尋找自己身份的掙扎與毀滅;整個故事發生在十天的時間里,卻借助人物的意識流動往前延伸到過去時間中幾個人物的一生,甚至父輩祖輩的三代家史。時間在現在與過去之間逆流,不斷地前后跳躍和交織,形成了一個縱橫交錯、多聲部的復合體敘述結構形式。
趙玫認為與歐洲意識流作家普魯斯特、喬伊斯、伍爾芙等作家相比,福克納的意識流敘述手法更為立體、多元和深入,“他似乎已經不再滿足于那種線性的意識的流動,而是讓來自四面八方的不同人物的不同思緒不停地跳躍和轉換著。那是一種環繞著的流動的聲音,復雜的,模糊的,多元的,由此便造成了他小說中的那種非常獨特的立體的感覺。這無疑也是更接近生活的原生態的”67趙玫:《靈魂之光》,鄭州:河南文藝出版社,2002 年,第7 頁。[ZHAO Mei, Linghun zhi guang (The Light of the Soul), 7.]。在趙玫看來,福克納的意識流表現手法突破了歐洲意識流作家單線條的意識流敘述,而拓展為多線索、多元、意義不確定的復合意識流敘事,這些敘述聲音各自獨立,甚至相互對立,相互拆解,形成了巴赫金所言的眾聲喧嘩中的“復調對話”藝術特色。福克納的小說開辟了一種獨特的福克納式的意識流與多角度疊加敘述同一個故事的范式,如《喧嘩與騷動》《我彌留之際》《押沙龍,押沙龍》等小說中多個人物根據自己的情感立場、價值取向和各自不同的理解對同一個事件從不同的角度予以解釋、推測,作者完全站在局外人的立場上,讓作品中的人物站在不同的角度講述同一個故事。作品對于每個人講述的故事是否可信,不作評價,交由讀者來評定。作家的權威性評判在此被打破,福克納的小說讓筆下的人物發出不同的聲音,從而讓讀者在眾聲喧嘩中獲得對作品不確定意義的印象,并參與作品意義的重構。新時期作家對福克納的借鑒也正是基于此。
馬原的《岡底斯的誘惑》是新時期先鋒小說敘事探索和革新的一部重要代表作,這部作品包含三個故事,使用了多重敘述視角,帶有明顯模仿福克納多角度敘事的痕跡,并且形成了一種拆解式的敘事結構,首先,每一個故事都有一個敘述人,他們分別是姚亮、窮布和作為探險顧問的老作家,構成了小說故事敘述三個敘事視角。而小說有一個全知的作者敘述人貫穿始終,在每個故事之后將故事的謎底道破。此外小說中還有一個第一人稱敘述,但很快被置換為替代敘述人姚亮,而在第一個故事的結尾,全知敘述人卻反問: “天吶,姚亮是誰?”68馬原:《岡底斯的誘惑》,見《上海文學》,1985年第2期,第47頁。[MA Yuan, “Gangdisi de youhuo” (The Temptation of Gangdisi), Shanghai wenxue (Shanghai Literature) 2 (1985): 47.]在第三個窮布敘述獵熊和遇到野人的故事中,作家對全知敘述人 的講述予以了解構:“現在你們知道了,窮布遇到的是野人;也叫喜瑪拉雅山雪人。這是個只見于珍聞欄的虛幻傳說;喜瑪拉雅山雪人早已流傳世界各地,沒有任何讀者把這種奇聞軼事當真的。”69同上,第55頁。[Ibid., 55.]”綜觀整個小說,各個故事各自獨立但又串聯在一起,這種把作者、敘述者、人物糅雜混合多角度、變幻無窮的敘述方式 ,營造了撲朔迷離的情節線索,表現了西藏原始、 瑰麗的自然景觀、神秘莫測的文化以及復雜的人性。從此意義上來說,《岡底斯的誘惑》是當代小說敘事革命的一次有益嘗試。
應當指出的是,馬原在借鑒福克納多聲部敘事的同時,對其又有接受變異和創造性改制,如張學軍所分析,馬原的《岡底斯的誘惑》不斷變換敘述者,“這不禁令人想起了福克納的《喧嘩與騷動》”,“馬原顯然借鑒了這種敘述方式”,《岡底斯的誘惑》沒有讓不同的敘述人講述同一個故事,而是讓不同的敘述人分別講述不同的故事,這與福克納的小說敘述視角有一些不同,后者更多設置了人物的獨白,讓不同人物敘述同一個故事。70張學軍:《中國當代小說中的現代主義》,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47頁。[ZHANG Xuejun, Zhongguo dangdai xiaoshuo zhong de xiandaizhuyi (Modernism in Chinese Contemporary Novels) (Jinan: Shando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147.]而且馬原的小說經常有意凸顯作者的身份和聲音,“馬原總是讓隱含作者在敘述中隨意出入,這樣做一方面是用來彌補小說人物敘述的不足;另一方面是提醒讀者注意故事的虛構性,以此來消解傳統小說的所謂真實性”71同上,第148頁。[Ibid., 148.]。這也印證了之前馬原對小說“虛構”性本質的看法。
楊義認為敘事視角“是一部作品,或一個文本看世界的特殊眼光和角度”, 也是“一個敘事謀略的樞紐”72楊義:《中國敘事學》,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191 頁。[YANG Yi, Zhongguo xushixue (Chinese Narratology)(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7), 191.]。福克納等西方現代派作家在敘述學上所做出的突破性貢獻即為運用多種不同的視角進行多聲部敘述,而新時期作家如馬原、莫言、格非等受其啟發,進行了多元視角敘事革新實驗,并且把作者植入了文本中,對故事情節的真實性予以闡釋或消解,甚至與作品中人物展開對話,從而拓展了作品的審美意蘊 。
在新時期作家中,李銳也曾受到福克納較大的影響,他的長篇小說《無風之樹》在敘事形式上帶有對《我彌留之際》多角度意識流敘事明顯的借鑒。這部具有濃郁的山西呂梁山地域特色的鄉土小說在敘事形式卻采用了不同人物意識流獨白的形式,小說共分為63節,每一節都以一個人物作為觀察者、敘述者,與《我彌留之際》由15 個敘述者(包括七位家人和八位鄰居)意識流動推動故事進展的敘事結構具有類似性,可以看出李銳在文體敘事上對福克納小說藝術技巧的模仿,正如李銳所言,“我的《無風之樹》中以第一人稱變換視角的敘述方法,也是借鑒了福克納的。”73李國濤,成一等:《一部大小說——關于李銳長篇新著〈無風之樹〉的交談》,《當代作家評論》1995 年第3 期,第15頁。[LI Guotao and CHENG Yi, “Yibu da xiaoshuo: guanyu lirui changpian xinzhu wufengzhishu de jiaotan” (A Great Novel:a Talk about Li Rui’s New Novel The Tree Without Wind), Dangdai zuojia pinglun (Contemporary Writers Review) 3(1995): 15.]閻晶明指出《無風之樹》“主題意義上的豐富性和由豐富性所發出的深刻性,與作家的敘事方式的獨特有著直接關系”74同上,第14頁。[Ibid., 14.]。李銳進一步闡釋這種借鑒的意義在于,“在不同‘形式’的背后,其實更是不同視線的眼睛,更是對世界不同的表達,說到底更是不同的變化了的更復雜、更深刻的‘人’”75同上,第14頁。[Ibid., 14.]。這種多視角的意識流敘述模式對揭示人性的豐富性無疑具有較強的闡釋力。
青年作家雙雪濤的代表作《平原上的摩西》敘事結構亦受到福克納《我彌留之際》多角度意識流敘事的影響,文中特別提到小說中的主人公從圖書館借閱的10本書,其中一本即是《我彌留之際》,從中可以看出雙雪濤所受這部小說的影響,“雙雪濤寫作《平原上的摩西》,明顯地致敬福克納,借鑒《我彌留之際》的敘事手法,以多視角多聲道的獨白的混響,拼貼出一段從1990 年代到本世紀第一個十年間的東北往事”76柳青:《〈平原上的摩西〉:成功的改編 全新的創作》, 《文匯報》 2023 年2 月3 日,第6 版。[LIU Qing, “Pingyuan shang de moxi: Chenggong de gaibian quanxin de chuangzuo” (Moses on the Plain: A Successful Adaptation of a New Creation), Wenhui bao (Wen Hui Newspaper), February 3, 2023, 6.]。與《我彌留之際》相類似,《平原上的摩西》亦以主要人物的內心獨白作為敘述主線, 引領讀者進入人物的內心世界,從而增強了小說表達的張力。
結 語
盡管福克納生活的時代與中國的現實語境相隔甚遠,但其作品的超越性和輻射力卻一直延展至中國當下的文學。福克納作品中的意識流和多角度敘述對新時期小說的“文體革命”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從而內化為新時期小說多聲部敘事結構范式,深化了新時期文學的主旨意蘊。從此意義上來說,福克納對推動新時期文學文體的變革功不可沒。
就中國新時期文學觀念的變革而言,重新認識和解決文學創作中的“寫什么”和“怎么寫”是兩個核心的要素。福克納對新時期小說的發生產生了深遠影響。其“約克納帕塔法”文本對中國新時期小說的生成意義在于激發了新時期作家的現代民族意識和尋根情結,使其認識到文學之根只有深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才能達至對歷史、文化、人性、生命、性、欲望等普遍性主題的深度書寫。另一方面福克納意識流、多角度敘事范式對中國新時期小說由外至內的敘述轉向產生了重要影響。應該指出的是,中國新時期作家對福克納的借鑒并不是一味模仿,而是在接受中有主體性改造,從而創作出了兼具“中國氣派”和“世界性元素”的文學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