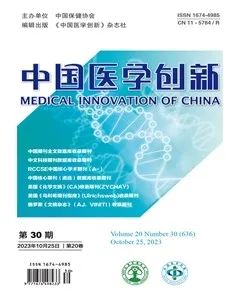乳腺癌放療抵抗機制的研究進展*
畢月
乳腺癌是嚴重危害女性身心健康的一種惡性腫瘤。近年來,乳腺癌發病率呈上升趨勢,且發病呈現出一定年輕化的態勢。目前,乳腺癌的治療方案以綜合治療為主,包括手術、化療、放療、靶向治療及內分泌治療等,其中放療發揮了重要作用。研究指出,乳腺癌患者術后輔助放療能夠顯著降低復發風險。雖然乳腺癌患者術后經過放療可以使得病情得到進一步控制,但是在治療過程當中出現的放療抵抗仍然是棘手難題。關于放療抵抗的發生機制目前尚未完全明確,大多數學者認為放療抵抗是多機制、多因子及多基因等共同作用的結果[1]。由于放療抵抗與乳腺癌患者的預后密切相關,因而及時了解放療患者的放療抵抗機制具有重要臨床價值。基于此,本文從腫瘤干細胞、自噬性調節及DNA損傷修復等多個方面進行了如下綜述,旨在為進一步的機制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1 腫瘤干細胞
1.1 腫瘤干細胞數量變化與放療抵抗的關系
研究指出,腫瘤干細胞與惡性腫瘤的發生及復發轉移密切相關[2]。腫瘤干細胞主要存在于乳腺癌、肺癌、胃癌等實體腫瘤當中,在治療惡性腫瘤時必須要盡可能清除腫瘤干細胞,以降低復發率。研究發現,相較于分化的腫瘤細胞,腫瘤干細胞的抗輻射性明顯增強,而且腫瘤干細胞數量越多,在同等輻射條件的情況下則抗輻射能力越高[3]。Ko 等[4]學者的研究發現,乳腺癌細胞的抗輻射能力與腫瘤干細胞的數量具有一定相關性,在放療抵抗細胞株RT-R-MCF-7 當中,特別是在高轉移性細胞株中,腫瘤干細胞的數量明顯增多;而且該研究亦發現,腫瘤干細胞可以通過內皮細胞黏附分子促進上皮間充質轉化,進而造成乳腺癌細胞的放療抵抗及侵襲性增強。
1.2 腫瘤干細胞與人表皮生長因子受體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HER2)亞型轉變的關系
HER2 靶向治療,如曲妥珠單抗等可提高HER2 陽性乳腺癌的無進展生存率和總生存率。值得注意的是,有回顧性研究表明,HER2 靶向治療也可能有益于HER2 陰性乳腺癌癥患者[5]。轉移性病變的HER2 狀態并不總是與原發性腫瘤的狀態一致。據報道,大約66%的患者原發灶和轉移灶的HER2 狀態一致,從原發性HER2 陰性腫瘤到HER2 陽性轉移性乳腺癌的分子亞型轉化率為9.7%,這表明原發性乳腺癌的分子亞型轉化發生在疾病進展過程中[6]。有學者研究發現,HER2 陰性乳腺癌細胞富集的CD44+/CD24-腫瘤干細胞介導了HER2的亞型轉變,表現出HER2 過度表達的放射抗性表型,這與放療抵抗的形成有關[7]。MCF7 人類乳腺癌模型已被證明是可靠的臨床前實驗模型,研究指出,CD44+/CD24-表型的表達可以作為乳腺癌患者DFS、OS 的潛在治療靶點,且CD44+/CD24-富集的MCF7 細胞具有更強存活能力[8]。HER2 陰性乳腺癌患者的腫瘤干細胞可促進HER2 介導的放療抵抗和分子亞型轉化,提高HER2 等放射抗性表型,進而導致放療抵抗發生。
2 自噬性調節
內質網應激是一種保守的細胞過程,細胞在應激條件下清除未折疊或錯誤折疊的蛋白質并維持細胞穩態。自噬可能是一種促進生存的策略,以應對腫瘤進展和遠處轉移中的多種應激條件。盡管許多研究表明輻射誘導的內質網應激與自噬之間存在密切相關性,但其分子機制目前尚不清楚。
2.1 c-Jun NH2-末端激酶(JNK)激活
輻射造成的內質網應激能夠引起細胞凋亡,這與未折疊蛋白反應信號轉導途徑被輻射誘導激活有關。研究顯示,輻射能夠誘導蛋白激酶樣內質網激酶及肌醇需求激酶1(inositol-requiring enzyme 1,IRE1)等內質網應激標志物蛋白的表達[9],X 射線能夠誘導內質網應激并激活兩個分支,即IRE1-JNK 和eIF2a-CHOP[10],造成細胞自噬及凋亡,進而促進MCF-7 細胞出現放療抵抗,抑制內質網應激誘導的自噬可能是提高放射治療對耐輻射乳腺癌療效的一種新策略。
2.2 缺氧誘導因子-1α( HIF-1α)異常表達
HIF-1α 是惡性腫瘤進展和惡性腫瘤靶向治療的關鍵轉錄因子[11]。過度表達的HIF-1α 及其下游基因通過多種機制促進惡性腫瘤進展,包括血管生成、細胞增殖和存活、代謝重編程、侵襲和轉移、腫瘤干細胞維持和治療抵抗。研究指出,低氧條件下乳腺癌MCF-7 細胞中的HIF-1α 表達水平顯著升高,放療抗性明顯提高[12];在敲低HIF-1α 表達后能夠對放療誘導自噬進行抑制,可以通過HIF-1/AKT/mTOR 通路提高MCF-7 細胞中放療誘導自噬的效果,從而使得HIF-1α 在乳腺癌患者放療抵抗的產生中發揮作用。
3 細胞周期調控
3.1 Ras 相關C3 肉毒桿菌毒素底物1(Ras-related C3 botulinum toxin substrate 1,Rac1)
Rac1 為Rho 家族的重要成員,與多種動態細胞生物學過程有關,包括細胞增殖、細胞存活、細胞-細胞接觸、上皮-間充質轉化、細胞運動性和侵襲性[13]。Rac1 缺陷減少了DNA 損傷檢查點反應,促進DNA 損傷修復,增加暴露于電離輻射和紫外線后的存活率。有研究指出,Rac1 在人乳腺癌細胞中高表達,其可增加乳腺癌細胞在放療后的存活[14]。Rac1 可以對核轉錄因子-κB、蛋白激酶B(protein kinase B,AKT)等信號通路活性進行調節,可提高細胞存活率,進而為改善乳腺癌放療患者臨床療效提供新的靶標。
3.2 轉錄激活因子3(activating transcription factor 3,ATF3)
ATF3 作為代謝和免疫調節因子的功能最近引起了人們的高度關注,ATF3 為轉錄因子家族重要成員,屬于適應反應基因的一種,在調節代謝、免疫和惡性腫瘤發生中發揮重要作用,而且多種細胞外信號如內質網應激、細胞因子、趨化因子和脂多糖等與ATF3 誘導有關[15]。在DNA 損傷劑、化療、細胞因子及缺氧等刺激下,ATF3 參與了細胞凋亡或者DNA 損傷的修復過程[16]。ATF3 過表達之后乳腺癌細胞的凋亡減少,使得G2/M 期細胞阻滯減少,從而激活了PI3K/AKT 信號通路,而ATF3 可以通過影響PI3K/AKT 信號通路中放療抵抗蛋白磷酸化蛋白激酶B 的表達,進而提高乳腺癌細胞放療抵抗能力;對ATF3 表達進行干擾之后能夠促進G2/M 期細胞阻滯,進而使得乳腺癌細胞放療抵抗能力降低。
4 上皮間充質轉化(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EMT)
EMT 是一種細胞程序,已知對胚胎發生、傷口愈合和惡性腫瘤進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EMT 過程中,細胞-細胞和細胞-細胞外基質的相互作用被重塑,這導致上皮細胞彼此分離和底層基膜分離,并且一種新的轉錄程序被激活以促進間充質命運。在惡性腫瘤發生的背景下,EMT 使癌癥細胞的致瘤性和轉移潛能增加,并對幾種治療方案產生更大的抵抗力。
4.1 α- 輔 肌 動 蛋 白4(alpha-actinin 4,ACTN4)激活AKT/GSK
ACTN4 是一種肌動蛋白結合蛋白,是細胞骨架結構蛋白的一員,與惡性腫瘤發生、染色體重塑、信號轉導及基因表達調控等密切相關,還可作為惡性腫瘤患者預后生物標記物[17]。有學者研究顯示,ACTN4 能夠直接提高MDA-MB-231 細胞侵襲能力及放射抗性[18]。糖原合成酶激酶-3β(glycogen synthase kinase-3β,GSK-3β)是AKT 的真核靶標,與上皮間充質轉化有一定關系。有學者在放療抵抗乳腺癌細胞MCF-7RR 當中發現,ACTN4 為AKT 途徑重要調節劑,可以激活AKT 及AKT 所介導的細胞存活;在提高p-AKT 的表達水平之后,MCF-7RR 細胞當中的p-GSK3β 表達水平也明顯提高[19]。GSK-3β 活化之后可以使得Snail 出現磷酸化,并促進了Snail 的降解,不過AKT 磷酸化能夠使得GSK-3β 活性降低,并提高Snail 的穩定性,進而促進上皮間充質轉化。ACTN4 可以通過提高AKT/GSK 活性的途徑促進上皮間充質轉化,進而參與乳腺癌放療患者的放療抵抗,作為放療抵抗潛在干預靶點具有一定臨床價值。
4.2 E-鈣黏蛋白(E-cadherin,E-cad)缺失
鈣黏蛋白屬于細胞黏附分子的一種,在細胞遷移及增殖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主要包括E-cad及N-鈣黏蛋白。Jiao 等[20]的研究發現,減少hsa_circ_0000745 通過上調E-cad 表達來抑制子宮頸癌中的細胞增殖、遷移和侵襲。E-cad 為細胞上皮的主要標志物之一,對其表達水平進行調控可以一定程度上影響放療抵抗。早期研究發現,在乳腺癌MCF-7 細胞中,當E-cad 濃度較低時則放療抗性更強;過表達E-cad 相對于低表達E-cad 的細胞,其放療的效果更加明顯[21]。因此,E-cad 低表達、不表達或者缺失促進了癌細胞放療抵抗,可能是上皮間充質轉化造成癌細胞出現放療抵抗的重要原因之一。
4.3 鋅指E 盒同源結合蛋白-1(ZEB1)異常表達
放療造成DNA 損傷,使得DNA 雙鏈斷裂,進而導致DNA 損傷反應。放療能夠誘導上皮間充質轉化相關轉錄因子及標志蛋白出現異常改變,在放療抵抗形成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高學忠等[22]的研究發現,沉默ZEB1 可以起到誘導乳腺癌細胞凋亡及抑制癌細胞增殖及阻滯細胞周期的作用。研究顯示,上皮間充質轉化能夠增強ZEB1 的表達水平[23]。ZEB1 為DNA 損傷反應以及放射敏感的調節器,將放療抵抗與上皮間充質轉化關聯在一起。乳腺癌SUM159-P2 細胞暴露于γ 射線電離輻射之后,共濟失調毛細血管擴張癥突變(ATM)激酶被激活,穩定ZEB1 并積極響應DNA 損傷而磷酸化,USP7 可以直接與ZEB1 互相作用,使得USP7穩定CHK1 及去泛素化作用得到明顯增強,促進了放療抵抗的發生[24]。ZEB1 表達水平上調之后可能會造成細胞周期檢測點激酶1(checkpoint kinase 1,CHK1)出現過表達的現象,可能導致放療抵抗的發生,并造成患者出現轉移復發,因而ZEB1 在上皮間充質轉化參與放療抵抗當中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4.4 遠端無同源盒基因2(distal-less homeobox 2,DLX2)表達
DLX2 在機體組織穩態、顱面發育及胚胎發育過程當中起到了關鍵作用,而且與惡性腫瘤患者的復發轉移、病情進展及預后相關[25]。研究發現,Smad2/3 參與了上皮間充質轉化的誘導過程,對細胞運動及間充質表型進行了調節,使得癌細胞遷移及增殖增強[26]。電離輻射能夠增強DLX2 基因的表達,而且DLX2 過表達后增加波形蛋白以及E-cad等包括上皮間充質轉化標志物的表達水平,進而增強了細胞遷移能力;在DLX2 表達降低之后,細胞放療的敏感程度明顯提高。Park 等[27]分析了DLX2在電離輻射誘導的非小細胞肺癌細胞放射抗性和CSC 特性中的作用,發現分批紅外線照射后存活的非小細胞肺癌細胞中DLX2 的過度表達與腫瘤干細胞、放射抗性、上皮間充質轉化、癌細胞存活和致瘤能力有關。
5 DNA損傷修復
5.1 整合素β1
整合素能夠對細胞外基質的結合進行介導,在乳腺癌患者呈現明顯過表達現象,并且與癌細胞遷移、增殖、放療抵抗及化療效果密切相關[28]。楊錢等[29]的研究顯示,過表達整合素β1 可以提高人乳腺癌細胞MCF-7 的遷移侵襲能力,并提高三苯氧胺耐藥程度,這與整合素β1 能夠提高上皮間質轉換通路活性,進而誘導細胞上皮間充質轉化相關。研究發現,過表達整合素β1 可以提高細胞同源重組的修復能力[30]。在細胞同源重組發生過程中,Rad51 起到了關鍵作用。癌細胞在經過電離放射處理之后,Rad51 表達水平顯著升高,使得乳腺癌細胞放射抗性得到增強,進而激活細胞同源重組及放療抵抗。
5.2 突觸核蛋白γ(synuclein-γ,SNCG)
SNCG 基因編碼γ-突觸核蛋白,該蛋白被認為是突觸核蛋白家族的第三個成員(α、β 和γ),與神經退行性疾病的發病機制有關[31]。SNCG 也稱為乳腺癌特異性基因1,在晚期乳腺癌組織中高度表達,SNCG 和胰島素樣生長因子1 受體在各種類型的腫瘤中相互調節,如乳腺癌、肝癌及結腸癌等,抑制SNCG 可能抑制胰島素樣生長因子1/胰島素樣生長因子1 受體誘導的細胞增殖和遷移[32]。在DNA損傷反應中p21 發揮了重要作用,SNCG 通過降低p53 信號傳導以及提高p21Waf1/Cip1的表達水平[33],進而使得放療抵抗性得到增強。
6 小結
乳腺癌是女性最常見的惡性腫瘤,具有高發病率及高轉移率等特征,嚴重威脅女性身心健康。放射治療是乳腺癌的主要治療手段之一,臨床效果滿意。然而,由于患者的放射敏感性存在差異,部分患者經放療后會出現放療抵抗現象,嚴重影響放療效果和預后,最終導致腫瘤復發和轉移,因此,放療抵抗是乳腺癌患者目前面臨的重大難題。積極探究乳腺癌放療抵抗的相關機制,如細胞周期調控及上皮間充質轉化等,以及尋找與乳腺癌放療抵抗相關的生物學標志物,為乳腺癌放療患者提供效能新干預靶點,對指導臨床患者的放療方案制訂、改善療效與預后均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