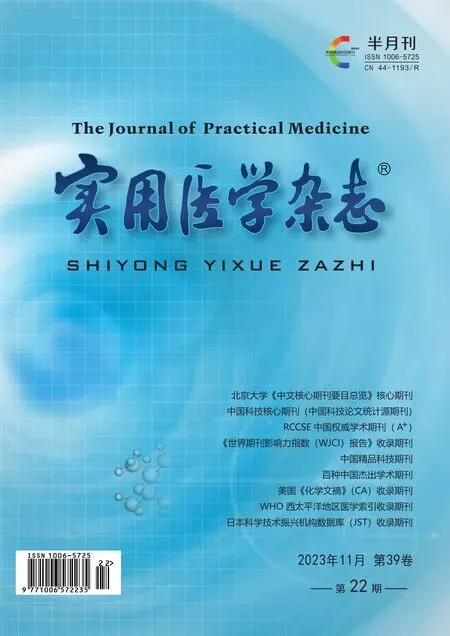DR-淚道造影術在淚道阻塞性疾病中的臨床運用價值
聶時淮 郭麗旭 劉詠 陳榮新
中山大學中山眼科中心、眼病防治全國重點實驗室、廣東省眼科視覺科學重點實驗室、廣東省眼部疾病臨床醫學研究中心 1放射科,2眼整形科(廣州 510060)
淚道阻塞性疾病是眼科臨床上的常見病,研究[1]表明原發性獲得性鼻淚管阻塞平均年發病率為30.47/10 萬,好發于中老年女性,病因尚未明確,有研究表明全身或局部激素水平的變化及其對下游產物的影響可能與原發性獲得性鼻淚管阻塞的發病有非常密切的關系。患者通常在40 歲以后出現溢淚,隨后出現慢性或急性淚囊炎的癥狀和體征,多由于鼻淚管狹窄或阻塞引起大量淚液蓄積在淚囊內導致。研究[2-12]表明,淚道阻塞性疾病可能與鼻淚管的解剖參數、竇口鼻道復合體解剖結構變異、鼻淚管損傷、抗青光眼藥物、性別、激素、眼表及鼻部的慢性炎癥等因素有關。患者可出現長期溢淚,伴隨黃色膿性分泌物增加,結膜充血的癥狀[13],嚴重者可致角膜潰瘍等有損視力的疾病,嚴重影響患者的生存質量。因此,其治療需要人為建立一個新的通道,保證淚液引流通暢。目前,臨床上該病的治療以手術為主,淚囊鼻腔吻合術是淚道阻塞性疾病的主要治療方式之一。由于先天發育或后天眼鼻相關病變導致淚道解剖存在個體差異,因此明確淚囊大小、形態、方向及淚道阻塞位置是手術成功的重要因素。數字X 射線攝影-淚道造影術(digital radiography-dacryocystography,DR-DCG)能為臨床提供強有力的影像學依據。為了解DR-DCG 在淚道阻塞性疾病中的應用價值,探討其對術前評估的指導意義,本研究對使用DRDCG 進行術前準備的913 例(1 129 眼)的影像學資料進行回顧性分析,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選取2019 年1-12 月因淚道阻塞性疾病在中山大學中山眼科中心就診的913 例患者(1 129 眼)作為研究對象。其中男95 例,女818 例;右眼351 例,左眼346 例,雙眼216 例;年齡4 個月至90 歲,平均(52.49 ± 17.05)歲。這項研究遵循了《赫爾辛基宣言》的原則,并獲得了中山大學中山眼科中心醫學倫理委員會的批準(編號:2023KYPJ237)。
1.2 檢查儀器與參數DR-DCG 使用德國西門子Siemens Ysio Maxs DR,雙板懸吊式數字X 線攝影系統,胸片架固定平板,床上移動平板DR 進行檢查。使用AEC 技術,曝光參數70 kV、攝影距離180 cm,劑量2.5 mGy,焦點1.0。
1.3 淚道DR-DCG造影劑采用37% ~ 41%的碘化油(注射前需排除碘過敏者),劑量0.3 ~ 0.5 mL/眼。淚道造影前常規進行淚道沖洗,清理膿性分泌物及淚液,避免影響造影結果。常從下淚小點進針(下淚小管不通時,選擇上淚小點)注入0.3 ~0.5 mL 碘化油。每例患者取坐位,于患眼側拍攝正、側位片或正、斜位片。見圖1。

圖1 DR-淚道造影示意圖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DR- dacryocystography
1.4 療效標準治愈:淚道完全通暢,溢淚等癥狀完全消失;未愈:淚道通暢明顯改善,溢淚等癥狀完全消失;好轉:淚道通暢明顯改善,溢淚等癥狀明顯改善;無效:淚道阻塞,溢淚無改善。
2 結果
2.1 淚道顯影情況在913 例(1 129 眼)淚道造影中,1 049 眼DR 圖像可見淚道引流系統內造影劑存留,971 眼(86.0%)顯影清晰,其中淚囊增大55 眼、正常438 眼、縮小478 眼;80 眼DR 圖像未見造影劑存留。
淚道阻塞共1 129 眼,根據DR 圖像將淚道阻塞分為淚囊前阻塞、鼻淚管阻塞、淚道狹窄,其中淚囊前阻塞80 眼,占7.1%,DR 圖像上可見淚小管或淚總管顯影,淚囊及以下淚道引流系統未見造影劑;鼻淚管阻塞971 眼,占86.0%,其中高位鼻淚管阻塞874 眼,低位鼻淚管阻塞97 眼,DR 圖像上可見淚囊清晰顯影;淚道狹窄78 眼,占6.9%,DR圖像上可見淚道引流系統完全或不完全顯影,可見造影劑存留。DR 圖像可顯示淚囊大小、位置情況,明確阻塞部位及狹窄程度。
2.2 術式選擇及治愈率913 例患者中,淚道引流系統阻塞826 例,占90.5%,淚道狹窄61 例,占6.7%,淚道炎癥25 例,占2.7%,淚點外翻1 例,占0.1%。見表1。

表1 913 例行DR-DCG 的患者臨床診斷Tab.1 Clinical diagnosis of 913 patients with DR lacrimal tractography
根據引起溢淚、溢膿癥狀的病因不同,個性化選擇手術方式,包括淚囊鼻腔吻合術(dacryocystorhinostomy, DCR)、結膜淚囊鼻腔吻合術(conjunc-tival dacryocystorhinostomy, CDCR)、淚囊切除術、鼻淚管成形術、淚小管成形/切開/吻合術、淚點切開術、淚道探通術等手術方式,治愈902 例,占98.9%,未愈僅2 例,臨床療效良好。見表2、3。

表2 913 例患者的治愈情況表Tab.2 Cure status of 913 patients

表3 913 例患者的手術情況Tab.3 Surgical conditions of 913 patients
3 討論
3.1 淚道阻塞性疾病治療現狀淚道阻塞性疾病是臨床上較常見的眼科疾病,常表現為持續性溢淚、流膿,擠壓淚囊區可見膿性或黏性分泌物、結石樣物質從淚小點溢出,嚴重者可出現淚囊區隆起形成淚囊囊腫,或導致急性淚囊炎,表現為淚囊區皮膚紅腫痛,促使患者有更迫切的就診以及改善的需求[14]。該疾病在淚道沖洗時可出現沖洗液反流、沖洗阻力增大、無法觸及骨壁的情況,提示臨床醫生淚道狹窄、淚道阻塞部位等情況。對于淚道阻塞性疾病,鼻淚道再通是治療過程中的關鍵,多年來治療方式的改良均在這一基礎上進行。
單純的淚道沖洗、淚道探通術,在操作上來說是簡易、經濟的,對于嬰幼兒淚道阻塞患兒來說,因為先天性淚道堵塞、排淚不暢、造成眼角不由自主流眼淚,同時可能還伴有眼皮紅腫等癥狀,治療上首選淚道探通術。有研究[15]表明,淚囊與鼻淚管之間存在角度,且整個操作是在非可視的基礎上進行的,在操作過程中極容易損傷淚道黏膜,形成假道,影響其他手術治療的療效。譚思敏等[16]的研究表明,激光淚道成形術聯合淚道支架置入術治療淚道阻塞療效顯著,但受淚道阻塞長度與直徑的影響,且術后需要增加淚道沖洗次數來確保療效。有研究者比較了淚囊鼻腔逆行插管吻合術和CDCR 在近段和中段淚道阻塞的成功率和并發癥發生率,發現兩者在治療近段、中段阻塞上的成功率是相似的,但CDCR 并發癥發生率較高[17]。DCR 經皮膚切口做造口建立引流通道,使淚液直接進入鼻腔,這一經典術式術后患者的面部可能遺留瘢痕。早期經鼻內鏡淚道系統的解剖學知識、內鏡外科技術經驗有限[18],但隨著內鏡技術的發展,鼻內鏡下DCR 得以開展,術前DR、CT 等影像學資料有助于術者了解鉤突、中鼻甲、上頜骨額突、篩竇等鼻淚管周圍結構的相對位置,在內鏡的幫助下,術者可在直視條件下進行操作,辨認鉤突、中鼻甲等結構,并根據淚道探針定位切開淚囊,保證不損傷眼輪匝肌、內眥韌帶等結構,且不遺留面部瘢痕等優點,使之成為目前大多數患者的首選。但對于初次接觸淚道阻塞性疾病的臨床醫生來說,如何在術中準確地找到淚道阻塞位置,以及如何確保已經完整的打開淚囊區,術前DR-DCG 圖像可以為其提供參考,通過判斷淚囊大小及明確的造影劑停留位置,可以為臨床醫生術中行手術操作提供依據。此外,對于患有干眼癥、因腫瘤阻塞導致的淚囊炎或反復發作的淚囊炎患者而言,有一種簡單、學習曲線較短的手術方式——淚囊切除術(DCT)[19]。
在本研究中,569 例患者選擇DCR 進行治療,占62.3%,上述術式均有患者選擇,且治愈率高達98.9%。目前有多種淚道阻塞性疾病的臨床治療方法,且都有其優缺點,術者在充分了解這些治療方法的適應證及禁忌證后,根據患者自身情況制定個性化治療方案,盡可能在降低并發癥發生率的同時恢復淚液引流通暢,在內鏡、生物材料及醫療器械不斷發展的輔助下,使得淚道阻塞性疾病的治療走向無痛、無痕、有效。
3.2 不同輔助檢查對淚道治療的應用價值為了更好地了解淚道阻塞性疾病患者的淚道系統情況及其與周圍組織結構的關系,許多研究者對超聲、CT-淚道造影術(computed tomography dacryocystography, CT-DCG)、MR-淚道造影術(magnetic resonance dacryocystography, MR-DCG)、淚道內窺鏡檢查、淚道造影術(dacryocystography, DCG)等在淚道疾病治療中的應用價值進行研究和比較。
超聲因其簡便、經濟、可反復操作的優點在眼科普遍應用,關于超聲診斷在淚道疾病中的應用,湯喜成等[20]利用超聲測量正常成人淚囊和淚道疾病患者的淚囊,得出超聲所測得的淚囊大小和形態與淚囊的實際大小基本一致,故在淚道疾病中可以利用超聲進行評估淚囊的大小及擴張程度。通過反射回來的超聲波成像后進行測量,但超聲的成像過程受到界面形狀、組織密度、聲波頻率等因素的影響,不穩定性較高,仍需進一步探索其對淚道阻塞性疾病的臨床應用穩定性。
CT-DCG 可以顯示淚道引流系統及其相鄰近的軟組織和骨組織結構,對于顱面外傷、淚囊腫瘤造成的復雜繼發性鼻淚管阻塞患者,CT-DCG 在術者行鼻內鏡下DCR 時,可以提供術中淚囊定位,使得手術以最大的安全性和精確性進行,從而降低并發癥發生率[21]。但患者在接受CT 檢查時受輻射劑量和時間較長,不能反復操作。
MR-DCG 與DR-DCG、CT-DCG 相比優勢在于:一方面可避免電離輻射,且沒有醫源性損傷淚小點的風險;另一方面,MR-DCG 無需注射黏性造影劑,可減少對黏膜的刺激,降低過敏風險。但是MR-DCG 會受到鼻淚管內黏液滯留的影響,導致錯誤診斷淚道阻塞部位,也不能提供淚道引流系統周圍軟組織和骨組織的信息,并且需要有經驗的眼科醫生和專門的內鏡設備[22]。此外,由于MRDCG 成本高、采集時間長及運動偽影的存在,使得其在基層醫院及中小型醫院開展較有難度[23]。
由于淚囊和鼻淚管均和鼻腔外側壁相毗鄰,武俊男等[24]通過解剖得到了經鼻內鏡下,鼻淚管-淚囊和周圍結構的解剖關系,淚道內窺鏡可以直觀地顯示淚道引流系統,正確診斷鼻淚管阻塞患者術前阻塞的部位,為在鼻內窺鏡下開展手術提供有用的信息,但同時淚道內鏡存在成本高和探頭不耐用的缺點。此外,有研究者表明MR-DCG 的檢查時間短于淚道內窺鏡檢查,且不需要局部麻醉和內鏡插管[22],說明淚道內窺鏡的舒適度較低。
DCG 和淚道內窺鏡均可以明確淚道阻塞部位,有研究者比較了淚道內窺鏡和DCG 檢查結果,發現DCG 在診斷部分或功能性淚道阻塞的靈敏度較低[25]。盡管如此,淚道內窺鏡的學習曲線較長,且受分辨率的影響使得新手醫生不能清楚辨認淚道走行,容易導致假道形成。對此,DR-DCG是一個簡便經濟的選擇,在所有DCG檢查手段中,DR-DCG在基層醫院的獲益是最大的。
在目前現有的關于淚道阻塞性疾病的輔助檢查方式中,淚道內窺鏡技術取得了一定進展,但影像學方法在部分阻塞和功能性鼻淚管阻塞等特定的適應證方面仍有用武之地。
3.3 DR-DCG 的目的及臨床應用價值由于現有的治療手段的適應證和禁忌證各有不同,所以淚道阻塞性疾病術前需要了解淚道引流系統的詳細情況,而DR-DCG 能為臨床提供強有力的影像學依據。為獲得顯影良好的DR 影像學資料,首先,先用生理鹽水將淚道內的分泌物基本清理干凈,再向淚道內注入碘化油,由于碘化油與周圍組織的密度不同,從而獲得形成鮮明對比的淚道引流系統DR 影像學資料。
借助DR-DCG,術者在術前可以獲得如下信息:(1)淚道阻塞的部位/淚道狹窄程度;(2)淚囊大小及其擴張度;(3)上頜骨、鼻骨是否骨折等。加之術前為避免鼻中隔偏曲、鼻息肉等鼻腔疾病對術中操作的影響,一般需于耳鼻喉科門診行鼻內鏡檢查。此外,若出現未顯影患者,在閱片的同時,需結合淚道沖洗情況及患者的情況做全面分析,通過觀察注入造影劑時淚囊周圍組織是否隆起、阻力是否過大,判斷是造影劑注入假道,抑或是造影劑未注入淚道,抑或是功能性溢淚。
3.4 DR-DCG 的局限性DR-DCG 能清楚顯示淚道情況,且具有簡便、經濟、直觀的優點,但無法顯示淚道引流系統與周圍骨性結構或軟組織的關系,因此,需要借助其他檢查手段才能排除淚道引流系統周圍的軟組織變化或骨骼異常導致的溢淚、溢膿癥狀。
目前DR-DCG 能在臨床上得以廣泛使用的原因如下:(1)能使術者清楚地了解淚道特點信息,對淚道系統疾病的診斷及治療提供強有力的臨床依據,為患者個性化的選擇手術方式,且為術中手術操作及預后評估具有臨床意義。(2)檢查時間較短、檢查費用較少,亦可準確判斷淚道阻塞部位、淚道狹窄情況、淚囊擴張度,臨床上可推廣應用于淚道阻塞性疾病患者。
【Author contributions】NIE Shihuai performed the conceptualization, methodology, writing-original draft preparation. GUO Lixu and LIU Yong performed the data curation. CHEN Rongxin revised the article. All authors read and approved the final manuscript as submit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