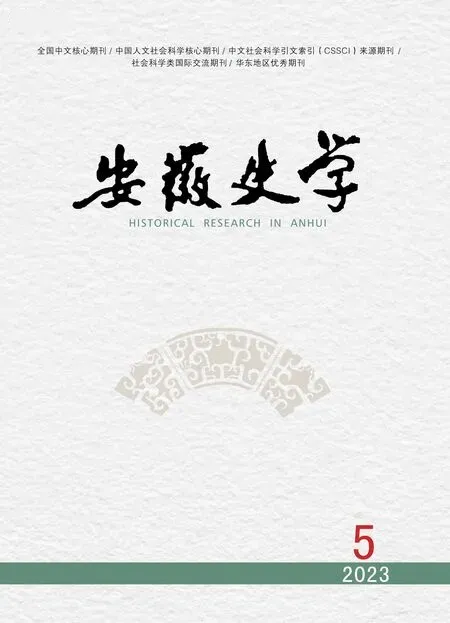明代品官誥敕的文本書寫
——基于明代家譜所輯誥敕文本的考察
江一方
(安徽大學 徽學研究中心,安徽 合肥 230039)
作為明代“圣旨”的一大類別,封贈不同品級的官僚以及世襲貴族,用以表明受封贈者在封建等級制度中地位(1)李福君:《明代皇帝文書研究》,南開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75頁。的誥敕文書歷來為學界所關注。最初是對一些誥敕原件進行介紹和考釋,進而從封贈制度、恤典制度、檔案辨析等角度對明代誥敕相關問題進行研究的成果亦較豐碩。但對于明代誥敕的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據萬歷《大明會典》,誥敕可授予品官及其命婦,亦可授予宗室、功臣、藩屬國國王、番僧等,但學界關注的多是文官的誥敕,且研究的主要依據是存世不多的誥敕原件以及封贈制度的相關記載,對其分類、行文的整理及共性把握有所欠缺,而對武官誥敕和其他類型的誥敕,也鮮有論及。此外,關于誥敕的書史功能以及史料運用,也尚未見有準確定位。誥敕的行文結構、行文特點,書史功能以及文本的可信度等均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明代誥敕原件散佚頗多,存世者藏地亦較為分散,為我們的研究制造了一定障礙。實際上,誥敕文本亦有其他形式的記載。如弘治《休寧志》、嘉靖《思南府志》等方志中即有本地士人所獲誥敕文本的輯錄,《高文襄公集》《許文穆公全集》等明人文集中亦收錄了一些誥敕文本。還有一些收錄或專門輯錄誥敕文本的古籍,如《尚書洪公榮哀錄》《畢氏四代恩綸錄》等。此外,更多的誥敕文本則被保存于家譜之中。存世明代家譜所輯誥敕大多為品官誥敕(以下簡稱“誥敕”),本文即以此為依據,并結合相關史料,對誥敕的文本書寫加以解讀。不當之處,敬請方家指正。
一、明代家譜所輯品官誥敕文書
明代家譜纂修發達,涵蓋誥敕的宸綸文獻成為家譜的重要篇章。這些誥敕文本來源于品官及其宗族庋藏、貯存誥敕原件的抄錄,“今但以家所珍藏誥敕頒于我明者,敬錄篇端”。(2)嘉靖《新安唐氏宗譜》卷上《唐氏恩榮錄》,明嘉靖十八年刻本。王世貞云:“家史人諛而善溢真,其贊宗閥、表官績,不可廢也。”(3)王世貞撰、魏連科點校:《弇山堂別集》卷20《史乘考誤一》,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361頁。因此,我們首先需要對明代家譜所輯誥敕的可信程度加以考訂和說明。相較家譜所輯其他文獻類型,誥敕的可信程度較高。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傳統王朝的官方制度規定。《大明律例》對包括誥敕在內“王言”的抄錄和傳播具有嚴格規定:“凡詐為制書及增減者,皆斬。未施行者,絞。傳寫失錯者,杖一百。”注解者云:“本無制書,假撰詞旨,謂之詐為;本有制書,更換詞語,謂之增減。以匹夫而擅天子之令,故已施行者皆斬。未施行者,為首,絞;為從,減一等。”(4)應朝卿校增:《大明律例(附解)》卷24《刑律七·詐偽·詐為制書》,明萬歷二十九年刻本。可見,明代詐為、增減誥敕文本均會受到極刑處置,抄錄失誤亦會受到處罰。此外,萬歷《大明會典》還規定,“凡寫完誥敕軸,類編勘合底簿。……用寶完備,收候每年終于御前奏過,送古今通集庫收貯。”(5)萬歷《大明會典》卷212《通政使司·中書舍人》,明萬歷十五年刻本。誥敕還具有底本留存、編號防偽的制度。
二是家譜的刊布過程不乏官府參與。從明代家譜實物和文獻記載可見,一些家譜的刊布均有官府介入。如天順二年刻《清華胡氏族譜》即鈐有“婺源縣印”,表明該譜的刊布經過了官府許可,其所輯誥敕自在審核范圍之內。歙縣等地方氏兩次修譜亦是如此:“前明成化四年,支裔方啟修成譜牒具呈本府,準給鈐印。正德八年,支裔方遠宜等會同編輯,呈請南畿戶部鈐印一百五十三顆。”(6)乾隆《歙淳方氏柳山真應廟會宗統譜》卷首《憲給印牒》,清乾隆十八年刻本。
此外,誥敕文本多會在社會上傳播。如江珍將其父母敕命勒石立碑,其文本與萬歷《蕭江全譜》所載完全一致。(7)該碑現藏歙縣博物館。碑文見萬歷《蕭江全譜》附錄卷1《贈江才為南京兵部車駕清吏司署員外郎配鄭氏為安人敕命一道》,明萬歷三十九年刻本。受誥敕者的名諱、散階、職官等亦多會輯入府、縣志的《封蔭》等節,部分方志還將誥敕全文一并輯入。
從時空分布上看,存世明代家譜最多的是徽州地區。據學者統計,現存明代徽州家譜至少有630種,已逾全國總數之半(8)祝虻:《現存明代家譜所輯文書論略——以徽州家譜為中心》,《檔案學通訊》2019年第4期。,浙江有百余部明代家譜存世(9)參見丁紅:《浙江家譜版本特征分析》,《圖書館理論與實踐》2006年第1期。,江蘇、湖南等省區亦有少量分布。存世明代徽州家譜開始輯錄誥敕的時間較早,嘉靖以前的《程氏貽范集》《陪郭程氏本宗譜》《婺源桃溪潘氏本宗譜》等均輯錄有誥敕文本。由于宗族聚居的特點和“東南鄒魯”“聚書千家,擇善而教,弦歌之聲,不弛晝夜”(10)潘潢:《樸溪文集》卷5《芳溪潘氏宗祠記》,明萬歷十三年刻本。的人文環境,出仕者與宗族之間關系密切,為家譜輯錄大量誥敕創造了條件。如正德甲戌(1514年)狀元唐皋所在的歙縣唐氏宗族,嘉靖年間所修譜牒輯錄了21道誥敕;“一門九進士,六部四尚書”的婺源潘氏宗族,崇禎年間所修譜牒中輯錄誥敕的數量更是多達62道;(11)嘉靖《新安唐氏宗譜》卷上《唐氏恩榮錄》;崇禎《婺源桃溪潘氏族譜》卷7、卷8《敕命、誥命、敕書、諭祭文》,明崇禎九年刻本。《靈山院汪氏十六族譜》《休寧范氏族譜》《蕭江全譜》等輯錄的誥敕亦在10道以上。(12)萬歷《靈山院汪氏十六族譜》卷10《典籍志》,明萬歷二十二年刻本;萬歷《休寧范氏族譜》卷7《大明誥敕符命制詞》,明萬歷三十三年刻本;萬歷《蕭江全譜》附錄卷1《恩綸》。目前所見其他地域輯錄誥敕的明代家譜刊刻時間略為滯后,但最遲至嘉靖年間,浙江家譜也輯錄了誥敕(13)筆者所見最早輯錄誥敕的存世浙江家譜為明嘉靖十九年刻本《陳氏增輯宗譜》,該譜輯錄有5道明代誥敕。,《山陰縣州山吳氏族譜》輯錄的誥敕亦有34道之多。(14)天啟《山陰縣州山吳氏族譜》卷首《誥敕》,明天啟刻本。此外,蘇州府的《古吳淀紫山徐氏世譜》等也輯錄有誥敕。這些家譜輯錄的誥敕文本具有集中性,修譜者多將誥敕與敕書、諭祭文等“王言”合為一類,列為單獨卷或單獨節,并根據誥敕文本中的信息設置標題,為我們查考相關資料提供了便利。通過對存世明代家譜所輯誥敕文本的考察,可以彌補現存誥敕原件的不足之處,從而整理出這一類文獻的行文結構和文本特點,對相關研究有所裨益。
二、明代品官誥敕的行文結構與文本特點
綜觀明代家譜所輯品官誥敕,可劃分為文官封贈誥敕、武官封贈誥敕以及追贈誥敕,五品以上為誥命,六品以下為敕命,存者稱“封”,歿者稱“贈”。各類誥敕均有其獨特行文結構和書寫規范,以下分別述之:
學者認為,明初的誥既是任命的文書,也是封贈的文書。(15)陳時龍:《明代詔令的類型及舉例》,《明史研究論叢》第8輯,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版。從家譜所輯明初文官誥敕中,亦能發現這一特征,洪武朝的誥敕文本,疑似將散階與職官一并授予文官,與僅授散階的后世誥敕文本區別較大,如洪武三年汪翔敕詞曰:“汪翔可授從仕郎、鳳翔府郿縣知縣”;洪武十九年汪仲魯敕詞曰:“茲特受(授)爾汪仲魯承務郎、左春坊左司直郎。”(16)隆慶《汪氏統宗正脈》卷15《鳳翔府郿縣知縣汪翔敕命》、卷12《翰林院左春坊左司直汪仲魯敕命》,明隆慶四年刻本。
宣德以降,文官封贈誥敕的行文結構趨于規范,按對象和功能又可再劃分為三類。一是授予文官本身散階的誥敕,行文句式大致為“制(敕)云云,具官某云云,進(授)某階云云,欽哉。”(17)一些宣德朝文官本身誥敕不用“進(授)某階云云”,而是在“具官某云云”前書寫其散階。如宣德元年胡永興誥詞曰:“爾奉議大夫、趙府長史司長史胡永興……茲特賁以寵章,錫之誥命。”參見萬歷《清華胡氏統會族譜》卷首《封長史胡永興誥》,明萬歷刻本。“制(敕)云云”書寫朝廷對文官所任具體職務的評價和認識,說明其職之重要性。“具官某云云”是對文官事跡的贊語,涵蓋其出身、德才、宦績等方面。“進(授)某階云云”則基于文官實職,授予相應品級的散階(如有兼官,散階以品級最高者為準),并對其履職加以期盼和勉勵。誥(敕)詞多以“欽哉”結尾(18)亦有少數誥敕省略“欽哉”,或使用表意相近的“懋哉”等語。如萬歷《休寧范氏族譜》卷7《江西建昌府南城縣知縣范淶并妻敕命二道》,崇禎《婺源桃溪潘氏族譜》卷8《刑部陜西清吏司郎中潘釴并妻誥命一道》等等。,亦有部分在誥(敕)詞后附有文官歷任官職信息。如弘治十一年蘄水知縣潘玨的敕詞曰:
奉天承運皇帝敕曰:“郡縣親民之政,非久不成,朝廷錫命之榮,惟賢是予。惟茲著典,實則茂恩。爾湖廣黃州府蘄水縣知縣潘玨,擢第甲科,分符劇縣,恤下式勞于撫字,持身克篤于慎勤。歷歲既深,薦章交至。宜頒寵渥,以示褒榮。茲特進爾階文林郎,錫之敕命。于戲!居官以盡職為賢,已徵嘉績,永譽以保終為善,勿替初心。尚有崇階,以需來效。欽哉。”(19)崇禎《婺源桃溪潘氏族譜》卷7《湖廣黃州府蘄水縣知縣潘玨并妻敕命一道》。
嘉靖九年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唐澤的誥詞曰: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我國家建都察院以重風憲之寄,崇紀綱之司。而副都御史實貳其長,必得剛直廉慎之士、識大體者以任之,始克有濟。爾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唐澤,發跡賢科,歷官中外,才猷茂著,累遷方伯,以至晉副都臺,經理邊務,為朕安民御侮,其功大矣。茲特進階通議大夫,錫之誥命,用示褒榮。爾尚益堅素志以樹風聲,務公激揚以勵庶官,庶副朕簡任之重。用終爾譽,光我訓詞。欽哉。”
初任直隸順德府平鄉縣知縣,二任刑部貴州清吏司主事,三任本部山西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四任本部江西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五任實授本司郎中,六任福建按察司副使,七任浙江按察司按察使,八任陜西按察司按察使,九任陜西布政司右布政使,十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十一任戶部右侍郎,十二任今職。(20)嘉靖《新安唐氏宗譜》卷上《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唐澤并妻誥》。
二是推恩文官父祖的誥敕,行文句式大致為“制(敕)云云,某云云,封(贈)某階某官云云”。此類誥敕中,父祖散階、職官多同于子孫,亦有“凡父職高于子者,依原職進一階。職卑者,從子官封”(21)萬歷《大明會典》卷6《吏部五·驗封清吏司·文官封贈》。的特殊情況。“制(敕)云云”書寫封贈父祖的理由,多闡述“盡忠榮親”“積善貽謀”道理,強調父祖應隨出仕子孫而顯。“某云云”書寫父祖與文官的親屬關系,以及對其生平的贊語。若父祖曾出仕,這一部分多側重宦績,若未出仕,則多描述德行。若父祖已有官職,則為“具官某云云”,書寫順序是原職在前,封(贈)官在后。“封(贈)某階某官云云”則書寫父祖應獲的散階、職官,并以一句話作結,若父祖已歿,此言多表達對逝者的哀榮和告慰;若在世,則多祝愿頤養天年,或垂范鄉閭等。如正德十六年陳好古誥詞曰: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祖之積善,慶必鐘于后人,臣之效忠,榮必及其先世。蓋天道可信,而報施之無差,肆禮制通行,而幽明之罔間。爾陳好古,乃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雍之祖父,心懷用世,學擅通經,積學德于一身,時稱嘉士,溯慶源于再世,卓有賢孫。顧其仕歷三朝,官聯八座,眷勛庸之茂著,舉渥典以初頒,百代其昌,九原益耀。茲特贈為通議大夫、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嗚呼!揚于王庭,丕著貽謀之美,告于家廟,永垂祝號之光。”(22)嘉靖《陳氏增輯宗譜》卷首《誥命》,明嘉靖十九年刻本。
嘉靖元年汪標誥詞曰: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子傳父業,允稱作述之賢,君錄臣功,特重褒嘉之典。義乃關乎激勸,清實遂其顯揚。爾云南按察司副使致仕汪標,乃兵部武選司署員外郎事主事溱之父,才識宏深,性資謹厚,起甲科而知巨郡,聲譽早彰,參戎幕而擢留曹,勤勞丕著。載受專城之命,尤稱理劇之能,惠澤著于碑祠,治狀傳乎紀頌。進遷憲職,坐鎮遐荒,輯眾安民,屹一時之保障,奉公守己,茂三事之操修。方柄用之有期,何求歸之益切。高風丕振,晚節能全,乃今甲第之英流,實為儒家之至訓。郎曹列職,名重班行,禮典推封,光增綸綍,被國恩之益厚,表慶之彌彰。茲特封為中憲大夫,職仍舊。于戲!儀刑丕著,式稱鄉黨之達尊,壽考未涯,益享庭闈之晚福。”(23)隆慶《汪氏統宗正脈》卷21《兵部武選清吏司主事汪溱父母誥命》。
此外,明代亦有“移封”的特殊情況,茲舉兩例:吳沔、江玄賜因子移封,敕文分別曰:“茲以覃恩移子之封,贈爾為登仕佐郎、鴻臚寺序班”(24)天啟《山陰縣州山吳氏族譜》卷首《誥敕》。,“茲移封爾為登仕佐郎、刑部司獄司司獄”。(25)萬歷《蕭江全譜》附錄卷1《封江玄賜為登仕佐郎刑部司獄司司獄敕命一道》。父祖的散階、官職在“封(贈)某階某官云云”中注明系移封所得。
三是推恩文官命婦的誥敕,行文句式大致為“敕(制)云云,某氏云云,封(贈)某階云云 ”。“敕(制)云云”亦是說明封贈的理由,多書寫敦睦人倫、朝廷榮親之意。“某氏云云”書寫命婦與文官的親屬關系,并表彰其事跡。若命婦曾受誥(敕)封,“某氏云云”為“封(贈)某階某氏云云”。“封(贈)某階云云”則基于文官品級授予命婦本等封階,嫡庶亦有區別。(26)萬歷《大明會典》卷6《文官封贈》曰:“婦人因其子封贈,而夫、子兩有官,亦從一高者”,“(弘治)十八年題準,凡當封贈母而父官高于己者,如系嫡母,照舊例從父之官,如系生母,止照子孫品”,如命婦因子、孫而受封,且其丈夫、公爹均已歿,則封階前加“太”字。誥敕文本亦以一句話作結,若命婦已歿,則寄予哀榮;若在世,則多寄希其延續“婦道”,或祝愿益壽延年等。如天順二年林氏誥詞曰:
制曰:“朕于任事之臣,既推恩于其親,而又榮及其配者,所以申恩典而厚人倫也。爾封孺人林氏,乃太仆寺卿程信之妻,柔順慈良,克敦婦道,因夫之貴,已受恩封,夫再進官,爾宜偕顯。特加封爾為淑人。祗服榮恩,永光閨壺。”(27)成化《程氏貽范集》甲集卷6《太仆寺卿程信授亞中大夫并封妻林氏淑人誥命》,明成化十八年刻本。
成化八年方氏敕詞曰:
敕曰:“孝子之愛親者,靡有存沒之間。故朝廷恩典必及之,所以體其心而重大倫也。爾方氏,乃四川道監察御史程宏之母,善著閨門,訓成其子。雖祿養弗逮,而恩所宜加。茲特贈為孺人。尚克承之,永賁幽壤。”(28)嘉靖《祁門善和程氏譜》附錄《封贈監察御(史)程宏父母敕命》,明嘉靖二十年刻本。
相較于文官封贈誥敕的種類、句式多樣,明代武官封贈誥敕的類型、結構則較為單一,多是本身、父祖、命婦共用一篇誥(敕)詞。該類誥敕文本可分為兩部分,前一部分為皇帝對武官的誡勉訓詞,以“奉天承運皇帝制曰”起始。筆者比較了洪武二十八年 “馬林誥命”、《程氏貽范集》所輯成化十年程佲夫婦誥命(29)參見杜承武:《明洪武二十八年“奉天誥命”和馬林夫婦雕像》,《文博》1988年第5期;成化《程氏貽范集》甲集卷6《直隸沈陽中屯衛指揮僉事程佲授明威將軍并封妻劉氏恭人誥命》。、《山陰縣州山吳氏族譜》所輯若干天啟年間武官誥敕,該部分文本完全一致。后一部分則書寫武官履歷,涵括年齡、籍貫、出身、歷官、應授散階等信息。以下書寫父祖、命婦所獲散階、封階,世襲者在此基礎上續寫。武官命婦的封贈資格同文官命婦類似。在一定條件下,武官亦可推恩義父母、妻父母、伯叔父母。(30)萬歷《大明會典》卷122《兵部五·誥敕》。如天啟四年吳從明誥詞曰: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昔者圣王之治天下也,必資威武以安黔黎,未嘗專修文而不演武。朕特仿古制,設武職以衛治功。受斯任者,必忠以立身,仁以撫眾,智以察微,防奸御侮,機無暇時。能此,則榮及前人,福延后嗣,而身家永昌矣。敬之,毋怠。”天啟四年 月。
吳從明,年四十二歲,系浙江紹興府山陰縣人。有父吳來臣,于萬歷十九年由武生考選將材,隨李總兵救援朝鮮。二十年正月內進克平壤,在陣斬倭三顆,五月內碧蹄館地方力戰陣亡。隨蒙經略侍郎宋題敘,巡按山東御史周勘明,覆授紹興衛后所試百戶。明系嫡長男,于二十五年二月本縣保送赴部,查對功冊相同,于本年九月二十一日襲授前職,中萬歷乙卯、戊午鄉試武舉,考選將材,京營效用。天啟二年壬戌會試,中式武進士,加升署副千戶。四年三月,推廣東總兵標下旗鼓守備,以都指揮體統行事,署指揮僉事。四月蒙恩例,題準實授本所副千戶、散官。今授武略將軍、副千戶。吳從明父吳來臣贈武略將軍,母章氏贈宜人,繼母趙氏封宜人,妻王氏贈宜人。(31)天啟《山陰縣州山吳氏族譜》卷首《誥敕》。
明代誥敕亦可用于追贈,對品官的一生進行官方評定,“事必待乎論定,恩豈容以久虛”。(32)王守仁撰,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編校:《王陽明全集》卷40《誥命》,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681頁。此類誥敕行文句式大致為“制云云,具官某云云,贈某官云云,于戲云云”。“制云云”闡述褒揚、告慰功臣之意,指出贈官、賜謚等為朝廷對功臣的恤典。“具官某云云”是對品官生平的簡要概括,其中重點強調突出宦績,并以皇帝名義表達對逝者的悼念。“贈某官云云”贈予逝者較生前更高級別的官職、謚號等。“于戲云云”則為告慰歿者的再次表達,與“制云云”首尾呼應。如萬歷二十五年許國誥詞曰: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朕光宅萬邦,式敘群品,必審名器之用,以篤始終之恩。眷予舊臣,特崇異數。蓋國體之所寄,匪耆俊而莫居。爾原任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許國,博大清明,方嚴信厚,儲英史局,納約經緯,持文炳而俗為還淳,長賢關而士知率德,直清著于南省,簡要名于左銓。屬渺躬更化瑟之初,以舊學踐宰衡之任,朝端正色,聿弘綏靖之功,國本系心,累效憂危之論,凝重見廟堂之器,公忠推社稷之臣。強健乞身,廉退可風于士類,老成去國,謀猷尚軫于朕懷。倏易簣而長終,悼賜環之無日,爰加殊錫,以飾全歸。茲贈爾太保,謚‘文穆’,錫之誥命。于戲!爵能馭貴,穹階已極于三公,謚以尊名,令問丕延于百世。卿靈不昧,尚克歆承。”(33)崇禎《重修古歙城東許氏世譜》卷1《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穆”許國誥命》,明崇禎七年刻本。
根據明代家譜所輯品官誥敕,我們可以發現其文本具有三大特點:一是文官誥敕繼承駢體文特征,武官封贈誥敕則行文平實,表意淺顯。從行文特色上看,文官誥敕多使用駢體文書寫,詞句對仗工整,文本結構清晰。整體而言,位高者誥敕辭藻較位低者華美,追贈誥敕辭藻較封贈誥敕華美。文官誥敕關于職務或任職地、官署等的書寫,多使用別稱或古稱,具有用典色彩。如唐澤誥詞中的“方伯”指代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都臺”指代都察院;許國誥詞中的“史局”“南省”“左銓”指代“翰林院”“禮部”“吏部左侍郎”。武官封贈誥敕不作褒嘉之辭與修飾之語,亦不用駢體文,文風較為通俗易懂。
二是重視歷官宦績,書功不書過。從誥敕文本中,我們不難發現褒嘉之辭是圍繞歷官宦績而展開的。唐澤誥詞描述的是其居官之才,以及任職都察院等期間操持政務之功。許國誥詞描述的是其在翰林院、禮部、吏部等官署任職期間以身為范、清廉正直之功,以及入閣以來在“國本”大政方針上的貢獻。汪標誥詞亦列舉其在武定、易州知州、左軍都督府經歷、南京刑部郎中、鶴慶知府、大理知府、云南按察司副使任上的政績。武官誥敕文本對宦績的書寫依托于履歷、戰功,程佲多次參與明軍與少數民族之間的戰爭,誥詞即有“二月八日,大同雷公山殺敗達賊”“豹尾箐等處節次擒斬賊級十一名顆”(34)成化《程氏貽范集》甲集卷6《直隸沈陽中屯衛指揮僉事程佲授明威將軍并封妻劉氏恭人誥命》。等內容。尚未發現有明書品官過失的語言表述,這和誥敕的褒揚、獎勵功能是相對應的。
三是倫理規范色彩濃厚。明代誥敕重視儒家倫理的宣揚,行文以倫理關系為主線,多從“忠”“孝”“節”“義”等方面展開。如誥敕對宦績的書寫,是為“勤于王事”之忠,推恩父祖的理由書寫,則為勸孝之意。以前文所述林氏誥詞為例,“朕于任事之臣,既推恩于其親,而又榮及其配者,所以申恩典而厚人倫也”,即是推崇夫婦倫理的說明。“柔順慈良,克敦婦道,因夫之貴,已受恩封,夫再進官,爾宜偕顯”,表明林氏是因其夫程信顯貴而“偕顯”有進封“淑人”的資格。換而言之,命婦能否受封,依靠的是其夫或者子孫的功績。“祗服榮恩,永光閨壺”則是對林氏提出的期盼,希望繼續保持“柔順慈良,克敦婦道”之風。總而言之,這道誥命集中反映了“夫為妻綱”以及女性主內的家庭定位,并借“王言”行式加以控制與傳播,體現了國家意志。
三、明代品官誥敕的書史功能與史料局限
筆者曾對包括明代品官誥敕在內的徽州家譜所輯宸綸文獻的史料價值進行探討,認為其對宗族史、歷史人物、歷史事件乃至相關制度研究均有重要參考價值。(35)參見江一方:《現存徽州家譜所輯宸綸文獻述略》,《合肥學院學報》2021年第6期。但是,誥敕史料亦存在局限性。因此,我們需要從文本生成等角度條別源流,對其書史功能進行整體判斷,從而加以有效利用。
傳統觀點認為,誥敕文書的文字多堆砌辭藻、內容空洞,實際的書史和記載功能較差。(36)李福君:《試論明代的誥敕文書》,《檔案學通訊》2007年第3期。這一說法似有可深入探究之處。本文認為,誥敕具有書史和記載功能,具體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誥敕文本對官制、人物事跡等有所記述。譬如,文官本身封贈誥敕的“制(敕)云云”書寫基于明代官制及職能,書史功能較強,史料價值不可否認。唐澤的誥詞“我國家建都察院以重風憲之寄,崇紀綱之司。而副都御史實貳其長,必得剛直廉慎之士、識大體者以任之,始克有濟”,即描述了都察院負責監察、糾劾官員的“風憲衙門”職能,左副都御史為該部最高長官都御史的副職,需要直臣廉吏、顧全大局者擔任。潘玨的敕詞“郡縣親民之政,非久不成,朝廷錫命之榮,惟賢是予”,則認為府、縣官直接接觸民生疾苦,需要久任方有成效。還有一些誥敕所載信息更為豐富,萬歷五年吳兌的誥詞曰:“朕惟上谷為神京北門,撫臣任保厘重寄,矧其職少司馬而統戎兵,乃復兼大中丞以操法紀。”(37)天啟《山陰縣州山吳氏族譜》卷首《誥敕》。表明宣府為軍事重鎮,亦是京師門戶,巡撫兼兵部侍郎之職,便于統兵御敵,兼僉都御史之職,易于監察執法,權限較重。
各類誥敕文本對人物具體事跡也有一定記載。文官本身誥敕的“具官某云云”涵蓋了出身、任職信息,武官封贈誥敕的履歷部分還增加了戰功、襲職等信息。此外,一些文官父祖、命婦誥敕亦不乏具體事跡的記述。如天啟三年許立德夫婦敕詞曰:“絕粒以祈母之生,廬墓荒煙無色”,“以新婦而喜服縞綦,事病姑而躬調藥餌。投環絕粒,矢黃壤以唱隨,忍死存孤,來白衣之呵護”(38)崇禎《重修古歙城東許氏世譜》卷1《尚寶司司丞許志才父母敕命》。,描述了許氏夫婦踐行傳統禮教的具體行為。
二是品官本身誥敕的書史功能有制度上的支撐,文本具有一定可信度。明代文官封贈誥敕的獲得通常與考績直接相關,其制度雖有流變,但只有稱職才能獲得誥敕。(39)參見萬歷《大明會典》卷6《吏部五·驗封清吏司·誥敕》。而記載官員政績的給由則是能否獲得誥敕的依據,吏部在收到給由后還需進行查核,“其文職官員申請封贈,本部行移保勘。如果于例相應,然后照例施行”。(40)萬歷《大明會典》卷6《吏部五·驗封清吏司·文官封贈》。因此,從制度層面上看,誥敕對文官事跡的書寫有其為官稱職的史實依據。如南城縣知縣范淶陳乞誥敕,給由勘合中包含了十余名上級官員對其政績的評語批示,并附有任職期間在戶口、田糧等方面的政績清單。建昌府考語:“守身如冰,如玉存心,若鑒若衡,閱歷已逾于三年,清勤無間于一日。稱職。” 江西按察司考語:“操持壁立,蘊藉淵停,六事舉而吏畏民懷,兩稅輸而政平訟理。稱職。” 江西布政司考語:“心醇而儀貌端莊,守潔而才猷諳練,糧無逋負,案鮮停留。稱職。”(41)萬歷《休寧范氏族譜》卷7《南城縣知縣范淶給由勘合》。與范氏敕詞“器識純明,才猷敏練,蜚英軒對,筮綰邑符,乃能持廉靖之操,敷愷悌之政,人和譽洽,臺章屢聞。茲以秩滿,所司上爾功狀”(42)萬歷《休寧范氏族譜》卷7《江西建昌府南城縣知縣范淶并妻敕命二道》。的評價是一致的。
武官封贈誥敕所書人物事跡亦有其制度上的支撐,“其有應合給授者,須憑各官報到從軍腳色,比對內外貼黃年籍,并見授職事,流世相同。然后奏聞謄黃,照品定奪散官,寫誥給授。”因襲職、替職,誥敕亦需“查對明白,照例續寫”,后又有“將各處送到貼黃文冊比對各官父祖從軍、立功、升職無差。應請續者,照例查撰”之例。(43)萬歷《大明會典》卷122《兵部五·誥敕》。由此可知,武官誥敕的書寫需同此前儲存的軍職黃簿等比照,確認履歷記載相同,方可授予散官、封階,撰寫誥敕文本。
追贈誥敕與恤典具有較多關聯,亦需對歿者的履歷、功業進行核實、審議,經過皇帝批準,方可撰寫誥敕文本。(44)參見宋繼剛:《明代文官恤典研究》,東北師范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5年,第72—73頁。《古吳淀紫山徐氏世譜》輯錄了致仕吏部左侍郎徐縉歿后請恤的公文,徐氏獲祭葬、賜謚即經歷了家屬題請、禮部、吏部審核、皇帝批準等環節(45)參見《古吳淀紫山徐氏世譜》不分卷《恤典公移六道》,明刻本。,其真實性亦有保障。
三是誥敕文本同史志記載具有一定對應性。如前文所述唐澤誥詞“經理邊務,為朕安民御侮,其功大矣”的評價與《明實錄》可印證,“澤,直隸徽州府歙縣人,弘治己未進士,授平鄉知縣,累遷至左副都御史巡撫甘肅。澤沉毅知兵,在鎮五年,虜報旁午,悉心經略,以勞瘁成疾卒于涼州。詔嘉其以死勤事,特贈戶部右侍郎,賜祭葬”(46)《明世宗實錄》卷337,嘉靖二十七年六月,臺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明實錄》校印本,第6162—6163頁。另,關于唐澤的贈官,亦有“戶部左侍郎”之說,參見嘉靖《徽州府志》卷16《名賢列傳》、嘉靖《新安唐氏宗譜》卷上《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贈戶部左侍郎唐澤誥》。,說明這道誥敕記載具有較強的寫實性。
方志多是根據地方有關文獻匯編而成,所以材料直接而具體,有相當的可靠性(47)陳高華、陳智超等:《中國古代史史料學》,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第400頁。,故品官在任職地的方志形象可以作為我們評判誥敕文本的一大依據。潘玨的敕詞“恤下式勞于撫字,持身克篤于慎勤。歷歲既深,薦章交至”在嘉靖《蘄水縣志》中有具體的表現,其傳記云:“直隸婺源人,進士,成化、弘治間任。凡十年,寬厚莊重,持身清苦,蒞事公明,尚德教,恥奔競,愛民重士,賦政優游。雖無赫赫聲,迄今蘄人慕之,立有去思碑。”(48)嘉靖《蘄水縣志》卷2《名宦》,明嘉靖刻本。此外,該志《惠政》中的“聚民倉”“預備倉”“惠民藥局”,《學校》中的“明倫堂”“儀門”“育賢坊”,《秩祀》中的“鄉賢祠”等條目中均有潘氏修建、重建的記述,《藝文》中亦有潘氏率屬修建浮橋的記載。
另一方面,明代誥敕亦有史料局限,除學界關注較多的辭藻夸侈現象之外,還有兩大局限性:
一是誥敕對品官本身的事跡描述并不全面,褒嘉之辭反映的多是朝廷的整體評價。從文本形成流程上看,誥敕的書史功能有制度上的依據和支撐,但是負責撰寫文本的詞臣所獲品官事跡材料卻極為有限。就文官誥敕而言,“本部遇有應給誥敕官員,具本奏聞,仍具印信手本,開寫合授散官,并年籍腳色,送中書舍人。”(49)萬歷《大明會典》卷6《吏部五·驗封清吏司·誥敕》。按此例,詞臣從吏部驗封清吏司所獲的材料僅有文官應授的散官及其履歷信息,給由等公文難以入詞臣之手,這在范淶陳乞誥敕的公文中亦能得到印證。(50)萬歷《休寧范氏族譜》卷7《吏部驗封司請給考滿敕命手本執照》。因此,詞臣對文官履職褒嘉之辭多是依照考績標準以及官職職責而進行的整體評價,表明其居官稱職,至于文官的具體政績如何,施政的詳細舉措又如何,誥敕文本則多淺嘗輒止。唐澤、潘玨、范淶等人的誥敕文本均為如此,評價雖然較為可信,但記載不夠深入。武官封贈誥敕的撰寫材料是從軍腳色與內外貼黃,但腳色、貼黃雖記載武官在某時某地立某功、升某職,其立功過程卻多無詳述。因此,誥敕對人物的事跡記載相較于史志、碑傳文字整體上不甚完備。
從書寫方式上看,誠如高拱追贈誥詞所云“茲巨美寧問微疵”(51)參見賈香鋒、趙炳煥:《明神宗賜給高拱的誥命》,《中原文物》1998年第4期。,誥敕對于品官存在的瑕疵采取不書或掩飾的態度。許國的誥詞“強健乞身,廉退可風于士類,老成去國,謀猷尚軫于朕懷”即美化了其受神宗猜忌而自請致仕之事。至于許國“性木強,遇事輒發。數與言者為難,無大臣度,以故士論不附”(52)《明史》卷219《許國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5774、5773頁。等負面評價,均不可能提及。故誥敕文本難以全面記載人物事跡,在史料運用方面需要其他史料的補充和印證。
其二,特例封贈以及文官父祖、命婦誥敕文本缺乏制度上的審核支撐,史料易于失真。除考滿封贈外,明代還有覃恩、旌忠、旌勞等特例封贈,其審核流程較為寬松。如萬歷二十九年,神宗因冊立皇太子覃恩,“在外方面官二品至五品,有司官正四品,未曾考滿,有正薦者,亦與應得誥命”(53)《明神宗實錄》卷364,萬歷二十九年十月,第6795—6796頁。,范淶即援此例獲得誥命。公文記錄了審核流程,先是本人提請,然后由吏部驗封清吏司進行資格審查,“查得右布政使等官范淶等曾經巡按馬從聘各有奏薦,又取具各官親供,并同鄉工部虞衡司等衙門郎中等官胡瓚等保結前來”(54)萬歷《休寧范氏族譜》卷7《吏部題請封贈三世從二品誥命疏》。,吏部驗封清吏司上書皇帝,獲得批準后,即可由翰林院撰文,中書舍人關軸書寫。可知在此次覃恩中,官員具體政績不是必要條件,僅需一次舉薦記錄、同鄉擔保,即可獲得誥命。因此,從形成流程上看,覃恩誥敕對官員政績的褒揚缺少考績制度支撐,滿足覃恩條件即可撰寫,其“具官某云云”的書史功能未免大打折扣。皇帝特賜的誥敕亦是如此。不過,特例封贈的誥敕文本多會說明其屬特例,《明實錄》載:“吏部右侍郎徐縉三品未滿考,援溫仁和、董玘例,乞誥命。上以其講讀效勞,特準與之。”(55)《明世宗實錄》卷94,嘉靖七年閏十月,第2190頁。徐氏誥詞即有“茲不限常制”(56)《古吳淀紫山徐氏世譜》不分卷《吏部右侍郎徐縉進階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妻王氏贈淑人繼室郁氏封淑人誥命三道》。語,為我們查考誥敕的獲得方式提供了便利。
從文官推恩父祖、命婦誥敕的形成流程上看,只要滿足規定的封贈資格,即可撰寫誥敕文本,給由等公文中亦不包含父祖、命婦的詳細生平事跡。如范淶陳乞誥敕的相關公文僅開具了范氏本人出身信息與歷任官職,其所推恩的父祖、命婦卻僅有名諱、歷封(贈)散官、職官、封階記載。(57)萬歷《休寧范氏族譜》卷7《吏部驗封司請給考滿敕命手本執照》《南京吏部驗封司咨戶部封贈手本》《吏部題請封贈三世從二品誥命疏》。此外,詞臣從官方所獲人物資料較為缺乏,所撰文本多描述的是理想中的父祖、命婦形象,難以保證“名實相副”。詞臣雖有可能通過其社會關系了解到父祖、命婦的具體事跡,進而撰寫誥敕文本,但其中多有美化和曲筆,亦不乏失真者。如許國曾為同鄉、同朝的兵部右侍郎汪道昆撰寫封贈二代的誥命,并為其父作墓志(58)許國:《封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長庚汪公墓志銘》,萬歷《靈山院汪氏十六族譜》卷10。,汪氏祖父汪玄儀的誥詞曰:“至以賈豎力抗中貴,憑籍信義持劵貸府庫金。”(59)萬歷《靈山院汪氏十六族譜》卷10《兵部右侍郎汪道昆祖父母父母并妻誥命三道》;許國:《許文穆公全集》卷9《汪道昆祖父母誥命》,明天啟五年刻本。按:該引文中“憑籍”在《許文穆公全集》中作“憑藉”。而汪氏所撰《太函集》中收錄了《先大父狀》一文,恰好描述了汪玄儀“力抗中貴”“貸府庫金”的故事,可用以印證誥詞的真實性。(60)汪道昆撰,胡益民、余國慶點校:《太函集》卷43《先大父狀》,黃山書社2004年版,第919—920頁。汪氏所述還原了事件的過程。宦官劉景掠奪商賈財富,同行商賈逃亡,汪玄儀的店業亦受沖擊,他以身代幼弟入獄,承諾向劉景獻上千金。由于資金難以籌措,汪玄儀即通過向官府貸款的方式才得以免禍。因此,汪玄儀獻金與借貸皆是為了免禍,并非反抗宦官對商賈的剝削,誥詞“力抗中貴”未免言過其實。可見,許國應是采用了曲筆,塑造了一個不畏強權、誠信經商的儒賈形象。至于汪道昆繼妻蔣氏,則以“悍婦”形象而著稱:“侍先生左右者,男皆四十以上,嫗皆六十以上,其它不得見也。先生所以嚴事之,亦至矣。然少不當意,輒責令蒲伏,盛夏則置蚊蚋叢中,隆寒則露處,以為常。先生每一聞夫人傳教,汗未嘗不灑淅也。”(61)謝肇淛:《五雜組》卷8《人部四》,明刻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誥詞卻曰:“性稟柔嘉,義存交儆”,“終溫且惠,克順而貞”(62)萬歷《靈山院汪氏十六族譜》卷10《襄陽府知府汪道昆父母并妻誥命四道》《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汪道昆父母誥命一道又并妻誥命一道》。,顯然存在明顯的失真之處。
此外,誥敕的資格審核中亦難免有失實、舞弊等現象,進而影響到其書史功能。譬如,從萬歷年間到明代亡國,考察制度已經遭到了嚴重的破壞(63)劉志堅、劉杰:《試論明代官吏考察制度》,《西北師大學報》2001年第3期。,而考績結果恰恰是文官封贈誥敕書史功能的制度支撐。
結 語
品官誥敕是明代誥敕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文本具有一定的書史和記載功能,品官本身誥敕所書之“史”相對可靠,對官制的描述、品官履歷等的記載亦具有較高的文獻價值,為我們研究相關問題提供了珍貴史料。但是,由于誥敕的獲得與品官政績、朝廷賞賜密切相關,無論是因考績合格而來的誥敕,還是因覃恩等特例封贈而來的誥敕,亦或是推恩父祖、命婦的誥敕,去世后的贈官誥敕,本質上均屬于朝廷的獎勵機制。這些誥敕文本的書寫目的在于激勵品官“勤于王事”,或是以官方權威的形式對歿者一生加以總結和高度評價,在告慰歿者的同時,激勵更多的文武官員、父祖、命婦以逝者為榜樣,為朝廷恪盡職守。因此,誥敕文本的書寫方式必然不同于史書。相較于史書的“善惡備書”,誥敕的文本書寫則是以“隱惡揚善”為主。由于文本形成流程的局限性、褒揚的行文基調、倫理關系的行文主線,誥敕所書之“史”并不全面,亦非皆為信史。史學研究者在運用誥敕史料之時,應采取去粗取精和去偽存真的態度,通過校勘和辨偽的方式,使之更好地為學術研究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