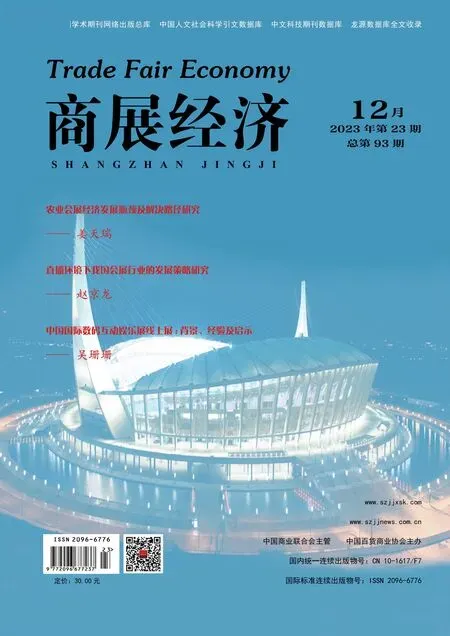中國文化產業發展與共同富裕耦合協調關系研究
張金浪
(西藏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 西藏拉薩 850000)
實現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要實現共同富裕,一方面要解決貧困問題,實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富裕;另一方面要消除兩極分化問題,實現相對均等、差距可控的共享[1]。文化產業作為滿足人們精神文化需要的重要產業,其增加值在2021年占GDP的比重達4.56%。如何利用文化產業來促進實現共同富裕是當下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
目前,還沒有學者直接研究文化產業發展與共同富裕的關系,現有研究主要從定性分析角度和定量分析角度考察文化產業發展對富裕度或共享度中某一方面的作用。從定性分析角度,學者主要分析了文化產業發展對共同富裕的影響機制。楊曉燕等(2017)認為,文化產業發展一方面可以教育人、引導人和滿足人們的多元化文化需求,提高人們的精神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可以將人們的文化需求轉化為文化消費,進而以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的方式,實現其經濟效益,提高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2];鄭自立(2022)認為,文化產業和旅游融合發展可以豐富居民消費的物質產品類別,促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提升地方經濟增長能力和居民收入水平,并能夠優化人文環境、保護和傳承優秀文化資源及提供優質的文化旅游體驗,提高人民群眾精神生活質量[3]。除了提高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文化產業發展還可以縮小地區差距、城鄉差距和人均差距;吳怡頻等(2023)認為,文化產業是基層公共文化服務供給的基礎,文化產業的發展能夠助力基層公共文化服務發展[4];尚子娟等(2023)認為,公共文化服務是實現人民均等享有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途徑,公共文化服務供給的增加可以保障人民均等享有精神文化生活,縮小地區和人均精神文化生活差距[5];葉林(2021)認為,文化產業的資源非排他性、產品異質性和正向收入消費彈性等特點可以促進鄉村產業結構優化,推動鄉村經濟振興[6];張金風(2009)認為,農村地區發展文化產業可以減少農業從業人數和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促進縮小城鄉差距[7];李忠斌等(2017)認為,文化產業發展有助于實現貧困人口持續脫貧和貧困地區持續發展,縮小城鄉和人均差距[8];從定量分析的角度,學者主要證實了文化產業發展對促進經濟增長、提高低收入群體的作用;袁連升等(2018)通過對中國的省際面板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發現文化產業發展對GDP和人均GDP均有顯著的促進作用[9];葉林等(2020)對2013年開始試點的貴州水城縣農民畫產業扶貧項目進行政策效果評估,發現參與該項目的貧困家庭年人均收入增長額外提高了22.6%[10]。
綜上所述,學者大多只研究文化產業發展對富裕度或共享度中某一方面的單向作用,并沒有關注文化產業與共同富裕的雙向關系。因此,本文以2011—2021年中國31個省份為樣本,在構建文化產業發展和共同富裕指數的基礎上,采用耦合協調度模型考察文化產業發展與共同富裕的耦合協調關系,對我國促進文化產業發展和實現共同富裕目標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1 文化產業發展與共同富裕的耦合協調機理
1.1 共同富裕為文化產業發展提供需求動力
共同富裕水平的提高可以為文化產業的發展提供需求動力。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將人類需求像階梯一樣從低到高按層次分為5種,分別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而且認為人類動機的發展和需求的滿足有著密切關系,低層次需求的滿足或基本滿足有助于高層次動機的出現[11]。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是人類基本物質生活有了保障之后出現的文化需求[12]。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必然衍生出更多元化的文化需求,進而促進文化產業的發展。
1.2 文化產業發展為實現共同富裕提供精神和物質基礎
文化產業具有意識形態屬性和商品屬性的雙重屬性[13]。文化產業發展一方面可以增強貧困人口的自我發展能力,緩解貧困群體的能力貧困和消除貧困文化[14],同時保障全體公民最基本的文化權益,促進實現精神生活共同富裕[15];另一方面可以將人們的文化需求轉化為經濟效益,提高居民收入和縮小地區、城鄉、人均差距,為實現共同富裕提供物質基礎。
2 研究設計
2.1 指標體系構建
文化產業是指為廣大社會公眾提供文化產品(及相關產品)的生產活動的集合[16]。根據中國省市文化產業發展指數的構建方法[17],本文構建了包括產業要素投入、產業產出水平和外界驅動力3個一級指標、7個二級指標和15個三級指標的文化產業發展指數(見表1)。共同富裕包括富裕度和共享度兩個方面,富裕度反映的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程度,共享度反映的是社會成員對財富的分配和占有方式[18]。本文的共同富裕指數充分考慮了袁惠愛等(2022)[19]、鄭中團等(2023)[20]的研究,構建了包括富裕度、共享度2個一級指標、4個二級指標及14個三級指標的共同富裕指數體系(見表2)。

表1 文化產業發展指數的指標體系

表2 共同富裕指數的指標體系
2.2 研究方法
2.2.1 熵值法
本文首先采用客觀賦值法中的熵值法分別對文化產業發展指數和共同富裕指數一級指標下的三級指標進行賦權,避免了主觀賦權法的缺陷。再對文化產業發展指數和共同富裕指數的一級指標分別賦予相同的權重。最后采用加權平均的方法合成綜合指數。
2.2.2 耦合協調度模型
借鑒相關學者的研究,本文構建了以下的耦合協調度模型:

表3 文化產業發展與共同富裕耦合協調等級劃分
2.3 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我國2011—2021年31個省份(不包括港澳臺)為樣本,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各省份統計年鑒和《中國文化及相關產業統計年鑒》,對于缺失的數據采用插值法進行補齊。
3 實證結果分析
3.1 中國文化產業發展與共同富裕指數分析
本文采用熵值法和加權平均法計算得到了2011—2021年的文化產業發展和共同富裕指數,如圖1和圖2所示。發現2011—2019年我國文化產業發展指數呈逐年上升趨勢,2020—2021年受新冠疫情影響略有下降,說明我國文化產業政策改革工作取得階段性成效,文化產業發展水平得顯著性提高。但文化產業發展指數存在東部和中部地區遠高于西部和東北地區的情況,說明東部和中部地區經濟發展基礎好,文化資源豐富,在政策的推動下文化產業能夠實現較快發展,西部和東北地區的文化產業則受限于經濟基礎差,產業結構不合理等原因而難以發展。2011—2021年我國共同富裕指數呈逐年上升趨勢,說明我國在提高經濟發展質量、消除絕對貧困促進實現共同富裕等方面的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此外,東部地區共同富裕指數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但中部、西部和東北地區之間的共同富裕指數差距出現縮小趨勢,說明我國的共同富裕是有差距的共同富裕,體現了我國的“先富”帶“后富”思想。

圖1 2011-2012年我國文化產業發展指數時空差異

圖2 2011-2021年我國共同富裕指數時空差異
3.2 中國文化產業發展與共同富裕耦合協調度時空變化分析
本文采用耦合協調度模型計算2011—2021年我國文化產業發展和共同富裕兩個系統的耦合協調度,并根據表3的標準劃分了耦合協調等級,結果如表4所示。總體來看,除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響外,2011—2021年我國文化產業發展與共同富裕耦合協調度逐年上升。其中,2011—2015年處于瀕臨失調狀態,2016—2021年處于勉強協調狀態,總體處于較低水平,但有向優質協調方向發展的趨勢,說明我國文化產業發展與共同富裕之間的相互關聯程度逐漸增強,耦合協調水平不斷提高。分地區來看,東部地區和中部地區的文化產業發展與共同富裕耦合協調度高于全國平均水平,東部地區由瀕臨失調發展為初級協調,中部地區由輕度失調發展為勉強協調,說明這兩個地區的文化產業與共同富裕能夠較好地實現協調發展,文化產業發展能夠保障人民的文化權益和推動經濟發展,促進實現共同富裕,同時共同富裕的實現能夠刺激文化需求的產生,推動文化產業發展。相比之下,西部地區和東北地區的文化產業發展與共同富裕耦合協調度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至今仍處于瀕臨失調狀態,而且東北地區耦合協調度增長緩慢,逐漸落后于西部地區,這是因為西部地區和東北地區受制于歷史、地理和政策等因素,產業結構不合理,產業基礎薄弱,導致文化產業發展水平較低,難以與共同富裕實現協調發展。

表4 2011-2022年我國文化產業發展與共同富裕耦合協調度演變
4 結語
本文通過構建文化產業發展和共同富裕指數分析其耦合協調關系,結果發現:(1)我國文化產業發展指數在2011—2019年呈上升趨勢,在2020—2021年受新冠疫情影響略有下降,共同富裕指數在2011—2021年呈逐年上升趨勢,二者均存在時空分布異質性。(2)除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響外,2011—2021年我國文化產業發展與共同富裕的耦合協調度發展趨勢向好,由瀕臨失調發展為勉強協調。(3)我國文化產業發展與共同富裕耦合協調度存在空間分布差異,東部和中部地區的文化產業與共同富裕能夠較好地實現協調發展,西部和東北地區則由于文化產業發展水平低,難以與共同富裕實現協調發展。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幾點建議。一是提高文化產業和共同富裕發展水平。加大對文化產業的財政投入力度,夯實文化產業發展的基礎,完善產品市場,刺激文化產品和服務消費,促進文化產業發展。同時,完善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制度,縮小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地區差距、城鄉差距和人群差距,促進實現共同富裕;二是推動文化產業與共同富裕協調發展。充分挖掘各省市文化資源的內涵,發揮文化的育人功能和經濟功能,提高人們的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水平,以文化產業發展為實現共同富裕提供精神和物質基礎。同時,提高低收入群體收入水平,培育文化消費市場,激發文化消費潛力,以共同富裕的實現為文化產業發展提供需求動力;三是采用政策扶持、財政支持和對口支援等方式推動區域協調發展。對經濟發展較為落后的地區,加大政策扶持和財政支持力度,優化產業結構,提高其經濟發展水平。同時,加大經濟發達地區對經濟不發達地區的支援力度,促進實現“先富”帶動“后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