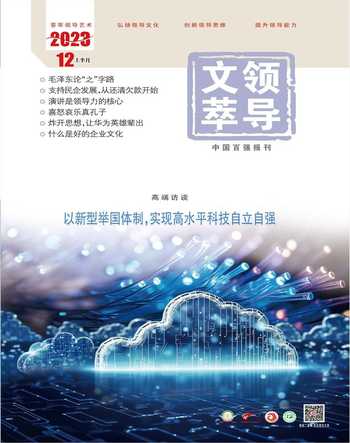權臣并非奸臣
熊召政
就說朱元璋炮打慶功樓一事,雖然于史無證,但這位皇帝在坐穩龍椅之后,的確是尋找各種借口,幾欲將幫他打下江山,建立朱明政權的開國功臣們鎮壓殆盡。他如此做,不能簡單用“狡兔死,走狗烹”六個字來概括。
對于朱元璋的這種做法,他的夫人馬皇后與太子朱標都表示過反對。朱元璋不為所動。傳說有一次,他撿起一枝棘條給太子,因滿是棘刺,太子無法把握,朱元璋把棘條上的刺一一拔干凈,再遞給太子說:“現在你可以很穩當地拿住它了吧?”接著便講了一個道理,其大意是我屠殺那些功臣,是為了讓你繼承皇位后,不至于有人跟你搗蛋。
立國之初,由于朱元璋嚴于約束,女寵、宦官、外戚、藩鎮等,都還形成不了勢力。唯一有可能對朱元璋構成威脅的,就只能是權臣和夷狄了。對于夷狄,朱元璋或剿或撫,恩威并施,處理得雖不是恰到好處,但也沒有大的過失。因此,在他的統治時期,邊患始終沒有對他的政權構成主要威脅。剩下的最后一個問題,就是權臣。前面已經講過,朱元璋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而大肆屠戮功臣,就是為了鏟除權臣。他提防權臣的方法就是“上下相維,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謹威福之下移”。上下相維就是君守君道、臣守臣道,看似兩方面都合道,實際上是要做大臣的對皇上愚忠。大小相制,就是小官管大官。防耳目之壅蔽,就是多設紀檢干部,讓六科給事中監察六部,他親自管束六科。明朝的紀檢干部除六科給事中外,尚有都察院御史以及大理寺的官員等,有的稱言官,有的稱憲臣。這部分官員的數目很大,大約占朝廷命官總數的三分之一。用這么多的紀檢干部來防止自己“耳目壅蔽”,朱元璋可謂煞費苦心。最后是“謹威福之下移”的問題。在他看來,權臣的突出表現,就是威福自專,與皇上分享權力,這是皇帝最忌諱的事。權臣嚴嵩倒臺后,他的繼任者徐階給嘉靖皇帝提出的施政綱領中就有一條“還威福于皇上”。徐階是松江人,狀元出身,是張居正政治導師。為人有正義感,但比較謹慎,也比較滑頭。他如此說是讓嘉靖皇帝放心,他永遠只是皇上的臣仆,絕不會僭越。
永樂皇帝雖然確立了內閣制度,但當時的閣臣都是直接對朱棣負責,尚無首輔之設。設置首輔是在孝宗時代,三楊之后。此后的內閣,便有點像朱元璋執政初年的中書省了。首輔也相當于宰相,但首輔能不能真正行使宰相的權力,則要看所服務的皇帝是英主還是庸君。譬如說張居正在隆慶六年當上首輔后,輔佐十歲登基的萬歷皇帝推行“萬歷新政”,其中有一個考成法,是整飭吏治的重要舉措。最核心的就是都察院監督全國各省官員,六科監督六部,而內閣則負責都察院與六科的考核,這樣一來,等于說所有的紀檢干部都不再直接對皇上負責,而是改在內閣的掌控之下。萬歷新政的順利實施,應該說得益于這個舉措。但這是分享了皇上的權力,用朱元璋的觀點看,張居正是十足的權臣。
朱元璋對權臣的定位是威福自專。威指權力,福指享受,為人臣者,其權力與享受絕不能超過皇上。皇上可以隨便殺一個人,也可以隨便提拔一個人。大臣就不行。生殺予奪大權,只能握在皇上一個人手上,大臣想要分享便是犯忌,就成了權臣。
在明代,被戴上權臣帽子的有不少,胡惟庸、李善長都是權臣。嘉靖朝當過二十年首輔的嚴嵩倒臺后,也被封以權臣。張居正死后遭到萬歷皇帝清算,再次被稱為權臣。把這幾個權臣放在一起研究,就會發覺他們之間的差別太大了。嚴嵩弄權,是為了賣官鬻爵,積斂錢財。即便這樣,他也從不敢威福自專,而是挖空心思討好皇上。張居正秉政時,倒是勇于任事,在他擔任內閣首輔的十年,他掌握了實際的權力,這也是因為皇帝太小,無法作為。張居正領導萬歷新政,在吏治、邊防、賦稅諸方面實施改革,使本已奄奄一息的大明王朝有了中興之象。對這樣的人,若以權臣來罪他,則是千古冤案。若用權臣來褒他,仍覺言過其實。事實上,萬歷皇帝雖然只是十歲的孩子,在張居正眼中仍是君父,每每受到這孩子的表揚,他仍然熱淚盈眶。這樣的記載,在萬歷朝的典籍中,不在少數。
后世的一些史評家,常常用權臣的概念來評判古代大臣,以此定忠奸、定褒貶,竊以為大謬。像朱元璋這樣討厭權臣的皇帝,我們可以理解。他之所以討厭,是害怕大權旁落,但喜好權力的人并不一定都是奸臣。
(摘自《明朝大悲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