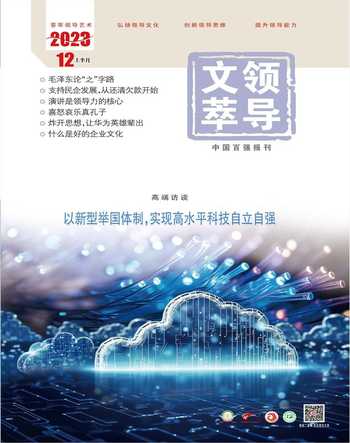用“疾病眼”看歷史
唐山
假如秦始皇能多活10年,秦是否會避免二世而亡的結果?假如霍去病不死于壯年,匈奴是否早被平定?假如諸葛亮長壽,蜀國會不會并吞天下……
類似的“假如”,相信每個人都會提出不少。歷史是解釋的學問,只能就已發生的事實進行解釋,所以歷史不可假設。正如黑格爾所說,“可能性是無窮的”,人類無法從“假如”的歷史中得到確定的知識,也無法因此達成共識。
然而,人們仍然會關注前面的這些問題,這恰恰說明,疾病也是塑造歷史的重要力量之一,只是它經常被忽視。既往的研究者們較關注“規律性”,而疾病作為“偶發因素”,似乎不值一提,這就讓歷史認知與直接經驗分離,使歷史成了“深奧”“復雜”的學問。
事實是,在很多情況下,疾病很可能是歷史的決定性因素。
歷代開國之君,長壽者多,而東漢中后期,乃至元朝中后期,帝王離奇地短壽,都造成了天下板蕩。
在現實中,疾病不是“偶發因素”,而是經常性事件。據考證,我國歷史上曾出現200多次大瘟疫,秦漢時13次,魏晉時17次,隋唐時17次,兩宋32次,元代20次,明朝64次,清朝74次,它們極大地影響了歷史進程。
很多作者基于古人平均壽命僅30多歲,便得出古人20歲便開始立遺囑的觀點,這顯然是對統計數據的誤讀。古人平均壽命低,是因1/3的嬰兒會在生育時死亡,而勉強渡過難關的嬰兒,1/5將死于10歲前。一旦成年,古人的平均壽命并不低,《二十四史》中有傳的人物,平均壽命約70歲。有學者據唐代5100個墓志銘中5053個樣本,得出唐代成人平均年齡59.3歲;據宋代4783個墓志銘統計,成人平均年齡為61.4歲;據2944個明代墓志銘統計,成人平均年齡為67.6歲。
曾肆虐歐洲的“黑死病”,被認為是因蒙古西征,從亞洲傳到了歐洲。西方文獻甚至繪聲繪色地寫道,蒙古大軍圍困卡法城時,將病死者的尸體用拋石機拋入城中,導致疾病蔓延,在網上,一些寫手稱“這是人類史上最早的生物戰”。但事實上,圍攻卡法城與“黑死病”流行,相距20年,不可能是同一場瘟疫。到目前為止,任何有關“黑死病”源于亞洲的說法都是種族歧視的產物,無非是把不可掌控的困境歸罪于“他者”。不明所以的網絡寫手們,反而推漲了這一刻板印象。
今人常抱怨,如今的“怪病”太多,歸因于環境污染等。其實古人的“怪病”也很多,關羽、盧照鄰、白居易、賀知章、忽必烈等均患痛風,漢武帝、隋煬帝、杜甫、歐陽修等則患糖尿病。蘇軾則患有近視眼、左手偏癱、耳聾、痔瘡、肺病、頭痛、牙病、瘡癤8種疾病。古代醫學條件差,大多數疾病得不到及時診斷,且資訊不發達,無法將各自的“疾病恐懼”形成共振。
其實,坊間不僅對歷史有誤會,對醫學常識也有很多誤會。
“限酒戒煙”,就是一個流行頗廣的誤說。據世界衛生組織最新發布的結論,沒有一滴酒精是對健康有益的,酒是一級致癌物,與口腔癌、喉癌、食管癌等有密切關聯,受基因影響,酒精對中國人的傷害尤其大。
網上有許多“健康指導”類的文章,給讀者提出各種飲食建議,整體看,這些建議是正確的,但從基因看,人體至少可分400種以上,基于不同類型的人,應采用不同的健康建議,沒有一種建議適合所有人。貿然聽信通用型的建議,可能會給身體帶來傷害。
比如“面有微毒”,覺得古人對面粉的恐懼純屬庸人自擾,別人請袁枚吃面,他必將面泡入涼水“去毒”后,才肯食用。后來才知道,面粉中含特種蛋白,可致少數人過敏,嚴重者甚至會導致臉上的肉掉下來,在孫思邈的《千金方》中即有類似記載。只是隨著基因淘汰,今人大多無此問題。
我們不僅要從“規律眼”“理性眼”“政治經濟學眼”看歷史,還要從“疾病眼”看歷史,因為疾病一直都在,它隨時可能改變歷史走向。
也許幾年后,人類仍可能遭遇重大疫情,該怎么辦?其實歷史已用無比豐富的案例,提醒我們該如何應對,唯有以史為鑒,方能打開智慧之門。
(摘自《北京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