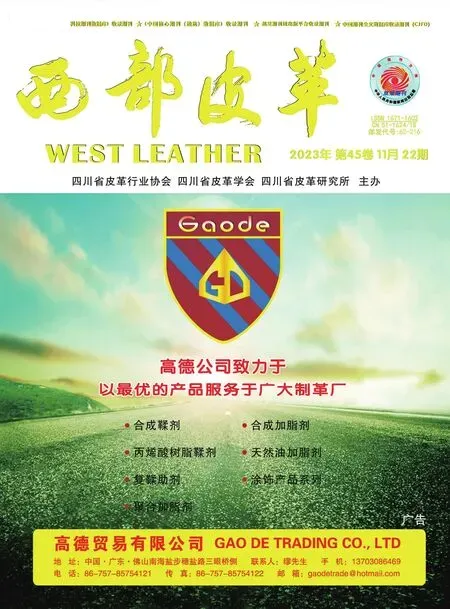簡析苗族百鳥衣紋樣的民族共享符號
——以中南民族大學館藏丹寨苗族百鳥衣為例
羅焱
(中南民族大學 美術學院,湖北 武漢 430000)
0 引言
苗族人們衣著百鳥衣在牯藏節跳舞時,伴隨著時而柔和時而宏偉的音樂,能幫助我們直觀地感受苗族的歷史,讓觀看的人深陷其中,贊嘆不已。百鳥衣作為普通平民百姓的穿戴服飾,是人們適應周圍環境的產物,具有實用功能,同時也有著更寬泛的意義,即更加功利地體現了黔東南人民對生命價值的追求。針對現有關于百鳥衣研究文章中多是對單個紋樣的論述,而缺乏對民族之間紋樣的聯系和對比研究。文章將從時間和空間來簡述苗族與周邊民族的服飾紋樣在使用意義上的共通性,從而得出結論:雖然不同民族對同一事物的表達方式不同,但其深層內涵卻有著共性。
1 百鳥衣
百鳥衣作為祭祀儀式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承載著族人們的精神信仰以及中華民族共通的文化愿望。如圖1,以中南民族大學館藏百鳥衣為例分析丹寨苗族百鳥衣的形制和文化內涵。首先,衣中所包含的三角形的山川和菱形的房屋是為了告誡后代幸福生活的來之不易。其次,衣服的結構是以前后中心線為軸線的十字型,這種“十字型”的平面結構體現了苗族人民仍保持著原始的衣飾結構狀態,同時這也一直是中華民族服飾的基本結構形態,兩者都體現了“敬物”和“節約”的思想。上衣的正面是以四個圓形為基本單位,在圓形中布滿紋樣,不留空隙,而在上衣的背面也布滿了飛鳥、花卉、魚類和幾何紋樣,空隙很少。這種不留空隙的布局方式與中原地區自古以來向往的“滿”類似,兩者都體現了對“圓滿”的追求。

圖1 中南民族大學館藏百鳥衣(背面)Fig.1 Bainiaoyi collected by South-Central Minzu University(reverse side)
2 民族遷徙與民族交融對百鳥衣的影響
法國藝術史學家丹納在其代表作《藝術哲學》中提出,地理環境、種族和時代對審美觀念發展變化起著決定性影響,三者缺一不可。地理環境是影響一個民族審美觀念形成和發展變化的最顯在的因素,“共同地域”是民族的基本特征之一,也是民族形成和發展的基本空間條件。據記載,貴州的苗族先民原是來自北方的民族,是經過多次大遷徙才到達今天的貴州省境內。在歷史的長河中,古苗疆走廊是連接西南邊陲云南與內地之間一條交通大動脈,是許多民族的家園,明清以后也深刻影響了以貴州省為中心的“苗疆”地域社會的歷史變遷[1]。在古苗疆走廊分布著眾多藏緬語族、苗瑤語族、壯侗語族的民族及族群,隨著族群之間的遷徙移動,有力地推動了民族的融合。自宋以后,由于歷史上的征戰,貴州高原成為西南民族流動的大走廊,這也是古代南方的四大族系,即氏羌、苗瑤、百越、百濮四大族系的交匯地。氐羌民族自西向東發展,苗瑤民族自東向西移動,百越民族自南而北推進,濮人則四處遷徙,漢族主要是從北面和東北面進入貴州,黔東南逐漸形成了多民族聚居的狀況。不同族源的古老民族陸續遷入。
這些民族雖然族源不同,但卻居住在同一區域,在經濟上互補互助,在藝術上出現了共創、共傳、共享的現象,通過視覺藝術視角去觀察就會發現其同源異流的共性。據考古發掘證明,苗族刺繡最初起源大約在大汶口文化時期或更早的河姆渡和半坡母系氏族時期。隨著歷史的演進,古越族群作為苗瑤族群的鄰居,也在不停地交流、交融[2],徐仁瑤在《苗瑤文化與越文化關系探源》中提到,先秦兩漢時期活躍一時的古越人,他們的文化在苗瑤民族中得以傳承,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寶庫增添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侯天江曾在《苗繡藝術》中提到,來到黔東南的苗族主要有兩支組成:一支沿湖南西部的沅水遷入,大約秦漢時期定居;另一支居住在雷公山麓的榕江等地,在秦漢時期后遷徙,基本定居格局在唐宋明時期。苗族先民由北向南遷徙,使得百鳥衣中的刺繡仍然帶著北方文化的影子。中南民族大學民族學博物館收藏的百鳥衣,其刺繡所包含的鎖繡、縐繡、平繡,就是中原繡法的延續。作為中原繡法的延續,百鳥衣中的刺繡與春秋時期的楚繡一樣顯得光滑、平整。在宋代,百鳥衣開始被世人所知,這是源于郭若虛在《圖畫見聞志》中描繪了唐代“東蠻苗謝元深”身著“卉服鳥章”的苗族服飾去見唐太宗。宋代初期的服飾流行大袖衫,雖然與“質樸”不掛邊,但大量運用了比喻、借喻、雙關和諧音等手法,例如宋代出現的“四君子”——梅、蘭、竹、菊紋樣成為人格道德精神的載體。而地處貴州中心的苗族也受其影響,例如館藏百鳥衣中的“卐”字紋與十字紋的結合寓意陰陽和諧、日月生輝與生命輪回,將其與“不間斷回紋”連在一起形成“萬字紋不斷頭”的吉祥寓意[3]。
3 百鳥衣文化特征中的共享性
百鳥衣文化特征中的共享性主要體現兩點,即形制和紋樣。在形制上,中原服飾文化延伸到南北之后,十字型平面結構成為中華民族服飾體系的一大特征,結構中蘊含著中華文化宇宙論的哲學思想[4]。館藏的苗族百鳥衣也具有中原特色的“十”字型平面結構,體現著共性。在紋樣上,百鳥衣中紋樣包括龍紋、鳥紋和幾何紋等承載著幾千年來形成的苗族形象,通過這些外在紋樣進入到苗族的精神世界就會發現,苗族與其他民族服飾中蘊含的文化內涵具有一致性,因此以紋樣為主要切入點,并列舉了兩個典型紋樣進行比較分析。
3.1 百鳥衣中的“龍”
首先,龍崇拜廣泛流行于民族之間,無論是百越和苗瑤族群的龍形象,還是中原地區的龍形象,都表征著中華民族文化對文化圈內其他多民族的影響,龍崇拜從未中斷,有著無限的生命力,只是各自表達的手法和方式有所差異。龍圖騰崇拜的起源往往和氏族傳說相聯系,大部分神話和傳說中有不少關于龍崇拜的相關記載,例如作為苗瑤支系的鄰居之一的百越族群,龍母卵生神話是百越文化圈始祖神話的普遍母題,并在環大明山壯族地區廣泛流傳[5]。與此同時,在人們的生產生活用具里,也能找到龍崇拜的影子,例如黎族婦女們所創作的龍被,黎錦服飾中的龍紋對龍紋結構的表現體現著平實和不拘一格的特點。生產力造成“龍”的成長環境和條件不同,但總體來說龍紋逐漸成為一種共享性的元素出現在不同民族當中。漢族傳統服飾龍紋經過歷史的不斷演變,造型由粗獷到復雜經過了一系列的變化,縱向來看,商周時期的龍紋造型較為粗獷質樸,類似爬行動物,后來在春秋戰國時期,開始走向寫實風格的獸形龍紋的轉變,慢慢體現出了中原地區的龍是作為封建君主政治權威的象征而出現的,逐漸成為“皇權標志”,但可以推測龍最初出現時屬于靈物崇拜。苗瑤與百越族群都是中華古老的族群,創造的龍紋至今體現著靈物崇拜。
其次,在族群內部關于龍紋的刻畫也不盡相同,在苗繡中關于龍的組合中,以黔東南苗族刺繡為例,龍的形象就有二十四種之多,水龍、旱龍兩大類各有十二條。中南民族大學民族學博物館珍藏的百鳥衣按照地域分類屬于丹寨式,其中的龍紋是從魚演變而來的,為龍頭魚身;黑領苗式的龍是從鳥的形象演變而來的,形成龍頭鳥身;臺江施洞最常見的是牛龍,身體呈蛇形。館藏百鳥衣的龍在構造上屬于半圈型,對比這種半圈型的魚龍造型與榕江擺貝型的螺旋形蟠龍紋研究發現,兩者的龍紋都沒有四足,即都沒有手腳及頸、身、尾三停之分,頗有先秦遺風[6]。先秦對黔東南的影響促使丹寨百鳥衣的龍紋像稚氣的兒童,造型笨拙而生動,使人倍感親切,延續至今也從側面體現了當地仍保持著樸素、純真的文化氛圍。除此之外,龍與蛇、魚、鳥的組合出現,是為了避免與古代的皇權沖突,引來滅頂之災,因此所創造的組合龍形象顯得憨態可掬。龍紋是萬物之魂的發展和生化結晶,自原始社會新石器時期各族人民對龍的崇拜就已萌芽,雖然苗瑤支系、百越支系與中原地區的龍紋形象大相徑庭,但其共通點都在于通過龍紋來傳達人們對自然環境、生活和祖先的精神訴求,以及呈現出了婦女們的智慧與創作能力。
3.2 百鳥衣中的“鳥”
蚩尤族的后裔認為鳥幫助過曾經落難的祖先,因此后來把鳥視為族人的崇拜對象,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也稱之為“羽族”的后裔。丹寨苗族自稱為“噶鬧”,“噶”為語氣助詞,“鬧”即“鳥”,因此丹寨又被稱之為鳥圖騰部落。百鳥衣顧名思義是由多只鳥兒組合而成的一件服飾,在祭祖儀式的“鼓藏節”中,人們穿著五光十色的“百鳥衣”,展現出苗族人們對鳳鳥的極度崇拜。鳥被苗族人們視為引魂歸宗的使者與向導,人們夜以繼日地在旗幡上印染鳳鳥紋,在神靈祭祀樹上沾滿鳥羽,在百鳥衣的條裙上縫上一根又一根的羽毛,種種行徑都表達了人們希望能夠和神靈溝通,隱藏著苗族的圖騰象征和祖先崇拜。
在早期民族的圖騰信仰中,鳥崇拜是一種普遍現象[3]。在中國南方的古老民族中,越人的圖騰標志主要是鳥,以及侗族對鳥紋的崇拜也體現在《小方壺齋輿地叢鈔》中:苗童(侗)之未妻者“羅漢”“皆髻插雞羽”。《史記·秦本紀》中:“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修。女修織,玄鳥隕卵,女修吞之,生子大業。”有人根據古籍所記,女修吞玄鳥卵而生先秦鼻祖大業的傳說,認為秦人的祖先是以玄鳥為圖騰的,說明了人與鳥之間的密切關系。據考古證明“觀音洞文化遺址”為原始布依族社會母系氏族的一寸,氏族以鳥作為“圖騰”崇拜,可見遠古時期的布依族就出現了對鳥圖騰的崇拜。
在館藏的丹寨式的百鳥衣中,鳥的功能主要是作為補充,具有豐富的造型、強烈的流動感以及浪漫的藝術效果,雖然鳥紋在此件百鳥衣中并不是作為視覺中心的圖案,但是鳥紋的出現卻比龍紋頻繁。楚文化是先秦時期中國南方傳統文化藝術的代表之一,在許多出土的楚國絲織品中,鳳鳥圖案在數量上同樣超過了龍紋,表明楚人對鳳的喜愛,同時也突出了楚人也將鳳鳥常常作為補充紋樣,增添浪漫效果[7]。館藏百鳥衣中的鳥紋與商代青銅器中的短尾式鳳鳥紋類似,尾巴長度都短于整體身體的長度,尾部的造型類似魚尾、燕尾或雀尾,短而精美,鳥身是將植物或羽毛狀紋飾沿魚尾造型向兩側陳列,混合成復合短尾式鳳尾。以鳳鳥紋為媒介,反映出中國傳統文化和藝術具有共通的審美特點,也體現出了人們崇尚生命、向往自由和發揚踔厲的民族精神。鳥紋的出現不僅為了滿足人們的審美需求,同樣也是對自然和日常生活的情感層次的強化。
4 結語
簡言之,要從整體上理解民族服飾,就應該采用縱向、橫向的多維度視角,與漢族、周邊服飾文化聯合起來進行比較研究,方能引領我們了解更加透徹。苗族在不斷遷徙和開拓新生地的過程中,一方面靠統一的苗衣、古歌來增強民族的團結,并作為連接民族內部的樞紐;另一方面也在不斷地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精華,反過來賦予中華民族文化生機和活力。中南民族大學民族學博物館中的苗族百鳥衣以夸張變形的紋樣符號來代表對生命的理解,從中能體會到苗族人們豐富的情感。以紋樣的審美以及寓意來看,民族之間互相影響、互相模仿,形成了一種共享性的文化符號和共同體理念,而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共同體意味著歸屬感,這種文化符號成為了多民族之間互相認同的體現。民族之間在沖突和遷徙中進行的交流,使得這一多元的民族文化融合成一套具有東方特征的文化,反映了文化群體的認同。民族文化認同是一個靜態的內部過程,也是一個有意識的動態過程,包含了共享性標識。通過研究具體紋樣的融合過程,使我們可以更好地了解并溝通民族文化的特點,從而更有助于增強民族凝聚力,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同時這也是民族服飾研究的重要文化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