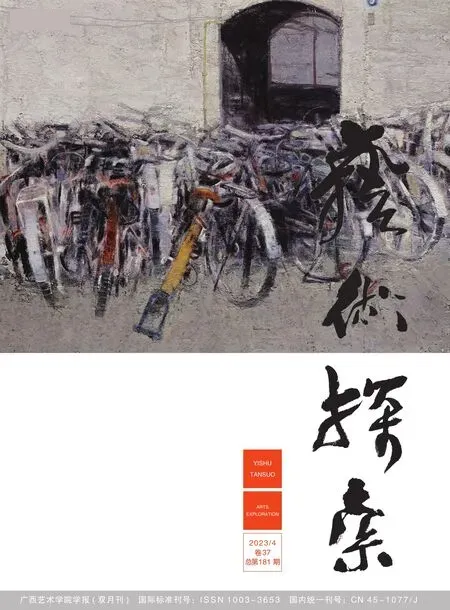從形象審美到身份認同:中國藝術史中的女性主題及其視覺反思
吳若明
(南開大學 文學院,天津 300071)
女性議題在當下藝術史研究中倍受關注,涉及中國藝術史中女性主題的研究,性別研究中對中國古代女性主題圖像的使用,中國古代藝術中部分典型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其反映的心理意識等多重領域。中國藝術史中的女性主題不僅有傳統仕女畫,也包括風俗畫、壁畫、版畫等不同視覺圖像。20 世紀以來中國藝術史的研究在關注女性形象審美的同時,對性別學觀點的借鑒及對古代女性主題圖像的使用,體現了藝術史領域的女性關注與視覺反思。
一、藝術史中的女性主題
目前對女性藝術的概念存在多元闡釋,[1]75女性藝術不僅包括女性藝術家直接參與創作的作品,也包括男性藝術家創作的女性主題作品。文學創作中的女性通常有三種表現方式:文本中被描繪的女性,作為作家的女性,以及女性群體的理想或混合類型。[2]196藝術領域中的女性也同樣體現了多元性,包括繪畫等藝術作品中的女性再現、創作藝術品的女性藝術家等。2020 年臺北“故宮”特展“她——女性形象與才藝”及相關圖錄中的兩大單元“群芳競秀”與“女史流芳”正是對女性藝術的二維解讀,推動了女性藝術研究。
藝術品中的女性形象,更多是以男性為主體的藝術家創作作品中的女性。諾克林曾提出“為什么沒有偉大的女性藝術家”的問題,并解釋其很大程度受制于社會環境的影響。女性主義運動興起后,女性藝術家越來越多地活躍在藝術領域,但其作品卻并非都以女性為表現對象,也沒有類似“女性氣質”的共同特質,而更傾向于同時期藝術的整體風尚。[3]182藝術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構成中國藝術史中女性藝術的重要載體,特別是在女性藝術家群體較少參與的中國藝術史早期階段。明清時期女性群體創作的藝術作品被《玉臺畫史》[4]等記載,近年來學者也不斷關注中國古代女性畫家和繪畫的研究。這些女性并非專職畫家,除少數宮掖女性外,以名媛、名妓和姬侍為主,且多與男性畫家及藏家有一定的家學淵源或師承關系,江南一帶尤盛。[5]6《故宮所藏女性畫家作品》一書列舉了從元到清代女性畫家的二百余幅傳世繪畫,除了少數對女性個體形象的描繪外,更多為山水、花鳥、宗教人物等主題,還有《歷代帝王道統圖》等男性形象。[6]25創作目的多為怡情或精神寄托,如以虔誠之心描繪觀音、羅漢等宗教人物形象。[7]37
因此,藝術史領域的女性主題是一個相對廣泛的范疇,而仕女等女性形象題材構成女性藝術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女性形象為表現主題的仕女畫或者稱美人畫,在中國美術史的傳統研究中并不具有重要地位,甚至被認為“俗甚”。特別是隨著文人畫興起,明清時期中國繪畫的主線體現了寫意和臨仿對自然寫實的背離,而仕女圖強調視覺真實感,滿足大眾通俗審美,在明清畫論中少見提及,甚至一定程度上被排斥。[8]隨著性別學研究的推進,藝術史學者對女性主題日益關注,古代視覺藝術中的女性圖像逐漸成為熱點。近年關于藝術史領域女性主題的研究著作包括三類:第一類是傳統的仕女圖賞鑒及技法研究,如《三希堂畫寶:仕女大觀》[9]、《唐代仕女畫研究》[10]等;第二類是對于人物形象和社會身份、生活空間的綜合探討,如《中國繪畫中的“女性空間”》[11]、《美的顯示:中國清代繪畫中的女性圖像》(Beauty Revealed:Images of Women in Qing Dynasty Chinese Painting)[12]及《致用與娛情:大清盛世的世俗繪畫》(Pictures for Use and Pleasure:Vernacular Painting in High Qing China)[13]等;第三類是受文學研究影響下的明清才女藝術研究,包括針對個人肖像畫及女性畫家的自身創作等。[14]此外,隨著女性圖像研究的增多,近年來更多學者側重于從跨文化與跨媒介角度討論,如繪畫中的女性形象反映的中外技法互鑒[15],以及從瓷器、玻璃畫等不同藝術媒介分析比較女性形象及其含義。[16]
二、性別學的圖文互證
盡管中國古代常見的仕女畫中以年輕女性的優雅形象為主,但從性別學角度來看,藝術圖像中的女性形象應當包括不同年紀的女性及其在多種社會身份中的綜合表現,以多種藝術圖像再現不同年齡、身份的女性在不同空間下的具體形態,從而表現中國古代女性的整體風貌。這些形象與性別學的文本敘述應當具有互補性,即藝術史領域的圖文互證關系。[1]56
20 世紀的法國學者西蒙娜·德·波伏瓦的《第二性》(1949 年)關注女性獨立問題,提到女性從成熟到老年各階段面臨的困境、挑戰和認知變化,即女性在不同時期體現出對不同問題的差異性關注視角。從童年到少女,再到婚后、成為母親的角色轉變過程中,女性的形象不是單一的,而是在錯綜復雜的社會內部的復雜形象。一方面,傳統觀念要求女性嫵媚、嬌柔、卑微、順從等,具有所謂的女性氣質;另一方面,如果女性要自我實現,改變在社會中從屬于男性的身份,則需要專注于學習、運動、職業培訓、政治社會活動等,以減少對感情和性的關注,而成為自主的個體,盡管有時會隨著婚姻而自我放棄這種獨立性。[17]88,130-131
《第二性》體現了女性在社會中被刻意塑造的各種特質,這一點與約翰·伯格《觀看之道》形成很好的互證性,后者在論證中更多地借鑒西方藝術史中經典的女性主題繪畫,從觀者身份及觀看的原作或復制品等不同載體去審視女性形象。伯格認知到所有圖像都是人為的,女性的形象不僅是寫實的肖像,也可以是符合審美標準的維納斯形象,復制的圖像和截取的方式突出了這種觀賞的重心。女性圖像往往注重通過服裝、飾品、家具等其他物品綜合呈現身份,符合男性為主的觀賞、收藏者的審美標準,是一種從男性畫家經驗及男性角度加以審視的美化了的人的本體。[18]65《第二性》描述了客觀存在于女性各階段形象的不同特質,而藝術生成則是有選擇地展示畫家或贊助人想表現的部分女性形象特質,這樣的表達方式和女性畫家的視角多少存在一定的差異。
近年來相關的性別學文獻也突出了中國古代女性身份的社會屬性問題,如《內闈:宋代婦女的婚姻和生活》(以下簡稱《內闈》),不僅肯定了女性在宋代社會中不變的妻子、母親與女兒角色,還提到女性在自身生活和介入社會歷史進程之中的身份。宋代的風俗畫為這一主題的研究提供了圖像場域的參考。《內闈》引用了宋代風俗畫《清明上河圖》《文姬歸漢圖》的相關場景,并結合劉松年《向茶販買茶的女人》這樣的一個公共空間,論證僅限于內闈的女性空間是上層階級用以顯示特殊地位的途徑,前提是有了在中間跑腿的仆人。[19]20,26反映普通女性在公共空間中的繪畫還有南宋李嵩的《骷髏幻戲圖》。即使在內闈之中,女性還可以通過紡織等活動參與社會生產,這一點同樣在劉松年的相關繪畫中得以呈現。才子佳人的主題,同樣借鑒了中國繪畫史中的一個常見題材——仕女形象。這樣的仕女形象或單獨出現,而更多地出現在與男性形象共存的敘事性組合題材中。《內闈》所引李唐等畫家的作品體現了女性相對于男性的從屬地位,反映的不僅是審美視角,也傳達出社會對于作為妻子、兒媳等的女性順從、殷勤和忍耐等要求。李公麟《孝經圖》《女孝經》中的圖像更形象地闡釋了女性的兒媳身份。《跨越門閭:宋代福建女性的日常生活》同樣關注宋代女性的生活細節,引用了《清明上河圖》以闡釋和轎子功能相近的篷車為女性在開放空間中提供的相對封閉的活動場所,畫中車簾半啟,車中女性的臉頰隨之隱現的細節表明篷車提供了內部獨處到探索外部的通道。[20]82-83該書還通過考古發現的墓葬壁畫探討宋代女性墓主生前日常寢居的細節。[20]296-302
在性別史視角下,《綴珍錄:18 世紀及其前后的中國婦女》關注18 世紀女性生活,也同樣關注了女性主題圖像與文本的結合。在對于博學女性的論證部分,書中援引清朝宮廷畫家金廷標所繪《曹大家授書》作為漢代宮廷女性學者的典型形象。乾隆時期反復出現在琺瑯彩瓷盤上的裝飾圖像也出現了類似的博學女性教子的場景。[21]106,133以教子為主題的才女形象是清代外銷瓷婦女嬰童題材的新興表達方式。
相較于繪畫作品以仕女題材為主,明清版畫呈現多重身份的女性圖像,包括在勞作、繁衍等多種情境下不同年齡的女性。《技術、性別、歷史:重新審視帝制中國的大轉型》強調了封建時代晚期女性從事的工作、所處空間,以及在不同領域中身份的傳承與變遷。在圖文互證的論述中,更多借鑒了版畫藝術,如1593 年版《便民圖纂》中的耕織圖像等。除了作為家庭勞動成員,女性也往往參與家庭祭祀等習俗活動。在一些祭祀活動中,女性以獻茶等輔助性活動幫助男性完成儀式。版畫《清俗紀聞》描繪了大型家廟祭祀中,妻子站立在祭拜中的丈夫身后,圖像中的人物組合關系表現了清代女性在家庭中的從屬地位及與丈夫的互補關系。[22]44,59-60
三、藝術范疇下女性形象的空間架構
性別與空間的關系是近年藝術史研究較為關注的論題之一。通常認為外部開放空間服務于男性群體,而女性被禁錮于封閉的內闈空間,或半封閉的庭院空間中。這種概念的形成可追溯到東漢時期,在儒學和皇權的結合下,女性角色的地位及女性所在內區域的社會秩序被確立。[23]109
園林屬于戶外空間,但并不是完全公開的外部空間。如晚明江南一帶興盛的園林,不僅是園林主人社交空間的載體,也是其控制和約束下的私人空間。[24]58閨閣與庭院空間也是中國古代繪畫,特別是仕女題材中女性形象的主要存在空間。仕女畫中多為“得閨閣之態”的年輕女性,即使是《女史箴圖》《女孝經圖》等女性典范的圖像也常傾向于年輕的仕女形象,并被列入廣義的仕女畫范疇。這些繪畫的空間也多集中在封閉的閨房或半開放的庭院空間。
宋代風俗畫和明清版畫對于女性形象的刻繪逐步走出這一種審美偏好。(傳)宋代王居正《紡車圖》中,表現了年長女性的容貌和裝束。在偏好表現民俗的宋元繪畫作品中,女性的紡織勞作場景并不是孤例,如劉松年《絲綸圖》表現了在庭院中紡織的仕女形象。[25]83類似的女性日常勞作圖像在明清版畫中經常出現,除了紡織場景外,還有桑蠶養殖,如1593 年刊刻的《便民圖纂》等,相對于繪畫作品,其更側重于全景式的客觀描繪。值得一提的是,桑蠶養殖也同樣在特定的室內空間完成。紡織和桑蠶題材受到女性主題藝術偏好,主要與其所具有的隱喻功能相關,即代表了女性對于家庭的貢獻。[22]122
在游春、狩獵等題材中,女性形象則出現在相對開放的外部空間。從封閉的閨房和半封閉的庭院到完全開放的外界空間,中國藝術史中的女性形象以年輕女性為主,但人物身份有所差別。如瓷器上的俠女、狩獵題材,以及昭君出塞等歷史題材,大多具有敘事性,且女性形象常和男性形象組合出現。戶外空間中的單獨女性形象相對較少,多為宗教中的女神。普通女性的勞作場景在版畫中偶有戶外空間表現,如1808年刻本《授衣廣訓》中采摘棉花的勞作場景等,這也是古代中國為數不多的幾項女性可從事的戶外農業活動之一。[22]95當然,我們不難發現中國藝術史表現的女性勞作都集中在紡紗織布這一范疇下,甚至表現宮廷女性日常的《搗練圖》同樣如此,成為古代中國男耕女織觀念的一種表現。
四、女性主題審美與理想形象建立
藝術史中的女性主題通常與年輕美麗的女性形象相關。六朝的秀骨清像,隋唐的豐腴多姿,宋元的端莊秀麗和明清的風露清愁,中國古代繪畫中的女性形象始終體態優雅,如顧愷之《洛神賦》《女史箴圖》《列女傳》等繪作品畫中的女性皆以“美者自美,翩以取尤”的唯美形象,在中國繪畫女性形象的發展中具有延續性影響。[11]99各時期的審美標準又有不同,唐朝周昉等作仕女多濃麗豐腴,儀姿雍容;宋元明仕女畫突出女子的甜美、嬌羞,有魏晉仕女之風范;清代仕女多見纖弱修長身姿,以削肩、尖臉、柳眉、細腰為美。[26]31-32
寫實并不是中國古代女性主題繪畫的審美標準,弱化的個性特征和對優雅體態的刻繪是主要表現方式。女性飄逸的服飾或繁復的發飾通常在畫面中成為區別人物的依據。西方早期藝術中的女性主題往往也采用了這些因素,古希臘帕特農神廟東三角門楣繪畫表現的是雅典娜在眾神環繞之下的誕生,三女神通常被認為是赫斯提亞(Hestia)、狄俄涅(Dione)和阿弗洛狄忒(Aphrodite),她們是對歐洲藝術影響深遠的理想女性形象。和當時更注重寫實自然的男性雕塑相比,三女神像的衣服褶皺感更強,褶皺的曲線呈現是一個縱切面,從而加強三維立體感覺。[27]132自古希臘普拉克西特列斯(Praxiteles)創作裸體的阿弗洛狄忒像開始,對歐洲女性的美的詮釋也從莊嚴感逐漸轉向來自世俗中女性的自然體態美,并在歐洲女性主題藝術創作上影響深遠。[27]143無論作品是對人主體的表現,還是有人物形象的敘事主題,視覺藝術的目標都是描繪身體的美。[28]47但中國女性主題藝術則延續了非寫實的表現手法,側重服飾的描繪,或借助于古物、書畫等物品表現人物身份差異。在特定的女性空間中,女性主題的表達具有程式化元素,且具有可置換性。如清代雍正時期的《十二美人圖》,人物形象相近,人物審美趨于一致性,包括面容姣好、儀態優雅和神情恬靜等,而根據屋內器物的設置表現各不相同的主題。事實上,元明之后美人畫少見“時世妝”,畫面中人物常帶有“集萃式”妝容,服飾也具有適用于各個時代的普遍特征,并延續了魏晉以來的宮廷美人(仕女圖)的審美范式。[29]31
除了審美形象上的標準化外,中國古代女性主題藝術在人物身份表達上也注重樹立典范。女性身份包括社會身份和人物身份,一方面是女性的典型社會屬性,即在家庭中的母親或妻女身份,或在社會中的職業身份;另一方面是具有說教性或敘事性的典型女性人物身份,可根據人物形象特征或榜題文字等對女性形象進行身份識別。如魏晉以來列女成為文本與繪畫中女性主題的重要表現對象。劉向《列女傳》中頌揚六種女子美德:母儀、賢明、仁智、貞順、節義和辯通,其中賢明與仁智也常用于評價男性。因此女性的美德不僅僅在女兒、妻子和母親等家庭角色中,但后世盛行的女性典型形象則以“婦德”“女教”等為基礎,強調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并形成了文本《閨范》。同《列女傳》相近,《閨范》給予了特定的人物案例,具有廣義上的社會典范性。[30]111-113依據這類文本形成的具有敘事性的圖像,在繪畫中多以手卷形式呈現。如《女史箴圖》和《列女仁智圖》等,畫面以界格將手卷分成一連串相互銜接的空間,表現不同身份的特定女性,強調女性形象體現的美德典范。[11]83不僅是模范的妻女,賢慈的母親也是傳統文化中推崇的典范,具體包括慈母、嚴母和賢母三種形象。[31]300依據文本樹立起的女性形象包括內外兩種特質,在外是得體、博學而有文化的,在內則為孝順、賢德、慈愛。二者相輔相成,如女性的博學往往與教育子嗣相關,成為女婦嬰童主題的重要表現。中國古代藝術從真實出發,到泛真實(general real)的理想女性形象構建,體現了具體女性人物身份與社會身份的理想統一。[32]46
五、他者凝視與自我觀看
從性別學角度審視,女性主題圖像在中國藝術史中體現了男性視角的他者凝視及女性的自我觀看雙重視角。仕女圖(或稱美人圖)大部分承載著男性或載道或言情的精神訴求,面容姣好的女性形象也多體現男性觀者的寄寓之思。如《十二美人圖》中女性形象周圍均是畫作定制者雍正所感興趣的東西,即已經擁有的富麗堂皇和向往的文人清雅。[29]34女性主題藝術的功能首先是為他者觀看,因此要符合以男性為主的畫家及作品所有者的審美需求。如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傳)五代顧閎中《韓熙載夜宴圖》,畫面以男性人物為主要敘事對象,但畫卷中共有女性26 人,體態均表現為秀麗典雅,五官妝容一致,人物體型相近,已非唐代豐腴之態,而是符合五代的審美時風。[33]190女性形象集中表現在聽樂及觀舞場景中,在畫面中是男性群體觀者的凝視對象,同時也愉悅了觀畫者,體現了女性形象在畫卷內外被凝視的功能。
中國古代藝術中的部分女性主題圖像也體現了女性繪制者與觀看者的自我審視。具有禮教意義的《列女傳》等即以畫卷與文本結合的形式成為宮闈女性觀看自審的對象。宋人《女孝經圖》、清焦秉貞《歷代賢后故事圖》冊等仍在延續這種題材。
明清之際盛行的女性肖像畫摒棄了傳統仕女圖對畫卷內外觀者審美時風的迎合,在體態及五官繪畫上也有所變化,注重所繪女性的個人身份及特質表現,通過人物裝束等突出女性的個體差異。如女性畫家金禮嬴(1772—1807 年)在乾隆乙卯年(1795 年)所繪《顧眉像》,著重表現了女性的文靜莊重及書卷氣,并以正面呈現五官,而非傳統美人圖傾向于描繪側面之風尚。[34]77關于特定身份人物的主題繪畫還形成多版本、多樣式的表達形式。如清光緒十七年(1891 年)張溥東本《顧橫波小像卷》是金禮嬴本《顧眉像》的摹本,由職業畫家臨摹人像,張溥東補圖樹石。[35]32清代顏翔在明薛素素繪《梅蘭竹菊卷》題跋中為其繪人物小像,并以書案擺設等表現薛素素的書畫修養。[6]43柳如是的肖像畫也是版本繁多,形象姿態各異,其中顧苓所繪更以男裝突出柳如是的人物性情與個人經歷。[36]48有一種女性肖像可能是女性以定制人身份介入其他畫家創作之中,如清順治八年(1651 年)由金陵名家樊圻、吳宏合繪的《寇湄像》,便是寇湄本人持紙乞請之作。畫面有松石溪流,畫中女性倚坐樹木,有林下高士之意。[37]73又或是自畫像成為女性自我觀看的表現形式,如《李香君自寫小照》等這種女性形象或者可以理解為繪畫者以主觀思維認知自我形象,自我再現。除畫家本人外,自畫像的觀眾對畫中人物姿態、手勢、面部表情和飾品等進行解讀,理解女性自觀的過程,即畫家本人為何以畫面中這種姿態示人。[38]22事實上,這些女性的肖像同樣受到同時期男性文人士大夫肖像畫盛行之風的影響。與宮廷畫家精心描繪的帝后肖像相比,二者雖畫面功能具有一定的相近性,女性肖像主要體現了自我認知的自觀之意,帝后肖像則因承載后代奉拜而端莊厚重。二者并非形象性別不同帶來的功能差異,而是體現了中國古代藝術史中女性主題從形象審美到身份認同的變化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