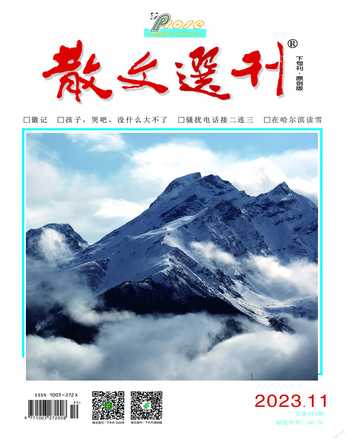在哈爾濱讀雪
呂永超

上帝說,造雪有兩種意圖:一是潤澤萬物,催生五谷;二是凈化人類靈魂。在哈爾濱讀雪,似乎這兩種具象都囊括其中。
2005 年1 月,受黑龍江文聯主辦的《章回小說》雜志社之邀,我到哈爾濱市去參加筆會,在現實主義城市里恢復浪漫主義色彩。在我們生活的南方城市里,我有許多年沒見到雪了。雙腳在北國雪地里發出清脆的“嚓嚓”聲后,滿身雪花中的我,剎那變成童話中的句子;雪落的聲音,如花般開放,芳香的語言,撒播大地。所有的道路,都躲在一片純潔的思想下,做著春天美麗的夢。而今,紛紛揚揚的雪,讓哈爾濱回憶起自己淙淙潺潺的源頭、朦朦朧朧的家園,森林、雪橇,暖閣里淚讀《石頭記》的少女,風廊上手捧《狂人日記》的少年,滿江紅,水調歌頭,竹林,黃昏,酒和紅泥小火爐……
只有一只小船,如島嶼,泊在水中,靜靜的,一動也不動。雪從身邊滑入江中,走了又來。船上的漁翁,破舊的斗笠下露出一雙沉著的眼睛,歲月滄桑寫滿蒼老的臉龐。
瘦小的身軀裹在單薄的蓑衣里,季節更迭改變不了悠閑的生活。穩坐船頭的釣者,是在釣一段失去的歲月,還是明年的希望?雪無聲,人無言。
哈爾濱的雪,和杜甫門外平平仄仄的唐朝雪,是否相似?和落在柏林街頭詩人嘴唇上的雪,是否相似?
“中國雪鄉”距離哈爾濱市有十多個小時的客車路程。在那里,我凍紅的雙手在這一米多深的雪地上畫了一匹馬,直到今天,它雪質的嘶鳴在耳邊繚繞不息。“中國雪鄉”構成了一種幻想、一種虛擬、一種擺脫真實的自由。于是,我躺在雪上,做一個白日夢,接納另一個世界給我的啟示。遼寧文學院的一位作家對我說,你在夢中尋求到一種恢復。
此言不虛。現實常常令我們傷痕累累,夢則提供了一種治療和休養。漫天飄逸的雪花,幻化成一只只純白的鴿子,那翩躚的舞翅,扇動我們思想的葉子。人在雪原,沒有喧囂的聲浪,不見形形色色的人流,久閉的心扉訇然中開,豁亮的胸襟與白皚皚的天地融成一色。這完全是透亮清心的體驗,一種被雪鄉彌漫的暖意之完全徹底的消融。
一天晚上,在哈爾濱冰雕公園,玲瓏剔透的冰磚和五彩斑斕的燈光,組成了“冰長城”。用手撫摸、用臉熨帖,激動之余,卻多了一分慵懶和愁意。“冰長城”啊,祖母因為你的介入而放棄了為孫子唱長城謠的美好角色,孟姜女和秦始皇在圖書館里鎖住內心世界。我不驚喜,孤獨的情懷演化成深深的庭院,一重又一重;“冰長城”的磚墻仿佛是庭院的圍墻,它不能使我完全歇息和歸家,因而在安靜中包含著對抗,愁緒就被燈光映射得格外無窮無盡。人類總耽于斑斕的色彩,“冰長城”怎么也難成就真實長城的精神世界。其實,這冰磚的本色更是一種永恒的美麗。
在哈爾濱讀雪的時候,我接到《北方文學》編輯喬老師的電話。他說來看我,送我三樣禮品:中篇小說即將發表的消息、墨寶、一場雪。
與其說喬老師為我送雪,不如說是傳遞雪的冷靜和理智。迎接與告別,落雪與落花,如同旅途上的里程碑和碑上的野鳥或月色,構建了我們每一個人漫長而短促、平淡且幽深的一生……
走在哈爾濱的路上,想及這些,再凝神注視這座城市,它已在白雪的映照中粲若一朵蓮花。哈爾濱的雪,我不能肯定它是否就是唐朝的雪。如是,那么,在這個雪天,又將有誰離開或抵達呢? 難道是你嗎?但我敢肯定它是我生命中渴望已久想讀的雪。
背著簡單的行囊,我走在“中國雪鄉”。
從來沒有什么事情給我走過雪地的那種快感,從來沒有在零下三十多度中生發那樣多的善思。我相信這種說法:當極地冰雪融盡,人類將不再有思想家,也不再有思想,不再有詩篇和詩人。
大雪飛揚,我常常睜不開眼睛。這時,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用睫毛打掃往事,與這里的雪合二為一,堆成一個雪人。然后,與雪人對話。
我問雪人,我的親人過得好嗎?我的朋友過得好嗎?我曾經的愛還在路上行走嗎?
雪人答非所問,這里真美!雪可以覆蓋你的憂傷、你的煩惱,讓你生不出一點邪念,只剩下愛,生生不息。
我的感覺被針深扎一下,又扎一下。
雪人在記憶中喚醒我的靈魂,并讓每一處針扎的地方,流出懺悔的鮮血。
不是戰斗,是戰斗之后的追念,是雪夜月光下的回憶;不是消沉,是消沉之后的覺醒,是生命與宇宙萬物在更高水平下的契合。有一種永不熄滅的熱烈,深入雪鄉的骨髓。
雪鄉的色調是一種總體的白。除了白,就是黑,黝黑的樹、籬笆以及萬物的輪廓。這樣的色調更合人的心境,比起其他的五顏六色,黑白兩色更接近事物的本質,簡潔而明快。這是世界的底色,是良心的顏色。
黑與白有一種抽象的力量。它是從繁雜的生活中提煉出的精粹。所以,老子騎牛慢走函谷關,李白跪而吻雪。黑與白是一種不帶妖氣的端莊,是一聲沒有濁氣的鳥唱。我喜歡讓那些花團錦簇的東西處在被等待的狀態,等待不是占有,占有讓生命迷失。
雪鄉的境界是沖淡。寒山,瘦水,木板房,紅燈籠,在安靜從容中,使境界遼遠、寬廣。沖淡是秋天收獲后廣袤田野的境界,無邊無際,清晰透徹。不是激流,是激流過后在深廣處的耐心積蓄、成熟。
蕭紅的境界接近雪鄉的境界,她是雪鄉的女兒,永遠走在冬天的最高處,從雪原走過。
雪鄉人豪邁地說,沒有雪的生活,是殘缺的生活。他們不貪戀雪景,需要的是雪天的心境,能安放一顆顆躁動不安的靈魂。
我累了,我想回家。
責任編輯:黃艷秋
- 散文選刊·下半月的其它文章
- 棒槌鳥
- 把灶火
- 大腳菱娃
- 魯迅先生與南充冬菜包子
- 孩子,哭吧,沒什么大不了
- 丟失的錢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