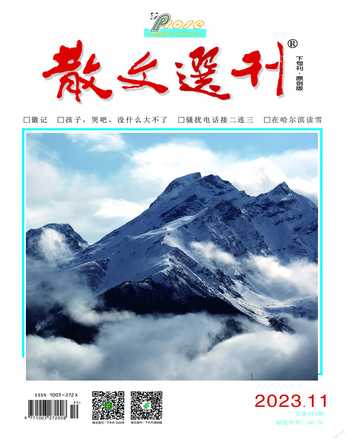過河
楊志華
我家北面三里左右是東、西河套和一條溪流的交匯處,稱三里河子,向北依次是五里河子和八里河子,主河邊上都分別有一個道袍袖,再北,就流入上都河了。
那時候,家鄉(xiāng)還沒有開采煤炭,又沒有電。做飯、取暖,一切燃料基本來源于牛馬羊糞、蒿草和麥秸。春天掃草末,秋天背大個(摟麥秸)、掃樹葉,常年撿糞是我們那個時代男孩子的擔當。一般都撿牛糞,主要是耐燒。把撿到的新鮮牛糞背到遠離河邊的干燥處,像和泥一樣攪拌好,拍成直徑20厘米左右均勻的牛糞餅,第二天去翻個,待成型后兩兩互架,晾干背回就可以直接碼放在小房,留作冬天備用了。每個人晾曬的牛糞都有標記,一般不會被別人弄錯。
背“大個”最發(fā)怵就是過河,背麥秸蒿草時,必須要用大繩經幾次踩踏、擠壓、煞捆成比自己身體高出一多半、自己能背得動的極限重量——“大個”,然后背運回家。
過河時需要脫鞋挽褲腿,幾十近百斤重的柴草如果不借助坡坎放下就起不來。
有時水大,踩空滑倒就會扔到河里。河水結冰后沒有積雪時最為愜意,經每天的淹冰水侵蝕,冰面平坦開闊,直通幾十里外的上都河,撿到的牛糞和柴火可以裝入麻包袋子用冰車運回。我家對門大哥竟然把家里的大門板卸下來做成冰車的面板,兩個人一起駕馭,一次能裝七八麻袋。有時趕上淹冰水大時也會把棉鞋濕透。
一次聚餐,有位家住八里河子村的師弟給我講起了他們當時上學蹚河的經歷,讓我明白了他們腳上結著厚厚皴痂的原因。因為一年只有兩雙媽媽給做的布鞋:一雙棉鞋、一雙夾鞋(單鞋)。除上學還要幫助家里干農活,鞋一般都穿不到頭就提前壞了,所以能光腳的地方就把鞋脫下拿著。布鞋尤其怕著水,鞋底雖然是媽媽親手納的千層底,可都是用舊布打的袼褙,幾次浸泡就爛了。遇到河套秋凍春化的冰碴水,他們必須光腳蹚著過。下游水也大,他們都是年齡大的背著年齡小的過河,腳上皴厚可以減輕冰碴刺骨的疼痛。拉荒每天來回走二十多里,就是走在雜草叢生的地面也感覺不到扎腳。
老家天氣涼爽,按氣象學劃分沒有夏天,伏天清晨在河岸撿糞也要穿棉襖。可每天腳是最受罪的:皴裂的口子鉆心的痛,凍傷的部位反復發(fā)作又痛又癢。母親看著心痛,晚上就用蒸鍋水泡一大鐵盆地花椒或艾蒿水給我們泡洗后涂上厚厚的凡士林,第二天接著蹚河。
中學五年也是學校上課晚,下學早,中午不休息。新建的學校在河的西岸,走大橋就得繞遠,一早一晚我們都要結伴在河邊撿糞干活,每天無數次蹚在河水中,不注意腿腳還會被冰碴劃破。有些長輩就會調侃我們:人家老毛子(蘇蒙聯軍)的女人三九天能在這里砸冰窟窿,鉆進去洗澡哩,你們蹚河涼點就怕了?
一晃四十年過去了,這條河留給我太多的美好記憶!
- 散文選刊·下半月的其它文章
- 棒槌鳥
- 把灶火
- 大腳菱娃
- 魯迅先生與南充冬菜包子
- 孩子,哭吧,沒什么大不了
- 丟失的錢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