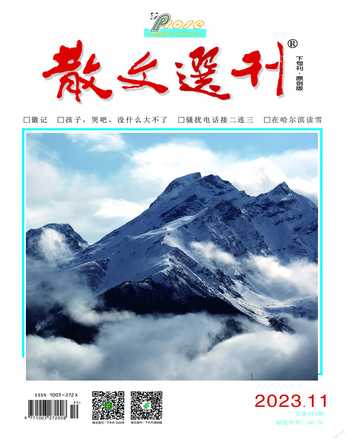中藥生香
張婉婧
一位老人戴著老花鏡坐在窗邊,陽光拂過她灰白色的發(fā)絲,灑在泛黃的書頁上。她捧著一本古籍,瞇起眼睛仔細閱讀,手執(zhí)一支紅筆,不時畫上兩句。每翻開一頁,便有一段光陰撲面而來。
小時放學早,父母還未下班,我便到奶奶家待上一段時間,由她指導我的語文作業(yè)。她年輕的時候是中學教師,也擔任校醫(yī),教育和醫(yī)藥之道均知一二,算不上深諳,但家用綽綽有余。暮色四合,便聽她講述中藥故事,扁鵲使人“起死回生”,華佗憑“神目”做手術,更有孫思邈升天成仙一說,很是吸引人。
曾經,奶奶領著年幼的我踏足中藥種植園,教我認識家鄉(xiāng)生產的中藥。“婧婧,你看,這個是白術,它的根莖是一味很常見的中藥。去掉泥沙和須根,曬干后切成片就制成藥了。”我似懂非懂地點點頭,好奇地看著那一爿植物。細薄的嫩綠色葉片,大部分沒有開花,花苞也是綠色的,尖尖的苞葉覆瓦狀排列,像一顆緊實的松果。有幾株開了花,花朵的顏色很鮮艷,是紫紅色的,像扁進去的紅毛丹。奶奶彎下腰輕摸葉片,惋惜地對我說,“現(xiàn)在白術都是人工培育的,野生種幾乎絕跡了。”除了白術,園區(qū)里還種植了石斛、元胡,她一樣樣講給我聽。奶奶教我識藥,也教我寫中藥名。取一張方格紙,寫下一撇一捺。那些長相普通的藥材,竟有如此詩意動人的美名。白芷,如江南女子,清麗素雅;佩蘭,是花中君子,高風亮節(jié);青黛,似大家閨秀,才情兼?zhèn)洹N殷w質弱,常常感冒,吃中藥成了家常便飯。每次開好藥,方子總要拿給奶奶看,按照她的意思,一是學習,二是看看有沒有不合理的用藥。熬藥的時候,奶奶幾乎是全程守在灶臺前,一站就是一個多小時,將所有的耐心和關愛傾注到這一壺被蒸汽籠罩的藥液里。
上大學之后,她在浙南,我在浙北,見面的次數(shù)越來越少。為了方便通話,我的父親給奶奶買了一部智能手機。奶奶開始學習用微信給我發(fā)消息。我拍好藥方傳給她,過了許久,她發(fā)來一大串文字,夾雜著許多錯字和不連貫的句子。我能想象在五百公里外,她看著不熟悉的手機鍵盤,慢慢敲下每一個字的模樣。
就在這兩三年,奶奶仿佛一下子老了十歲,各類疾病和疼痛悄然而至,腿腳不便,聽力視力衰退,眼睛也做了手術。電話是去年打來的,說奶奶得了皰疹,胸背部大片紅色皮疹,疼痛難忍,最痛時寢食難安,躺在床上猶如針扎,話也說不出來。起先,她并不知道這是皰疹,只當普通過敏,后來愈發(fā)嚴重才去醫(yī)院,因此錯過了最佳治療時間,免不了受一番折磨。她心疼我學業(yè)重,不讓我看望,只是偶爾打通電話。一次,我給她打電話嘮家常,聊著聊著她就把話題引到了自己的病上。手機那頭停頓了幾秒,她忽然說,痛死我了。這一下我愣住了,心猛然揪緊。想起以前我嫌藥太苦,奶奶看著中醫(yī)開的藥方,仔細研究,添了一味甘草上去,這樣就沒那么苦了。如今想著她生病難受的樣子,我心如刀絞,真希望能承擔她所有的痛楚。
家人陪她輾轉兩家醫(yī)院,配了藥,花了萬把塊錢,病情總算逐漸好轉,疼痛也減輕。病治好后,又開了調理身體的中藥,一勺一勺喝下去。感謝中藥,她恢復健康了。今年過年的時候,我返回家鄉(xiāng),帶著奶奶去了一趟許久不見的利濟醫(yī)學堂。那天陽光正好,光透過樹葉間的縫隙,斑斑點點地落在她的身上。風從我們身邊快意拂過,又溫情脈脈。我說,奶奶,我給你拍張照吧?她同意了,看著鏡頭露出歡快的笑容,雖是深冬,皺紋里卻盡是初春的溫柔。
透過靜謐的光柱,我看見一個小女孩坐在屋檐下,手握鉛筆畫著藥圃里的草木,一位老奶奶站在邊上,目光柔和。身后藥房的木架子上,三排整齊的青花瓷藥罐,正散發(fā)出幽幽的草藥香。
責任編輯:朱麗蓉
- 散文選刊·下半月的其它文章
- 棒槌鳥
- 把灶火
- 大腳菱娃
- 魯迅先生與南充冬菜包子
- 孩子,哭吧,沒什么大不了
- 丟失的錢包